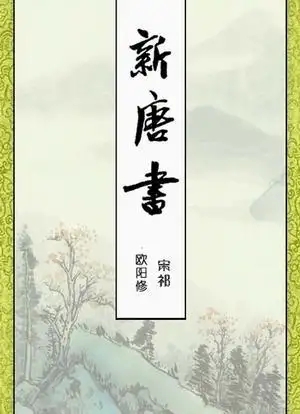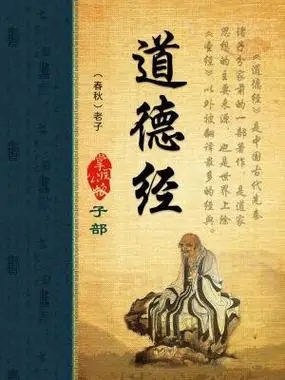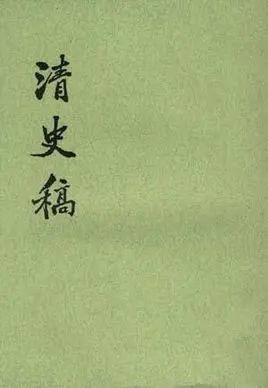一 春秋这样变成了战国
我们这本讲战国历史的书,自然要从战国的起始年头说起。
可偏偏就是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在历史学界却充满着各种争议。作为东周列国时代中最高潮的一段,战国究竟起于哪一年,放在不同的史料里,却有好几种说法。
比较通用的说法,就是司马迁《史记》里的观点:公元前476年,也就是周元王元年。之所以定在这一年,主要还是为了尊重周天子权威。
而宋朝人认同的说法,则是吕祖谦《大事记》里的说法:公元前481年。这是孔子作《春秋》的终结年份。在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封建社会,这一划分方法也十分流行。
当然宋朝的司马光并不同意,他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把公元前403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之前那么多折腾,都算在了春秋年间。直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了韩赵魏三国的诸侯身份,等于扒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才意味着战国的开始。
当然依照清朝许多学者的说法,公元前453年才是战国真正的开始: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确立了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标志着战国时代正式形成。
同一个时代,为啥被划分成不同的起点,只因在不同年代的史家眼中,战国与春秋之间,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前一代人看不懂的变革,着实太多太多。
但无论哪一种划分,一个真相无可争议:这是一个有别于春秋时代,几乎堪称全新的时代,中国历史将在一场剧烈的厮杀中,完成一次至关重要的浴火重生。
战国就是打
不管怎样划分,战国这个年代,最主要的标志就一个字:战!
而且和春秋年代最大的不同是,春秋虽然不乏战争,但列国诸侯名义上是都还是周天子的臣子,因此讲的是春秋礼数,哪怕是规模惊人的争霸战争,争的也主要是名分。
发展到战国年代,这条才是最大的不同。为什么很多史家眼里,韩赵魏瓜分了晋国,或者田氏取代了齐国,往往被看作战国的开始?那是因为在春秋年间,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春秋时代任何一个强大的霸王,都可以肆意凌辱周天子,但绝不可能取代周天子一样。从大国到小诸侯,春秋时代也没有一家权臣,可以名正言顺地取代原有国君。这基本的尊卑礼数关系,到了战国就彻底没有了。
自家国君,说废就废,自家国君的土地,说分就分。春秋时代大逆不道的事,却在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中,表现得毫无负担。照着教科书里通用的说法,这也就意味着,旧有的奴隶主贵族制度,正在走向瓦解中。
自家的争斗,都能如此地你死我活,国与国的争斗,自然更加凶狠惨烈。
其实“战国”这个称呼,在最初的中国史料里,并不是指这个年代,而是指这个年代七个主要争雄的大国。就如《战国策》里所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对这个年代,一开始《史记》上的称呼,也只是叫“六国之时”,直到西汉《战国策》之后,才开始有了这个叫法。
从称呼国家,到指代这个年代,真正开始这一称呼,还是到了《汉书》上,有了“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一句。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史家论及这段历史,都开始以“战国”来指代。
战国者,正是此时热衷于兼并战争的七大强国:“秦楚齐燕韩赵魏。”
这段列国争霸的历史,论规模和惨烈程度,堪称中国历史之前所未见,而如果再计算上人口与伤亡比率,它的剧烈规模,甚至要远远超过这以后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乱世时期。
对比春秋时代,这个全新的战国年代,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对待战争的态度。以春秋时期的通用说法,国家的大事就两件:祀与戎。也就是祭祀和打仗,而到了战国年间,所有的大事,都是以战争为中心。列国的变法,用人,改革,为的只有一件事:打赢!
孟子的一句话,足以概括当时战争的凶残程度:“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如果再对照一下《史记》,就知道战国时代的战争,惨烈到何等的地步:比如大名鼎鼎的秦国名将白起,亲自指挥的四大战役,杀敌数量就在一百万以上。而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也不过两千万上下。
如果说春秋年代,列国间还有一层温情脉脉的礼节,那么在战国时代,这已彻底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厮杀。
厮杀的主角,正是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大强国。对比春秋年代来说,表面看这其中有熟脸,比如秦楚齐燕,也有生脸,比如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但事实上,无论生脸熟脸,比起春秋时期的他们,这时的七雄早已大不同。
以教科书的说法,这是中国奴隶制制度崩溃,新兴封建制度勃兴的时期。因此能在这历史时期存在下来的国家,都必然做出了巨大的改变,有的像秦国一样变法,有的像田家一样代齐,有的像韩赵魏一样分家。但无论怎样做,目的都是一样,就是要脱去旧日奴隶制制度的外壳,全力向着封建制度狂奔,只有活出一个全新的自己,才有资格在这场角逐中角力。
而作为这个年代里的主角,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在这个热血时代开始初期,版图力量也都各自有了不同的变化。
首先从分完家的赵魏韩三国开始说起。
赵国分到的,是晋国当年北方的主要国土,包括山西吕梁山以西和山西北部与东南部,往南还占有了今天河南、山东、河北的部分领土。地理位置十分好,却摊上了好几位强悍的邻居,比如东北的中山,西北的楼烦和林胡,参考下西汉历史就知道,全是赫赫有名的强悍游牧民族,后来又崛起了强大的匈奴,一直不消停。
但这块地除了给赵国找麻烦,也送了个大礼物,例如北面的代地,不但是战国时代的良马产地,更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战马孵化地,堪称中国骑兵的摇篮。因此胡服骑射发生在赵国,丝毫不意外。
相比之下,魏国的运气表面要好一些,分到了陕西东部至河南河北的大片地区,全是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宝地,可战略位置就悲催了,号称“四战之地”,夹在齐赵秦楚四大强国中间,等于是被挤压住,极容易被包围痛打。
但对早年的魏国来说,这真不算个事,魏国自从分家之后,就是三家里最为自强的一家,首先启动了伟大的变法运动,率先实现了变法图强,坐上了早期战国列强里的头把交椅,且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几乎到了战无不胜的地步。四战之地?它不打别人就谢天谢地,这段光辉历史,后面会详细讲述。
而其中相对较弱的,就是韩国,韩国一开始分家,运气就十分不好,分到了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地区,不但国土狭长无险可守,国力也十分贫弱。所以在整个战国年代里,韩国都是最弱的一家,它不是挨打的对象,而是跟在人家后面做小弟。但韩国也吃柿子拣软的捏这一套,尤其是灭掉了郑国,奠定了自己的大国地位。
而这三家的老邻居,就是春秋晚期曾与晋国争霸的齐国。
齐国的特点是换了马甲,虽然还叫齐国,但已经由当年的姜氏齐国,变成了这时的田氏齐国。田氏继承的除了国君的名分,更有强大的家业,齐国资源丰富经济实力强大,国土在田氏代齐的演变中更加膨胀,领土包括了山东大部分地区和今天河北的一部分,尤其是把春秋时期的大国鲁国,吞并得只剩下几个小城。它有地有技术有钱,这时候的齐国,正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因此在战国初期,其与新崛起的三晋国家,也开始了相爱相杀的历史。
而另一家与三晋关系密切的强国,就是西部的秦国。
在后人的印象里,秦国在战国早期,国力一直相对薄弱,直到商鞅变法,才真正实现了自强。
而事实上,商鞅变法以前的秦国,一点都不弱,国土的膨胀尤其厉害,战国早期已经占有了关中平原和甘肃部分地区,领土十分广袤,治下民族更十分复杂,以华夏族为主,却也兼有各类少数民族。
但秦国比起中原来,最弱的一条却是经济。虽然坐拥物产丰富的地区,但是经济技术和制度却严重落后,生产力更是极其不发达,反映到战场上,就是战争的支持能力极差,秦国在战国早期的战争剧本,就是一开始尚能取胜,但没赢几次,就粮草接济不上,然后就被人痛打,相似的狼狈,复制了好多回。
早期欺负秦国最厉害的,就是魏国,自从魏国强势崛起后,就把秦国当作了提款机,隔三岔五就要来打一把,打得秦国完全丢掉了西河之地。也正是这番的狼狈,才逼得后来秦国痛定思痛,决心变法。
但要问从春秋到战国,有谁一直保持国土最大的纪录,答案就是楚国。
楚国对比当时北方各国,堪称是战国早期最为嚣张的超级大国。楚国的国土包括了今天河南南部和湖北全部,包括湖南、江西、安徽等部分地区,到了春秋战国之交,楚国更干脆吞并了吴越两国,实力扩展到今天的江南地区,以《史记》的说法,就是“南吞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可以说,当时的楚国,以国土面积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
而要问当时七国之中,谁的国土面积是最接近楚国的,答案恐怕出人意料,并非齐秦这样的传统强国,相反却是一个传统弱国:燕国。
燕国在整个战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被欺负的,但它的国土却十分广袤:既拥有包括今天北京在内的河北地区,更有辽宁西南部,与东胡部落接壤。就像楚国通过吞并百越扩展领土一样,燕国也曾经北击东胡,极大地扩展了自家的实力范围。
从这七个国家的实力说,我们不难看到能成为“七雄”的准入标准:国土面积至少得千顷以上,军队数量更要“带甲数十万”,像楚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更要有百万以上的兵力。战国轰轰烈烈的争霸,就在这七个战争魔兽之间展开了。
这些事情都变了
战国的主旋律就是打,但是对于主要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改变,却不只是战争。
为了能在这弱肉强食的时代里生存下来,列国除了整军精武,就是要变法图强。不变法的国家,不是被推翻,就是被吞并,而变法的结果,却是让这些原本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外壳之下的各种制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有了解这些改变,才能更清楚地了解战国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各个国家的官僚制度。同一类国家,比如齐国秦国楚国,其主要官僚运转制度,从春秋到战国时代的变化,套老百姓的俗话说,真叫“老母鸡变鸭”。
在春秋以前,特别是西周时期,中国的主要官僚制度,就是世袭制。贵族永远是贵族,贵族的儿子生下来就是贵族,大小官职都是世袭继承,老爹过世儿子来,以文言文的说法,叫“世卿世禄”。
这样的制度的改变,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先是一些有实力的卿大夫,开始有了家臣,然后就是一些破落的贵族离开原先的家族,外出闯世界,凭借自身的才能获得任命。但在当时的年代里,这样的情景还是非主流。
而到了轰轰烈烈的战国变法年代,新型的用人制度更成了大潮,所谓的世卿世禄,更成了浮云。各国的主要人才,外来人才极多,其中草根出身的尤众,“举贤”的理念取代了往日的世袭,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才有了更多出头的机会,搅动了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而在各国掀起的变法狂潮中,大家殊途同归的一条,就是确立新的用人制度,废除往昔的世袭制度。以清朝历史学家赵翼的说法,战国时期诸如苏秦、张仪成功与否,商鞅这类人物,他们的功过是非有待评判,但公认的一条贡献,就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布衣为相”的先例。而比这些草根上位已属以往不能想象,而各国官僚制度的改变更是更翻天覆地的。
首先直观的一件事,就是将相分立。最典型的代表,比如“将相和”的典故,老将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留下千古美谈。但实际上这样的千古美谈,也就只能是自战国起才会有,因为之前的春秋时代,将相的职权,基本都是不分家的。
从战国开始,除了楚国之外的几个主要国家,政治制度都有一个类似改革:专门设置了负责行政事务的相和负责军事的将,这也就是“将相”关系的由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战国时代,相的称呼往往是叫“相邦”,直到西汉开国,为了避讳汉高祖刘邦,才改成叫“相国”。今天很多战国题材的电视剧,管吕不韦之流叫“相国”,分明就是要把刘邦穿越来的节奏。
随着这两个部门的分离,相关的新型配套部门,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比如秦国和赵国,就有了掌握财政的内史,赵国的都尉负责管理人事任免,韩国的少府,除了管理税收,还要负责武器铸造与研发。而在武将方面,将军之下也有各种尉职,用以辅佐军务,这类新型官职,对于两千年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影响都非常深远。
与新型官职相对应的,就是新型的官吏任免制度。
战国时期还没有科举,但这并不妨碍草根阶层的出头。国君选拔人才的方式,除了举荐还有招贤,比起春秋时代的世袭制度来,这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的任免权力,完全掌握在国君的手中,特别重要的一条是,国君通过授印来授予官员权力,因此从战国起至清末,官员倘若丢掉官印,都是几乎要掉脑袋的大事。
同样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俸禄制度。
战国时期的官员工资,通常都是用谷物来支付。各国的工资标准也不同,比如在魏国做相国,基本就是“食禄千钟”,标准高工资,齐国相对更大气,齐宣王当年为了挖孟子,许了“万钟”的高工资,但还没留住人。
而除了这种直接支付外,还有一种福利,就是封地。战国有很多高官,在获得官职的时候也获得了封地。可和春秋时代不同的是,大多数官员,对于封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继承权,一旦任期到期下课,封地也大多要原样交回。以韩非子的说法,就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这个关系的改变,才是跨时代的。春秋时代的国君和大臣,虽说是上下级,但彼此却是一种世袭的关系。到了战国时代却不同了,国君和大臣已经是一种完全的雇佣关系。以前是吃祖宗的饭,现在要吃国君的饭。国君说话,比起春秋年代,真是胆大气粗。
而胆大气粗的国君,做另一件事也就得心应手:考核制度。
既然吃着国君的饭,那么就要被国君管,不再世袭的士大夫们,命运也从此被国君捏住。
而官员考核制度,也因此发生变法,掌握考核大权的,首先是相,也就是“相邦”,但除了少数几位权倾朝野的人物,绝大多数的相邦,都是直接对国君负责。以荀子的说法,列国每年都要由相邦主持,对官员进行考核,而考核的结果判定,则完全由国君来主持。这在春秋时期,基本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战国年代,对于地方官来说,这种考核也有一个名称:上计。“计”就是统计的簿册,上面记载着田产、人口、土地等事项,年初时做好规划,年终时由国君一一对照,进行考核。这样的考核模式,也沿用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
也正是从这样的改变里,我们不难看出战国时代战争扩大的重要原因。比起春秋时代的集体负责,话语权更大的战国国君们,自然可以放开手脚,为争霸兼并大打出手,每个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指挥效率,比起春秋时期,可谓高速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高速运转中,战国时代轰轰烈烈的争霸大戏开场了。
而比起三家分晋之类的爆炸新闻,真正催动战国早期战争大戏的,却是另一个劲爆事件:田氏代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