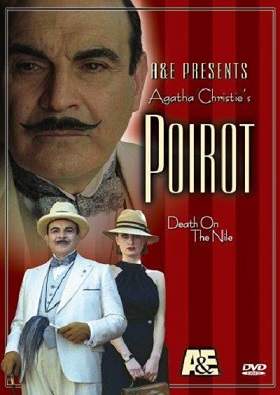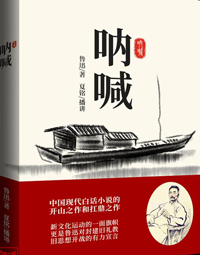《魏书·灵征志》所列的“雾”,主要是大规模和严重的沙尘暴天气,如“雨土如雾”,“黄雾,雨土覆地”,“土雾四塞”,“黄雾蔽塞”等。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十二月,从丙戌日(489年1月28日)开始,连续六天“土雾竟天”,“勃勃如火烟,辛惨人鼻”[《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第3169—3170页。原文作十一月,从校勘记应作十二月,见第3184页。]。该志记北魏这类大雾凡九次,其中七次在宣武帝时期,并总结说:“时高肇以外戚见宠,兄弟受封,同汉之五侯也。”[“汉之五侯”指汉成帝同一天封五个舅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侯,时在河平二年六月乙亥(前27年7月17日)。]《魏书》把宣武帝时期沙尘暴天气频发归咎于高肇兄弟受宠,反映了北魏后期的一个主流,那就是对高肇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立场。《魏书》继承了这一立场。
高肇兄弟于景明二年(501)上半年被招入洛阳,骤然宠贵,大概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但高肇本人至迟已于景明三年秋被授予尚书右仆射的重要官职。《魏书·北海王详传》:“世宗讲武于邺,详与右仆射高肇、领军于劲留守京师。”宣武帝到邺城阅兵讲武,在景明三年(502)九月。那时高肇以尚书右仆射留守洛阳,高显以侍中陪同皇帝出行,兄弟二人兼顾内外,看起来是宣武帝特意的安排。高肇进一步高升,做到尚书令。《魏书》和《北史》都没有记高肇始任尚书令的时间,我推测在正始四年九月。高肇为尚书右仆射时,尚书令是广阳王元嘉。《魏书·世宗纪》载正始四年九月己未(507年9月24日)诏书,以“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司空”。元嘉腾出的尚书令位置,自然立即为高肇所占据,任命时间很可能在同一天或稍后。
高肇担任尚书令差不多四年半。《魏书·世宗纪》延昌元年正月丙辰(512年2月27日)“以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公”。延昌三年(514)冬以高肇为主帅统军征蜀,加大将军之号,仍居司徒之位,次年春回到洛阳被杀,司徒就是他的最终官职。《北史·外戚传》说高肇升司徒时,“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众咸嗤笑之”。这时司徒最称荣耀,可高肇还是更看重把持行政实权的尚书令一职,这反映了他看重实际、专注于当下的风格,浸润于官场文化的那些人当然无法理解。
史书斥高肇恃宠专擅,核以记事,每虚多实少。《魏书·裴粲传》:“时仆射高肇以外戚之贵,势倾一时,朝士见者咸望尘拜谒。”朝士如此巴结(或畏惧)高肇,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不“望尘拜谒”,就会有麻烦呢?传文表彰裴粲,因为他就没有那么做,他见高肇时,只是按照常规礼节“长揖而已”。家人怪责,裴粲回答:“何可自同凡俗也。”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倒霉,高肇不曾给他穿小鞋。高肇当尚书令时,御史中尉是游肇,二人同名。高肇让游肇改名,游肇说自己的名字是孝文帝所赐,因此坚决不肯改名。《魏书·游肇传》:“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虽然惹得高肇不高兴,却博得宣武帝赞赏,高肇也拿他没办法。高肇为司徒时,有个儒生刁冲因高肇“擅恣威权”而上表攻击他。《北史·刁冲传》记刁冲“抗表极言其事,辞旨恳直,文义忠愤,太傅清河王怿览而叹息”。很显然,刁冲也没有遭到高肇的打击报复。事实上,高肇的话宣武帝也不是都听。《魏书·良吏传》记宋世景特别能干,“台中疑事,右仆射高肇常以委之”,后高肇和尚书令元嘉一起推荐他做尚书右丞,因王显从中作梗,“故事寝不报”,宣武帝竟然没有批准。
见于史书的高肇主要罪状似乎都与几个亲王之死有关。北海王元详之废,《魏书·北海王详传》说是高肇诬告:“后为高肇所谮,云详与(茹)皓等谋为逆乱。”元详与茹皓勾结亲昵,已见前述,茹皓之败,牵连及于元详,而元详确有诸般劣迹。《魏书·彭城王传》把元勰遇难全都推给高肇:“尚书令高肇性既凶愎,贼害贤俊。又肇之兄女,入为夫人,顺皇后崩,世宗欲以为后,勰固执以为不可。肇于是屡谮勰于世宗,世宗不纳。”京兆王元愉反于冀州,元勰的舅舅潘僧固“见逼从之”,也就是说,潘僧固加入了元愉的叛乱。可是,潘僧固跟随元愉到冀州做官,恰恰是元勰推荐的。于是,传文称高肇诬告元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元勰死后,其妻李妃号哭高叫:“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还当恶死。”在宫里率领武士逼元勰喝下毒酒的元珍,据《北史·魏诸宗室传》,“曲事高肇,遂为帝宠昵”。宣武帝让自己宠昵的元珍动手处死元勰,恐怕不能说是高肇的主意。元愉在冀州称帝造反,据《北史·孝文六王传》,“称得清河王(元怿)密疏,云高肇谋为杀害主上”,兵败被俘,至野王“绝气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杀之”。同传又说:“司空高肇以帝舅宠任,既擅威权,谋去良宗,屡谮(元)怿及(元)愉等,愉不胜其忿怒,遂举逆冀州。”这就把元愉造反的责任也推到高肇头上。元怿向宣武帝指控高肇,比之于王莽,提出“宜杜渐防萌,无相僭越”,“宣武笑而不应”。
史书有关高肇“贼害贤俊”“谋去良宗”的这几个事例,都与宣武朝权力斗争的核心问题有关,那就是宣武帝对几个叔父十分警惕。在一度威胁皇权的元禧、元详死后,宣武帝又担心皇叔元勰在背后支持几个皇弟,后来还的确出现了皇弟称帝造反的大案。在这几个亲王的不幸故事中,高肇当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与其说他是罪魁祸首,不如说他只是宣武帝用得称手的一个工具而已。这个道理,当时朝中诸贵,包括几个遭遇不幸的亲王,一定也都明白,只是不可点破。李妃见到元勰尸体,伤恸已极,愤怒已极,却也只敢咒骂高肇,其实她当然知道谁是真正拿主意的。
可以说,高肇代宣武帝担负起全部骂名,本是皇帝制度的内在要求。《魏书·任城王传》:“于时高肇当朝,猜忌贤戚。澄为肇间构,常恐不全,乃终日昏饮,以示荒败。所作诡越,时谓为狂。”元澄为孝文帝所亲用,名列六辅,元禧、元详亦颇为忌惮,宣武帝对他不可能不提防。元澄“常恐不全”,决不会仅仅因为高肇的“间构”。眼见元禧、元详、元愉、元勰如此下场,元澄采用自秽策略,“终日昏饮,以示荒败”。
当然,宣武帝最亲宠的高肇也是元澄不敢得罪的。《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传》记元澄子元顺事(元顺很可能是李令徽所生,李令徽的弟弟李子岳娶高琨之女,即高猛的姐妹,所以元顺和高肇是沾亲带故的):
时尚书令高肇,帝舅权重,天下人士,望尘拜伏。(元)顺曾怀刺诣肇门,门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贵客”,不肯为通。顺叱之曰:“任城王儿,可是贱也!”及见,直往登床,捧手抗礼,王公先达,莫不怪慑,而顺辞吐傲然,若无所睹。肇谓众宾曰:“此儿豪气尚尔,况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闻之,大怒,杖之数十。
元澄杖责元顺,可能是听说了高肇的那句评论。不过,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高肇还是有一定心胸的。元澄怕的不是高肇,而是高肇背后的宣武帝。不过宣武帝对高肇也不是盲目信用的。《魏书·乐志》记公孙崇为考定音律事于正始四年上表,以为金石音律所关至大,请求皇上派重臣主持,因为“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能识其得失”。谁是这样的人呢?公孙崇表曰:“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赏入微,徽赞大猷,声光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这样神乎其神的美誉,高肇那时一定享受了很多,如今保留在史料里的已相当罕见。不过宣武帝不是糊涂蛋。《魏书·乐志》说“世宗知肇非才”,一方面同意公孙崇的表请,另一方面下诏“可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找来一个真正的专家与高肇一起主持其事。
叙述与事实脱节是生活的常态,不过对于高肇,以及千千万万有幸被历史提到的人来说(虽然进入历史就意味着变形),更大的不公平和不真实发生在身后,在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中。试举一例。《魏书·天象志》有如下一条: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壬辰,有大流星起轩辕左角,东南流,色黄赤,破为三段,状如连珠,相随至翼。左角,后宗也。占曰:“流星起轩辕,女主后宫多谗死者。”翼为天庭之羽仪,王室之蕃卫,彭城国焉。又占曰:“流星于翼,贵人有忧系。”是时,彭城王忠贤,且以懿亲辅政,借使世宗谅阴,恭己而修成王之业,则高祖之道庶几兴焉。而阿倚母族,纳高肇之谮,明年,彭城王竟废。
这一段叙述与分析的时间终点在景明元年(500)的“明年”,事件标志是“彭城王竟废”。如前所述,彭城王元勰“悲喜交深”地“释位归第”,在景明二年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那时高肇兄弟还在平城,未曾参与宣武帝从辅政诸王手中夺回权力的宫廷政变,与洛阳的权斗毫无干系,说宣武帝这时“阿倚母族,纳高肇之谮”,是一点也不符合真实历史的。事实上,正是在高肇担任尚书右仆射以后的景明四年(503)七月,被废的元勰才重新起用,高拜太师。上引这段对于星占的历史分析更违背史实的,是说“是时,彭城王忠贤,且以懿亲辅政”,似乎不知道元勰本来就不在六辅之列,说什么“借使世宗谅阴,恭己而修成王之业,则高祖之道庶几兴焉”,更是离题万里了。
身份制与等级制社会对出身与流动限度是非常敏感的,出身寒贱者只宜在一个限阈内流动,如果因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定的流动极限,进入由特定身份等级社会所专属的那个阶层,他就成为通常不受欢迎的特例。对高等级政治职务的垄断,反映了国家对高等级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制度性保障,与此相配合,就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设置,其基本舆论不仅是当时政治的晴雨表,也会反映在历史编纂中。突破身份的制度性极限,意味着必然面对否定性的社会舆论。清人钱大昕说:“六朝人重门第,故寒族而登要路者,率以恩倖目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七南史三“恩倖传条”,方诗铭、周殿杰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05页。]目之为恩倖,就是对其权位予以伦理性的否定。
高肇家族既非拓跋崛起所赖的代人,又与华北名族的社会网络无关,骤得权势,超然于宗室及旧族之上,当然会被权贵社会视为异类,和那些被列入《恩倖传》的人物差不太多。《北史·外戚传》:“(高)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表面上是针对高肇的出身,其实是因为他过于突然地闯入了权势阶层。权势是限量供应的绝对奢侈品,在高等级社会内也存在着血与火的竞争,现在一个外人未经竞争而轻松攫取,可想而知,他必定成为整个高等级社会的眼中钉。
然而,皇帝制度又在法理上决定了一切政治权力都不过是皇权的延伸,也就是说,皇帝既是一切官爵合法性的来源,也是一切官爵的终极分配者。皇帝制度内在属性之一,就是皇帝可以突破已有制度。由此决定了官职竞争中总有弯道超车者,也总有火箭式干部。当宣武帝这样一个内心安全感甚弱,对外界难以信任的皇帝在位,他总是更容易信任那些与他有个人性联系的人。那么很自然的,他会信用当他还处在弱势地位时与他亲近的人,也就是东宫时期和亲政之前的侍卫、御医、宦官等等,再就是与他母亲有关联者,包括宫女和外戚。高肇兄弟“数日之间,富贵赫奕”,要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
高肇以帝舅之尊,深得宣武帝信任,封以高爵,授以重官,只要这种信任不变,朝野内外是无人能奈他何的。但加官晋爵是一回事,操弄权柄是另一回事。有名有位,只是理论上有权有势,要实际上享受权势而不是被权势吞噬,还需要一定的个人条件或个人努力。《北史·外戚传》称高肇“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显然他具备一定的政务能力,而且他还喜欢做事。这样一个与既得利益集团全无联系的人,有政务才能又热衷政务的人,母舅之亲,把他放到尚书省长官的位置上,年轻的宣武帝就有了控制朝政的安全感。高肇虽一开始只是担任尚书右仆射,但尚书令元嘉“好饮酒,或沉醉”,不爱管事(或不敢管事),高肇实际上控制了朝廷政务。有了宣武帝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说高肇在官僚体系里不需要担心遭遇抗衡或威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肇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肇并不是宣武帝最亲近的人。有人比他更靠近皇上,更懂得怎样与皇帝相处,也更得皇上信任,他们就是《恩倖传》重点写的赵修和茹皓等侍卫出身的亲信。跟他们比起来,高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够让宣武帝对他的信任保持长达十三四年,可以说始终不渝。而赵修、茹皓这样的亲信,固然一时亲宠无两,但他们都没有能力长期维持宣武帝对他们亲宠的热度。而且,当六辅消散,权势为宣武帝亲信人群所独享时,这个人群内部势必存在着权势分配的竞争。高肇能够成功上升,就因为他在所有竞争中都胜出了。当竞争对手一个一个被扳倒,高肇就成为宣武朝一个耀眼的政治现象。
据《魏书·恩倖传》载宣武帝黜落赵修的诏书,赵修最后的官职是散骑常侍、镇东将军、领扈左右,三者之中最有实际意义的是领扈左右。领扈左右,即领左右,是皇帝禁卫系统中最内层、靠近皇帝的卫士长(北魏末年的权臣如尔朱荣都要亲自兼任这个低级别武官)。赵修在东宫只是“白衣左右”,宣武帝即位后“仍充禁侍,爱遇日隆”,至迟在宣武帝亲政后就开始担任领左右了。宣武帝这封诏书写得十分讲究,显然是高聪、邢峦这一级别文士的作品。诏书为宣武帝开脱,说赵修“昔在东朝,选充台皂”,指赵修以白衣左右的身份服务于太子宫,在这个过程中与宣武帝建立起个人感情,所谓“幼所经见,长难遗之”。诏书以此解释为什么即位后不只要用他(“故纂业之初,仍引西禁”,东指太子宫,西指皇宫),而且还要重用他(“识早念生,遂升名级”),尽管他是不值得重用的(“地微器陋,非所宜采”)。
赵修的高光时刻并不长,延续了不到两年。他在宣武朝所做的事情中,长期政治影响最大的,是说服宣武帝立于劲的女儿为皇后。据《魏书·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己亥(501年10月5日),即处死元禧三个多月后,“立皇后于氏”。《北史·后妃传》记宣武顺皇后于氏:“以嫔御未备,因左右讽喻,称后有容德,帝乃迎入为贵人,时年十四,甚见宠爱,立为皇后。”这个能对宣武帝施加影响的“左右”,就是赵修。于劲是领军将军于烈之弟,于劲应该与其家多人一样,都在禁军任职。他们在宣武帝夺权和挫败元禧谋反的斗争中立下大功,因而也与宣武帝身边的亲信侍卫建立了私人联系。
《魏书·恩倖传》:“初,于后之入,(赵)修之力也。”一年多后赵修被捕时,他正在于劲家玩游戏(樗蒲),尽管可能是于劲受命为稳住他而特意招他来玩(如此怀疑是因为赵修被捕后带到领军府受审),于劲和赵修关系亲密是无疑的。《魏书·恩倖传》:“(赵)修死后,领军于劲犹追感旧意,经恤其家,自余朝士昔相宗承者,悉弃绝之,示己之疏远焉。”史书不记于劲为领军的时间,我猜可能在景明三年八月。《魏书·于烈传》:“顺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弥见优礼。八月,暴疾卒,时年六十五。”于烈死后,于劲继为领军。
景明三年八月也是赵修偏享皇上亲宠的最后时刻。这之前,每次赵修升官,他都在家里大摆筵席,宴请宣武帝及王公百官。《魏书·恩倖传》:“每受除设宴,世宗亲幸其宅,诸王公卿士百僚悉从,世宗亲见其母。”赵修酒量奇大,宴席上凭自己酒力强劝客人暴饮(“逼劝觞爵”,劝人一碗,自己也得喝一碗),即使贵如北海王元详、广阳王元嘉,都被他折腾得吃不消(“必致困乱”)。宗庙祭典时,皇帝总是让赵修和自己同乘一车。而且,赵修还获得了在皇家北苑华林园骑马的特权,从那里一直骑到禁内。
《魏书·咸阳王禧传》也把元禧谋反归因于“赵修专宠,王公罕得进见”。《魏书·恩倖传》:“(赵)修起自贱伍,暴致富贵,奢傲无礼,物情所疾。”所谓贱伍,就是最低等级的士兵(白衣左右)。何况赵修没有受过教育,“不闲书疏”,“不参文墨”,自然为内外朝臣所敌视。不过只要赵修跟皇帝在一起,别人再敌视也没有办法。到景明三年秋,赵修回乡葬父,他意识不到,这次与皇帝的短暂分离,是他告别荣华的开始。
不仅意识不到危险,而且他可能还误以为这是展示权势的大好时机。赵修家在赵郡房子县(今河北赞皇),他先把大宗物资如在洛阳制作的碑铭、石兽和石柱等,先送到房子去。赵修为亡父所制碑铭,是请高聪写的。《魏书·高聪传》:“赵修嬖幸,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碑石。”赵修从洛阳出发时,一行丧车近百辆。路上所有花销,都从官出。《魏书·恩倖传》:
(赵)修之葬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酒犊祭奠之具,填塞门街。于京师为制碑铭、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财用之费,悉自公家。凶吉车乘将百两,道路供给,亦皆出官。
恰好这时宣武帝要到邺城阅兵讲武。据《魏书·世宗纪》,景明三年九月丁巳(502年10月18日)“车驾行幸邺”,这是从洛阳出发的时间,二十天后,宣武帝在邺城以南“阅武”。赵修参与了这个过程。阅武结束,赵修要告别皇上,北上回乡了。可是宣武帝另有展示神射的计划,他要赵修陪他直到御射结束,赵修的行程因而拖延了一个月。这次御射在史书上又写作“马射”,御射的地点是“射宫”。十月庚子(502年11月30日),赵修和宣武帝乘同一辆车进入射宫,可是从东门进入时,车上的旒竿撞断了,后来这被视为赵修的不祥之兆。御射结束,赵修赶回赵郡。因担心赶不上早已确定的葬期,宣武帝允许他“驿赴窆期”,就是利用国家的高速驿传系统。同时,“左右求从及特遣者数十人”,即宣武帝所派遣,以及自愿要求跟随赵修回乡的御前侍卫,还有几十个人。据说回乡路上赵修做了很多坏事,全无葬父之悲戚,还聚众奸掠妇女。不过我猜,这些罪行都是扳倒赵修时临时拼凑的,未必属实。
前面提到的宣武帝黜落赵修的诏书,在列举赵修罪失后说:“法家耳目,并求宪网。”意思是,向他检举揭发赵修罪行的两个人,分别上书请求处理赵修。法家指御史中尉甄琛,职在司法监察,耳目指王显,虽然那时官廷尉少卿,但“仍在侍御”,为宫内第一御医,在宣武帝眼里还是耳目和左右。据《魏书·甄琛传》,甄琛是朝官中巴结赵修最卖力的三个人之一(另两个是李凭和高聪):“于时赵修盛宠,琛倾身事之。琛父凝为中散大夫,弟僧林为本州别驾,皆托修申达。”甄琛巴结赵修的实际好处,是为老父谋得一个中散大夫,为弟弟谋得本州别驾,其实都无职无权,图的不过是个虚名。甄琛表劾赵修,在宣武帝决意拿下赵修之后,是被动仓促的自救行为。真正撬动赵修的是王显。
王显跟赵修一样为宣武帝东宫旧人,同样在对六辅的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而且也是和皇帝日常厮混在一起,极为亲密。王显跟赵修本来关系不错,但不知怎么发生了争执,王显竟暗暗起了敌忾之心。《魏书·恩倖传》:“初,王显祗附于修,后因忿阋,密伺其过,规陷戮之。”只是赵修自己全无觉察(“都不悛防”),还忙着回老家当孝子。就在赵修离开的这段时间,王显本人,以及他指挥下的左右侍从,开始在皇帝耳边灌输赵修的种种劣迹,所谓“因其在外,左右或讽纠其罪”。效果明显,即使宣武帝还没有决心抛弃他,也不如以前那么喜欢他了,即所谓“自其葬父还也,旧宠小薄”。
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在景明四年春夏间,王显启动了最后一击,密表赵修罪行,包括回乡途中“淫乱不轨”,私匿民间所献玉印(玉印非人臣所宜有),违规扩建私宅,等等。《魏书·恩倖传》说“高肇、甄琛等构成其罪”,实际过程应该是,宣武帝认真对待王显的控告后,把尚书省长官高肇和御史台长官甄琛叫来,也许还有别人,问他们的看法,他们都支持王显。这样宣武帝只好下决心,也才有甄琛的正式表奏,及随后宣武帝的诏书。
高肇乐于除掉赵修容易理解,甄琛本来和赵修关系甚好,他为什么也积极参与“构成其罪”呢?《魏书·甄琛传》的解释是,他是为了自保。宣武帝亲政后提拔甄琛为御史中尉,在肃清诸王影响、整顿朝官秩序方面立下大功,但也因此结怨甚广。如今赵修倒台,一方面为了自保不得不痛下杀手,另一方面还有点恻隐疼惜。虽然宣武帝判决赵修“可鞭之一百,徙敦煌为兵”,但宣武帝还是存了一点旧情,他让尚书右丞元绍复核此案。据《北史·魏诸宗室传》,元绍是常山王拓跋遵的曾孙,“断决不避强御”,奉宣武帝诏命后,没有按照程序回报皇上,而是就地宣布立即执行前诏的判决。这也显示了朝臣中存在一种共识,不只是打他一顿远徙敦煌而已,那样他还有机会回来(年轻的皇上对他仍有不舍),所以必须尽快结束他的性命。
甄琛和王显一起“监决其罚”。据《魏书·恩倖传》,行刑官“先具问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先已定了当场打死的目标,于是找力气大的行刑者往死里打,怕行刑者力竭,让五人轮换着打。甄琛作为监刑者,眼见过去的好友如此遭罪,难免心下不忍。《魏书·甄琛传》:“及监决修鞭,犹相隐恻。”甄琛这一矛盾心情,传文有形象的描述。看着一鞭一鞭打得赵修皮开肉绽,甄琛故作轻松,向其他官员开玩笑道:“赵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这个态度也引起旁人反感,“有识以此非之”。御前侍卫出身的赵修胖大强壮,特别耐打。《魏书·恩倖传》:“(赵)修素肥壮,腰背博硕,堪忍楚毒,了不转动。”不可思议的是,一百鞭打完,赵修离死还远。于是行刑官、监刑官都不顾诏书所判的明确数字,硬是又加了二百鞭,所谓“旨决百鞭,其实三百”。三百鞭打完,赵修竟然还没有死。于是叫来驿传快马送他去敦煌,直奔洛阳城西门。赵修这时已上不了马,在马上也坐不住了,于是被捆绑在马鞍上,打马飞驰。赵修的母亲和妻子跟在后面,却说不上话。奄奄一息的赵修这样奔行八十里,终于一命呜呼。
随后展开的是对赵修余党的清查。甄琛在整赵修时表现再积极,也无法逃脱被清查。后来弹劾他的表奏,特别指出他与赵修勾结已久:“生则附其形势,死则就地排之,窃天之功以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为鄙诈,于兹甚矣。”表奏作者很可能是与甄琛结下私怨的邢峦,他受宣武帝之命主持对甄琛的审查,又与元详一起上奏审查结果。一番清理审查,“(赵修)所亲在内者悉令出禁”,“左右相连死黜者三十余人”,甄琛、李凭“免归本郡”,另一个与赵修亲好的朝官高聪,因与高肇认了远亲(疏宗),也就是说,正牌出自勃海高氏的高聪愿意接纳高丽高肇为宗亲,高肇出面帮他脱困,所以高聪算是幸免了。
赵修之败,高肇也许发挥了顺水推舟的作用,但肯定不是主谋。那时他入洛不足两年,刚刚过了刘姥姥初入大观园的适应期,应该还不至于冒险出击。但长远地看,赵修之死对于高肇来说有一个重大利好,那就是改变了后宫的力量平衡。于皇后的地位,固然与她的伯父于烈多次立功有关,也与赵修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现在于烈、赵修双双死去,虽然她父亲于劲继为领军,毕竟没有于烈那样的功劳地位,这一变化为宣武帝后宫后来的一系列的新发展准备了条件。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变化,发生在赵修死后,就是《北史·后妃传》所记宣武皇后高氏以贵嫔身份进入皇宫。据“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40——141页。],这位宣武皇后高氏就是高英,是高肇亡兄高偃的女儿。墓志说她“世宗景明四年纳为夫人,正始五年拜为皇后”。这些变化的进一步发展,是本书下一节的主题,这里且按下不表。
听说赵修被司法主官们刻意整死,宣武帝是不高兴的。他把主持案件核查的元绍叫来,发了一通火,元绍一番狡辩,最后不了了之。宣武帝不多追究,很可能是因为,这时原来赵修的那个座位,已经有人坐着了。这个人就是茹皓。茹皓在宣武帝即位之初就已进入亲信核心圈,但被赵修看出他的潜力,把他排挤出去。景明三年初冬,赵修在邺城告别宣武帝回乡葬父时,本在兖州阳平郡担任太守的茹皓跑来邺城朝见皇帝,就此留下,替代了赵修的角色。茹皓从景明三年底重归权力中心到正始元年(504)五月被赐死,享受权宠最多也就一年半,比赵修时间还短。《魏书》和《北史》记茹皓事,零碎混乱,大致上把茹皓之败归为高肇嫉妒,且主要是为了搞倒北海王元详。其实搞倒元详的一大动力可能来自于氏家族。《魏书·于忠传》记元详痛恨于氏,曾以死威胁于忠。后来元颢入洛,杀于劲之子于晖,应该是为其父元详报仇,见《魏书·外戚传》。
前面提到,当时和后世都存在把宣武帝的问题推给高肇的倾向,茹皓事也一样。高肇把从妹嫁给茹皓,显然是为了在内廷结一个盟友。但茹皓与元详走得太近,引起宣武帝警惕。对高肇来说,勾结茹皓的元详与他另一个从妹的不伦之恋,也会激发他极大的敌意,使他乐于协助宣武帝除掉元详和茹皓集团。这次权斗比赵修那一次更危险,牵涉更广,不过归根结底也只是狐狼之争而已,这里就不啰唆讲述了。
赵修也罢,茹皓也罢,似乎都没有把高肇视为竞争对手,因为他们各自在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不一定是竞争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高肇的个人素质和风格还是很不一样,他没有如赵修、茹皓那样在极短时间内八面树敌,在长达十三四年的时间里从没有引发宣武帝的疑忌和疏远。
现在我们随着高肇的目光,越过权斗,把注意力转向宣武帝的后宫。因为,正是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把我们的主人公慈庆/王钟儿再次卷入历史旋涡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