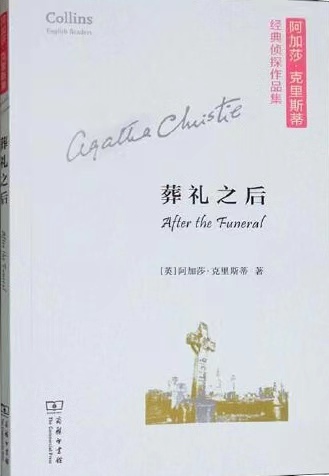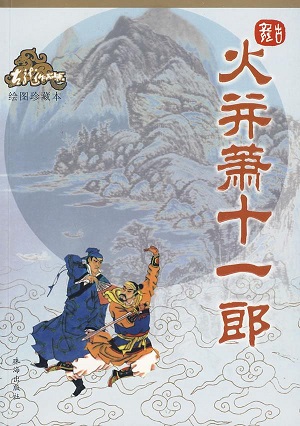第73章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
话说1959年7月21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举行汇报会。
此时,毛泽东已经没有一周前那种轻松了,也没有3天前决定印发《阿Q正传》时那样坦然了。在庐山会议与会者中,已经分成了两大派: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但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刘澜涛、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朱德。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起而反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除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的一些负责人以外,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站在了彭德怀的对立面。而且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了。
支持彭德怀的人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毛泽东“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不像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那么得心应手”。会下还有人议论说:“举凡是犯路线错误,自己都是不能纠正的。”
反对彭德怀的人说:彭德怀是拉队伍。书记处快一半对一半了。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他在西北组发牢骚说:“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他在南京的火车上讲:“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和各大区负责人在这天晚上的汇报会上都发言说,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度难关。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说: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为了你彭德怀,我给林彪发了复员费,叫贺龙登门道歉,叫萧克做检查,还有刘伯承泪洒怀仁堂。请苏联红军来?苏联红军就听你的?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胸膛开始起伏,喘息声也逐渐变得粗重起来。又有人汇报说:
“今天总理召集开会,曾希圣、谭震林同黄克诚拍桌子大吵一通。”
“吵什么?”
“周惠说,各省第一书记应该各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毛泽东“噢”了一声,将大手一扇,说: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党内一部分材料我还没看完。”
他略一停顿,嘴角浮出带有嘲讽的浅笑,接着说道: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要顶住,顶1个月,2个月,半年,1年,3年5年,10年8年。”
有人插话说:
“打个持久战。”
毛泽东说:
“赞成。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作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劝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作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我劝同志们沉住气,继续往后看。”
毛泽东多年来从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晚上失眠了。他吃了3片安眠药,但仍然无法入睡,只好在屋里来回踱步,以待黎明。
那些批评他的人,用孔子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来咒骂他。毛泽东在不眠之夜,忍受着诅咒他断子绝孙的那种不公开的指责和折磨。
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彭德怀则认为三面红旗本身有问题,应当解决指导思想问题。毛泽东把国内外阶级斗争与彭德怀的意见联系起来,认为彭德怀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怀疑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有联系。赫鲁晓夫1958年在北京嘲笑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刚从东欧回来的彭德怀也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认为彭德怀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想在党内“出来挂帅”,要篡党夺权。
他彻夜难眠,写信给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准备答复彭德怀的发言稿。
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说她马上飞到庐山来,以便在这场斗争中和毛泽东待在一起。毛泽东说:
“不要来了,斗争太激烈了。”
江青还是来了。
7月22日,毛泽东找来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泽东的。他说:
“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
7月22日晚,毛泽东后半夜吃了安眠药,还不能入睡,便打电话找来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和刘少奇、周恩来议定: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凌晨3点,刘少奇走后,毛泽东吃了3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管理员急了,问道:
“主席,你这几天吃不好,是不是饭做得不好?”
“不是你们的事。”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句,管理员不便再问了。值班卫士对管理员说:
“3天,整整3天不怎么吃饭。端上去了,又拿下来了,吃也只吃一点。咱不知道什么事,不但我们不知道,再往上七八个级别的也不知道。不是中央委员级的,谁也不知道,不准进去呀。”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来到交际处西餐厅,走到前台,他见政治局委员应该坐的第一排交椅上没有彭德怀,便四处张望,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望望会场,以下巴示意说:
“那边,门口。”
毛泽东终于看到了彭德怀剃了很亮的光头。他远远地坐在门那边,一脸的不悦之色。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坐了下来。他的眼圈里布满了红丝,以沉闷抑郁的声音开始讲话。他面无表情地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
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3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笔者注)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作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三个月,平均每天有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穷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个地方3个月当中,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要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3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杖,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3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平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3、4月或5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
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笔者注)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笔者注),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笔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6级会议、5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1年2年,3年5年,8年10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4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4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4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有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
“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对众人说:
“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1/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4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4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
接着,毛泽东就讲了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这个典故,而后说:
“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动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 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炼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作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它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