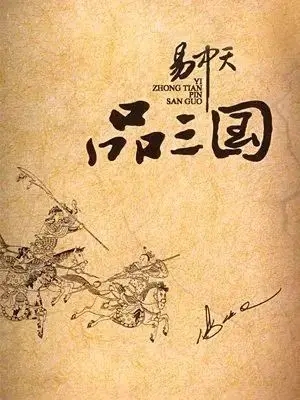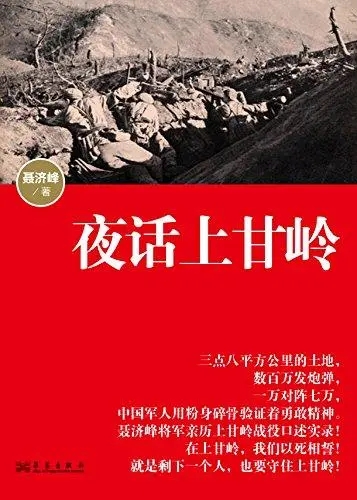人家都是一对对,孤零零撂下你干妹妹。亲亲!
卷心白菜起黄苔,心上的疙瘩谁给妹妹解?亲亲!
打碗碗花儿就地地开,你把你的白脸调过来。亲亲!
白格生生脸脸弯格溜溜眉,你是哥哥的心锤锤。亲亲!
满天星星只有一颗明,前后庄就挑下你一个人。亲亲!
干石板上的苦菜盼雨淋,你给哥哥半夜里留下个门,亲亲......
兰花听着酸歌,常常臊得满脸通红,她真想破口骂这些骚情小子,但人家又没说明是给她唱的,她凭什么骂人家呢?
但是,也有人真的在半夜来敲她的门。这时候她就不客气了。为了不吵醒孩子,她穿好衣服溜下炕,走到门背后,把这些来敲门的男人骂得狗血喷头。罐子村想来这里"借光"的人先后都对她死了心。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使这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对那个二流子男人保持着不二忠贞。只要他没死,她就会等待他回来。她在一年中漫长的日月里,辛劳着,忍耐着。似乎就是为了在春节前后和丈夫在一块住几天。几天的亲热,也就使她忘记了一年的苦难。她爱这个二流子还象当初一样深切。归根结底,这是她的丈夫,也是猫蛋和狗蛋的父亲呀!
今年和往年一样一进入腊月,母子三人就开始急切地等待他们的亲人归来。在老父亲和少安的帮助下,兰花今年在地里收回不少粮食,看来下一年里不会再饿肚子。腊月中旬,她就做上了年饭,要让一家人过个好年。孩子们不时念叨着父亲;她兴奋得碾米磨面忙个不停......可是一直到快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还没有回来。两个孩子天天到村中的公路边,等待从黄原那里开过来的长途汽车,每当有车在路边停下,猫蛋和狗蛋就发疯似地跑过去,看是不是父亲回来了。结果一次次都失望地看着汽车向米家镇那里开走。车上下来的都是别人家的父亲——村里所有在门外的人都回家过春节,唯独他们的父亲没有回来。
大年三十那天,兰花默默地作好了四个人的年饭,然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手拉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从家里出来,立在公路边上,等待从黄原开过来的班车。
村中已经响起了一片爆竹声,到处都飘散着年茶饭的香味;所有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嗷嗷喊叫着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清冷的寒风中,兰花母子三人相偎着站在公路边上,焦灼地向远方张望。
黄原的班车终于开过来了!
但车没有在罐子村停,刮风一般向米家镇方向开了过去,车里面看来没坐几个人——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大年三十才回家呢?
汽车走了,只留下一条空荡荡的路和路边上三个孤零零的人。
猫蛋和狗蛋几乎一齐"哇"地哭出了声。兰花尽管被生活操磨得有点麻木,但此刻也忍不住伤心,泪水在那张饱经忧患的脸上淌着。她只好哄儿女说:"甭哭了,咱们到你外爷爷家去过年......
兰花拉着两个孩子回到家里,把做好的年茶饭用笼布一包,然后锁住门,母子三人就去了双水村......兰花和孩子门怎能想到,大年三十那天,王满银还踯躅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身上的钱只够吃几碗面条,甭说回家,连到黄原的一张汽车票都买不起。
这位生意人通常作不起大买卖。因为没有本钱,他一般只倒贩一点猪毛猪鬃或几张羊皮,赚两个钱,自己混个嘴油肚圆就心满意足了。在很多情况下,他象一个流浪汉,往返流落在省城和黄原之间的交通上;这条线上的大小城镇都不止一次留下了这个二流子的足迹。他也认识不少类似他这样的狐朋狗友;有时候嘴巴免不了要吊起来,就在这些同类中混着吃喝点什么。当然,他也得随时准备款待嘴巴吊起来的朋友。他从没想到过要改变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浪荡的品质似乎都渗进了他的血液。有时候,他记起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心里忍不住毛乱一阵。但二两劣等烧酒下肚,一切就又会忘得一干二净,继续无忧无虑地往返于省城和黄原的大小城镇,做他的无本生意。
入冬以后,生意更难做了。政策一活,大量的农民利用农闲时节,纷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使得象王满银这样的专业生意人陷入困境之中。
眼看走投无路,身上的几个钱也快吃光的时候,他突然听说上海的木耳价钱很贵,一斤能卖二十多元。这"信息"使王满银萌发了到上海贩卖一回木耳的念头。本地木耳收价每斤才十来元,可以净赚十多元呢。好生意!
可是想想他身上剩了四五十块钱,只能买几斤木耳,跑一回上海实在划不来。他只好望"海"而兴叹。
但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天,他在黄原和省城之间的铜城火车站碰见他丈人村里的金富。他和金富在这一线的各种车站常常不期而遇。王满银明白金富是干什么行当的,知道他身上有钱。他于是就低声下气开口向这个小偷借贩木耳的钱。"得多少?"金富很有气派地问。
"有个五百......来块就行。"
"那太多了!我只有一百来块。"
"也行!"
这位小偷慷慨解囊,给王满银借了一百块钱。金富有金富的想法。他知道王满银的妻弟孙少安是双水村的一条好汉,和他爸他二爸的关系也不错。和一个乡邻总比惹一个强。再说,二流子王满银还不起帐,他将来也有个讨债处——据说少安家现在发达起来了。
王满银拿了金富的一百块钱,很快托一位生意人朋友买好木耳,就立刻坐车去了上海。他是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做生意,除不心怯,情绪反倒十分张狂,似乎想象中的钱已经捏在手里了。
到上海后,他一下子傻了眼。这里木耳价并没有"信息"传播得那么高,每斤在自由市场上只能卖十四六元。他又没拿自产证,一下火车就被没收了,公家每斤只给开了十三元钱。妈的,这可屙下了!
王满银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仓惶逃出了这个冷酷的城市。
他从上海返回省城时,象神差鬼使似地,碰巧又在火车站遇见了金富。他只好给小偷还了一百块债,身上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连原来带的几十块钱,也大部分贴进了这趟倒霉的生意中。
金富当时念老乡的可怜,引他在街上吃了一顿饭,然后又把他带到自己住的一个私人开的旅店里。
两手空空的王满银跟着这位小偷走进一间阴暗的小房子。
金富拉过一条枕巾把皮鞋擦了擦,然后在洗脸盆里撒了泡尿,对王满银说:"你做那屁生意能赚几个钱?你干脆跟我学几手,票子有的是!"
王满银畏惧地笑笑,说:"我怕学不会......"
"只要下苦功,就能学会!看,先练这!"金富说着,便伸开两只手,将突出的中指和食指连续向砖墙上狠狠戳去。他一边示范,一边对王满银说:"每天清早起来,在吃饭和撒尿之前,练五百下。一直练到伸出手时,中指和食指都一般齐,这样夹钱就不会拖泥带水。另外,弄一袋豆子,每天两只手反复在豆子中插进插出几百下。这些都是基本功。最后才练最难的;在开水里放上一个薄肥皂片,两个指头下去,练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你速度自然就快了;肥皂片在水里又光又滑,你能夹出来,就说明你的功夫到家了......"
王满银坐在床边上,听得目瞪口呆。他绝对吃不了这苦,也没这个心胆。他摇摇头说:"我怕没本事吃这碗饭......"
金富一看王满银对此道不感兴趣,也就对王满银不感兴趣了,说:"我下午就走呀,马上得结房费!
这等于下了逐客令。王满银只好离开这个贼窝子,重新来到省城的大街上。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这会儿心里倒怪不是滋味。往年他总要年前的十来天赶回家里;而且身上也有一点钱,可以给两个孩子买点礼物。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血,他在心里也亲他们,只不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记不得他们的存在。只有春节,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
可是现在,别说给孩子买点什么,连他自己也没钱回家了。
王满银在省城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遛达。他也坐不起公共车,在寒风中缩着脖子,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一直逛到两只脚又疼又麻才返回到火车站的候车室——他临时歇脚的地方。
因为临近春节,候车室一天到晚挤得水泄不通。他要等好长时间,才能抢到一个空座位,而且一坐下屁股就不敢离椅子,否则很快就被别人抢占了。
他就这样在省城一直滞留到春节。他一天只敢到自由市场买几个馒头充饥。有时候,他也白着脸和一位卖菜的农民死缠赖磨,用一分钱买两根大葱,就着馒头吃,算是改善一下伙食。
大年三十夜晚,火车站的候车室一下子清静下来。除过少数象他这样的人外,只有不多一些实在走不了的旅客。
这一晚倒好!市委书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亲自推着煮好的饺子,来到候车室慰问旅客,王满银高兴地从市委书记手里接过一盘热腾腾的大肉水饺——在市委书记给他递饺子时,还有一群记者围着照相,闪光灯晃得他连眼睛也睁不开(他并不知道,他和市委书记的这张照片登在了第二天晚报的头版上)。
这会儿,王满银不管三七二十一,喜得咧开嘴巴,端了一大盘饺子回到一个角落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过了一会,他才发现他旁边有位妇女,也端一盘饺子在飞快地吃。这女人吃饺子时,还把自己的一个大提包别在胳膊上。王满银心想,她大概把他看成个小偷了。哼,我才不是那号人呢!
这妇女竟然搭讪着和他拉起话来。口音一听就是外路人!王满银老半天才弄明白,这位妇女是个生意人,是从广东来的。
同行遇同行,倒使两个人很快成了知音。这妇女告诉他,她提包里装的是电子手表——说着便拿出来一只让王满银看。
"一只卖多少钱?"满银惊讶这妇女带这么多手表,看来是个大富翁——他想文化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有个洪常青,说是南洋来的大富翁......嗯,这女人大概也是从南洋来的!
"南洋女人"告诉他,一只手表卖二十元。
"才二十元?"王满银顿时惊讶得张开嘴巴,连饺子也忘记吃了。他对"南洋女人"说:"要是在我们那里,一只起码能卖一百多块钱!"
现在"南洋女人"又惊讶得张开了嘴巴,她说:"只要一只能卖五十块,给我抽二十块红利!"
王满银本来没有光气的眼睛一亮,把盘子推到旁边,说:"可惜我身上没钱,要么我一下都买啦!唉,我的钱......让小偷偷了,现在连路费也没有。你要愿意,干跪跟我到黄原去,肯定能卖大价钱!"
"一只能卖五十元吗?"那女人两只眼睛也闪闪发光了。"六十元都能卖出去哩!"
"能卖五十元就行了。"
"为什么?"
"这表是香港走私来的,是玩具表,里面都是塑料芯......"
那女人冲王银满诡诈地笑了笑。
王银满又瞪住了眼。他问:"那能走多长时间?""最长大概半年吧......"
"不怕!半年以后谁能找见卖表的人?你愿意,明天就跟我走!不过,你得先给我买一张到黄原的汽车票!"这女人立刻表示同意。
这真是狗屎到头上了——交了好运!王银满来了神,兴致勃勃地说:"虽然你是个女的,咱们也就算是拜识了,我就称呼你是干姐!"
"干姐?""南洋女人"一时明白不了。
王银满解释了半天,那女人就乐意认了这个"非常关系"。
于是,大年初一,王银满带着他新结识的伙伴,坐汽车回到了黄原。然后这"干姐弟"俩就在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以每只六十五元的价格,开始出售这批香港产的塑料芯玩具手表......
过罢正月十五的灯节以后,农村的节日气氛就渐渐淡了下来。人们又周而复始地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有些勤快的庄稼人,已经往山里送粪了;等惊蛰一过,农事就将繁忙起来。
兰花和两个孩子作梦也想不判,正月十八,王银满突然回家来了。不是他一个人回来,还带着一个操外路口音的女人。满银给妻子解释,这是和他一块作买卖的生意人,是从"南洋"来的。那女人也就嬉笑着对兰花说了许多话,可兰花一句也没有听懂。
厚道的兰花并没有因为丈夫带回个女人就乱猜想什么,她反而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远地来的客人。在这个农村妇人的眼里"南洋女人"是个大人物,能进她的寒窑穷舍,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她热情地把那些留下的年茶拿出来,款待丈夫和这位女宾。
兰花和两个孩子兴奋得象重新过年一样。"南洋女人"从提包里抓出大把的奶糖,撒土坷垃一般撒在炕席片上,让猫蛋和狗蛋吃。王满银让这两个娃娃学城里人的样,叫这女人"阿姨"。只是"阿姨"说的话,娃娃们一句也解不开。
王银满带回一个"外路"女人的消息,一天内就传遍了罐子村。村中的大人娃娃就象看"西洋镜"一般轮番涌进兰花家那孔破窑洞,稀罕地来看这个说话象绵羊叫唤的女人。
看完稀罕以后,罐子村的精明人都不出声地笑了。他们知道王银满和这女人是怎么一回事。也有人羡慕地巴咂着嘴,对他们村这个二流子油然生出一种"敬意";哈呀,这家伙本事不小,竟然挂回来个外路货!
不用说,兰花立刻成为全村人同情或耻笑的对象。
但这个迟钝女人并没有感觉到这一切。全村人突然挤到她家来所造成的热闹气氛,使她更加高兴起来,觉得她男人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她和孩子们脸上也有了光彩。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可怜的女人才知道这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晚上,兰花忧愁地把丈夫叫到院子里,和他商量,让这位"南洋女人"睡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家就这么一孔破窑洞,得开口向别人家借个地方让这女人休息。象样一些的人家他们不敢开口;穷家薄业的人家又怕委屈了客人。
但王银满无所谓地说:"借什么地方呢?就睡在咱们炕上!"
兰花听满银这么说,又惊讶又难受,她一年没见男人,这一晚上对她是多么宝贵呀!她问丈夫"那你到什么地方去睡呢?"
王银满倒惊讶起来:"我也在家里睡呀!"
"那......"
"那什么哩?"
兰花尽管心里不畅快,也只好就这样忍受了。
晚上睡觉时,兰花本指望这位尊贵的客人自己能提出异议,但她却心安理得睡在她为她铺好的被褥里了。"南洋女人"睡在靠锅头的地方,中间隔着两个孩子"兰花紧挨孩子,王银满睡在靠窗户的边上。这个编排还算"合理"。熄灯以后,兰花躺在被窝里,胸膛里象塞进去一把猪鬃。她多么希望钻到丈夫的被窝里去,可羞耻心使她连动也不敢动。她敢怎样呢?后炕头睡个生人,稍有动静,人家就能听见。唉,什么地方来了这么个勾命鬼呀!她躺在黑暗中,开始痛恨起这个女人。
前半夜她怎么也睡不着,后半夜,瞌睡终于压住了骚动的欲望。她睡着了,但还能听见自己的鼾声。
突然,沉睡中的兰花觉得她的脚被什么碰了一下。她的心立刻缩成一团。黑暗中她微微睁开眼,看见丈夫光身子象狗一样从她脚底下慢慢往后炕头爬去。她牙齿拼命咬住嘴唇,才没让自己喊出声来。
她狠狠踹了一脚那个爬行动物!
王银满立即调过身子,悄悄摸着爬进了自己的被窝。
不一会一只求饶的手伸进;她的被窝,企图抚摸她。她用指甲在这只手上狠狠掐了一下。那只手象被蜂蜇一般,猛地缩回去了。兰花忍受着煎熬,终于等到了窗户纸发亮。
她起身穿好衣服,没等孩子睁开眼,就一个人溜下坑,出了门。
她象受伤的母牛一般,几乎是小跑着转到公路上,在黎明中出了寂静无声的到罐子村,向石圪节公社走去——她要向公家告那个不要脸的"南洋女人"。
当兰花气喘吁吁地进了公社院子的时候,公家人刚刚吃完了早饭。公社干部过春节后大部分还没有回来,只有文书和主任涂治功。
兰花一进徐治功的办公室,就鼻子一把泪一把向主任叙说起了她的苦情。
徐治功几乎一直笑着听这位农村妇女说完她的不幸。他喷了一口烟,说:"现在这社会,这号事不算事!我们管不了"
"你们连坏人也不管了?"兰花瞪着红肿的眼睛,问徐主任。
"那你写状子告嘛!"徐主任仍然笑着说。
"我不识字。"兰花难住了。
"那你找个人写嘛!"
"你给我找个人......"
"这又不是我的事!"徐治功不耐烦地说,"我把这号事也管了,其它大事谁管呀?"
"你不找个人,我就住在你这里不走!"创伤深重的兰花也不顾一切了。
"咦呀,你给我耍起了赖!"徐治功叫道。
"我就不走!"兰花说完,竟然放开声嚎了起来。
心烦意乱的徐治功只好把公社文书叫来,对他挤挤眼:"你去给她代写个状子!"
文书对主任会意地点点头,便劝说兰花不要哭,跟他到隔壁窑洞写状子。
兰花立刻顺从地跟文书别了隔壁;接着又向这位年轻的公家人叙说了一遍"南洋女人"和她丈夫的长长短短。不一会,徐主任过来了,声色俱厉地对文书说:"你带两个民兵,立刻到罐子村去,把王银满和那个女人捆到公社来!"文书马上站起来,说:"我这就去!"
兰花瞪大眼,喊叫说:"怎连我男人也绑呀?"徐治功说:"怎不绑你男人?这号事主要是整治男的!""那不能!"可怜的女人叫道,"我是来叫你们光把那个女人撵跑......"
徐治功对文书挤挤眼:"快去吧!把王满银绑紧些!"
文书一本正经正准备往门外去,兰花一扑起来,从文书手里夺回"状子",说:"你们不要去,我不告了!"
她说完,便很快起身出了公社大门。徐治功和文书站在门台阶上张开嘴只是个笑。
可怜的兰花出了石圪节,又折转身往家里走。她原指望公家把那个坏女人赶跑就行了,结果公家要把她男人一齐绑走。她舍不得让男人受罪......当她痛不欲生地返回家里后,无耻的丈夫和那个女人正在锅灶上做饭。狗蛋在炕上嚼奶糖;猫蛋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兰花本想扑上去撕那个不要脸女人的脸,但"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又使她放弃了这种打算——她一闹,一家人在村里就要臭一辈子!
她问儿子:"你姐姐呢?"
"姐姐到外婆家去了"狗蛋津津有味地吃着糖。女儿一个人跑到双水村去干什么呢?
痛苦的兰花脑子已经完全乱了。她不知道她应该怎么办。王银满若无其事地厚着脸和她说话,她也不搭理,一个人走到后窑掌的黑暗处,两只手胡乱地翻搅着,耳朵里塞满了各种杂乱的声响。
当她糊里糊涂在一个角落里翻出一些红绿纸包时,突然怔住。她想起,这是几年前满银贩卖剩下的一些老鼠药——当年正是这些药让公社把他拉到双水村的工地上,劳教了十几天。
兰花面对着这些小纸包,心脏剧烈的跳动起来。这些药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使她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死。是呀,她真不想活了,虽然她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她也是个人——正因为她大字不识,她心中就更容纳不了如此的事情!她不愿让公家拿法绳把她的男人绑走;但又没能力把那个女人赶走;她更没勇气为这事公开闹一场——这样她的孩子和娘家门上的人都没脸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死的念头一刹那间便占据了她的心。
她在黑暗中哆嗦了一下。
她看见男人和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在说话。她没听清他们说什么。但她知道,那两个人现在装得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凤凰窝里钻进来个黑老鸦,这个坏女人已经完全象这个家里的人了。她被她挤在了一边。她半辈子受死受活,如今落了这么个下场,她也没脸活了。去死呢!她相信人死了以后还能轮回转世,有可能转成人,也可能转成动物。不管来世是人还是牲灵,她都还要转生到罐子村来;这里有她的亲骨肉;她要来看她的猫蛋和狗蛋......怎个死法?不能死在这个家里。不能死在仇人的面前。老鼠药没水吞咽不下去......对,到前河湾的水井边去;那里僻静,也有水。
兰花这样想着,就拣了一些绿纸包的药揣在衣袋里。她喜欢绿纸包而不喜欢红纸包。她从小就喜欢绿颜色,因为山里的庄稼,树木和草都是绿的;她记起她小时候也常爱用绿线绳来扎头发......
兰花随即调过身,从后窑掌的黑暗中走出来,脸色灰白,嘴唇紫黑,两只眼睛模模糊糊。她没管锅台边那两个不要脸的人,一直走到前炕边,一言不发地的把狗蛋抱在怀里,接着便出了家门。
她恍恍惚惚来到村前的公路边,把儿子放在地上,泪水汹涌地从两只皱纹包围的眼睛里淌出来。她拼命在儿子脸上亲了又亲,然后对他说:"你到双水村找你外爷外婆去......你不要回来了......"
狗蛋瞪着一双大眼睛,用两只脏手为母亲揩去脸上的泪水,问她:"妈妈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不去外婆家?"兰花哽咽着说:"你先去,妈妈过一阵就来了......"狗蛋听妈妈的话,就象个大人似的,背抄起两条小胳膊,挺着胸脯去了。从罐子村到双水村只有几里路,他常和姐姐相跟着去外爷家,因此,一个人上路也不胆怯。
兰花用手扶住路边一根电线杆,哭着对远去的儿子喊:"你靠路边走,不要走路中间,操心汽车......"儿子调过头向她招招手,说:"噢!"
当狗蛋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公路上后,兰花就迈着两条软绵绵的腿,向公路下面的河湾走去。
她来到河边的水井旁,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从衣袋里掏出那几包老鼠药。她立刻感到胸脯上象压了个什么东西,气也出不上来,好象已经把毒药吞咽了似的。她张开嘴巴,呼出的气在隆冬中变成了一团团白雾。
东拉河覆盖着厚厚的坚冰,水流在冰层下咕咕地响着。山野里灰漠漠地看不见任何一点活物。寒风吹着尖锐的口哨从沟道里刮过来,把地上枯黄的树叶和庄稼叶一直扬到半空中。
天阴了。寒冷中夹带着一种潮湿。看来要有一场雷。是呀,应该下雪了,她想。一个冬天没见一片雪,麦子旱干不说,开春动农怕也没办法下籽种。今年要象去年就好了,一年雨水不断,秋夏都是好收成......一个要死的人坐在水井边,手里捏着几包致命的毒药,心里还在盘算着日月和天年——这就是我们的兰花!
唉,可怜的人儿,对你来说,好象死是一回事,日月天年是另一回事。你也不想想,你死了以后,这一切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可你不会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因为你相信你死了以后还会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的,你怎能不再来这个世界呢?不管活在这世界上有多苦,但你总归还是那么爱这世界!你在黄土地上劳动惯了,再说,你也舍不得离开亲爱的猫蛋和狗蛋——你还要来看他们;哪怕转生成猪狗,也要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兰花将那几包老鼠药打开,把那些灰土一样的药粉倒进手心里,头扬起来,瞥了一眼阴沉沉的天空,然后就把药粉全部倒进了自己的嘴巴。
她用两只手在冰冷的水井中捧了一掬凉水,低下头喝一口,把药粉冲下了肚子。
现在她坐在水井边的石头上,闭住眼睛,静静地等待死神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