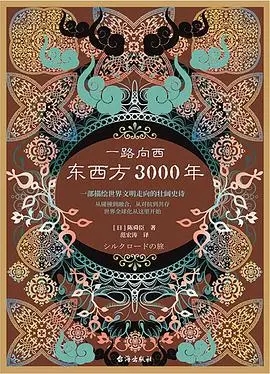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2〕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蹰”,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
新近就因为豫想的不对,自己找了一个苦吃。《世界文库》〔3〕的编者要我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没有细想,一口答应了。这书我不过曾经草草的看过一遍,觉得写法平直,没有现代作品的稀奇古怪,那时的人们还在蜡烛光下跳舞,可见也不会有什么摩登名词,为中国所未有,非译者来闭门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样的名词,譬如电灯,其实也不算新花样了,一个电灯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样:花线,灯泡,灯罩,沙袋,扑落〔4〕,开关。但这是上海话,那后三个,在别处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5〕,讲到铁厂,后来有一位在北方铁厂里的读者给我一封信,说其中的机件名目,没有一个能够使他知道实物是什么的。呜呼,——这里只好呜呼了——其实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纪末我在江南学习挖矿时,得之老师的传授。不知是古今异时,还是南北异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学家靠它修养的《庄子》和《文选》或者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来。没有法子。“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最没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还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灵》,以为这倒不算什么,担当回来,真的又要翻译了。于是“苦”字上头。仔细一读,不错,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要感得到;虽然重译,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锋头。里面确没有电灯和汽车,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菜单,赌具,服装,也都是陌生家伙。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但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罚酒是应该喝干的:硬着头皮译下去。到得烦厌,疲倦了的时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灾乐祸之意,其意若曰:这回是轮到我舒舒服服的来看你们在闹什么花样了。
好像华盖运还没有交完,仍旧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学》四卷六号,一翻开来,卷头就有一幅红印的大广告,其中说是下一号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题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编辑先生的确曾经给我一封信,叫我寄一点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谓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广告来了,情同绑票,令我为难。但同时又想到这也许还是自己错,我曾经发表过,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挤出来的〔6〕。他大约正抓住了这弱点,在用挤出法;而且我遇见编辑先生们时,也间或觉得他们有想挤之状,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说:“我的文章,是挤也挤不出来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
但是,积习还未尽除,稿费又究竟可以换米,写一点也还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的“挤”的本领。袖手坐着,想打盹,笔一在手,面前放一张稿子纸,就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写出些什么来。自然,要好,可不见得。
二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7〕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传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但副词的“地”字,却还是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惯了这字的读者已经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发见我的新职业了:做西崽〔8〕。
还是当作休息的翻杂志,这回是在《人间世》二十八期上遇见了林语堂先生的大文,摘录会损精神,还是抄一段——“……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辫子,然则‘快来’何不因‘快’字是状词而改为‘快地的来’?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怪相,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今文八弊》中)
其实是“地”字之类的采用,并非一定从高等华人所擅长的英文而来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况且看上文的反问语气,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实际上也并不将“快来”改为“快地的来”,这仅是作者的虚构,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谓“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之例了。不过不切实,倘是“自称摩登”的“今人”所说,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还住在故乡,看了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们那里只有几个洋教堂,里面想必各有几位西崽,然而很难得遇见。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标本,虽不过“颇”,也够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后来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许多洋人,因此有着许多西崽,因此也给了我许多相见的机会;不但相见,我还得了和他们中的几位谈天的光荣。不错,他们懂洋话,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这是他们的吃饭家伙,专用于服事洋东家的,他们决不将洋辫子拖进中国话里来,自然更没有捣乱中国文法的意思,有时也用几个音译字,如“那摩温”,“土司”〔9〕之类,但这也是向来用惯的话,并非标新立异,来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10〕;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不过要戴草帽,眼镜也不用玳瑁边的老样式,倘用华洋的“门户之见”看起来,这两样却不免是缺点。
又倘使我要另找职业,能说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为我以为用工作换钱,西崽和华仆在人格上也并无高下,正如用劳力在外资工厂或华资工厂换得工资,或用学费在外国大学或中国大学取得资格,都没有卑贱和清高之分一样。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乐,除非你扫了他的兴头。三
由前所说,“西崽相”就该和他的职业有关了,但又不全和职业相关,一部份却来自未有西崽以前的传统。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11〕,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的文素臣〔12〕,就是这标本。他是崇华,抑夷,其实却是“满崽”;古之“满崽”,正犹今之“西崽”也。
所以虽是我们读书人,自以为胜西崽远甚,而洗伐未净,说话一多,也常常会露出尾巴来的。再抄一段名文在这里——“……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
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今文八弊》中)〔13〕
但是,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14〕,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从而“闻”的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15〕,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外国的文人,要在中国闻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够的,他反要得到轻薄。
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16〕,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对于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语堂先生的训词移到这里来的——
“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不过后两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来思去,不过“奴”得巧妙一点而已。中国宁可有未“思”的西崽,将来的文学倒较为有望。
但“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国却确是不遇的。中国的立学校来学这四国语,为时已久〔17〕,开初虽不过意在养成使馆的译员,但后来却展开,盛大了。学德语盛于清末的改革军操,学法语盛于民国的“勤工俭学”〔18〕。学英语最早,一为了商务,二为了海军,而学英语的人数也最多,为学英语而作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最多,由英语起家的学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军不过将军舰送人,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19〕,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20〕。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
然而现在又到了“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的危机,弱国文人,将闻名于中国,英美法德的文风,竟还不能和他们的财力武力,深入现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没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动手,但见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些洋话,“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时,这才来“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当然也是好极了的,然甲则曰不佞望洋而兴叹,乙则曰汝辈何不潜心而探求。旧笑话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闻股肉可疗,而自怕痛,执刀出门,执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惊拒,孝子谓曰,割股疗父,乃是大孝,汝竟惊拒,岂是人哉!〔21〕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说法虽乖,功效实同”,是好辩解。六月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一号。
〔2〕严又陵(1853—1921)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及“定名之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3〕《世界文库》郑振铎编辑,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每月发行一册,内容分中国古典文学及外国名著翻译两部分。该刊于第一年印出十二册后,第二年起以《世界文库》的总名改出单行本。鲁迅所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在印单行本前曾连载于该刊第一年第一至第六册。
〔4〕沙袋旧式电灯为调节灯头悬挂高低而装置的瓷瓶,内贮沙子,故俗称沙袋。扑落,英语Plug的音译,今称插头或插销。
〔5〕指略悉珂所作的《铁的静寂》。《一天的工作》,鲁迅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内收作家十人的作品十篇(其中二篇系瞿秋白译,署名文尹),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6〕关于文章是挤出来的,作者曾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说:“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
〔7〕上田进(1907—1947)日本翻译家。曾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多种译成日文。
〔8〕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林语堂在《人间世》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今文八弊(中)》一文中说:“(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赶时髦,生怕落伍,于是标新立异,竞角摩登。……譬如医道,以西洋爱克斯光与中国阴阳五行之说相较,……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说法虽乖,功效实同。……一入门户之见,便失了自主,苦痛难言,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下面就紧接着这里所引的一段文字。
〔9〕“那摩温”即英语Numberone的音译,意为第一号,当时上海用以称工头。“土司”,即英语Toast的音译,意为烤面包片。
〔10〕《探母》即京剧《四郎探母》。演的是北宋杨家将故事。
〔11〕“事大”服事大国的意思。语出《孟子·梁惠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12〕文素臣小说《野叟曝言》中的主角,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这里说他“崇华,抑夷”,是因为书中有关于他“征苗”、“平倭”的描写。这书写的是明代中叶的事,说他是“满崽”,似有误。
〔13〕这一段引文见于《今文八弊(中)》之二“随行随失,狗逐尾巴”一节中。
〔14〕《小说月报》一九一○年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容是刊载文言小说和旧诗词笔记等,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主编,经过改革,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停刊。一九二一年十月该刊第十二卷第十号曾出版“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增刊,刊有鲁迅、沈雁冰等译的波兰、捷克等国的文学作品和介绍这些国家的文学情况的文章。
〔15〕“花旗”旧时我国一些地方对美国的俗称;“茄门”,英语German的音译,通译日耳曼,指德国。
〔16〕《天方夜谈》现译《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
〔17〕清同治元年(1862)在北京设立了培养译员的学校,称“京师同文馆”,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馆,次年添设法文、俄文馆,后又设德文、日文馆。
〔18〕“勤工俭学”一九一四年蔡元培等成立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到法国“勤劳作工,节俭求学”;当时赴法求学的人不少。该会于一九二一年停办。
〔19〕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文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英国的如司各德(WScott,1771—1832)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迭更斯(CDickens,1812—1870)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狄福(DDefoe,约1660—1731)的《鲁滨孙飘流记》,斯惠夫特(JSwift,1667—1745)的《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等。
〔20〕田汉参看本卷第214页注〔9〕。他曾在一九二一年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罗蜜欧与朱丽叶》和《哈孟雷特》,由中华书局印行。
〔21〕这则笑话见于清初石成金所著《传家宝》的《笑得好》初集,题为《割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