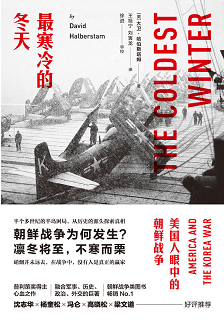子由述苏轼书学渊源说:“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仿佛近之。”可见苏轼从小就喜欢书法。少时开手学写,所经过的一段临摹功夫,苏过作《书先公字后》:
公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俗子初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
其实徐浩书法,也是出于二王,苏轼学过兰亭,就会有几分徐浩的面目;苏轼自言写字稍得意处,则似杨风子,风子上承唐颜,其传承如徐浩之与兰亭一样。所以论苏书渊源,以黄庭坚的说法,最中肯綮: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宋〕黄庭坚:《山谷集》。]
书法自来分两派,一派是王羲之,一派是颜真卿。王字劲逸,颜字雄浑。苏轼兼通其意,如其自言:“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形成苏书独有的特点。
前人论中国书法,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说,意言晋人重自然,襟怀雅达,所以顾盼风流;唐人拘泥古法,刻画临摹,虽然典型宛在,而生气遂失;宋人书风,大都以意为之,莫顾陈式,率由胸襟,所以能够充分见出自我,表现出极为自由的特色。
颜书陶铸万象,隐括众长,苏轼倾倒万分,他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行者,殆难复措乎。”(《书唐氏六家书后》)学颜者出沈传师、柳诚悬的瘦硬通神,苏轼中年以前的作品,时有此意;五代杨凝式(景度)虽亦师法鲁公,但他自有精神气魄,表现一流天真的风神,而且笔笔敛锋入纸,兼有兰亭的笔法。
杨氏的书法,是由唐入宋的一大枢纽,而苏轼字学的基础,完全与他相同,所以庭坚每赞轼书,就常常提及杨氏,苏轼自己也说过:“仆书作意为之,颇似蔡君谟(襄),稍得意则似杨风子,更放则似言法华。”师承和气质交互影响,相辅而成一家之法,像什么人,其实并不重要。
“宋人尚意”,亦须至北宋中叶以后,始成风气,前于此的蔡襄,还是“笔有师法”,不能完全自由创意。欧阳修与蔡襄论书:“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其实并非“忽不为尔”,还是因为当时的人墨守《淳化阁帖》迹和古贤遗法,无法跳出唐人的传统窠臼之故。
苏轼经过初步的学书阶段后,他首先扬弃的,就是束手缚脚的石刻碑帖。他不取石刻,不临碑帖,认为书经镂刻,神气总不完全,他不要那些遗神袭貌的东西,独重古人真迹,每有所得,将它悬诸壁间,行起坐卧,随时注目,心摹手追,但求得其大意,领悟笔墨间的精神,再不措意于点画的形似。他是从学书旧法中获得解放的第一人,所以有一首《与子由论书》诗曰: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
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
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所以他绝不规规矩矩临摹点画,也不以一家一体为满足,而所见墨迹日益丰富,解悟也就随时增进,从此肆其雄健的笔力,千变万化,写出他自己胸中的学问文章之气。
他一面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但语舒尧文有言:“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任何学问都要有根柢,要能“通”,书法也不例外。
他对专工临摹者,非常轻视。章惇元祐间被逐居颍,闲来无事,日临兰亭一本。苏轼听人传说,笑道:“工摹临者非自得,从门入者非宝,章七终不高耳。”
书须出自己意,意则包括见识学问,除此之外,还需有极其熟练的技法。苏轼少年习字,则与常人不同,他以抄经史练字,一举两得。
北宋中叶,雕版印书虽已相当发达,但像他这样一个生长眉州偏鄙之地的寒士,得书不易,还是需要手自抄写的,而这抄书的习惯,他复终生不懈,即使在黄州行年五十了,仍以抄书为日课。晁补之说:“苏公少时抄书,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后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
由此可知,苏轼抄书,不单为了便于记诵,同时亦即习字,而且习以己意为书,随时变化,因此,他的书法,时时不同,李之仪跋苏书曰:
余从东坡游旧矣,其所作字,每别后所得,即与相从时小异,盖其气愈老,力愈劲也。
又曰:
东坡从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观之,几不出于一人之手。(《姑溪集》)
苏轼自跋诗卷,也说:“观此真迹,如觉伪者,甚可笑也。”则如时日久远,连他自己也真赝莫辨起来。
书法学者常将苏轼书法分为三个时期。自少至贬谪黄州以前为第一期,以学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黄庭经》为主,多写小楷和小行书,笔致华丽而刻意求工过甚;后期学颜真卿,元丰元年书《表忠观碑》,就有东方先生画赞的气象。第二期从黄州开始,历元祐一朝为止,这时期身遭挫折,以笔墨发泄感情,如《寒食帖》写得笔飞墨舞,既遒劲,又飘逸,纵横变化,痛快淋漓,黄山谷说:“此书兼有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元祐八年书《李太白仙诗》则酒酣放浪,神游八表,纯以神行于笔势墨气之间,已经到了化境。第三期则是海外东坡的晚年时期,笔力雄健无匹,纵笔所至,无不惬意,到了精纯圆熟的巅峰。
苏轼执笔近下,且取斜势,像操刀治印的姿态一样,固然有顿挫深入、笔笔有力的好处,但非正轨的执法。有人说他写字腕著笔卧,所以左低右高,左秀右枯,作戈(斜钩)多成病笔。山谷替他辩护道:“此则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写字,爱用浓墨,墨浓必须有极大指力,才能笔不凝滞。苏轼之所以要以侧笔多用中锋,盖求力透纸背;要运侧笔,使浓墨,则又非紧握笔管的下方不可,都是互相关联的。李之仪跋《孙莘老寄墨四首》诗说:
东坡捉笔近下,特善运笔;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浓研几如糊,然后濡染。
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苏书真迹,幅幅都是墨色如漆,虽历千年,而光彩照人。有人评议苏书太肥,本来字肥易俗,杜甫就认为瘦字好看,苏轼不服,作《墨妙亭诗》说:“少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又云:“余书如绵里铁。”但如肥得有力,有何不可?
明董其昌评苏书《赤壁赋》:
坡公书多偃笔,亦是一病。此赤壁赋庶几所谓欲透纸背者。乃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真迹在王履善家,每波画尽处,隐隐有聚墨痕,如黍米珠琲,非石刻所能传耳。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笔法,况墨法乎?(《画禅室随笔》)
说到运笔的方法,历来书家,多重悬腕,谓悬笔始能力聚毫端,笔笔中锋;而陈师道《后山谈丛》说:
苏黄两公皆喜书,不能悬手。逸少非好鹅,效其腕颈耳,正谓悬手转腕;而苏公论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此其异也。
其实,苏轼这种运笔方法,却得之于欧阳修的传授,《东坡题跋》云(“记欧公论把笔”):
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柳诚悬之语良是。
使指运而腕不知,正是以手抵案、腕著笔卧的写法,书多偃笔,当是不能悬腕之故,不能悬腕,当然更不能悬肘,运笔的幅度小,放不开,所以苏轼自认他写不好径尺以上的大字,即是此故。
苏轼认为学书须以端楷为基础,他说:“真(楷)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本集:《书唐(坰)氏六家书后》。]
关于各种书体的写法,苏轼按他自己的经验说:“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患无法。……”
苏轼因以抄书习字,所以擅于写小字和行书,而自认“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与谢民师推官书》)。但是山谷说:“东坡尝自评作大字不如小字,以余观之,信然。然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虽时有遣意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
一般人的见解,认为草书的功用在于简便快速,苏轼非常反对这个说法,他喜欢草书,在于草书的体势得以自由流走变化,易于发挥作者的个性,抒写作者的感情,使书法更为接近艺术的境域。所以,《再和潜师》诗:“东坡习气除未尽,时复长篇书小草。”另有《书赠徐大正》一段颇含禅意的话:
或问东坡草书,坡云:“不会。”进云:“学人不会?”坡云:“则我也不会。”[〔宋〕苏轼:《东坡志林》。]
其实,他是很喜欢草书的,本意在求书写时的自由流走之乐,不在写得好与不好。有一则草书题跋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他作草书,是假借笔势的挥洒,自求创作的快乐,所以说:“遇天色明暖,笔砚和畅,便宜作草书数纸,非独以适吾意,亦使百年之后与我同病者有以发之也。”[〔宋〕朱弁:《曲洧旧闻》。]
苏轼所谓“不践古人”者,已通古人之法而不践一家之谓,否则任性乱涂,还成什么书法,所以他说:“草书患无法。”有个黄庭坚学草的故事,可以参看:
元祐间,山谷与东坡、穆父(钱勰)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为称赏,旁观的穆父说:“鲁直之字近于俗。”
“何故?”山谷问。
“没有别的,只因没有见过怀素的真迹。”穆父说。
当时,庭坚心里很疑惑,不过从此也就不敢再替人写草书。到绍圣年间,庭坚谪居涪陵,才得见到怀素《自叙帖》真迹于石扬休家,借了回来,专心临摹,至于废寝忘食的地步,由此悟出草法。所以,草书要有法,也非易事。[〔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赵令畤《侯鲭录》略同。]
气势是苏轼作书的动力,因此,他有个特殊的习癖,无论写字作画,都非于酒后不可,尤其是写大字或草书,更须醉后才作。苏轼自言酒后作书的快感:“吾醉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宋〕赵令畤:《侯鲭录》。]
自题草书云:“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无择法师求他写大字,复书说:“吾师要写大字,特为饮酒数杯。……”若不喝酒,他即不能写字,与李廌(方叔)书说:“暑中既不饮酒,无缘作字。”
黄庭坚是目睹他此一特癖的人,记曰:
东坡居士性喜酒,然不能四五仑,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者。
艺术家而有这种习癖者,不止苏轼一人。吴道子“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张长史的草书,苏轼称其“颓然天放,恣态自足,号称神逸”者,他也是必须酒喝够,才能写,苏轼讥评他:“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醒醉之辨。若逸少(王羲之)何尝寄于酒乎?”他不自觉察,这话也说着了自己的毛病。
苏轼鉴评他人书法,也很严格,不轻许可,论前人者,如欧阳率更,体貌寒寝,便说他“劲险刻厉,正称其貌”。于褚河南,则曰:“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同时代人中,他最佩服的是蔡襄(君谟),于欧阳修则字以人重,兹不具论。
评米元章、王定国曰:“自君谟殁后,笔法衰绝。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亦必有传于世也。”
黄庭坚类于苏轼的书法,再三再四地赞叹,苏轼也很欣赏山谷书的功力,但以为与其为人不类,题山谷草书《尔雅》后曰:“鲁直以真实心出游戏法,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磊落人录细碎书,亦三反也。”实则他们两人的书道,完全不同:苏宗晋唐,黄追汉魏;苏才浩瀚,黄思邃密;苏书势横,黄书势纵。因为有这么许多异处,即使字形,一个横出,一个纵长,所以留传一段轶话:
苏轼论山谷书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反唇相讥道:“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这当然是互相调笑的话,不是正评。但你如有兴趣将苏、黄二帖,放在桌上,对照来看,相信你也定会莞尔一笑的。
苏轼成名后,所至之处,向他求书乞画的人,从无休歇,他亦不甚矜惜,纵笔挥染,随纸付人。但乞者亦必须有术,如纸墨不佳,或指定尺寸大小,或托书的文字不雅,则他亦一定拒绝,这是书画家的通例,不足为奇。宋画习用细绢,有以绫绢求书者,苏轼便说:
“币帛不为服章,而以书字,上帝所禁。”这是他惜物的本性。
黄庭坚曾将求苏书的诀窍教与王立之,致柬云:“来日恐子瞻来,可备少纸,于清凉处设几案陈之,如张武笔,其所好也。”
纸笔精良,墨佳汁稠,他必乐于挥洒。不过,更不能忘记准备好酒佳肴。
苏轼在翰林院日,有个朋友韩宗儒,常常托故写封信来换取他手写一纸复帖。苏帖到手,便拿到殿帅姚麟那儿去,换十几斤羊肉来饱餐一顿。黄庭坚听到了这个秘密,便对苏轼说笑道:“从前王右军写的是换鹅书,如今二丈书,可名为换羊书了。”苏轼大笑。
一日,苏轼在院,圣节撰制甚忙,宗儒连来数简,派来的人立庭下催索复信,苏轼便到庭前对来人说:“传语本官,今日断屠。”[〔宋〕赵令畤:《侯鲭录》。]
苏轼不耐空闲,得闲而又兴致来时,不待求他亦会一口气写好多张,分与身旁的人。某日在翰林院,清闲无事,忽令左右取纸笔,写渊明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两句,大字小楷,行书草书,各体皆有,连写七八张,掷笔叹口气道:“好,好!”恰似热渴者饱饮了凉水一样痛快。既已发泄,便将这些字幅,分赠左右给事的幸运者,毫不矜惜。[佚名:《道山清话》。]
但如苏辙那样,将他写赠的书件,随便送人,他却大不满意,跋所书《清虚堂记》云:
世多藏余书者,而子由独无有。以求之者众,而子由亦以余书为可以必取,每以与人而不惜。昔人求书法,至拊心呕血而不获,裸雪没腰,仅乃得之。今子由既轻以余书与人,何也……
黄山谷说:“蜀人极不能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又曰:“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者,例不工书,而东坡则例外,故为世所重。”[〔宋〕赵令畤:《侯鲭录》。]
大文豪的蜀人苏轼,岂仅工书,而是融会二王和颜鲁公的字艺,建立宋人自由创意的书风之一大家。
轼书名重一代,但在元祐党祸时期,摧碑断石,被人珍藏的墨迹,也尽归隐没,灭失甚多。至徽宗好苏书,群又贡书作为进取官爵之用,一时成为风气,谁藏苏书多,谁就可以夸耀于人,因此便产生了许多赝品。苏过说,从此“朱紫相乱,十七八矣”[〔宋〕苏过:《斜川集·书先公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