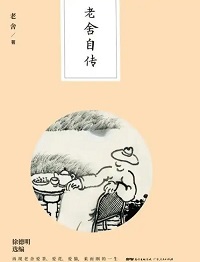苏轼爱好绘画,一半由于天性,一半由于家庭熏陶。老苏是个“燕居如斋,言笑有时”,态度严肃的人,于物一无所好,独喜收藏绘画。他的门人弟子为讨他欢喜,争相赠送他所嗜好的画件,希望能看到他解颜一笑。所以苏轼虽然是个布衣,但藏画之富并不输与公卿人家[本集:《四菩萨阁记》。]。苏轼自幼耳濡目染,养成他在这方面深厚的兴趣与鉴识的能力。
但在同一家庭里生长的苏辙,却完全没有这个兴趣。苏轼说:“子由之达,自幼而然。当先君与某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唯子由视之漠然,不甚经意。”[〔宋〕苏轼:《东坡志林》。]苏辙非但没有这个嗜好,而且根本否定绘画,充分表现他的天分中毫无艺术细胞。苏轼在《石氏画苑记》里,曾记其言。
子由尝言:所贵于画者,为其似也,似犹可贵,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见人物,皆吾画笥也;所不见者独鬼神耳,当赖画而识,然人亦何用见鬼。
年长一辈的苏洵,心理上不免向往盛唐时代富强灿烂的文化,所以也就特别喜爱代表这一时代精神的吴道子的画风,年轻时期表现欲望非常强烈的苏轼,对于笔力雄放、气势蓬勃的吴道子,盛赞曰:“道子实雄放,浩然海波翻。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几句话如移来称扬苏轼自己的诗文字艺,正也非常恰当,可以说是异代人之间性情与气谊的十分投合。
苏轼曾于凤翔东塔夜观王维壁画,残灯影下,恍惚觉得画上僧人踽踽欲动,徘徊观摩,久久不能离去。古来画人,皆是职业画家,都不读书,与诗人气息不通,而王维则“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他是个出生早于杜甫的唐代大诗人,兼工绘画,曾颇自豪地说:“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即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对于这位融诗画于一身的大师,寻到了自己美感的归宿,不禁顶礼膜拜:“吴生(道子)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苏轼是诗人爱画,摩诘的画使他觉得气血相通,如相知心;但他对于吴道子大气磅礴的画艺,依然非常向往。元丰八年《书吴道子画后》将吴画比颜字、韩文和杜诗,备极倾倒,如言:
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苏轼激赏吴道子者,是他绘事的气魄;倾倒于王摩诘者,是他画中的诗情;非但毫无低昂二人之意,并且承认他们各有千秋的地位。苏轼自许:“平生好诗仍好画。”(《郭祥正家醉画竹石》诗)认为吴道子的笔力气势,王摩诘那种诗不能尽,溢而为画的艺术精神,则是他于绘画的最高理想。
在西洋,虽然公元前的罗马批评家贺拉斯(Horace)在其《诗艺》中已经揭出“诗即是画”的理论。后来须到十九世纪,英国的文艺复兴史专家佩特(W. H. Pater, 1839—1894)才指出“诗是有声之画,画是无声之诗”。文艺复兴时代,此论在欧洲方才大为盛行;而在中国,唐朝的王维创之于先,苏轼发扬于后,他明白说出诗与画是不分的,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无形的画,如读杜甫诗和观韩幹画马,本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然而他说:
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幹丹青不语诗。
此画此诗真已矣,人间驽骥漫争驰。(《韩幹马》诗)
他在精神上,已将诗画融合一体,认为诗与画的表达功能是可以合一的,其目的同为追求一种脱离尘俗的意境,为人们在混沌的世俗生活中带来清新的感受。因此诗、书、画是一个思想整体之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哪一种表现,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互相呼应出作者的憧憬和追求,作者的思想抱负及其为人之基本态度。诗画之理一律,所以在情绪反应上,诗画之趣也当一致。
苏轼自幼好画,全集中题画诗统计约有六十一题,一百零九首之多。他观画作诗,多数出于一种品赏的态度,只从画中景物下手,直接抒写画面所给予他的感受,因此深得画中之趣。读这类诗,常会忘记他是在题别人的画,误以为这正是他自己用文字(诗)来描写同一题材,将诗与画的表达方法揉而为一,也可以说是“画不能尽,溢而为诗”者。
如《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又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之一:
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
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如前者,陈善《扪虱新话》便谓:“此便是东坡所作的一幅梅竹图。”
苏轼深爱杭州西湖,作诗曰: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是千年来写西湖景色最好的一首诗。诗中所写的西湖,同时有阴晴浓淡两种景色,则又不是一幅画面的空间所能容纳的了。
苏轼似乎有意要证明“画即是诗”,如题《王伯扬所藏赵昌花四首》之一(黄葵)诗,简直要使在夏日下的那一丛折枝黄葵,色彩鲜明、风姿绰约地活现在读者的眼中:
弱质困夏永,奇姿苏晓凉。
低昂黄金杯,照耀初日光。
檀心自成晕,翠叶森有芒。
古来写生人,妙绝谁似昌?
晨妆与午醉,真态含阴阳。
君看此花枝,中有风露香。
苏轼读画,不但深得画趣,而且常借画中形象,抒述自己的怀抱:如《韩幹画马赞》,说画中这四匹“丰臆细毛”的厩马,虽于山林间悠游自得,萧然如贤士大夫之临水濯缨,但终不如野马之无拘无束、得遂自由的天性;如《李潭六马图赞》,强调“络以金玉,非为所便”之可悲;如《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诗,则以为御厩之马,养尊处优,毫无贡献,不如山西战马,吃苦耐劳,勇于赴险,更为可贵。
以上虽论画马,实是苏轼自述其志。
苏轼诗作中,有一绝大特色,即最爱用颜色字,在他集中,不胜枚举。不但用颜色渲染境界,而且更常使用颜色增加读者视觉上的享受,加强事物的观照,与画家使用颜料涂抹画面,毫无二致。现在摘录数则,以证苏轼“诗亦是画”的理论。
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黄菊为谁开?(《九日寻臻阇黎》)
日上红波浮翠巘,潮来白浪卷青沙。(《次韵陈海州乘槎亭》)
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鸣。(《溪阴堂》)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病中游祖塔院》)
碧玉碗盛红马脑,井花水养石菖蒲。(《赠常州报恩寺长老》)
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望湖楼醉书》)
上述几个例句,岂不每联都是色彩缤纷的图画?再举一首全诗,其笔下的强烈色调,竟像是凡·高(Van Gogh)的画作,通幅燃烧着生命热情,强烈奔放。那时他在惠州,和朋友野外散步,望见有一人家,篱间杂花盛开,他便叩门求观。出来的主人林姓老媪,白发青裙,独居已经三十年了。苏轼便用他的诗笔来作画道:
缥蒂缃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春忙。
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桑。
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篱破屋为谁香。
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娘。
苏轼用文字画的是浅绿浅黄色的缥蒂花苞从大红的花萼里绽露出来,绿树丛中结着青色的果子,紫色的含笑花,如火如荼的红棉杂生在篱落间,落日红霞里有缕袅袅青色的炊烟,短篱破屋衬出高洁的白发青裙。最妙的是他能利用杜诗“黄四娘家花满蹊”来做结语,以“黄四娘”对“青裙袂”,真是神来之笔。[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一:“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诗不如画者是画面上的线条和色彩,画不如诗者是形象上的轻重疾徐,感官上的冷暖,性分中的理趣。所以画是静态的,诗可以写动态。德国的莱辛(G. E. Lessing)指出视觉术中,绘画的范围是空间,诗歌的范围是时间[〔德〕莱辛:《拉奥孔》(Laoccon),论绘画与诗的界限。]。而苏轼作画,尝欲突破这两大缺憾。苏诗多用颜色字,是要用此来掠取图画之美,又如画风竹即欲加强诗中的动态。守湖州日,游山,途遇大风雨,他便到朋友贾耘老(收)筑于苕溪上的澄晖亭去避雨,画兴忽至,令官伎执烛,画风雨竹一枝于亭壁上。我们今日固已无缘亲见此画,但读他所题诗:
更将掀舞势,把烛画风筱。
美人为破颜,正似腰支袅。
从经验意识上想象一个笑得弯腰婀娜的女郎,那种摇曳生姿的动态,岂不就是竹在风雨中掀舞摇晃的姿势。《说文解字》:“笑字,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故苏轼以女郎的娇笑来比喻画中的风竹。诗耶?画耶?归于圆融一体了。
黄山谷题苏轼画《竹石图》:“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又为苏轼与李公麟合作的《枯木道士图》撰赋,说他们的画是“取诸造物之炉锤,尽用文章之斧斤”。莫不说他的画即是他的诗篇,即是他的文章,以文学的修养,直接移入画面的创造。这创造,就是中国美术史上文人画派的成熟。
照西洋美学家的说法,美感的经验,当为形相之直觉,所以美感应该诉诸人的感觉,而非诉诸人的知识。轼诗: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形似”只能传达知识概念,画虎不可类狗,画马不可似骡,单是形似,不能发生美的感觉,亦即不是艺术。我们在生活的各种形相中,吸收若干知识概念,要将这种概念用艺术方法表达出来,以经过美化创造的形相来触发他人的感情,而不直接诉诸人的知识。这种表达的工具,在绘画即是形色,在音乐则是声音,在诗歌则为文字。
形色不是图画,文字非即诗歌,苏轼所以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事物有一定的形相,固不可失,而事物形相有其一定的常理,尤不可违。《净因院画记》言: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水石、竹林,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亦有不知。……
苏轼读画,观察敏锐,他评同时代最有名的花鸟画家黄筌画雀,说他所画飞鸟,颈足皆展,是违背常理的,因为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鸟飞时绝不两展颈足。《东坡志林》里他又记载一个故事:以画牛独步晚唐的戴嵩,有幅斗牛图,被一牧童见到,大笑道:“牛斗,力在角,尾当搐入两股间。这幅画上的牛,掉尾而斗,错了。”
伟大的画家李龙眠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某一暇日,黄、秦诸君在馆中观画,庭坚取出一幅龙眠画的《贤己图》来看。图中聚博者六七人,围据一局;骰子在盆内旋转,已定者五枚,都是六点,一枚还在转;其中一人俯首盆边,张口大叫,余人注视,神情画得惟妙惟肖。苏轼从外来,在众人同声赞叹中,看了图,便说:“龙眠天下士,怎么学起闽语来了?”
众皆不解所谓,轼曰:“四方语音,说‘六’都是闭口音,只有闽语才张口的。现在盆内都是六点,只有一子未定,法当呼六,而呼者张口在叫,却是为何?”
皖人李公麟本来不解闽语,听了这个批评,只能笑服其言。[〔宋〕岳珂:《桯史》。]
苏轼既承王维诗画的影响,纯粹的画技已经不能使他满足,要更进一层追求形理以上的自我精神的发挥,达成形神两全的艺术创造。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称顾恺之“格调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意者,是画人把自己内心世界的生命感情(即神或气)表现出来。立意是画之始,是全画的灵魂,建立意境是绘画的基本原则。
创作必先通过“实对”的阶段,实对即现代所说的写实功夫,其中包括形和理。经过画家形象思维的过程,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被画的客观事物做有机的联想,通过外部的形相,传达出内部蕴涵的精神,古人称为“迁想妙得”。
苏轼论书法:“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他对绘画也持同一意见,作《次韵水官诗》:
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
譬如善游者,一一能操船。
这是说写字作画,要有学问的根柢,精神的修养;若无精神学问的修养,一味讲求技术,刻画求工,最多只能画出形象的皮相;或者因袭古人的成法,不成其为创作,画中没有画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修养,只剩形相的空壳,即是画工的俗笔。书“宋汉杰画”说: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气,看数尺许便倦。
意即精神,气则为势、为力。作用必须自有创意,在题材的形象之间,悟出可以寄托精神的所在,以形写神,即是借外部的形相,抒写自己内在的思想感情,才能表露画的生动性和真实感;以纯熟的笔墨,纵横挥洒,使机无阻滞,才能将画者的生命感情注入这幅画件。意气所到,则此画便气韵生动,神完意足,成为一幅“真士人画也”的艺术品了。
被画的对象,常是块然无情的外物,必须使无情的山水、竹石、花鸟等等题材,化成我的生命感情所寄托的有情天地,于是画者与读者才能获得感情的沟通,从而得到情绪的解放与满足,此即苏轼称文同画竹所说的:“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欣赏一幅好画的趣意与欣赏一首诗的美感就自然趋于一致,诗情画意融化浑成为一时,即已达到中国文人画的最高境界。
文人品画,脱离不掉文学欣赏的习惯,以鉴赏文学的观念来评量一幅画作的价值。诗画既成一体,则当代文学的风尚,便领导了美术思想和绘画发展的方向。
宋诗的理想,一反唐代富丽的词藻和激烈的感情,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当代文宗欧阳修对于诗的主张是:
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宋〕魏庆之:《诗人玉屑》。]
如将上面的这个“言”字改成“画”字,亦即当时画学的主流。
中国的文学传统,在于追寻自然。敏感的知识分子要逃避痛苦的现实,只想把这无限烦恼的人生,安放在大自然中去,期求心志的宁静,精神的解放,使人与自然在精神上得到美的合一。因此田园诗和山水画成为诗与画之主要的内容。
从王维开始,才有完全排除人物或故事的,纯粹以山水为内容的水墨画出现;后与宋代疏易平淡的诗风互为呼应。李成创枯木寒林图法,王诜是继承营丘的高手之一;苏轼虽以画竹为主,但在黄州,也画寒林,而且颇自得意,与王定国书说:“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这种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的《寒林图》,正如萧散淡泊的诗境,同为宋代文人所特别爱好的境界。
苏轼本是文同后一人的画竹名家,受了《寒林图》的影响,便加变化,用淡墨扫老木古蘖,配以修竹奇石,形成了古木竹石一派。苏轼自负此一画格,是他的“创造”。在黄州时,他作枯木一帧,又竹石一帧,寄章楶(质夫):
某近者百事废懒,唯作墨木颇精。奉寄一张,思我者,当一展观也。
后又书云:
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前者未有此体也。
在苏之前,未有此体,而苏轼为此创格,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本画竹,不过把所画的领域略作扩大而已。重要的是苏轼所作,性与画会,能把内部生命中满溢的感情、高洁的品格和迈往的豪气,完全贯注到简单平易的画面中去。山谷说:“东坡居士作枯槎、寿木、丛筱、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此即是他所鼓吹的“意气所到”的成就。
苏轼性好尝试,许是受了李公麟的影响,也曾戏作人物画,画乐工一幅,作乐语以汉隶题曰:“桃园未必无杏,银矿终须有铅。荇带岂能拦浪,藕花却解流连。”[〔宋〕何薳:《春渚纪闻》。]又画过应身弥勒像,相传是南迁途中寄与秦观者,原录是“东坡居士游戏之作”,实在太不了解流人心理上的痛苦和祈求解脱的迫切。[释德洪《石门文字禅》:题东坡画应身弥勒。]
最有趣的是苏轼南迁后,画一背面人像,举扇障面,上书“元祐罪人写影,示迈” 八字,人在无可奈何的痛苦中,只有自嘲能够轻减心理负担,这也是苏轼所惯用的。[吴师道《吴礼部集》:“自画背面画。”]
据著录说,兰陵胡世将收藏过一张苏轼画的螃蟹。蟹是那么细琐的小动物,应非惯于大笔挥洒的苏轼的题材。胡托夏大韶持请晁补之鉴定,补之还特地做了一篇文章大论苏轼奇文高论,大处固然豪放不羁,但也有细针密缕的功夫。[〔宋〕晁补之:《鸡肋集》。]
据说,苏轼曾试以蔗渣画石,松煤作枯木[〔元〕王沂:《竹亭集》。]。主张画与书法相通的赵孟頫曾说:“石如飞白木如籕。”按汉之飞白书,今已不得见,似为渴笔健锋之作。苏轼用这新工具画石,当是利用它易作渴笔,易着腕力;以松煤作枯木,效果或许像今之石炭画,不知何以后不继作,亦无记述。总之,苏轼无处不用他的聪明而勇于尝试。
苏轼写字用墨,浓研如糊,作画亦然。方薰《山静居画论》记所见:“老坡竹石,石根大小两竿,仰枝垂叶,笔势雄健,墨气深厚,如其书法,所谓沉着痛快也。”吴修说:“东坡墨竹,写叶皆肥厚,用墨最精。”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说:“东坡墨竹,干粗如儿臂,墨色浓润沉郁。”——这些都是后代书画家所见真迹之共同认识。我以为苏轼书画用墨浓厚,与作诗喜用颜色字,完全由于他性喜沉着痛快和一种强势发挥的表现欲望所造成的。
另一特色是无论书字作画,都以醉笔为胜。酒能解放精神上的束缚,助长笔墨的气势,可以将他郁积在内部生命里的感情,痛痛快快地宣泄出来,画中的精神意气,即是其人肝肺所生的牙角。
即使一向对苏轼存有成见的朱熹,也不得不说:
东坡老人英俊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几似之。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百世之下,尚可想见也。[〔元〕王沂:《竹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