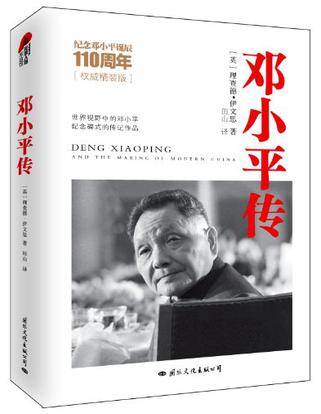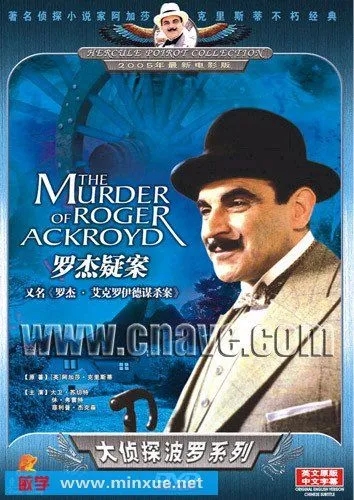段誉被鸠摩智点了穴道,全身动弹不得,给几名大汉横架在一匹马的鞍上,脸孔朝下,但见地面不住倒退,马蹄翻飞,溅得他口鼻中都是泥尘,耳听得众汉子大声吆喝,说的都是番话,也不知讲些什么。他一数马腿,共是十匹马。
奔出十余里后,来到一处岔路,只听得鸠摩智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话,五乘马向左边岔路行去,鸠摩智和带着段誉那人以及其余三乘则向右行。又奔数里,到了第二个岔路口,五乘马中又有两乘分道而行。段誉心知鸠摩智意在扰乱追兵,叫他们不知向何处追赶才是。
再奔得一阵,鸠摩智跃下马背,取过一根皮带,缚在段誉腰间,左手提着他身子,便从山坳里行去,另外两名汉子却纵马西驰。段誉暗暗叫苦,心道:“伯父便派遣铁甲骑兵不停追赶,至多也不过将这番僧的九名随从尽数擒去,可救我不得。
鸠摩智手中虽提了一人,脚步仍极轻便。他越走越高,三个时辰之中,尽在荒山野岭之间穿行。段誉见太阳西斜,始终从左边射来,知道鸠摩智是带着自己北行。
到得傍晚,鸠摩智提着他身子架在一株大树的树枝上,将皮带缠住了树枝,不跟他说一句话,甚至目光也不和他相对,只是背着身子,递上几块干粮面饼给他,解开了他左手小臂的穴道,好让他取食。段誉暗自伸出左手,想运气以少泽剑剑法伤他,哪知身上要穴被点,全身真气阻塞,手指空自点点戳戳,全无半分内劲。
如此数日,鸠摩智提着他不停的向北行走。段誉几次撩他说话,问他何以擒住自己,带自己到北方去干什么,鸠摩智始终不答。段誉一肚子的怨气,心想那次给妹子木婉清擒住,虽然苦头吃得更多,却绝不致如此气闷无聊。何况给一个美貌姑娘抓住,香泽微闻,俏叱时作,比之给个装聋作哑的番僧提在手中,苦乐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般走了十余天,料想已出了大理国境,段誉察觉他行走的方向改向东北,仍然避开大路,始终取道于荒山野岭。只是地势越来越平坦,山渐少而水渐多,一日之中,往往要过渡数次。终于鸠摩智买了两匹马与段誉分乘,段誉身上的大穴自然不给他解开。
有一次段誉解手之时,心想:“我如使出‘凌波微步’,这番僧未必追得上我?”可是只跨出两步,真气在被封的穴道出被阻,立时摔倒。他叹了口气,爬起身来,知道这最后一条路也行不通的了。
当晚两人在一座小城一家客店中歇宿。鸠摩智命店伴取过纸墨笔砚,放在桌上,剔亮油灯,待店伴出房,说道:“段公子,小僧屈你大驾北来,多有得罪,好生过意不去。”段誉道:“好说,好说。”鸠摩智道:“公子可知小僧此举,是何用意?”
段誉一路之上,心中所想的只是这件事,眼见桌上放了纸墨笔砚,更料到了十之八九,说道:“办不到”。鸠摩智问道:“什么事办不到?”段誉道:“你艳羡我段家的六脉神剑剑法,要逼我写出来给你。这件事办不到。”
鸠摩智摇头道:“段公子会错意了。小僧当年与慕容先生有约,要借贵门六脉神剑经去给他一观。此约未践,一直耿耿于怀。幸得段公子心中记得此经,无可奈何,只有将你带到慕容先生墓前焚化,好让小僧不致失信于故人。然而公子人中龙凤,小僧与你无冤无仇,岂敢伤残?这中间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公子只须将经文图谱一无遗漏的写出来,小僧自己绝不看上一眼,立即固封,拿去在慕容先生墓前火化,了此宿愿,便即恭送公子回归大理。”
这番话鸠摩智于初入天龙寺时便曾说过,当时本因等均有允意,段誉也觉此法可行。但此后鸠摩智偷袭保定帝于先,擒拿自身于后,出手殊不光明,躲避追踪时诡计百出,对九名部属的生死安危全无丝毫顾念,这其间险刻戾狠之意已然表露无遗,段誉如何再信得过他?心中早就觉得,南海鳄神等“四大恶人”摆明了是恶人,反而远较这伪装“圣僧”的吐番和尚品格高得多了。他虽无处世经历,但这二十余日来,对此事早已深思熟虑,想明白了其中关窍,说道:“鸠摩智大师,你这番话是骗不倒我的”。
鸠摩智合什道:“阿弥陀佛,小僧对慕容先生当年一诺,尚且如此信守,岂肯为了守此一诺,另毁一诺?”
段誉摇头道:“你说当年对慕容先生有此诺言,是真是假,谁也不知。你拿到了六脉神剑剑谱,自己必定细读一番,是否要去慕容先生墓前焚化,谁也不知。就算真要焚化,以大师的聪明才智,读得几遍之后,岂有记不住之的?说不定还怕记错了,要笔录副本,然后再去焚化。”
鸠摩智双目精光大盛,恶狠狠的盯住段誉,但片刻之间,脸色便转慈和,缓缓的道:“你我均是佛门弟子,岂可如此胡言妄语,罪过,罪过。小僧迫不得已,只好稍加逼迫了。这是为了救公子性命,尚请勿怪。”说着伸出左手掌,轻轻按在段誉胸口,说道:“公子抵受不住之时,愿意书写此经,只须点一点头,小僧便即放手。”
段誉苦笑道:“我不写此经,你终不死心,舍不得便杀了我。我倘若写了出来,你怎么还能容我活命?我写经便是自杀,鸠摩智大师,这一节,我在十三天之前便已想明白了。”
鸠摩智叹了口气,说道:“我佛慈悲!”掌心便即运劲,料想这股劲力传入段誉膻中大穴,他周身如万蚁咬啮,苦楚难当,这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嘴上说得虽硬,当真身受死去活来的酷刑之时,势非屈服不可。不料劲力甫发,立觉一股内力去得无影无踪。他一惊之下,又即催劲,这次内力消失得更快,跟着体中内力汹涌奔泻而出。鸠摩智大惊失色,右掌急出,在段誉肩头奋力推去。段誉“啊”的一声,摔在床上,后脑重重撞上墙壁。
鸠摩智早知段誉学过星宿老怪一门的“化功大法”,但要穴被封,不论正邪武功自然俱都半点施展不出,那知他掌发内劲,却是将自身内力硬挤入对方“膻中穴”去,便如当日段誉全身动弹不得,张大了嘴巴任由莽牯朱蛤钻入肚中一般,与身上穴道是否被封全不相干。
段誉哼哼唧唧的坐起身来,说道:“枉你自称得道高僧,高僧是这么出手打人的吗?”
鸠摩智厉声道:“你这‘化功大法’,到底是谁教你的?”
段誉摇摇头,说道:“化功大法,暴殄天物,犹日弃千金于地而不知自用,旁门左道,可笑!可笑!”这几句话,他竟不知不觉的引述了玉洞帛轴上所写的字句。
鸠摩智不明其故,却也不敢再碰他身子,但先前点他神封、大椎、悬枢、京门诸穴却又无碍,此人武功之怪异,实是不可思议,料这门功夫,定是从一阳指与六脉神剑中变化出来,只是他初学皮毛,尚不会使用。这样一来,对大理段氏的武学更是心向神往,突然举起手掌,凌空一招“火焰刀”,将段誉头上的书生巾削去了一片,喝道:“你当真不写?我这一刀只消低得半尺,你的脑袋便怎样了?”
段誉害怕之极,心想他当真脑将起来,戳瞎我一只眼睛,又或削断我一条臂膀,那便怎么办?一路上反覆思量而得的几句话立时到了脑中,说出口来:“我倘若受逼不过,只好胡乱写些,那就未必全对。你如伤残我肢体,我恨你切骨,写出来的剑谱更加不知所云。这样吧,反正我写的剑谱,你要拿去在慕容先生墓前焚化,你说过立即固封,决计不看上一眼,是对是错,跟你并不相干。我胡乱书写,不过是我骗了慕容先生的阴魂,他在阴间练得走火入魔,自绝鬼脉,也不会来怪你。”说着走到桌边,提笔摊纸,作状欲写。
鸠摩智怒极,段誉这几句话,将自己骗取六脉神剑剑谱的意图尽皆揭破,同时说得明明白白,自己若用强逼迫,他写出来的剑谱也必残缺不全,伪者居多,那非但无用,阅之且有大害。他在天龙寺两度斗剑,六脉神剑的剑法真假自然一看便知,但这路剑法的要旨纯在内力运使,那就无法分辨。当下岂仅老羞成怒,直是大怒欲狂,一招“火焰刀”挥出,嗤的一声轻响,段誉手中笔管断为两截。
段誉大笑声中,鸠摩智喝道:“贼小子,佛爷好意饶你性命,你偏执迷不悟。只有拿你去慕容先生墓前焚烧。你心中所记得的剑谱,总不会是假的吧?”
段誉笑道:“我临死之时,只好将剑法故意多记错几招。对,就是这个主意,打从此刻起,我拼命记错,越记越错,到得后来,连我自己也是胡里糊涂。”
鸠摩智怒目瞪视,眼中似乎也有火焰刀要喷将出来,恨不得手掌一挥,“火焰刀”的无形气劲就从这小子的头颈中一划而过。
自此一路向东,又行了二十余日,段誉听着途人的口音,渐觉清雅绵软,菜肴中也没了辣椒。
这一日终于到了苏州城外,段誉心想:“这就要去上慕容博的坟了。番僧逼不到剑谱,不会就此当真杀我,但在那慕容博的墓前,将我烧上一烧,烤上一烤,弄得半死不活,却也未始不可。”将心一横,也不去多想,纵目观看风景。这时正是三月天气,杏花夹径,绿柳垂湖,暖洋洋的春风吹在身上,当真是醺醺欲醉。段誉不由得心怀大畅,脱口吟道:“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
鸠摩智冷笑道:“死到临头,亏你还有这等闲情逸致,兀自在吟诗唱词。”段誉笑道:“佛曰:‘色身无常,无常即苦。’天下无不死之人。最多你不过多活几年,又有什么开心了?”
鸠摩智不去理他,向途人请问“参合庄”的所在。但他连问了七八人,没一个知道,言语不通,更是缠七夹八。最后一个老者说道:“苏州城里城外,呒不一个庄子叫做啥参合庄格。你这位大和尚,定是听错哉。”鸠摩智道:“有一家姓慕容的大庄主,请问他住在什么地方?”那老者道:“苏州城里么,姓顾、姓陆、姓沈、姓张、姓周、姓文............那都是大庄主,那有什么姓慕容的?勿曾听见过。”
鸠摩智正没做理会处,忽听得西首小路上一人说道:“听说慕容氏住在城西三十里的燕子坞,咱们便过去瞧瞧。”另一人道:“嗯,到了地头啦,可得小心在意才是。”说的是河南中州口音。这两人说话声音甚轻,鸠摩智内功修为了得,却听得清清楚楚,心道:“莫非这两人故意说给我听的?否则偏那有这么巧?”斜眼看去,只见一人气宇轩昂,身穿孝服,另一个却矮小瘦削,像是个痨病鬼扒手。
鸠摩智一眼之下,便知这两人身有武功,还没打定主意是否要出言相询,段誉已叫了起来:“霍先生,霍先生,你也来了?”原来那形容猥琐的汉子正是金算盘崔百泉,另一个便是他师侄追魂手过彦之。
他二人离了大理后,一心一意要为柯百岁报仇,明知慕容氏武功极高,此仇十九难报,还是勇气百倍的寻到了苏州来。打听到慕容氏住在燕子坞,而慕容博却已逝世多年,那么杀害柯百岁的,当是慕容家的另外一人。两人觉得报仇多了几分指望,赶到湖边,刚好和鸠摩智、段誉二人遇上。
崔百泉突然听到段誉的叫声,一愕之下,快步奔将过来,只见一个和尚骑在马上,左手拉住段誉坐骑的缰绳,段誉双手僵直,垂在身侧,显是给点中了穴道,奇道:“小王爷,是你啊!喂,大和尚,你干什么跟这位公子爷为难?你可知他是谁?”
鸠摩智自没将这两人放在眼里,但想自己从未来过中原,慕容先生的家不易找寻,有这两人领路,那就再好没有了,说道:“我要去慕容氏的府上,相烦两位带路。”
崔百泉道:“请问大师上下如何称呼?何以胆敢得罪段氏的小王爷?到慕容府去有何贵干?”鸠摩智道:“到时自知。”崔百泉道:“大师是慕容家的朋友么?”鸠摩智道:“不错,慕容先生所居的参合庄坐落何处,霍先生若是得知,还请指引。”鸠摩智听段誉称之为“霍先生”,还道他真是姓霍。崔百泉搔了搔头皮,向段誉道:“小王爷,我解开你手臂上的穴道再说。”说着走上几步,伸手便要去替段誉解穴。
段誉心想鸠摩智武功高得出奇,当世只怕无人能敌,这崔过二人是万万打他不过的,若来妄图相救,只不过枉送两条性命,还是叫他二人赶快逃走的为妙,便道:“且慢!这位大师单身一人,打败了我伯父和大理的五位高手,将我擒来。他是慕容先生的知交好友,要将我在慕容先生的墓前焚烧为祭。你二位和姑苏慕容氏毫不相干,这就快快走吧。”
崔百泉和过彦之听说这和尚打败了保定帝等高手,心中已是一惊,待听说他是慕容氏的知交,更加震骇。崔百泉心想自己在镇南王府中躲了这十几年,今日小王爷有难,岂能袖手不理?反正既来姑苏,这条性命早就豁出去不要了,不论死在正点儿的算盘珠下或是旁人手中,也没什么分别,当即伸手入怀,掏出一个金光灿烂的算盘,高举摇晃,铮铮铮的乱响,说道:“大和尚,慕容先生是你的好朋友,这位小王爷却是我的好朋友,我劝你还是放开了他吧。”过彦之一抖手间,也已取下缠在腰间的软鞭。两人同时向鸠摩智马前抢去。
段誉大叫:“两位快走,你们打他不过的。”
鸠摩智淡淡一笑,说道:“真要动手么?”崔百泉道:“这一场架,叫做老虎头上拍苍蝇,明知打你不过,也得试上一试,生死............啊唷,啊唷!”
“生死”什么的还没说出口,鸠摩智已伸手夺过过彦之的软鞭,跟着拍的一声,翻过软鞭,卷着崔百泉手中的金算盘,鞭子一扬,两件兵刃同时脱手飞向右侧湖中,眼见两件兵刃便要沉入湖底,那知鸠摩智手上劲力使得恰到好处,软鞭鞭梢翻了过来,刚好缠住一根垂在湖面的柳枝,柳枝柔软,一升一沉,不住摇动。金算盘款款拍着水面,点成一个个漪涟。
鸠摩智双手合什,说道:“有劳两位大驾,相烦引路。”崔过二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鸠摩智道:“两位倘若不愿引路,便请示知燕子坞参合庄的途径,由小僧觅路自去,那也不妨。”崔过二人见他武功如此高强,而神态却又谦和之极,都觉翻脸也不是,不翻脸也不是。
便在此时,只听得(矣欠)乃声响,湖面绿波上飘来一叶小舟,一个绿杉少女手执双桨,缓缓划水而来,口中唱着小曲,听那曲子是:“菡萏香连十顷陂,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滩,笑脱红裙裹鸭儿。”歌声娇柔无邪,欢悦动心。
段誉在大理时诵读前人诗词文章,于江南风物早就深为倾倒,此刻一听此曲,不由得心魂俱醉。只见那少女一双纤手皓肤如玉,映着绿波,便如透明一般。崔百泉和过彦之虽大敌当前,也不禁转头向她瞧了两眼。
只有鸠摩智视若不见,听如不闻,说道:“两位既不肯见告参合庄的所在,小僧这就告辞。”
这时那少女划着小舟,已近岸边,听到鸠摩智的说话,接口道:“这位大师父要去参合庄,阿有啥事体?”说话声音极甜极清,令人一听之下,说不出的舒适。这少女约莫十六七岁年纪,满脸都是温柔,满身尽是秀气。
段誉心道:“想不到江南女子,一美至斯。”其实这少女也非甚美,比之木婉清颇有不如,但八分容貌,加上十二分的温柔,便不逊于十分人才的美女。
鸠摩智道:“小僧欲到参合庄去,小娘子能指点途径么?”那少女微笑道:“参合庄的名字,外边人勿会晓得,大师父从啥地方听来?”鸠摩智道:“小僧是慕容先生方外至交,特来老友墓前一祭,以践昔日之约。并盼得识慕容公子清范。”那少女沉吟道:“介末真正弗巧哉!慕容公子刚刚前日出仔门,大师父来得三日末,介就碰着公子哉。”鸠摩智道:“与公子缘悭一面,教人好生惆怅,但小僧从吐番国万里迢迢来到中土,愿在慕容先生墓前一拜,以完当年心愿。”那少女道:“大师父是慕容老爷的好朋友,先请去用一杯清茶,我再给你传报,你讲好(口伐)?”鸠摩智道:“小娘子是公子府上何人?该当如何称呼才是?”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啊唷!我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叫做阿碧。你勿要大娘子、小娘子的介客气,叫我阿碧好哉!”她一口苏州土白,本来不易听懂,但她是武林世家的侍婢,想是平素官话听得多了,说话中尽量加上了些官话,鸠摩智与段誉等尚可勉强明白。当下鸠摩智恭恭敬敬的道:“不敢!”(按:阿碧的吴语,书中只能略具韵味而已,倘若全部写成苏白,读者固然不懂,鸠摩智和段誉加二要弄勿清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