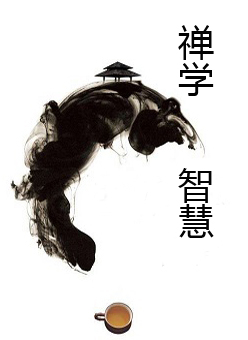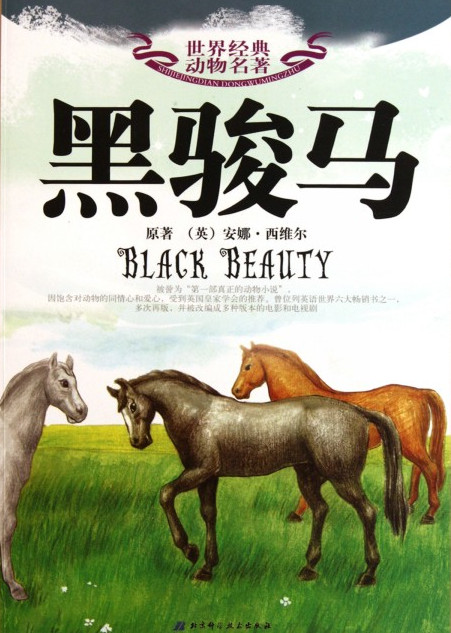她从混乱的梦中惊醒过来;她凝视着白色的天花板一、两分钟,直到她能让自己相信:刚才的一切,只是一个梦而已。
——那确实只是一个梦。
带着寒意的刺目的阳光从打开的窗户中倾泻进来。寒风吹动了窗帘,吹散了窗台上积的一层薄雪。这寒风给小小的房间带来了生气;桃乐丝·布朗特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它似乎让血液的流动加快了。
一切都很正常。她处在乡村的小别墅里,那个她和父亲还有哈利曾下楼在附近结冰的湖上滑冰的地方;也许还能轻轻的滑一下雪,如果能依照天气预报下雪的话。雪确实下了。她本应为此感到高兴的,然而处于某些理由,窗台上的景象让她感到恐慌和震惊。
她一边在温暖的床上发抖,把衣服往上拉盖住了下巴;一边看着床边的时钟——她又睡过头了,父亲和哈利想必已经在等着她吃早饭了吧。她再一次告诉自己一切都很正常;尽管现在她已经全醒了,她仍知道那不是真的。昨天的不愉快感再一次笼罩了她:隔壁的托普汉姆太太,那个老泼妇、那个贼……
那是唯一会破坏这个愉快周末的事。他们一直渴望着去滑冰:锋利的冰刀在冰上滑过时发出的声音、拐弯时留下的长长的划痕,直插入晴朗、寒冷的天空的榆树……但隔壁住着有着极坏习惯托普汉姆太太:她和她偷来的手表一起住在那里。她的存在破坏了一切。别再想了!这样郁闷地想一点好处也没有。别再想了!
桃乐丝·布朗特振作起来,起床了0她去拿睡袍和拖鞋。但放在椅子上的并不是她的睡袍;那是她的毛皮大衣。地上确实有一双软皮拖鞋:那本来是哈利为她从美国带回来的,有着珠子装饰的,用柔软的鹿皮做的拖鞋;但现在那鞋底变得又冷又潮又硬,几乎要结冰了。这时下意识的恐惧感笼罩了她,并且难以驱除了。
她关上窗户,轻轻地走到浴室。有着白色亚麻窗帘和老旧木材味道的这所小别墅很安静,以至于她能听到楼下传来的声音;但只能听到嗡嗡声,分辨不出他们在说什么。她能听出哈利的又快又高的声调,父亲的稍慢和低沉的声音,但还有一个最慢、最低沉的声音不知道是谁。
出什么事了?她匆匆忙忙地洗漱,更衣。他们不但已经起来,而且已经在准备早饭了:她能闻到煮咖啡的味道。但她动作很慢:尽管她睡了9小时,她却感到神经衰弱、全身乏力,就像昨晚整晚没睡一样。
在猛地梳了一下她那棕色的短发后,顾不上涂脂抹粉,她匆匆忙忙地下楼去。到了起居室的门前她突然站住了——在她父亲和她的表弟哈利中间,站着本地的警察局长。
“早上好,小姐。”警察局长说道。
那个小小的起居室里的景象和人们脸上的表情是她终身难忘的。阳光倾泻进来,照在了亮色调的粗纺的地毯和石制的壁炉上。透过侧面的窗户,她可以看见20码开外的被雪覆盖的草坪,以及仅仅靠一道有门的高高的月桂树篱笆与草坪分隔开的,有着白色的耐久的木板墙的,托普汉姆太太的小房子。
在她进门时,屋内的谈话戛然而止;一阵警告似的震动侵袭了她。她惊讶地注意到屋内人此时的表情:他们快速且面色阴沉地周围扫视着,好像就算是个照相机也能让他们惊讶似的。
“早上好,小姐。”警察局长重复道,并且敬了个礼。
哈利·范特纳激动地插了进来。他原本就发红的脸色现在更红了;甚至连他那双大脚、宽阔的肩膀和小而有力的双手,看上去都激动不已。
“别说话,多莉!”他急切地说道,“别说话!他们不能强迫你说什么的,直到……”
“我想,”她的父亲慢慢的开口道。他往下看,目光扫过鼻子、他的烟斗,以及其他的一切,除了桃乐丝,“我想,”他清清嗓子继续说,“现在先别急着说,直到……”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先生。”警察局长梅森清了清嗓子,说道,“现在,小姐,很抱歉我必须问你几个问题。出于我的职责,我需要提醒你你有权不回答,直到见到你的律师为止。”
“律师?我并不想见律师。为什么我要见律师?”
梅森局长意味深长地看了她的父亲和哈利一眼,像是要让他们记住这句话。
“是关于托普汉姆太太的一些问题,小姐。”
“哦!”
“为什么你会说‘哦!’?”
“请继续吧,要问的是什么?”
“我明白了。小姐,你跟托普汉姆太太昨天是谈过话吗?一场小小的争吵?”
“是的,你完全可以这样说。”
“我能问问争吵的具体内容吗?”
“很抱歉,”桃乐丝说道,“我不能告诉你这个。这只会给那只老母猫一个起诉我诽谤她的机会!就是这样了!她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噢,小姐,”梅森局长答道,他玩弄着一支铅笔并在他下巴上划了一道痕,“我想以她目前的状况她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了。她现在躺在吉尔特福德的医院里,头盖骨被狠狠地砸碎了。请勿把她的情况外传:她现在情况很不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
一瞬间桃乐丝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了,接下来则像是在很响地猛烈地跳着。警察局长直直地看着她。她强迫自己镇静下来,说:“你的意思是她出意外了?”
“不完全是这样,小姐。医生说她被一个很大的玻璃纸镇砸了三、四下。你应该在她家的桌子上见过这个东西吧,嗯?”
“你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不是说那是某个人干的吧?故意干的?那是谁?”
“呃,小姐,”梅森局长更加严肃地看着她,并且摆出一副清教徒的样子,鼻子上有一小块黑痣,“我决定告诉你,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那是你干的。”
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发生。她一边回想,一边观察他们:在日光照射下显现的哈利眼睛旁的小皱纹,他匆忙梳就的发亮的头发,他那松松垮垮只拉了一半拉链的皮夹克。她想着尽管他有运动员般的体格,但他看起来一点用也没有,甚至有点愚蠢。她的父亲,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但那太荒谬了!”
“我希望如此,小姐。我真诚地希望如此。现在请告诉我,你昨晚上出去过吗?”
“什么时候?”
“昨晚上的任何时候。”
“是的。噢,不。我不清楚……是的,我想我出去过。”
“以上帝之名,多莉,”父亲说道,“别再说话了,直到我们找到律师为止。我已经给镇上打过电话了;我不想吓着你,我甚至不想叫醒你;这件事会有合理的解释的,它一定会有的!”
这不是她自己的感觉;这是她父亲的悲哀神色影响了她。笨重,半秃顶,总在担心着生意,总是在担心着世界上的一切,这就是约翰·布朗特。他的残废的左臂和黑色的手套紧紧夹在他身侧。他站在阳光之中,脸上写满了痛苦。
“我去看过她了,”他解释道,“一点也不好看,一点也不。我倒不是没见过比那更糟的情况,只是在战争中。”他指指自己的手臂,“但你还是个小姑娘,多莉。你不可能会干出那样的事。”他的忧郁的声调似乎是在向她求证。
“请稍等一会,先生!”梅森局长提出,“现在,小姐!你告诉我你昨晚离开过这屋子?”
“是的。”
“在雪中?”
“是的,是的,是的!”
“你能想起具体时间吗?”
“不,我想我忘了。”
“告诉我,小姐,你穿的鞋子是几号的?”
“4号。”
“这真是一个很小的尺寸,是吧?”
她默默地点头。梅森局长合上笔记本:“好了,现在你能跟我走一趟吗?”
小别墅有个侧门。梅森局长没有用手指去碰门钮,而是转动了把手把门打开。突出的屋檐使得门前的两级台阶保持干净,但除此以外,一层薄薄的雪像石膏一样覆盖着从这里开始的整条小路,一直到那边那所关上了的房子。
雪中有两行脚印。桃乐丝很清楚这些脚印都是谁的。它们已经变硬,痕迹很清晰。一行像蛇行一样从这里的阶梯出发,通过月桂树篱笆组成的拱门,停在了托普汉姆太太的房子侧门外的阶梯上。另一行有着同样的轨迹——有点模糊,间隔变大了——很明显地那个人正在拼命地从那所房子往回跑向这边的阶梯。
那个无声的恐怖的迹象扰乱了桃乐丝的记忆。不是一个梦。她确实干了。在潜意识中她一直知道这一点。她还能记起别的事情:扣在睡袍外的毛大衣、湿的拖鞋里的碎冰块、在黑暗中盲目的乱闯。
“是你的脚印吗,小姐?”梅森局长问道。
“是,呃,是的,这是我的脚印。”
“放松点,小姐,”梅森局长轻声道,“你看起来脸色发白。过来这边坐下;我不会伤害你的。”然后他的声调带上了怒意,也许是这个女孩呆滞、直率的态度刺伤了他作为公务员的自尊,“但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天啊,为什么你要那样做?难道是说,仅仅是为了砸开她书桌,拿走那些不值十镑的小玩意?而且还根本不试图在事后抹去自己的脚印?”他突然咳起来,阻止了他继续说下去。
约翰·布朗特的声音听上去带着讽刺:“很好,我的朋友。非常好。这是迄今为止你第一次显示出你的智力水平。我猜想你不会认为我的女儿疯了吧?”
“我并没有这么想,先生。不过我听说那些小玩意是她母亲的。”
“你从哪听来的?是你吗,哈利?”
哈利·范特纳拉上了夹克的拉链,紧紧地裹住了自己。他看起来试图在表现出:自己是个总被每个人所迫害的好人;他其实想与全世界为友,只要别人愿意的话。从他的容貌的细微变化中闪现出的诚挚让人难以怀疑他的良好目的。
“看起来,爸爸,老家伙。我不得不告诉他们;隐瞒事实是没有好处的。我是在看故事时知道这个的——”
“故事?!”
“嗯,你爱怎么称呼都可以。他们总在调查,而且他们把事情弄得更糟。”他试图让他的话被大家理解,“告诉你,局长,你们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算是多莉跟托普汉姆太太为了珠宝的事吵了一架,就算她昨晚确实出去过,就算那些脚印是属于她的,这就能证明她袭击了托普汉姆太太吗?倒不是说你们的调查不充分,但那就不能是个小偷干的吗?”
梅森局长摇摇头:“正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先生。”
“那是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
“告诉你也无妨,先生,如果你想听的话。你应该记得昨晚刚过11点就开始下雪了。”
“不,我不知道。那时我们都睡了。”
“好吧,那你可以相信我的话。”梅森耐心地跟他解释,“晚上一半的时间我都呆在警察局。雪是大概半夜里停的。你也可以相信这个,我们很容易能证明它的真实性。先生,你知道,托普汉姆太太直到半夜以后还活得好好的。我也知道,因为她打电话到警察局,声称她被惊醒,很紧张,觉得附近有个贼。因为这位女士总是这样子干,”他的表情有点严峻,“平均每个月三次,所以我并没放在心上。我想告诉你的是:她打电话的时间是12点10分,那时雪已经停了至少10分钟。”
哈利犹豫了。梅森局长继续耐心地说着:“你看出来了吗,先生?托普汉姆太太在雪停前并未受到袭击。在她的房子周围方圆20码,覆盖着干净、无暇、没有印痕的一层雪。唯一的痕迹,任何形式的痕迹也好,就是布朗特小姐已经承认了的——她的脚印。”
接下来他恼怒地提高了音量:“这不像是任何其他人所能干到的。就算布朗特小姐不肯承认,我也绝对可以肯定没有别的人能做到。你,范特纳先生,穿着10号的鞋子;布朗特先生穿的是9号。穿着4号的小鞋子走路?啊哈!还要用钥匙开门,狠狠地砸那个老妇人的脑袋,抢劫她桌子里的物品,然后还要逃跑。如果雪上没有别的脚印或者是任何形式的痕迹,谁能这么干?谁可能会这么干?”
桃乐丝现在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了。她想起了那个用来袭击托普汉姆太太的纸镇。它就放在托普汉姆太太那乏味的房间里的桌子上,是个沉重的玻璃球,里面有幅风景画。当你晃动它时,里面会产生微型的暴风雪——这让袭击事件看起来更可怕了。
她想知道自己是否在那上面留下了指纹。但是脑海中浮现出的是芮妮·托普汉姆的脸——芮妮·托普汉姆,曾是她母亲最好的朋友。
“我恨她!”她说道。接着,毫无征兆地,她哭了。
詹姆森法律公司的丹尼斯·詹姆森,猛地关上他的手提箱。当比利·法恩斯沃斯往办公室里看时,他正在穿外套和戴帽子。
“嗨!”法恩斯沃斯说,“准备去萨里解决布朗特那个案子?”
“是啊。”
“嗯,还相信会有奇迹,是吗?”
“并非如此。”
“那个女孩是有罪的,伙计。你应该清楚这点。”
“这是我们的事务,”詹姆森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客户尽责。”
法恩斯沃斯精明地看着他:“我从你的红脸颊中看到,唐吉诃德在你身上复活了。年轻的理想主义的骑士要把美女从痛苦解救出来,他发誓——”
“我见过她两次,”詹姆森说,“我是有点喜欢她。但是,仅仅用一点点的头脑来想,我就已经不能理解他们竟然会把这样异乎寻常的罪名加在她的头上。”
“噢,伙计!”
“好吧,来看看这件事情。托普汉姆太太被人用一个玻璃纸镇砸了数下。那个纸镇上没有任何指纹,显示出所有的痕迹都被抹掉了。但是,在想到去细心擦拭掉她的留在玻璃纸镇上的指纹之后,桃乐丝却走回了她家,留下两行清晰得从数英里的高空都能看见的脚印。这合理吗?”
法恩斯沃斯沉思着:“也许他们会说这个女孩失去了理性,”他指出,“先不管心理学那一套。你首先得解释客观的证据。神秘的寡妇孤身一人住在那所房子里,唯一的佣人在白天才来。现在只有一个人的脚印,而且只有那个女孩才能留下那样的脚印。并且,实际上,那个女孩也已经承认了。客观上任何其他人都无法进出那所房子。你打算怎样解释这一问题?”
“我不知道,”詹姆森绝望地说,“我想先听听她自己的说法。有一样东西,似乎从来没人去倾听过,甚至从来没人关心过,那就是她对自己的看法。”
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分,他在小别墅里见到了她。她动摇了他的想法的基础。
当他拐进大门时,一缕蓝色的微光照了出来,使得雪看起来变成了灰色。詹姆森在门前站了一会,盯着那排把这个屋子和托普汉姆太太的房子隔开的月桂树篱笆。那个篱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大概六英尺高,在大门处被修剪成了哥特式拱门的风格。拱门前面,站着一个戴着鸭舌帽穿着雨衣的大块头,凝视着被雪覆盖着的篱笆的上边缘。不知何故他看起来有点脸熟。在他的肘边,另一个男人,毫无疑问就是地方警察局长,正举着个照相机,闪光灯对着天空一闪。尽管离得太远,根本听不见什么,詹姆森却有个古怪的感觉:那大块头男人正在捧腹大笑。
哈利·范特纳——对他只有一点了解——在前门迎接詹姆森。
“她在那里,”哈利解释道,朝着面对着的房间点点头,“呃……请不要打扰她,好吗?那些人到底在对篱笆干什么?”他的目光穿越草坪盯着那边。
“打扰她?”詹姆森话中带着怒意,“我来这里,是为了尽可能的帮助她。难道你或者布朗特先生就不能支持一下?难道你真的认为布朗特小姐,在她的理性驱使下,干出了那些人所宣称的事情?”
“在她的理性驱使下?”哈利重复了一遍。在怪怪地看了詹姆森一会后,他不再说话,突然转身,跑过了草坪。
然而桃乐丝,在詹姆森见到她的时候,并没有给人留下她已经失去理性的印象。他一直以来都很欣赏她的坦率,此刻这种坦率让他感到温暖。他们坐在家常的,生着火的房间里,旁边的壁炉上放着银质奖杯——显示出哈利在田径和体操上的能力,还有约翰·布朗特的战利品——那是早年在圣莫里茨①获得的。桃乐丝本人也是个喜爱户外运动的女孩。
“给我的建议?”她说,“你的意思是,你要给我一些关于当他们来逮捕我时我该说什么的建议?”
“是的,他们现在尚未逮捕你,布朗特小姐。”
她向他微笑:“我打赌我一定吓着你了,是吧?哦,我很清楚我陷得有多深!我猜想他们现在只是在搜集更多的证据而已。另外,有个新来的男人,叫做马彻的,是从苏格兰场来的。我真应为此感到荣幸。”
詹姆森坐直了。他现在知道为什么篱笆边那个大块头会让他觉得脸熟了。
“难道是马彻上校?”
“就是他。相当好的一个人,真的。”桃乐丝答道,用双手捂住了眼睛。他能感到,在她轻轻的声调下,她的神经被触痛了,“然后他们就搜遍我的房间。他们没找到那些手表啊、胸针啊、耳环啊本以为是我从芮妮阿姨那里偷走的东西。芮妮‘阿姨’!”
“这些我都听说了。但问题是: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手表、胸针、耳环?为什么不能是你从其他人那里偷的,而只能是她?”
“因为那些不是她的东西。”桃乐丝说道,突然仰望,脸色发白,语速也变快了,“那些是属于我母亲的。”
“小心周围。”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桃乐丝说,“我想它们并不仅仅是手表、耳环这么简单。那只是个借口,是爆发的临界点,是事件的导火索。我母亲和托普汉姆太太是好朋友。当我母亲还在世时,总是纵容她,‘芮妮阿姨’这‘芮妮阿姨’那的。但我母亲想把那些小饰物留给我,尽管它们不值钱,然而芮妮·托普汉姆‘阿姨’若无其事地就占有了它们,就像她占有任何她能占有的东西一样。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昨天。你了解那种类型的女人吗?托普汉姆太太是个有魅力的女人:有贵族气派,富于魅力。凭着无所顾虑的魅力,她拿走一切她能拿到的,以及期望继续拿到的东西。我所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她非常有钱,尽管我难以想象她是如何用这些钱的。她隐居在乡下的原因是她太吝啬,不敢冒风险去投资;而是选择在镇上挥霍。我从来就不能容忍她。我母亲死后,我就不用再纵容芮妮‘阿姨’了,尽管她觉得我应该继续那样。一切都变了。那个女人太喜欢说我们的闲话了!从哈利的债务,到父亲不景气的生意。还有我。”
她停了下来,向他微笑:“我很抱歉给你造成了麻烦。”
“你并没有麻烦我什么。”
“但那的确很可笑,不是吗?”
“‘可笑’,”詹姆森冷冷地说,“不是我应该用的词。那么你跟她吵架了?”
“噢,一次辉煌的吵架,一次美丽的吵架。简直是所有吵架之母。”
“什么时候?”
“昨天。当我看见她带着母亲的手表时。”她看着火堆,在那上面银质奖杯闪闪发光。
“也许我说得太多了,”她继续道,“但我得不到父亲和哈利的支持。我不怪父亲:他为生意操了很多心,而且他那残废的手臂时时给他带来不便。他只希望能平静地生活。至于哈利,他也不喜欢她;但她迷上了他,这让他感到满足。他是芮妮阿姨那种类型的男人。失业了?哦,他依赖着某人过活。我则处于中间。他们总是说:‘多莉,干这个。’‘多莉,干那个。’‘老好人多莉,她不会介意的。’但我介意。当我看到那个女人带着母亲的手表站在那儿,还摆出副同情的样子在议论我们家请不起佣人,我感到有些事需要做了。因此我猜想我应该是做了某些事。”
詹姆森伸出手握住她:“好,”他说,“那你确实干了吗?”
“我不知道!麻烦就在这里。”
“但的确——”
“不。那就是托普汉姆太太总是嘲弄的我的事情之一。你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当你梦游的时候。很可笑吧?”她又停了一下,然后继续道,“绝对太可笑了。但不是我!一点也不是!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我过于疲劳或者神经紧张的时候,就会梦游。有一次我还下了楼,生了火,收拾桌子准备做饭。我得承认这并不是常常发生的,而且从没发生过像这次这样的事。”她试着笑,“但你觉得为什么父亲和哈利会那样子看我?这是最糟的。我根本不知道我究竟是否是一个谋杀犯。”
——太糟了。
詹姆森也得承认这一点,尽管他的理智还在反驳。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她的棕色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他的身上。他不能把脸转过去;他看得见她的脸上的每个角落的紧张。
“看着这儿,”他平静地说,“这只是无稽之谈。”
“噢,请别那样说了。这不是凭空捏造的。”
“但你真的认为你去了那个女人家,到现在仍一无所知?”
“难道这能比生火还难吗?”
“我不是问你这个。你真的认为你干了那事吗?”
“不。”桃乐丝答道。
这个问题达到了目的。她已经相信他了。他们之间产生了理解和共鸣,一股精神的力量和交流变得有如身体释放的热量般可感知了。
“在我内心深处,不,我不相信我干了。我想如果我真的干了我应该会醒过来。而且,呃——我的身上一点血迹都没有,你知道的。但你要如何推翻那个证据?”
——证据。还是那个证据。
“我确实穿过了那里。我不能否认,当我回来时,已经半醒了。我在雪中站在草坪中间。我的睡袍外套着毛大衣;我能感到雪飘落在我脸上,还有我脚下湿了的拖鞋。我在发抖。我还想起来我在往回跑。就这些了。如果不是我干的,那还能有谁干呢?”
“原谅我打扰一下,”一个新的声音插了进来,“你是否介意,既出于字面上的意义,也包含着比喻义,让我开灯照亮这里?”
丹尼斯·詹姆森认识声音的主人。一阵摸索电灯开关的声音过后,马彻上校带着微笑和满足的表情出现在他们面前。马彻上校的17英石②重的身子被裹在雨衣里,就像个帐篷那么大。他戴着大大的斜纹软呢的鸭舌帽。帽子下面他那满是斑点的脸被冻得通红;他还吸着烟,发出汩汩的声音,那个大碗状的烟斗似乎随时都可能烧焦他的黄棕色的胡子。
“啊,詹姆森!”他说道。他取下烟斗,做了个手势,“原来是你。我想我看见你进来了。我不想闯进来的;但我想至少有两件事布朗特小姐应该了解。”
桃乐丝快速地转过去——
“首先,”马彻上校紧随着,“托普汉姆太太脱离危险了。她至少能说几个词了;尽管跟我们已经掌握的大致相同。其次,在你们的草坪外,我发现了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奇怪的物事之一。”
詹姆森吹了声口哨:“你见过这个家伙了吧?”他对桃乐丝说,“他是‘怪事汇总处’的头儿。当警察们发现了奇怪的事情,也许只是愚弄或者笑话;但另一方面,也许就是严重的罪行,这时他们就会找他。他的头脑非常清晰,这使得他每次都能成功解决事件。在我的印象中,他研究过会消失的房间,会行走的尸体,还找到了隐形的家具。如果他出马,只要他承认这件事是有点不寻常,你就要提防危险了。”
马彻上校严肃地点点头:“他说的没错,”他说,“这就是我来的原因。他们认为我们会对脚印感兴趣。”
“脚印?”桃乐丝惊呼,“你是说——”
“不,不,不是你的脚印,布朗特小姐。是另一个人的。让我来解释吧。我希望你们,你们两个,从这窗户向外看;我希望你们看看两所房子之间的月桂树篱笆。外面没什么光了,不过请认真地看一下。”
詹姆森走到窗户旁向外注视:“嗯?”他问道,“有什么特别的吗?只是篱笆而已。”
“正如你敏锐地指出,这就是篱笆。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认为有人能在那篱笆上面行走吗?”
“天啊,当然不能!”
“不能?为什么?”
“我理解不了你这个玩笑。”詹姆森答道,“但我会试着给出合适的回答。因为那个篱笆只有一两英寸宽,它连一只猫都承受不起。如果你打算站上去,你就会像一吨砖块那样掉下来。”
“完全正确。那么如果我告诉你,有个至少重12英石的人很可能爬上去过,你怎么说?”
没人回答。这件事如此明显地不合常理,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回答。桃乐丝·布朗特和丹尼斯·詹姆森面面相觑。
“噢,”马彻上校说道,“应该说看上去就像是有人爬上去过一样。再看看那个篱笆吧。你看见那个拱门了吗?就在那上面,在篱笆的上边缘覆盖的雪中,有一个脚印。那是个大脚印。我想通过分析脚跟的形状能判断出它的主人,尽管大部分已经模糊不清。”
桃乐丝的父亲匆忙而步伐沉重地走进了房间。他准备说话,但当他看见马彻上校也在时改变了注意。他转向桃乐丝,她拉住了他的手臂。
“那么,”詹姆森强调,“确实有人爬上过那篱笆?”
“我很怀疑,”马彻上校说,“他怎么能做到呢?”
詹姆森振作起来。
“看这儿,先生。”他平静地说,“很正确,‘他怎么能做到?’我知道在你找到合适的理由之前,你不会就这样子算了的。我知道这跟此案一定有关系。但我对是谁爬上了篱笆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也不会对他是否把纽约城也弄了上去有任何兴趣。那个篱笆不会通向任何地方:它到不了托普汉姆太太的家;它只是用来分隔这两所房子的。关键就是,凶手是如何不在雪上留下任何痕迹地穿过了60英尺的距离?我这样子问你,是因为我相信你并不认为布朗特小姐有罪。”
马彻上校脸上现出歉意:“我知道她是无罪的。”他答道。
桃乐丝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晃动那个球形的沉重的纸镇时的情景:微型的暴风雪在里面产生了。她现在的神智也正如那样被撼动和搅乱了。
“我就知道不会是多莉干的。”约翰·布朗特开口了,突然地把手臂搭上了他女儿的肩膀,“我一直都知道。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但是——”
马彻上校让他停嘴:“布朗特小姐,那个真正的小偷,并不想要你母亲的手表、胸针、还有项链、耳环那些东西。你也许会感兴趣他到底想要什么。他想要的是1500镑的纸币和金币,也是塞在那个破旧的书桌里。你不是曾对托普汉姆太太是如何用掉她的钱感到好奇么?她就是这样子用的。托普汉姆太太,根据她刚刚在半清醒状态下的呢喃,仅仅是个普通的守财奴而已。她房间里那个难看的书桌,是任何盗贼所不会注意到的收藏财产的地方。任何盗贼,只除了一个人。”
“只除了一个人?”约翰·布朗特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双眼似乎靠拢了。
詹姆森突然产生了一个恶意的猜测——
“只除了一个你们都认识的人。你,布朗特小姐,被故意地嫁祸了。并不是有人恨你。这只是让那个‘绅士’避免痛苦和麻烦的最简单、最容易的办法。听听他是如何干的吧,”马彻上校说,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你昨晚在下雪的时候出去了。但你并没有走到托普汉姆太太家;你也没在雪地上留下那两行精致的脚印。当你跟我们陈述你的故事时,你说你感到雪飘落在你脸上和脚下。这不需要特别的注意就明显能看出那时还在下雪。你走进雪中,就像许多别的梦游者一样;然后你被雪和冷空气迷迷糊糊地弄醒了;你在雪停的很久以前就回来了,雪把你留下的一切脚印全盖住了。真正的小偷——他一直都醒着——听见你回来和倒在床上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天赐的机会,可以让罪名落在你头上,而且你甚至会认为你自己犯罪了。他溜进你的房间,拿走了你的拖鞋。等到雪停后,他去了托普汉姆太太家。他本不打算袭击她的;但她醒着,吓了他一跳;于是,理所当然地,哈利·范特纳把她打倒了。”
“哈利——”桃乐丝几乎是尖叫着说出这个词的,然后戛然而止。她迅速转过头去看着她的父亲;她直直地向前呆视,然后她笑了。
“当然,”马彻上校说,“如同往常一样,他会要他的(怎么称呼呢?)……他的‘老好人多莉’来替他背黑锅了。”约翰·布朗特看上去如释重负,但表情中仍带着迷惑和不安。他对马彻上校感到吃惊。
“先生,”他说,“我愿意用我这只正常的手臂来证实你的话。我有一半的麻烦都是这小子弄出来的。但你是不是在说疯话?”
“不是。”
“我告诉你,不可能是他干的!他是艾米丽——我姐姐的儿子。他也许很坏;但他并不是个魔术师。”
“你忘了,”马彻上校说,“忘了还有一个10号的大脚印。你忘了那个有趣的景象:在连一只猫都承受不起的篱笆的上边缘,有个抹出来的模糊的10号的脚印。一个不同寻常的脚印。一个没有着落的脚印。”
“但那才是整个麻烦的核心,”另外那人吼道,“雪地中的两行脚印是4号的鞋子踩出来的。哈利不可能弄出这些脚印,比我更不可能。这是客观上的不可能事件。哈利穿多大的鞋?10号。你不会认为他能把脚塞进正合我女儿脚的鹿皮拖鞋里吧?”
“不能,”马彻上校说,“但他可以把手塞进去。”
全场哑然。马彻上校显出一副梦幻般的表情;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
“凭着这副不寻常但却极为实用的手套,”他继续说下去,“哈利·范特纳用手倒立走到了那边的房子。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体操运动员(那些银质奖杯暗示了这一点)来说这件事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对于一个头脑空虚又急需要钱的人来说,这个方案非常理想。他穿过了薄薄的积雪覆盖的地面,雪的厚度不足以让脚印显出体重上的差别。而由于有突出的屋檐,门前的台阶很干净,这很好地保护了他;让他在两端可以正着站。他有无数机会去弄到一把侧门的钥匙。很不幸地,篱笆那里有个不太高的拱门。他的体重全支撑在手上,他得把脚弯起来越过拱门以保持平衡;他犯了个大错,他的脚在篱笆的上面抹出了那一个没有着落的脚印。实话说,我对这一方案真感到欣喜:这是一起上下倒置的犯罪;这留下了一个天空中的足迹;这是——”
“已经依法逮捕了,长官。”梅森局长从门缝中伸进头来,下了结论,“他们是在吉尔特福德的旁边抓住他的。当他看见我们在那里拍照时,一定感到不妥了。他那些东西都带在身上。”
桃乐丝·布朗特站了好一会,看着那个衣冠不整的胖家伙在咯咯地笑。然后她也笑了。
“我相信,”丹尼斯·詹姆森礼貌地说,“每个人现在都很高兴。对我来说,我今天已经经历了两次不愉快的冲击;刚才曾经有一会我差点以为我还要再经历一次。有一会我真的以为你要指控布朗特先生了。”
“我也是,”桃乐丝表示赞成,并对她的父亲微笑,“所以我现在才这么高兴。”
约翰·布朗特吃了一惊。不过他吃惊的程度尚不及马彻上校的一半。
“这样的话,”上校说,“我就不太能理解你的想法了。我是负责‘怪事汇总处’的,如果你在你家的阁楼上发现一个幽灵,或者在篱笆上方发现一个脚印,尽管给我打电话好了。但成功赋予了我们是因为,正如詹姆森先生说的,我所追寻的是明显的真相。上帝保佑!如果你已经明确,这件罪行是某个能用手倒立行走的人所犯下的,我只能忍住痛苦,坚持这一观点:你把这屋子里的一个手臂有残疾的人猜测为凶手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
注释:
①圣莫里茨:瑞士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是个美丽的小村庄。
②英石,重量单位,等于14磅,约6.4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