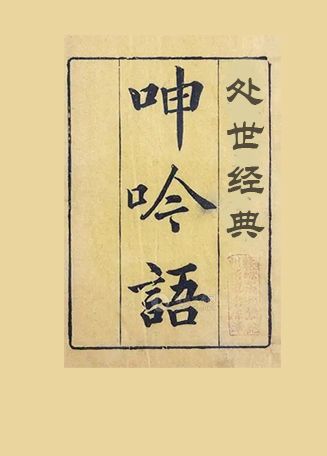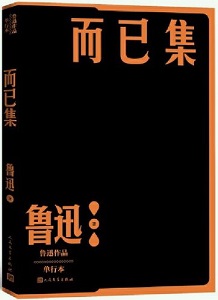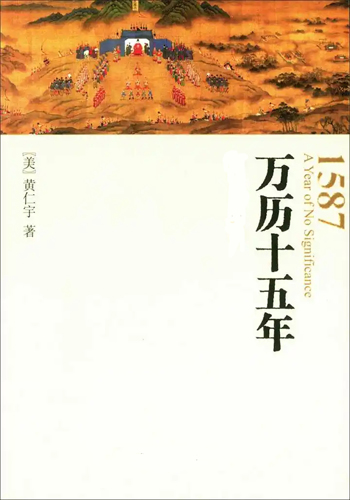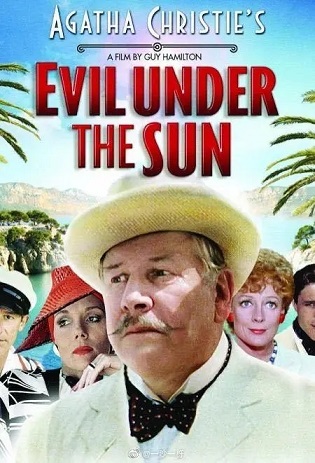佛教发源于古代印度,从印度向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传播。传播所到达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后来都有很多人修行佛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得到修证体验,进入到释迦牟尼佛教法所说的各种圣贤的境界。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修证体系,跨越了语言、地区和国度,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民族习俗、国家制度里面,能够让这么多的众生得度,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现在的学者经常说,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首先中国化。中国化的意思是说它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适应这个国家的制度,适应中国人的根性。
佛教除了适应中国,同时它也教化了中国,所以有学者写了一本书叫《佛教征服中国》,这是外国人写的。它教化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无数众生,也有无数的高僧大德、修行人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
如果我们要观察佛教在中国文化里所发生的这种教化的力量,我们就一定要理解,作为一个宗教,它首先要适应中国,这个中国化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生的。
在信仰的层面上,中国汉地的众生,有他表达信仰的方式。中国汉地的佛像有逐渐从印度到中国的中国化痕迹,不同朝代有不同的佛教造像风格。
在解的层面,从印度到中国来,释迦牟尼佛在印度传讲大乘、小乘、显教、密教的佛法。这些大、小、显、密的经典,都先后被传译到汉地,但是中国汉地的祖师们对这些经典所给予的关注、研究和修行,并不是完全不加选择的,它是有特殊侧重的,而且在表述上(最早是在翻译上,然后在对佛法的义理阐述上),也有非常明显的跟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的痕迹。这是解的层面。
然后是行的层面——修行实践,在中国汉传佛教体系里,就更加有中国特色。中国唐朝有八大宗派,中国的佛教徒修证佛法,有其特殊的倾向、趣味和方式。
其实最重要的是证。因为佛法最终的实证境界是超越于语言、文字、文化差异、民族和国家的差异及分别思维的。大家想,佛法从印度传到中国来,释迦牟尼佛的见地、印度祖师的见地,能被中国的祖师原封不动、原汁原味地体证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能原汁原味地体证到佛的见地、印度祖师的见地,一定必须是超越于分别心和妄想,由此超越于建立在分别妄想之上的语言、逻辑、符号和文化习俗。我觉得这个是佛法从印度到中国来最核心的地方,是佛教与中国相适应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中国的祖师们体证到了佛法的精髓。
他只有体证到这个境界,才有可能完全自由地、灵活地、不拘一格地以中国本土文化的风格,把那个境界表达出来,在教学中完全自由、不拘一格地用中国人能适应的方式来展开教学。
也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祖师对佛法的体证深入到了极点,才有可能“浅出”地教化,浅出到这个国家的人一听就懂,表现为完全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语言的教学方式。祖师们所创立的这个“深入浅出”的宗派,就是禅宗。
我们看禅宗祖师的语录,看祖师们讲修行,讲佛法,他们的语言完全是灵活的、生活化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人一定要注意的,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当我们学习古代祖师的开示,特别是禅宗祖师的教导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由于他们已经证入了佛法超越语言文字的那个见地,所以当他在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环境里讲法、讲开示、接引人,他就是纯粹中国化的,他很少用到佛经里的术语,而中国祖师这些讲修行方法、修行体验的开示,我们作为中国人听起来就特别直接、简洁、清晰明了。
但是那个时代过去了,时代差异来临了。今天的我们读古代禅宗祖师的开示,会有语言隔阂,有时代文化差异的隔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跨越这种隔阂,能适应中国古代禅宗祖师开示的语言方式,能理解他们用中国本土的语言、生活的语言讲我们用功,可以说那你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因为你能完全直接地聆听祖师关于修行的开示啊!所以我们讲到在禅堂用功,古代的祖师他讲用功的表达,就不一定是那种佛学理论术语。
其实,达摩祖师到中国来,有一个教导,是几句口诀,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这四句话,我相信一定是达摩祖师的教导。
我同时也相信,达摩祖师的这个教导的意思,一定是被他的门人根据他的教导,把它用中国化的语言概括出来的。因为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传法,我相信他有这种智慧。假如他的语言还没有完全中国化,我也相信这几句话。
“外息诸缘”这个意思我们懂。我们修行,要把外面的缘“息”,息是休息的息。“内心无喘”,你看这个词,在佛经、佛学理论里面,你就找不到了。
“喘”是指什么?喘是说我们的呼吸很紧促、很急切,喘气。人跑,剧烈运动,喘气、喘息嘛。这里讲的内心无喘,也许在另外一个文化环境里的人,比如说西方人,甚至说印度人,他会觉得很模糊。
什么叫内心无喘呢?有点模糊,有点不清晰。但是它妙就妙在这个模糊、不清晰,它很直观。内心无喘是指我们的心没有波动,完全松弛,没有紧张,我们的心是平的,不刻意、不造作的本然的状态,叫内心无喘。
第三句话更加模糊,但是也更加直观和形象。说“心如墙壁”,他说的心如墙壁是指什么呀?这个很形象啊,墙壁是硬的,对吧?你想把一个东西贴到墙壁上,很难,它是坚硬的、陡峭的、直的。你要把一个东西贴在墙上,贴得住吗?你要把它放在墙上,放得了吗?
它会掉下来,所以心如墙壁是指心的“无住”,不住著。任何东西放在上面,它会掉下来,不入心,跟心不会粘黏,不会粘著。这就是一个很中国式的表达,这种开示我们听起来就很亲切。
如果在禅堂里用功,你听祖师这种开示,你就很容易懂,很容易知道他在说什么。也许你没有太多的佛学理论,但是好像不妨碍你明白他的开示,也不妨碍你按照这个开示去纠正自己的修行,纠正自己的用功。
后来的祖师也有类似这样的开示,也很生活化。他怎么讲呢?他说 “内不放出,外不放入”。你看,“内”、“外”。那么这两句是指什么?这两句是指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如果你参话头,相应了,你的心孤立起来了。这个心孤立起来,古代祖师还用一个很感性的话描述它,叫“孤明历历”。孤明,孤独的孤,它是明;历历就是很清晰啊!历史的历,历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清晰。
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外不放入”。外不放入,“外”是指所有的外境。我们在用功的时候面对两个问题。第一,所有外境你会生心动念。为什么禅七中建议大家不要讲话,别人说了你一句什么话,或者行茶的人没给你倒满,他把点心从你跟前过的时候,过得特别快,你怀疑他是不是故意的,这就是外境让你心动。
打你香板,你感觉到他打得有点重,是不是刻意地特别对我啊?平时对我有意见,现在找机会发泄一下。由外境导致你的心动,外就放入了,简单来说外面有东西进到你心里。
汉语里还有一个词叫“阴”、叫“贼”,就是阴暗的,在你心里落下了一个阴影,这就叫“外放入”了。这个外放入也包括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对你的心来说也是一个外境,腿痛、腰酸,令你心烦。身体是最直接、最有效地影响我们内心的一个对境。所有这些让我们心动的外境,它不再能让我们心动,仿佛有一个门关死了,叫“外不放入”。
“内不放出”是指什么?你用功,不管你是参话头还是念佛,你用功的那个念头没有孤立,没有在心里居于主导地位,内心翻出来一个妄想——这个妄想有很多种啊,有的是妄念,比如想着打完七去哪里参学?这是念头。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想”,就是色受想行识的“想”,一个景象、一个图景在你心里翻腾。
当它们在内心出现的时候,你对它们产生了认同——认同是现代心理学的话,意思是说,那个念头就是我,那是我的念头。这里有两种认同,第一种叫我执,第二种叫我所执。
打个比喻,有时候我们在街上过,也许我们会遇到一个有神经病的人,他在那里大喊大叫说:我看到什么什么了,我怎么怎么了,有人要杀我呀,等等。其实没有,他是幻觉。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认同吗?你会认同说有人要杀我?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是他的幻觉,不是我的幻觉。
但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心里出现的情绪波动,冒出的妄想,我们却有那种认同,叫我所执——我的。也许你冒出一个很糟糕的念头,感到很有负罪感。我怎么修行会想这个?哎呦,罪过太大,这个也是我所执,也是内心有喘,“内不放出”就是指这个放出。为什么叫放出呢?内心的妄想、杂念,让你产生执著了。
打坐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往往你会特别期待你的心听话,不要有妄想,不要有杂念。只要你有这种期待,那么你的妄想就会很多,因为这个期待就是一个大大的妄想,一个大大的错误。
为什么你期待你没有妄想呢?因为你首先把妄想当成你的了,如果你看你内心的妄想,如同看街上某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他的妄想一样,你会在乎吗?不会。所以打坐用功的时候,内心有杂念、有妄想,这是正常的。我们要做的只是不被它转,不跟它跑,更不对它产生爱和憎:
坏念头你很憎,怕它;好的妄想,你贪著它。产生不良情绪,要压制它;产生美好情绪,会跟随它……只有你能做到不落在这两边,看你心里的妄想,就如同看路边那个精神失常的人,看他的妄想一样,妄想才不会支配你、影响你、主宰你。这个“内”就没有放出(这个“出”是指的变成一种现行)。
其实说,你现在有一个认为是很糟糕的妄念,你只要不认同它,它不成为业,对你没有影响,你不要紧张。你的紧张恰恰是被它所牵制了,是一个放出。
大家体会一下祖师的这种开示。“外不放入,内不放出”就是用功的这个正念。“一念蓦直去”,这个语言也是中国式的,直着去,不回头,没有第二念。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在用功的时候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