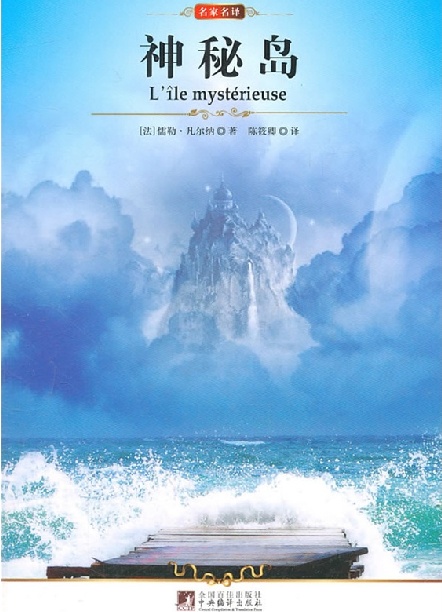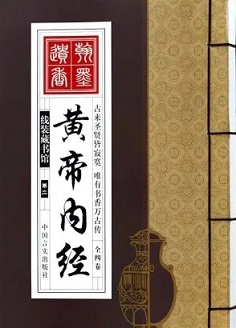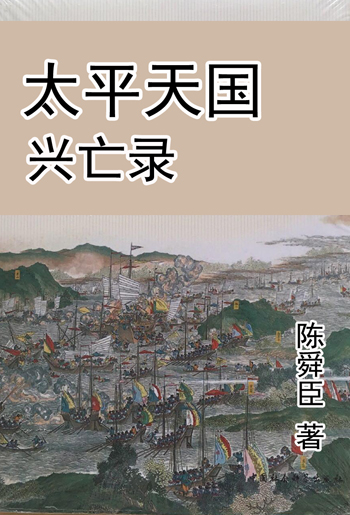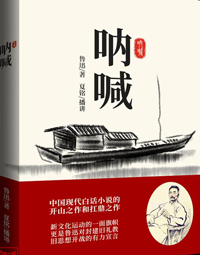和我们禅堂直接相关联的禅宗的修行方法就是参话头。当然在用参话头这种方法之前,禅堂在好多禅宗寺院早就有了,唐朝就有,而参话头这种方法被提倡、最盛行是在宋朝以后。所谓的参禅讲的就是参话头,这个方法可以说是中国祖师对佛教的一大贡献、一大发明,因为在印度这种方法起码没有普遍受到重视。
这个方法的特点我们可以这样讲:它是让念头自己解决自己。通俗地说,就是让心念自己认识、解决自己。禅堂里行香、坐香(过去禅和子也是住在禅堂的——住广单),行、住、坐、卧都在禅堂里,用功就是每个人在心里都要抱定他的话头,他的问题。
从用功的人接受参话头这个方法来说,这个话头好像是外面来的,可能是师父教给你、提示你,可能是你看书从祖师的开示中获得的,但是实际上,话头本身也只是一个工具、方便而已,古人说就像敲门的砖,门敲开了,砖也就没用了,话头就是这样一个敲门砖。当参话头的人真正进入状态之后,那个特定的话头是可有可无的。
参话头的形式通常是不断地在心里反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样的问题不是能用逻辑思维、推理或书本上的知识就可以解决的。明清以来,在禅宗的禅堂里流行的话头是什么呢?是“念佛的是谁”。参话头的人静坐在那儿,心里可能要默念一段佛号,心里反问自己“念佛的人是谁啊?”用功的人在心里要接受这个问题,先要明白这确实是个问题,然后愿意把心念专注在这个问题上,去跟它挨、跟它磨。
至于这个问题本身,比如“念佛的是谁”,可能我们会说:就是“我”喽!那么“我”是谁呢?追问一下:这个“我”在哪里呀?有人说“我”就是我这个身体,好像也不是。前面我也讲过,假如你家里有一个很心爱的手镯,结果被摔碎了,你知道了以后,会很难过,那个手镯在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之外,不在你身体范围之内,它坏了怎么你会难过呢?所以说是你身体是经不住考验的。
有的人说我的心就是“我”嘛!心在哪里呢?这也有问题。你们研究一下《首楞严经》,很有意思。《首楞严经》很像一本参禅的书,一个参禅的心路历程。心在哪?心在身体里面?眼睛里面?眼睛外面?眼睛和身体的交接部位?都经不住推敲,都有问题。
现在假设我们面前有个人,知道自己念佛的是谁,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你在这儿坐着苦参,你在问自己“念佛的是谁”。多累啊,你问他得了,他告诉你不就完了嘛!他是可以告诉你,但是并没有完。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你的,对你来说是一种知识,在佛学里叫比量的知识,不是你亲自体验到的。
其实知道“念佛的是谁”的这个人已经有了,是谁呢?释迦牟尼佛嘛!历代祖师嘛!他们千经万论很多开示都讲了,但是你把千经万论这些开示背熟了,不等于你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禅堂里问这个问题,要得到的那个“知”不是知识的“知”;也不是知解的“知”,知解就是概念、思想、见解;不是比量的知,比量就是通过概念符号、逻辑推理得到的,而是要你亲自现量地了解。
佛教里经常用比喻,打个比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水是热的还是冷的,只有喝了你才知道。已经喝过的人告诉你说是冷的或是热的,在你来说,那只是一个概念,不亲切、不直接,你并没有体验到这个水的冷暖。
喝茶也是这样。如果你从来没有喝过茶,有的人喝后告诉你,这个茶有点涩,这个“涩”对你来说只是个概念。“涩”这个概念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可能你以前吃过涩的柿子,你马上会想起柿子,觉得这个茶的味道可能是柿子的味道。但是茶的味道到底是不是柿子的味道呢?好像也不是。
那个喝茶的人说,喝完之后有点甜味。“甜”也是一个概念。你可能会把这个概念和糖果联系起来,觉得茶可能是糖果的味道,这个也离题太远。究竟茶是什么味道呢?你得直接喝。但是直接喝也有问题啊!我们每天都在喝茶怎么会有问题呢?基本上,没有几个人在喝茶的时候,完全把心里的各种东西全部放下,真正地、直接地喝。
你现在如果刚刚遇见特别开心的事,志得意满,端起茶开始喝的时候,感觉这个茶真香啊!如果你刚刚遇到很失败的事,遭受了严重打击,端起这杯茶喝的时候,感觉这杯茶真苦。如果你和你亲爱的人远离、分手,曾经你们在一起喝过这个茶,当你喝这个茶的时候,你眼前出现的是你和她在一起的情景。
好了,现在说的是个什么问题?说的是,其实我们喝茶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地用心去喝,我们还是用了很多概念、情绪、心态、感觉,透过这些,我们在喝茶。
当然还有很多关于茶的知识的见解。也许你是一个对医学很有研究的人,对茶科学很懂的人,当你端起这杯茶的时候,你心中的茶就是一味药,可以清热,健胃;绿茶是寒的,普洱茶是温的,你眼中的茶又是这样。所以透过了解种种的知识、概念、情绪、见解,这个茶在你的生活中呈现出千差万别的面貌。
现在我要讲一句话,其实,整个你生活的世界就如同这杯茶,你并没有真正地、直接地喝过,你一直以来,都是生活在种种的情绪、见解、思想、回忆、知识中。也就是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透过了我们心中的这些烦恼的,究竟我们生活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其实你不知道。究竟你自己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我们透过烦恼障、所知障,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
刚才我讲了,参禅就是让心念自己解决自己。这个心念在佛学里讲很复杂,光意识就分为八九个层次。但现在就让你拿这个“念佛的是谁”的敲门砖,作为解决心念问题的一个下手处,追问自己,但一定要注意,你必须是自己亲自了解,而不是逻辑的、知识的。换句话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谜语,如果是个谜语,我们把谜底告诉大家就完了。这个问题必须要你亲自体验,亲自喝那杯茶,亲自体验到、看到究竟念佛的是谁。
参话头的要害在于你能在心里生起疑情,真正有一种欲望要了解、体验到那个“谁”,如果我们以“念佛的是谁”这个话头为例来说的话,疑情的“情”这个字太好了、太妙了。疑情的情是什么呢?我们汉语里有个词叫“情不由己”,什么意思啊?当你被一种情绪抓住的时候,你会身不由己,由不得自己,所以疑情的情,是你在参话头的时候情不由己,放不下,非要亲自看到,非要亲自搞明白才肯罢休,这就是情不由己。
这个情不由己太妙了,造成了你的心念要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就是什么呢?这就叫“止”,专注。你还打其他妄想吗?现在这个妄想是最重要的妄想,别的妄想都不重要,它把你所有的念头吸引住了,情不由己,而且念念相续,所以情不由己让你专注,不自主地想了解,想搞透,这个在佛学里是一种寻伺心,寻伺,就是搜索,也是一种观察。
所以参话头是一种止观双运的方法。这个止观双运和你通常数息还不太一样。刚才我讲,参话头这个法门是中国祖师的一大贡献,因为它里面这个观非常特殊、锐利、猛利,容易穿透无明的黑漆桶。
参禅的话头很多,明清以来用得比较多的是“念佛的是谁”。话头本身涵盖了一切的谁,念佛,走路,说话,我现在讲话听话的是谁,吃饭的是谁,睡觉的是谁,生气的是谁,骂人的是谁……都有这个问题在。总而言之,主人公是谁?每天醉生梦死,谁在主宰你?实际上是这个问题。现在只是把它聚焦到“念佛的是谁”这个“谁”上。
也有人问“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父母生我们以前我们在哪里,父母生我们以前我们的面目是什么?可能刚开始你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思维一下,你可以思维,不是让你不思维,但是思维以后会发现,光靠思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如果有人打它一下我们都会生气,觉得侵犯我们。但是我们想一下,在我们有这个身体以前,没有这个身体可供别人打,这个能生气的东西那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又怎样从那个时候的样子到了现在的样子呢?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基本上所有人生的问题都在这里。
再比如,你没有汽车,当然就没有围绕汽车的问题。有一天你突然买了一部汽车,结果被人偷走了,那你就烦恼了,围绕汽车的烦恼也就来了。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产生的呢?很奇怪,为什么在没有汽车的时候,不会因为汽车而生这种烦恼,后来有了汽车以后,汽车丢了你就生起烦恼了呢?这个中间你的心念是怎样过渡的?
问题相当严重,因为现在讲的这个问题,每天每时每刻每一个念头都在我们的心里发生。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是完全不自主的,不断地在认同一些东西,而被这些东西主宰。这些东西包括汽车,身体,某种观点、思想、见解等,这一切构成佛学所讲的我、我执、我所执。
我们生活在我执、我所执中,就不可能见到世界的本来面貌。我执、我所执好比是一个监狱,把我们囚禁在里面,无论你是普通的人,还是伟大的英雄豪杰。参禅就是要我们离开这个监狱,而且不是外面的人把锁打开,是自己打开它,你自己就能打开这个锁、这个监狱、这个门、这个房子,突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