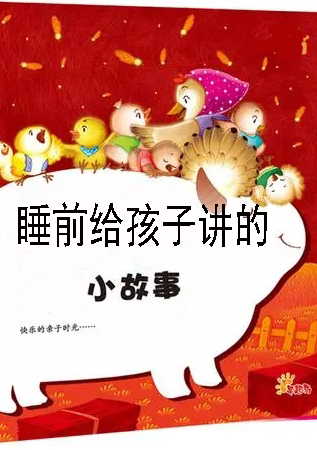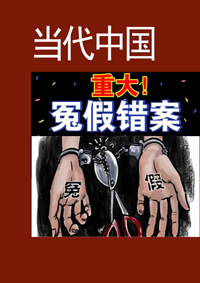佛法禅修的要害就是要认识我们的心,但我们学过佛学的人都知道,佛教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最难把握的就是心。从理论上说,“心”这个词有很多个意思,有很多种不同的叫法,有时叫“意”,有时叫“识”,有时叫“念头”,有时叫“信”……
大概地讲,我们的心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凡夫状态下,由执著、分别体现出来的心识。这种心识状态总体来说是二元对立的,总有是与非,对与错,有和无,来和去,一和多,过去、现在和未来,空和有,能和所等。这种层面的心只要一动,一定是对待。这种对待状态的意识活动主宰、支配了我们,就叫“轮回”。
轮回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没有什么难懂的。有分别和执著,于是就有妄动。分别、执著二元对立这样层面的心,在佛学里有个词,就叫“识”。识支配我们妄动造作,妄动造作让我们有业,业又让我们受苦,感受那个果报。众生的生活就是这样三个环节,由识——二元对立的活动,而有妄动的造作,由妄动的造作又随之受报。
心的另外一个层面是智。凡夫从生到死,从过去世到未来世,一直都是识心在支配,这是与生俱来、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我们的生命是一条河流,浩浩荡荡,从过去奔涌到现在,又要继续向未来奔腾。因此,凡夫在这样的境界中,很难想象我们的心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活动,这个层面的心叫智。这个层面的状态,没有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消融了。
你可能说:没有二元对立,那就是一了?你又错了,你这样一问已经把一和二对立了。在智心的这个层面,佛学里通常讲“不可思议”。因为凡夫众生从过去到未来一直都在识心的活动层面。我们的社会活动、学到的知识、受到的教育、得到的观念、概念等,全部是识心的活动,由二元对立建立。现在,我们要用二元对立的心去把握那个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智那个层面的心,你怎么描述都不对,不好把握。
但是,是不是就不描述了呢?还要描述,通常都是用否定的方式来描述。智心层面的活动无形相,无方所,无来去,既非一也非二,既非来也非去,既非有也非无,它是把识心所有的对立都统一了。
有人要问:这个智的心是不是我们修出来的呢?这个智的心是我们每个众生本来就有的,不是修出来的,不是说我们要制造一个东西,用材料去制造,而是它本来就有。
有的人问:这个智的心和识的心是什么关系呢?智的心和识的心,它不是两个:一念迷就是识,一念觉就是智。说来说去,我们的生命本来具足,识的心和智的心不是分开的,也不是对立的,刹那回头,瞥而转念,你就可能见到超越二元对立的那个层面的心体。
打个比方:乌云遮盖了天空,我们不知道天的本来颜色是蓝的,我们以为是黑的,刹那间这乌云漏出一点缝儿,我们就看见天空了。当然也有另外的比喻:这个识心就像是大海上的波浪,智心像大海本身,波浪从来没有离开过大海。
所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一定要善于透过名相领会佛意,不要被这些名相迷惑,陷到里面去。它们只不过是心的不同状态,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它们安一些名,本质上都是那个东西。你要把这两个对立起来,那又错了。
现在我们回到禅修的要害处——直指人心。这直指人心,就是要让我们体认到我们生命中本来就有超越二元对立的这样一种状态。一旦你认识到,自己的心有一个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超越二元对立的境界,那么我们就能获得对自己生命的一个全新的了解,就能建立对自己生命的一个全新的认识。
打个比方,就像一只青蛙从来没有离开过井,所以它的世界就像井底那么大,它觉得整个宇宙也就像井这么大。突然有一个机会,它蹦到井口,向外面看了一眼,然后掉下去了,又掉到井底了。即使它还掉到井底,这一眼也足够了,足够改变它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原来世界不是像井口那么大,而是这样广大,天地山川,花草树木……
在我们的禅修中,这直指人心也许只是刹那让我们对超越二元对立的心之境界的一瞥,但这一瞥足以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观、世界观。也可以说,你只有有了对自己心里智的层面的一瞥,你才真正地有了正知见——正知见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停留在理论上,一定要真地“看”了一眼,才可能生起真实的信心。
我们以前的信心是一种崇信,只有你对超越二元对立的那个层面有一个直接的了解,那时候你的信心才坚定不可动摇。那时人们劝你不修行,你不会为之所动。不管在什么环境,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时你修行,没有人支持、奖励你,你仍然会做。为什么?这就像一个人离家出走,迷失了方向,现在知道了回家的路,那还不赶紧走啊?还在外面流浪做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对于这个智的心,我们怎样认识呢?中国禅宗的大德们给我们开示了参话头这个方法,真的是一个直指人心的善巧方便,再没有其他办法比这个更巧妙。
古往今来有很多的话头。近代以来,人们打坐参禅,参得比较多的就是“念佛的是谁”。扬州高旻寺最提倡这个话头,虚云老和尚也提倡参这个话头。你每天念阿弥陀佛,那这个念佛的人是谁?这是一个问题。
有人说是“我”在念,你在哪里,嘴巴里?舌头里?脑子里?胸腔里?四肢里?你去找,找不到;找不到,可是你又能念,是什么在那里起作用呢?
这个问题相当于:是什么东西在支配你、让你起作用呢?我们从生到死做很多事,是什么东西在支配我们?把这个问题聚焦到“念佛的是谁”,聚焦到“谁”这个疑问上(这个疑问不是让我们寻找知识、理论的答案),你也不要用理论思维,因为你找不到,而且你找的东西也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你还是不明白究竟是“谁”。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答案。达尔文说,我们是猴子变来的,这是答案。现代生物学家也有一些说法,那也是答案。但是,这些答案有什么用呢?没用!我们还是不明白,还是像做梦一样,被一种力量支配着,我们仍然没有认识那个真正的自己,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心,所以说知识、逻辑推理这些都用不上。也就是说,你大脑的思维用不上,可是你又要去找,去明白它,这就是参话头。
我们寺院提倡参“狗子无佛性”,这个来自于赵州和尚的公案。有一天,有人问赵州和尚:“狗子还有佛性吗?”赵州和尚说:“无。”我们知道,佛经里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为什么赵州和尚讲“无”呢?他这个“无”字之下有他的境界在那里,这不是判断,也不是知识。那为什么他要说“无”呢?他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他居心何在呀?
就是以这个“无”作为话头生起疑情,也是要把所有的逻辑推理,把你所掌握的佛学知识全部放下,让我们的识心、分别心、落在二元对立的心的活动歇下来。这个层面的心歇下来的时候,你还想弄明白,这就是参话头的妙处。
有一种禅修的方法叫“观”,比如说观“万法皆空”。观这句话,然后让我们各种情绪歇下来。但是这个跟参话头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参话头是你不得不把所有的分别心的活动歇下来,停下来,那个工具用不上,在另一个方面,你又有一种力量,也可以说有一种欲望非要想弄明白它,非要想透过这个“无”字,抓住赵州和尚“无”字后面的心,所以它除了歇下我们的妄想分别,还有一个力量,就是去探究、参究,实际上这个力量就是观察的力量。但是这个观察不是用概念、逻辑进行的,它是用全部的身心进行的。
在这个话头之下,你想明白“念佛的是谁”,想明白这种状态就是疑情,情不自禁:赵州和尚为什么说“无”?你想明白,情不自已,这个力量使我们不旁骛,相当于“止”;同时,你放弃了平时所惯用的逻辑推理、知识活动,直接用自己的心去顶那个问题,去撞那个门,去探究、参究,这个就是“观”。参话头里面同时具足了止和观,它的特殊之处就在止和观,它是活的。
为什么说它是活的呢?如果你用功得力,你不用作意,会情不自禁,与生命有关的疑惑牢牢地抓住了你,你放不下,这就是止,是情不自禁的止;你想追究,想明了这个疑问,这是情不自禁的观。
这与我们用其他的法门去止观双运不一样。你用功得力,打坐会那样,行香自然也放不下,乃至吃饭、睡觉都放不下。放不下这个心中的疑团,一直到这个疑团跟你的心融为一体,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一直到这个疑团把你整个占据,把你的身心裹住。你一旦生活在那个疑团中,离到家也就不远了。到那个时候,生也好,死也好,开悟也好,不开悟也好,所有这些你都置之度外了。你走上一条路了,这条路是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