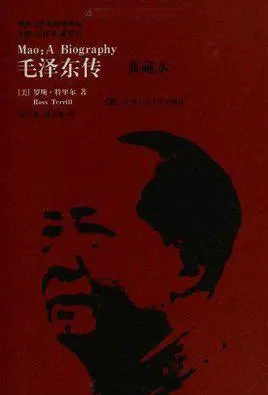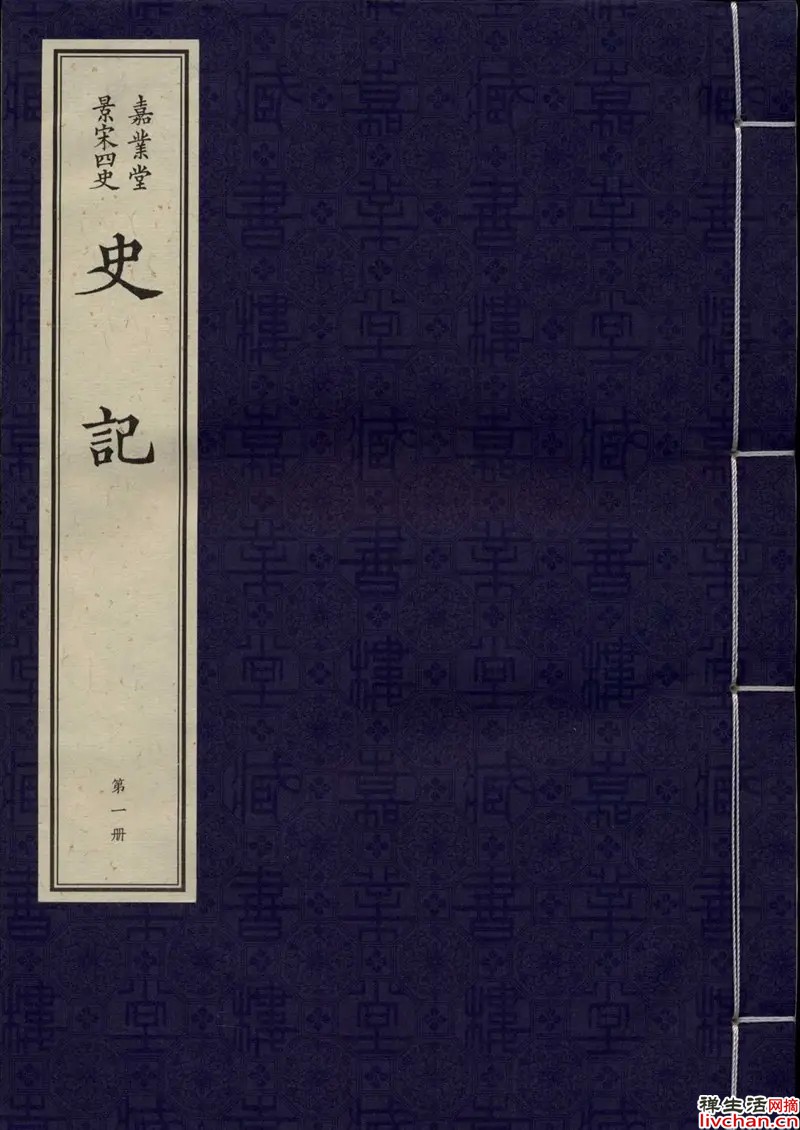王贲刚在府门前下马,守候在门厅的家老立即迎了上来。
散朝之后,父亲的护卫骑士给王贲传了父亲四个字:夜来回府。王贲当时只点了点头,一句话没说匆匆上马走了。晚汤之后,左右想不出推托事由,王贲只好快快过来了。依目下爵位,王贲在咸阳出行当乘六尺伞盖的轺车,然王贲素来不事张扬,更不想在父亲府邸前冠带高车,故此便服骑马,护卫也不带只身来了。近日,王贲自己也觉迷惑,原本一见父亲便局促不堪,很有些怕这个上将军父亲。可自从南下中原独当战局之后,王贲却越来越觉得父亲很有些令他不适的做法:对王命太过拘泥,对军政大略太过收敛,多次放弃该当坚持的主张,言行举止诸方面都不如从前洒脱。以前,王贲是极其敬佩父亲的。但南下之后,尤其是父亲班师还都后在大朝会的老态,令王贲既觉难堪又觉困惑,既往对父亲的崇敬流水般没了踪影,只要看见父亲便不自觉地郁闷烦躁。
“少将军,请跟老朽来。”家老恭谨细心一如往昔。
“这是家,我找不见路么?”王贲脸色很不好。
“不不不,上将军在另处等候少将军。”
“你只说地方,我自己去。”
“还是老朽领道。府下格局稍变了些许,只怕少将军不熟也。”
“旧屋重修了?”
“走走走,少将军沿途一看便知,老朽不饶舌了。”
王贲跟着家老曲曲折折一路走来,果然眼生得不认路了。原本,这座上将军府邸占地虽然很大,却是空阔简朴,中轴六进偏院三处后园一片,王贲闭着眼都可以摸到任何一个角落。可今日进来,层层叠叠亭台楼阁水池树林灯火摇曳,恍如山东小诸侯的宫殿一般。若非家老带路,王贲当真不辨方向。蓦然之间,王贲有些恼怒了。父亲与自己一样,常年在外征战,如何有闲暇将府邸整治得如此华贵?定然是这班家老管事挥霍铺排。
“家老办得好事!”王贲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老朽不明,敢请少将军明言。”家老惶恐地站住了。
“如此铺排府邸,不是你的功劳?”
“啊呀呀少将军,老朽一言难尽也!”
“秦法连给君王贺寿都不许,你等不怕违法?”
“说得是说得是。”家老连连点头,却再不做一句辩解。
王贲也黑着脸不说话了,对这班管家执事说也白说,必须得跟父亲说。如此默然又过了两道木桥,来到池畔一片树林,又登上一座草木摇摇的假山,才在山顶茅亭之下见到了布衣散发的父亲。亭廊下点着一束粗大的艾草,袅袅烟气驱赶着蚊蝇,秋月照着水面,映得山顶一片亮光。山风习习,父亲半靠亭柱坐在一张草席上,疲惫懒散之态确实与军中上将天壤之别。
“父亲……”
“来了。坐下说话。”
“父亲,容我先见母亲与大哥再来。”
“不用了。家人全数回频阳老家了。”
“父亲……”
“惊个甚,坐了说话。家老,任谁不许近山。”
父亲的话语很平淡,家老却如奉军令一般匆匆去了。王贲走进茅亭,从石案上提起陶罐给父亲面前的陶碗续满了凉茶,便站在亭柱前不说话了。灭赵大战之后,秦王派李斯将王氏家族百余口迁来咸阳,还大修了一番当时的上将军府。三两年来,虽然王翦王贲父子一直不在咸阳府邸,可这座上将军府依旧是热气蒸腾勃勃生机。因为,王氏家族的根基已经从频阳转到了咸阳。母亲执掌内事,大哥与一班族兄族弟则已经开了铁木作坊,做起了造车与农具生意。王贲在大梁战场时,曾接大哥一信说:父亲不许王氏子弟入仕做官,只能做农做商或者从军打仗。其中几个兄弟都是才能之士,能否劝说父亲允许他们入仕,只我一人做商贾便了。王贲当时专注战局心无旁骛,只给大哥简短复信:父命无差,兄当一心,无由再说父亲。王贲心下清楚,定是几个族兄弟不想做商贾,从军又觉太晚,于是说动大哥生出这般主意。那时,王贲以为父亲没有错,国人都去做官,谁却去周流民生?身为庙堂栋梁,王氏理当有大局气度。可如今,一个偌大家族刚刚安稳下来,如何又突兀地搬回老家去了,连他也不知会一声?若没有父亲的严厉命令,王贲相信,谁都会跑来找他劝说父亲的。他近在咫尺却一无所知,足证父亲是有备而为周详谋划的。然则,如此这般究竟为何?王贲实在有些无法理解父亲了,而且,诸多不解一时还不知从何说起。
“灭楚之战,你举李信为将?”父亲淡淡开口了。
“唔。”
“好。不好。”
“唔。”不管父亲说法如何蹊跷,王贲都没有论说国事的兴致。
“好在有胸襟,利于朝局,亦利于自固根基。”父亲似在自说自话。
“身为上将,唯虑国家,没有自固之心。”王贲不能忍受父亲的评判。
“心者何物?岂非言行哉!”
“就事说事,李信足以胜任。”
“错。就事说事,灭楚领军王贲最佳,比李信更可胜任。”
“……”
“不说话了?”
“……”
“秦王知人,必察贲、信之高下。然则,秦王必用李信。”
“朝会尚未议决,秦王亦未决断,父亲何须揣测。”
“揣测?”父亲嘴角轻轻淡淡地抽出一丝冷笑,依旧似在自说白话,“秦王者,大明之君也。明知李信不及王贲扎实,却要一力起用李信,其间根由,不在将才之高下,而在庙堂之衡平。天下六国,王氏父子灭其三,秦国宁无大将哉!秦王纵然无他,群臣宁不侧目?秦人尚武,视军功过于生命,若众口铄金,皆说王氏之功尽秦王偏袒所致,群将无功皆秦王不用所致,秦国宁不危哉?王氏宁不危哉?”
“虑及自家安危,父亲便着意退让?”
“苟利国家,退让何妨,子不见蔺相如么?”
“纵然退让,亦当有格。何至老态奄奄,举家归田?!”
“老态奄奄何妨?老夫要的不是自家气度,是国家气度。”
“大臣尚无气度,国家能有气度?”
“驳挡得好。”父亲一反常态,从来没有过的温和,点头称赞了儿子一句,又饮下一口凉茶,依旧自说白话了,“当此之时,唯有一法衡平朝局,凝聚人心:大胆起用公议大将,做攻灭最大一国之统帅。成,则战功多分,衡平朝局;败,则群臣自此无话,战事大将可唯以将才高下任之……”
“父亲是说,秦王是在冒险用将?!”
“明君圣王,亦有不得不为之时也。”
“父亲!”王贲终于不堪忍耐了,冲着父亲一泻直下,“此等迂阔之说,王贲不能认同!自家退让也罢,老态奄奄也罢,举家归田也罢,王贲都可以忍了不说,但凭父亲处置。然父亲既然察觉秦王起用李信是在冒险,宁肯坐观成败,却不直谏秦王,王贲不能忍!秦王雄才大略,胸襟开阔,王贲是认定了跟准了!纵然心有歧见,纵然与秦王相违,王贲也要坦诚陈述以供决断!这既是臣道,更是义道!如今父亲洞察诸多微妙,却包藏不说,放任国家风险自流,心下岂能安宁!朝野皆知秦王曾以父亲为师,父亲却隐忍不告,宁负‘秦王师’之名,宁负直臣之道哉!王贲明言,父亲当以商君为楷模,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不当以范蠡那般舍弃国家只顾自身的全身之道为楷模!父亲不说,是疑惑秦王顾忌王氏功高,这与山东六国攻讦秦王有何两样!王贲直言,父亲不说,我自己上书秦王,争这个攻楚主将!”
父亲只淡淡笑着,始终没有说话。
“父亲,儿告辞。”
“给我坐下!”父亲突然一声厉喝。
王贲没有坐,也没有走,只黑着脸钉在大柱旁气喘咻咻。
“你小子尽公不顾私,何以举荐李信为将?”
“我……”
“你自以为不如李信?”
“……”
“能使铁将军王贲违心举荐,足证此事不可轻慢。”
“不一样!……”王贲突然憋出一句,又默然了。
父亲叹息一声,突然贴着大柱笔直地站了起来,其剽悍利落之态虎虎生风。瞬息之间,王贲双眼瞪得溜圆,对也!这才是父亲,这才是秦国上将军!父亲没有理睬王贲,大步出亭在山顶转悠了几圈,这才走了回来,拍打着亭栏正色道:“你小子,谅也不至于将老夫看做奸佞。然老夫还是要说,你小子还嫩。自以为心无二虑,自以为忠于国家,自以为任何时日可以说任何话,做梦!学商君?说得容易。商君面对的君主是谁?我父子面对的君王是谁?商君面对的大势是甚?今日大势是甚?一样么?不一样!只说目下秦王:一则,起用李信确有大局筹划之考量,该当赞同,说甚去?二则,战场事奇正万变,冒险多有,战胜者也屡见不鲜,况且,楚军也确实疲弱不堪。此时,老夫若说李信必不成功,只怕连你小子也要反对,况乎群臣?况乎秦王?三则,秦王天纵之才,多年主持灭国大计从无差错,朝野声望如日中天,秦王自己也更见胸有成算,说秦王已经有些许自负也不为过。当此之时,老夫以自家评判,强说秦王改变决断,可能么?更何况,秦王决断也有你等一班新锐将军一力赞同,并非秦王独断,老夫何说?说亦何用?只怕除了君臣离心,再没有任何好处!你小子说,将老夫这个秦王师让给你,你能去纠缠着秦王憨嚷嚷么?”
“……”
“世间多少事,只有流血才能明白。”末了,父亲淡淡补了一句。
王贲瘫坐在亭栏不说话了。良久,王贲提起陶罐猛灌了一通凉茶,向父亲一拱手,匆匆大步离去了。父亲再没有喝阻,也没有说话,只若有若无的一声叹息飘进了耳畔。蓦然之间,王贲有些怜惜父亲,但还是没有回头。
三日之后,王贲奉命入宫,共商对楚大战的最后决断。
这次是小朝会。秦王的庙堂谋划三大臣(丞相王绾、长史李斯、国尉尉缭)加上将军王翦、蒙恬,再加王贲、李信、杨端和、辛胜、章邯等几员主力大将与老将军蒙武,长史丞蒙毅里外行走,算是半个与会者。没有了大朝会的齐楚先后之争议,小朝会简短了许多。先是丞相王绾禀报:由丞相府总领,各方官署已经做好了相关的伐楚筹划,相关郡县的粮草器械民力已经开始预为囤积。接着李斯禀报:几日来已经征询了几位王族元老之伐楚谋划,没有新方略提出,均大体赞同李信将军方略。之后,老尉缭的竹杖遥遥指点着地图,陈述了秦王与几位大臣在大朝会之后谋定的伐楚用兵方略。最后,秦王征询诸人评判,说明如无重大异议,则照尉缭陈述之方略进兵。三大臣之外,王贲李信等一班年青大将均表赞同,蒙恬申明无异议。只有王翦说了一句题外话:“伐楚之战,贵在正,不在奇。主将但有韧性,此战未必不成。”却没有就进兵方略表示可否。因了此前王翦已经明白陈说了自家看法,秦王与大臣将军们也再没有要王翦说话。
此次朝会明确的进兵方略是:
其一,以李信为主将,蒙武为副将,率二十万大军直下楚都寿春;
其二,以王贲部秘密进兵淮南江北,隔断楚军渡江南逃之路;
其三,以巴蜀水军顺江东下,占据彝陵房陵,隔断楚军荆楚逃路;
其四,以李斯、姚贾为后援大臣,全力督导中原郡县粮草民力。
王贲很有些沮丧。没有想到小朝会的几乎一切部署,都被父亲事先说中了:大将果然起用了李信,兵力果然是二十万,文武大臣们果然是无人异议,秦王也果然没有再度征询父亲谋划的意思。唯有两处王贲没有想到,却也暗合了父亲的预料,一是派老将蒙武做伐楚副将,二是派自己做了外围偏师将军。这般分派,王贲确实没有感觉到战事谋划的合理性,却隐隐嗅出一股军功多分的气息。这令王贲很是郁闷。蒙武固然资望深重,所率老军也是昔日秦军精锐,然蒙武毕竟久在国尉署,没有做过领军大将,其将性又偏于柔弱,既不能补李信之缺,又不能纠李信之错,如何能是最佳的幕府格局?再说,不教王贲做伐楚主将也罢,至少该派自己独当一面追歼燕代余部。王贲确信,只有自己的轻装飞骑,才能彻底干净地荡平残赵飞骑与辽东猎骑之患,最终平定北中国。可如今,他王贲却只能担任淮南江北之遮绝偏师。如此使命,秦军任何一个大将都会做得很出色,秦王若想均分功劳,何不将这个偏师之功也让给冯劫或冯去疾等大将,何须一定要派给他?
郁闷归郁闷,王贲还是没有再去见父亲。
那座上将军府没有了母亲,没有了家人,王贲也没心思回去了。与父亲再度探讨朝局,王贲实在没有心绪,何况大军已经开始集结,也该赶赴军中了。可是,就在王贲马队开拔的前夜,大哥匆匆赶来了。大哥说,父亲教他传话:子为国家大将,唯当以战局为重,无虑其余。大哥说,这是父亲的郑重叮嘱,说不清其中奥秘,父亲也不许他过问。王贲说,没甚,教父亲放心,王贲不会荒疏国事。大哥言犹未尽,似乎有话,又吞吐不说。王贲送大哥上路时一再追问,大哥才说,父亲有告老还乡之意,吩咐他不要说给兄弟,可他忍不住,因为他吃不准朝局究竟发生了何等变化,父亲与兄弟有没有危险?王贲听得无可奈何,气哼哼说,甚危险?树叶下来砸破头!他要做田舍翁,大哥陪他做,左右我是不做!大哥不相信,反复追问。王贲又气又笑道,大哥务过农经过商,该知道老地主老商贾毛病:老商贾金钱多了,老地主家业大了,怕遭人顾忌,怕人眼红,怕人闲话!知道么?就这个理!能有甚!大哥惶惑道,不就灭了两国嘛,仗是大家打的,谁眼红甚了?王贲心烦,索性不再辩解,只说自己事多,送大哥走了。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深秋,秦国南进大军隆隆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