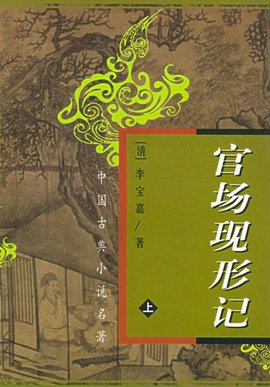午后的阳光照进汉考斯庄园的那间实验室。屋子里已经摆上了一些安乐椅和一张长沙发,与其说它们点缀了这个房间,莫不如说更凸显了这间屋子的空寂。
梅瑞迪斯·布莱克有点儿局促不安。他一边用力揪着他的胡子,一边和卡拉东拉西扯地闲聊。有一回他突然停了一下,然后说:“亲爱的,你很像你妈妈,但是又跟她不一样。”
卡拉问道:“我哪里像她?哪里又不像?”
“你的肤色像她,走路的样子也像,但是——我该怎么说呢——你看上去比她要积极得多。”
菲利普·布莱克眉头紧锁地望着窗外,不耐烦地敲着窗玻璃。他说:“所有这一切究竟是要搞什么名堂?一个好端端的周六下午——”
赫尔克里·波洛赶忙出来打圆场。
“啊,我很抱歉——我知道,打乱了你原本打高尔夫的安排实在是罪不可恕。不过算了吧,布莱克先生,这是你最好的朋友的女儿。你会为了她破一回例的,对吗?”
男管家在外面通报:“沃伦小姐到。”
梅瑞迪斯走过去迎接她。他说:“你能够抽空来,这太好了,安吉拉。我知道你很忙的。”
他领着她来到窗边。
卡拉说:“嗨,安吉拉姨妈。今天早上我刚刚看了你在《泰晤士报》上写的文章。能有这么个杰出的亲戚可真好。”她指了指旁边一个方下巴、有着一双坚定的灰色眼睛的高个子年轻人。“这位是约翰·拉特里,他和我——准备结婚。”
安吉拉·沃伦说:“噢!我还不知道……”
梅瑞迪斯又去迎接下一位客人。
“啊,威廉姆斯小姐,多年不见。”
上了年纪的家庭女教师走进屋来,她的外表看似弱不禁风,实际上却是百折不挠。她的目光在波洛身上若有所思地停留了片刻,然后又投向了那个肩宽体长、穿着剪裁考究的粗花呢套装的身影。
安吉拉·沃伦迎上前来,面带微笑地说道:“我感觉自己又要变成女学生了。”
“亲爱的,我为你感到无比自豪,”威廉姆斯小姐说,“你给我也争了口气。我猜这是卡拉吧?她不会记得我的,那时她还太小了……”
菲利普·布莱克烦躁地说道:“这到底在干什么啊?没人告诉我——”
赫尔克里·波洛说:“我自己,把它称为重回旧日之旅。我们不能都坐下来吗?这样一来,当最后一位客人到达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就绪了。等她一到,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题——驱除鬼魂。”
菲利普·布莱克叫道:“你到底搞什么鬼?不会是要举行个降神会吧?”
“不,不。我们只是要讨论一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讨论一下,也许我们就能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更清楚。至于鬼魂嘛,它们当然不会现身,不过尽管我们看不到,可谁敢说它们不在这里,不在这个房间之中呢?谁又敢说埃米亚斯和卡罗琳·克雷尔夫妇没有在这里聆听呢?”
菲利普·布莱克说:“无稽之谈,荒唐透顶——”这时候门又开了,打断了他的话,管家通报狄提斯汉姆夫人到了。
埃尔莎·狄提斯汉姆带着她一贯的那种淡淡的兴味索然的傲慢神情走了进来。她冲梅瑞迪斯微微一笑,冷冷地盯着安吉拉和菲利普,然后走到窗边,在离其他人都比较远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在松开脖子上那条昂贵的浅色皮草围巾并任其滑落之后,她先是打量了这间屋子片刻,然后瞧着卡拉。那个女孩儿也回看着她,心里默默揣度着这个给她父母的生活带来了灭顶之灾的女人。她那张年轻而真挚的脸上没有憎恨,只有好奇。
埃尔莎说:“抱歉,波洛先生,我可能有点儿晚了。”
“夫人,你能来就已经很好了。”
塞西莉亚·威廉姆斯用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她眼中充满敌意,但埃尔莎只是毫无兴致地瞟了一眼。她说道:“安吉拉,我都认不出你来了。多久没见了?十六年?”
赫尔克里·波洛赶忙抓住了这个机会。
“是啊,我们将要谈起的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六年了,首先我想告诉诸位我们为什么会重聚于此。”
接着他用了寥寥数语简述了卡拉向他提出请求和他接受这项任务的过程。
他说得很快,全然无视菲利普脸上显现出的阴云密布,以及梅瑞迪斯带有震惊的厌恶表情。
“我接受了这项委托,于是就着手调查,想要找出真相。”
卡拉·勒马钱特远远地坐在宽大的单人沙发里,模模糊糊地听着波洛所说的话。
她用手遮住了双眼,偷偷地从指缝间研究这五张面孔。她能看出来这群人中的哪一个杀了人吗?是时髦而迷人的埃尔莎,面红耳赤的菲利普,既和蔼可亲又善良的梅瑞迪斯·布莱克先生,严厉凶悍的家庭女教师,还是冷静干练的安吉拉·沃伦?
如果她努力去想,能否想象出他们其中的一个去杀人的场景呢?对,有可能,但那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谋杀。她能够想象菲利普·布莱克在盛怒之下掐死某个女人——没错,她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她也能想象梅瑞迪斯·布莱克拿着左轮手枪去恐吓一个窃贼——然后不小心枪走了火……她还能想象安吉拉·沃伦开枪杀人,但并非意外,绝不掺杂个人的感情——只是为了保证探险行动的安全!还有埃尔莎,在某个古怪的城堡中,在铺着东方丝绸的长榻上说:“把这个浑蛋扔到城下去!”都是些胡思乱想——不过即使动用她最大胆最疯狂的想象力,她也完全想象不出瘦瘦小小的威廉姆斯小姐能杀人!又一幅荒诞不经的画面浮现出来——“威廉姆斯小姐,你杀过人吗?”“做你的算术题,卡拉,别问傻问题。杀人可是很邪恶的事情。”
卡拉想:“我脑子有病了——我必须要停下来。你这个傻瓜,好好听,听那个自称什么都知道的小个子男人怎么说。”
赫尔克里·波洛正在滔滔不绝。
“这就是我的任务——可以说就像是给自己挂上了倒车挡,穿越多年的时光回到过去,去发现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菲利普·布莱克说:“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你谎称还有其他的可能,那不过是个骗局——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厚颜无耻的骗局。你就是要通过弄虚作假,从这个姑娘身上骗钱。”
波洛并未让自己被这番话激怒,他说:“你刚才说,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么说未免欠考虑。大家公认的事情未必就是事实真相。举个例子来说,就比如你吧,布莱克先生,从表面上来看,你极其厌恶卡罗琳·克雷尔。你的态度尽人皆知。但是对心理学稍有认识的人就会立刻看出来事实恰恰相反。你一直极度迷恋卡罗琳·克雷尔,你对此感到愤怒,于是一再提醒自己她有各种毛病,反复强调自己有多么厌恶她,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来克服那种迷恋的感觉。同样的,梅瑞迪斯·布莱克先生多年来对卡罗琳·克雷尔一直痴心不改。在他讲述的关于惨案的故事里,他把自己说成是因为她的缘故才痛恨埃米亚斯·克雷尔的行为。但是你只有仔细地从字里行间去发掘,才能明白其实这份倾其一生的爱慕已经逐渐消磨殆尽,当时占据他全部心灵的是年轻漂亮的埃尔莎·格里尔。”
梅瑞迪斯结结巴巴地想要辩解什么,狄提斯汉姆夫人嫣然一笑。
波洛继续说道:“我提起这些事情只是为了做个说明,不过它们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也都有关联。很好,那么我准备开始我的回溯之旅——尽我所能去获悉所有与惨案有关的事实。我想告诉你们我是如何着手调查的。我和当年为卡罗琳·克雷尔辩护的法律顾问、代表检方的年轻法律顾问、和克雷尔家族关系密切的老律师、庭审过程中始终在场的律师事务所的职员,以及负责本案的警官分别谈过话——最终找到了五位当年在场的目击证人。所有这些人帮助我在头脑中描绘出了一幅图画——那是一个女人的合成图。而且我得知了如下事实:
“卡罗琳·克雷尔从未申辩过自己是无辜的(除了在那封写给女儿的信里)。
“卡罗琳·克雷尔并没有在被告席上显露出恐惧,事实上,她表现得事不关己,自始至终都采取了一种完完全全的失败主义者的态度。在狱中她也很平静安详。法庭裁决之后她立即给她的妹妹写了一封信,信里表达了自己会接受并服从命运的安排。而且与我交谈过的每个人(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都认为卡罗琳·克雷尔是有罪的。”
菲利普·布莱克点着头说道:“她当然是有罪的。”
赫尔克里·波洛说:“不过我的角色并不只是去轻易接受别人的判断。我必须亲自调查这些证词。调查事实,并且确信这件案子中的心理学因素与它们相符,这才能够令我满意。为此我仔细翻阅了警方的案卷,而且我也成功地得到了五位当时在场的人为我写下的他们自己关于惨案的记述。这些记述弥足珍贵,因为它们包含了某些我从警方的案卷中无法获知的事情——也就是说:首先,一些从警方角度来看无关紧要的谈话和事件;其次,这些人自己对于卡罗琳·克雷尔当时的想法和感觉的看法(这在法律上并不会被作为证据来接受);第三,某些故意对警方有所隐瞒的事实。
“现在我可以自己来断这个案子了。卡罗琳·克雷尔有充分的犯罪动机,这一点似乎毫无疑问。她爱丈夫,她丈夫则公开承认要为了另一个女人弃她而去,而她自己也承认她是个嫉妒心很强的女人。
“说完动机,再来看看作案的手段,在她的衣柜抽屉里发现了一个装过毒芹碱的空香水瓶子,上面只有她的指纹。当被警察问起的时候,她承认那就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间屋子里拿的。这里的毒芹碱瓶子上同样有她的指纹。我问过梅瑞迪斯·布莱克先生,当天五个人离开这间屋子的顺序——因为在我看来,无法想象任何人能够在五个人全部在场的情况下拿走毒药。大家离开实验室的顺序是这样的——埃尔莎·格里尔,梅瑞迪斯·布莱克,安吉拉·沃伦和菲利普·布莱克,埃米亚斯·克雷尔,最后是卡罗琳·克雷尔。而且,梅瑞迪斯·布莱克先生在等克雷尔太太出来的时候是背对房间的,因此他不可能看到她正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她有机会。至此,我确信她的确拿了毒芹碱。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明。那天梅瑞迪斯·布莱克先生对我说:‘我能记起站在这里,从敞开的窗口闻到阵阵茉莉花香。’但当时可是九月,那扇窗外的茉莉花应该已经过了花期。茉莉花通常是在六七月间盛开的。不过在她房间中找到的那个还残留着一点点毒芹碱的香水瓶子,原本就是用来装茉莉花香水的。于是我敢肯定,克雷尔太太是想好了要偷毒芹碱的,她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倒空了她包里的这瓶香水。
“后来我又做了第二次试验,那天我让布莱克先生闭上眼睛,努力去回想大家离开房间的顺序。结果一点点茉莉花香气立刻就勾起了他的回忆。可见气味对我们的影响是超乎我们预料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那个事关重大的早晨。目前为止,所有的事实都无可辩驳。格里尔小姐对于她和克雷尔先生打算结婚这件事的突然透露,埃米亚斯·克雷尔对此的确认,以及卡罗琳·克雷尔深陷痛苦不能自拔——所有这些都有不止一个证人能够证明。
“第二天早上夫妇两人在书房里发生了一场争吵。最先被听到的一句话是卡罗琳·克雷尔说:‘你和你那些女人!’她说这话的时候愤愤不平。最终她又说道:‘哪天我一定要杀了你。’菲利普·布莱克从大厅当中听到了这些,格里尔小姐则是从外面的阳台上听到的。
“她接着又听到克雷尔先生让他的妻子理智一些,然后她听见克雷尔太太说:‘在放你去找那个女孩儿之前,我会先杀了你。’这之后不久埃米亚斯·克雷尔就出来了,有些粗鲁地告诉埃尔莎·格里尔下去继续给他摆姿势做模特。她去拿了件毛衣之后就跟着他走了。
“到现在为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在意料之中。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有件事情不那么协调了。
“梅瑞迪斯·布莱克发现他遭窃了,于是打电话给他弟弟;他们在码头会面后一起走上来,路过巴特利花园,卡罗琳·克雷尔正在那里和她丈夫讨论安吉拉去上学的事情。这件事给我的感觉非常奇怪。这对夫妻之间刚刚还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以卡罗琳显而易见的威胁而告终的,然而才过了二十多分钟,她就又下来和他争论一件家庭琐事。”
波洛转向梅瑞迪斯·布莱克。
“你在你的叙述中提起了你听到克雷尔说的那几句话。他说的是:‘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我会帮她收拾行李的。’对吗?”
梅瑞迪斯·布莱克说:“差不多就是这样,没错。”
波洛转向菲利普·布莱克。
“你所记得的是这样吗?”
后者紧皱着眉头。
“在你说之前我确实不记得——不过现在我想起来了。确实说到了收拾行李的事!”
“是克雷尔先生说的,而不是克雷尔太太?”
“是埃米亚斯说的。我听到卡罗琳说的只是一些对那个姑娘太严厉了之类的话。不过说到底,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再过一两天安吉拉就要去学校了。”
波洛说道:“你还没有抓住我所说的重点。为什么是埃米亚斯·克雷尔替那个姑娘收拾行李?这也太荒唐了!家里有克雷尔太太,有威廉姆斯小姐,还有个女用人。收拾行李本来就是女人的活儿,不是男人干的。”
菲利普·布莱克不耐烦地说:“那又怎么样?这跟罪案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啊。”
“你觉得没关系?在我看来,这正是第一点提示。紧接着还有另一点。克雷尔太太,一个伤心绝望的女人,刚刚还在威胁她的丈夫,而且肯定不是在计划着自杀就是在策划着谋杀,现在却用最为友好的方式提出要去给她的丈夫拿一些冰啤酒下来。”
梅瑞迪斯·布莱克慢悠悠地说道:“如果她正在策划着谋杀的话,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无疑那正是她打算做的事情。不过是掩饰一下罢了!”
“你这么认为?她已经拿定主意要毒死丈夫,她也已经拿到了毒药。她丈夫在巴特利花园一直存了一些啤酒,显然她要是稍微有点儿头脑的话,就应该趁着周围没人的时候把毒药放到其中的一瓶里面。”
梅瑞迪斯·布莱克提出了异议。
“她不能那么干。其他人也有可能喝了啊。”
“是的,还有埃尔莎·格里尔。你是要告诉我,在已经下定决心要谋杀她丈夫以后,卡罗琳·克雷尔还会对同时杀死那个姑娘心存顾忌吗?
“不过我们先别为此争论不休,还是让我们只谈事实吧。卡罗琳·克雷尔说她要给丈夫送一些冰镇啤酒下来。她上去回到屋子里,从存放啤酒的温室里拿了一瓶给他带下去。她还把酒倒好了递给他。
“埃米亚斯·克雷尔一饮而尽,然后说道:‘今天所有东西都这么难喝。’
“克雷尔太太又上去回到屋子里。她吃了午饭,表现得一如平常。有人说她看起来有点儿担心,有点儿出神。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杀人凶手的行为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有些杀人犯很冷静,有些则很激动。
“午饭以后她又下去到巴特利花园。她发现她丈夫死了。我们可以说,她做的事很显然是意料之中的。她流露出了悲伤之情,然后让家庭教师去打电话叫医生。而我即将说到的是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事实。”他看着威廉姆斯小姐,“你不反对吧?”
威廉姆斯小姐的面色有些苍白,她说:“我没有要求过你保密。”
波洛平静地叙述了家庭教师看到的那一幕,结果却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埃尔莎·狄提斯汉姆挪动了一下位置,眼睛盯着坐在大椅子中的这个了无生气的小个子女人,以难以置信的口气说道:“你真的看见她这么做了?”
菲利普·布莱克一跃而起。
“那不就结了!”他大叫道,“彻底弄清楚了。”
赫尔克里·波洛温和地看着他,说道:“未必吧。”
安吉拉·沃伦厉声说道:“我不相信。”她迅速地瞥了一眼瘦小的家庭教师,目光中闪出一丝敌意。
梅瑞迪斯·布莱克揪着他的胡子,神情惊愕。只有威廉姆斯小姐不为所动。她坐得笔直,双颊微微泛起红光。
她说:“那正是我所看到的。”
波洛慢条斯理地说道:“当然,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是我的一面之词。”她那双不屈不挠的灰色眼睛迎向波洛的目光,“波洛先生,我还不习惯我所说的话受到怀疑。”
赫尔克里·波洛低下头,说道:“我不是怀疑你说的话,威廉姆斯小姐。你所看见的事情正如你所说——也正是由于你看见了这一幕,我才意识到卡罗琳·克雷尔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有罪。”
那个一脸忧心忡忡的高个子年轻人,约翰·拉特里,第一次开口说话:“波洛先生,我很感兴趣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波洛转向他。
“没问题,我会告诉你的。威廉姆斯小姐看见了什么?她看见了卡罗琳·克雷尔急切而又小心翼翼地擦掉啤酒瓶子上的指纹,接着又把她死去的丈夫的指纹印在了上面。注意,是印在啤酒瓶上。但毒芹碱是在杯子里的——并非在酒瓶中。警方没有在酒瓶里发现任何毒芹碱的痕迹。酒瓶里从来就没放过毒芹碱,卡罗琳·克雷尔却并不知道。
“这个被认定毒害了她丈夫的人根本不知道她丈夫是怎么被毒死的。她以为毒药是下在酒瓶中的。”
梅瑞迪斯反驳道:“可为什么——”
波洛迅即打断了他的话。
“对,为什么?为什么卡罗琳·克雷尔要如此费尽心机地建立起一套自杀的说法呢?答案必定非常简单。因为她知道是谁毒死了他,她愿意做任何事情——忍受一切——也不愿意让这个人被怀疑。
“现在离终点已经不远了。那个人会是谁呢?她会袒护菲利普·布莱克吗?或者梅瑞迪斯?还是埃尔莎·格里尔?或者塞西莉亚·威廉姆斯?都不是,只有一个人能让她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
他停顿了一下:“沃伦小姐,如果你随身带着你姐姐写给你的信,我想把它大声地念出来。”
安吉拉·沃伦说:“不行。”
“但是,沃伦小姐——”
安吉拉站起身来,话音响起,冰冷如铁。
“我很清楚你在暗示什么。你不就是想说是我杀了埃米亚斯,而我姐姐知道这件事情吗?对于这个指控我完全否认。”
波洛说:“那封信……”
“那封信只是给我一个人看的。”
波洛把目光投向了房间里两个最年轻的人所站的地方。
卡拉·勒马钱特说:“求你了,安吉拉姨妈,你不愿意按照波洛先生说的做吗?”
安吉拉·沃伦愤愤地说:“你真是的,卡拉!难道你连一点儿脸面都不想要了吗?她可是你妈妈啊——你——”
卡拉的声音清晰而狂热。
“是的,她是我妈妈。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权要求你这么做。我这是在替她说话,我要让波洛先生读这封信。”
安吉拉·沃伦这才缓缓地把信从包里拿出来递给波洛,她恨恨地说:“真希望我从来没让你看过。”
接着她背转过身去,望向窗外。
就在赫尔克里·波洛大声念着卡罗琳·克雷尔最后一封信的时候,房间角落里的阴影逐渐浓厚起来。卡拉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感觉,仿佛有人正在这间屋子里显形,聆听,呼吸,等待。她想:“她在这儿——我妈妈就在这儿。卡罗琳——卡罗琳·克雷尔就在这间屋子里!”
赫尔克里·波洛读信的声音停了下来。他说:“我想,你们应该都同意这是一封极其不同寻常的信。当然,信写得也很美,但确实不同寻常。因为这里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疏漏——竟然通篇没有申明自己是清白的。”
安吉拉·沃伦头也不回地说道:“没有那个必要。”
“对,沃伦小姐,没有必要。卡罗琳·克雷尔不需要告诉她的妹妹她是无辜的——因为她认为她妹妹已经知道这个事实了——而且有最好的理由知道。卡罗琳·克雷尔所关心的全部就是去安慰,去打消疑虑,从而避免安吉拉去自首的可能性。她在信中一再重申——不要紧,亲爱的,真的不要紧。”
安吉拉·沃伦说:“你不明白吗?她是希望我幸福快乐,仅此而已。”
“没错,她想让你幸福快乐,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一件她念念不忘的事情。她有个孩子,但她想到的却并不是孩子——那只是后话。不,占据她全部心思,让她罔顾其他一切事情的就是她的妹妹。必须让她的妹妹打消疑虑,鼓励她过自己的生活,要让她幸福快乐,要让她成功。这样想来,代人受过接受错判的重负也就没有那么不可承受了,卡罗琳自己把这归纳成了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话:‘谁欠的债谁就要还。’
“这句话解释了一切。它实际上明显是指卡罗琳多年以来的一块心病。少年时期的她曾经在一阵失控狂怒之下将一个镇纸扔向她的小妹妹,给妹妹留下了终身的伤害,自那以后她便背负起了沉重的心理负担。现在,她终于有机会去偿还她所欠下的债了。说到安慰的话,我可以真诚地告诉你们,我相信在还债之后,卡罗琳·克雷尔确实能够获得从未体验过的内心安宁与平静。由于她相信此举就是还债,因此审判的折磨及最终的定罪对于她来说都已经无关痛痒。这么去说一个已经被定罪的杀人凶手也许有些奇怪——但她的确从中体会到了快乐。是的,这或许超出了你们的想象,而我接下来还会继续说明。
“按照这种解释,再去想想卡罗琳自己的反应,你们就会发现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让我们从她的角度再来审视一下这一系列的事件。一开始是在头天晚上,当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迫使她回想起了自己顽劣不羁的少女时代。那就是安吉拉把一个镇纸冲着埃米亚斯·克雷尔砸了过去。要记得,那正是多年之前她做过的事情。安吉拉大吼大叫说希望埃米亚斯死了才好。接着第二天早上,卡罗琳去温室的时候发现安吉拉正在摆弄啤酒。还记得威廉姆斯小姐的话吗?‘安吉拉在那儿,她看起来显得很愧疚……’威廉姆斯小姐说这话的意思是指她因为逃学而愧疚,但对于卡罗琳来说,安吉拉那张由于冷不丁被抓到而显露愧疚的脸,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别忘了,以前安吉拉至少有一次往埃米亚斯的饮料里放过东西。这也许是她很容易就能想到的事情。
“卡罗琳接过了安吉拉给她的这瓶酒,带着它下去到了巴特利花园。在那里她把酒斟满杯子,并且递给了埃米亚斯。而他在一饮而尽之后露出一脸苦相,说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所有东西都这么难喝。’
“卡罗琳当时并没有起疑心——但是当午饭以后她又去巴特利花园的时候,就发现她丈夫已经死了——她知道毫无疑问他是被毒死的。不是她干的,那么,会是谁呢?猛然间,整件事情涌入了她的脑海——安吉拉的威胁;安吉拉的脸贴在啤酒瓶子上,在不经意间被抓到——愧疚……愧疚……愧疚。这个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作为对埃米亚斯的报复,也许她并不是存心要杀死他,只是想让他生病或者感到不舒服吧?又或者她是为了卡罗琳的缘故才这么做的?难道她是因为意识到了埃米亚斯要抛弃她姐姐而对他感到怨恨?卡罗琳想起了自己在安吉拉这个年纪也是如此桀骜不驯,真是历历在目啊。此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怎么才能保护安吉拉?安吉拉拿过那个酒瓶,安吉拉的指纹也会留在上面。她迅速地把酒瓶擦拭得干干净净。要是所有人都能相信这是一起自杀就好了——只要那上面只有埃米亚斯的指纹。于是她试着用他僵硬的手指去握住酒瓶——孤注一掷——同时还得听着有没有人来……
“一旦认可了这种假设,这以后的所有事情就都解释得通了。她自始至终都为安吉拉担忧。她坚持要把她送走,不让她和眼前发生的一切有任何接触。她害怕安吉拉可能会受到警方的过分盘问。最终演变成了她不顾一切地要在审判之前把安吉拉送出英国。因为她一直都担心安吉拉会坚持不住而坦白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