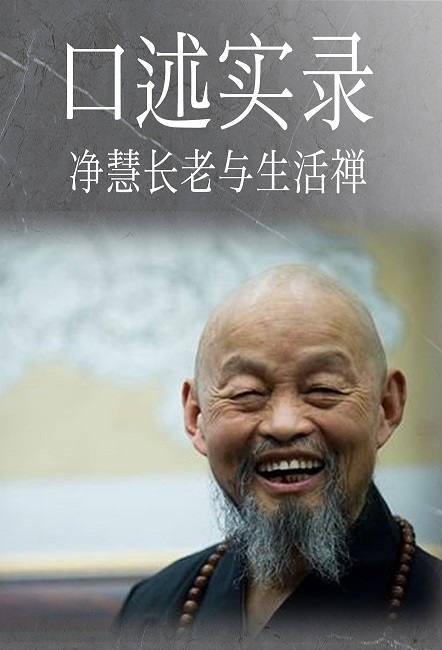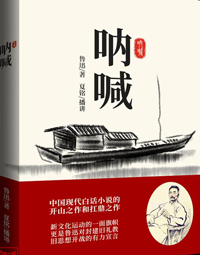安吉拉·沃伦慢慢地转过身来。她的眼睛将每一张转向她的面孔一一扫过,目光中透出严厉和鄙夷。
她说:“你们都是瞎了眼的傻子——所有人都是。你们难道不知道,如果是我干的,我一定会坦白的吗?我永远都不会让卡罗琳因为我所做的事去承受痛苦。永远不会!”
波洛说道:“但你确实摆弄过那瓶啤酒。”
“我?摆弄那瓶啤酒?”
波洛转向梅瑞迪斯·布莱克。
“听着,先生。在你的这份记述中提到过,命案发生的那天早上,你听到在你卧室下方的这间屋子里有声音。”
布莱克点点头。
“不过那只是一只猫。”
“你怎么知道那是一只猫呢?”
“我——我也记不得了。但那就是只猫,我非常确定是一只猫。窗户打开的大小也就够一只猫钻进去的。”
“不过它并非固定在那个位置上。它可以被随意推动,因此完全可能被推起来,这样一来一个人也同样可以钻进钻出。”
“没错,但我知道那就是只猫。”
“你没有看见那只猫吧?”
布莱克一脸困惑。他慢吞吞地说道:“没有,我没看见它——”他顿了一下,皱起了眉头,“不过我还是知道。”
“我马上就告诉你为什么你会知道。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那天早上可能有人来过你的房子,在你没看见的情况下进了你的实验室,从架子上拿了一些东西之后就又溜走了。如果是从奥尔德伯里来的,那么这个人不可能是菲利普·布莱克,不可能是埃尔莎·格里尔,不可能是埃米亚斯·克雷尔,也不可能是卡罗琳·克雷尔。我们很清楚这四个人当时在做什么。剩下的就是安吉拉·沃伦和威廉姆斯小姐。威廉姆斯小姐确实来过这边——你出去的时候正好碰见她了。她告诉你她正在找安吉拉。安吉拉一早就去游泳了,但威廉姆斯小姐无论在水里还是在岸边的石头上都没有看见她。她可以很轻易地游到这边来,实际上那天上午晚些时候,当她和菲利普·布莱克一起游泳的时候她也确实游过来了。我认为她游过来以后,上岸来到这所房子,从窗户钻进了实验室,然后从架子上拿走了一些东西。”
安吉拉·沃伦说:“我没干过这种事儿——没有——至少——”
“啊!”波洛发出一声胜利般的欢呼,“你已经想起来了。你告诉过我,为了跟埃米亚斯·克雷尔搞恶作剧,你曾经偷拿过一些你称之为‘猫食’的东西——你就是这么说的——”
梅瑞迪斯·布莱克脱口而出:“缬草!难怪啊。”
“完全正确。那就是使你心里确信有只猫进过这个房间的原因。你对鼻子极其灵敏。也许你在不知不觉中闻到了那股淡淡的令人不快的缬草气味——而你的潜意识受到了暗示,认为这和‘猫’有关系。猫喜欢缬草的味道,它们会到处去找。而缬草的味道极其难吃,也正是由于前一天你的讲述,才使得喜欢恶作剧的安吉拉小姐想到要拿些缬草放到她姐夫的啤酒里,因为她知道他喝东西总是喜欢一饮而尽的。”
安吉拉·沃伦惊讶地说道:“真的是那天吗?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偷拿过。没错,我也记得我把啤酒拿出来,然后卡罗琳进来了,差点儿抓到我!我当然记得……但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和那天联系起来过。”
“当然不会有——因为在你心中觉得它们之间并无关联。对你来说这两件事毫不相干。一件事完全和你平时搞的恶作剧一样——而另一件则是事先没有任何预兆的飞来横祸,一下子就让你把心里那些小事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我注意到当你提起这些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偷拿了这个,偷拿了那个,要放到埃米亚斯的饮料里。’却并没有说你真的放了。”
“对,因为我从来没放过。就在我要拧瓶盖的时候卡罗琳进来了。噢!”她惊呼了一声,“而卡罗琳认为——她认为是我干的!”
她停住了,环顾四周,然后用她一贯的那种冷静语调说道:“我猜,你们也都是这么想的。”
她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我没有杀埃米亚斯。那既不是我恶作剧的结果,也不是什么其他的。如果是我干的,我绝不会保持沉默的。”
威廉姆斯小姐急忙大声说道:“亲爱的,当然不是你干的。”她看着赫尔克里·波洛,“除了傻子,没人会那么想。”
赫尔克里·波洛温和地说:“我不是傻子,而且我也没有那么想。我很清楚是谁杀了埃米亚斯·克雷尔。”
他停了一下。
“在事情还没有被证实之前就盲目接受总是很危险的。我们就来看看奥尔德伯里的情况吧。这种情形屡见不鲜,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埃米亚斯·克雷尔打算为了另一个女人而抛下他的妻子。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他从未想过这么做。
“他以前确实迷恋过很多女人。这些女人在某一段时间可能会令他着迷,但很快就会成为过眼云烟。他爱上的通常都是具有某种共性的女人——那就是她们对他并不寄予太高的期望。但这次这个女人却不一样了。要知道,她还算不上是个女人呢。她就是个小姑娘,用卡罗琳的话来说,她真挚得要命……她也许看起来老于世故,说出话来也头头是道,但在对待爱情问题上却偏执得可怕。由于她自己对埃米亚斯·克雷尔一往情深,于是就认为他对她的感情也是同等的。她毫不怀疑他们之间的激情可以一生不渝。她连问都没问就认为他一定会离开他的妻子。
“你们可能会问,那为什么埃米亚斯·克雷尔没有跟她挑明,从而让她不再抱有幻想呢?我的答案是——那幅画。他想要完成那幅画。
“对有些人来说,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对于任何了解艺术家的人来说,却是见怪不怪了。而且我们已经基本上接受了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克雷尔和梅瑞迪斯·布莱克之间的谈话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克雷尔有些尴尬——他拍拍布莱克的后背,很乐观地向他保证整件事情就要搞定了。要知道,对埃米亚斯·克雷尔来说,所有的事情都很单纯。他正在画一幅画,结果却被两个女人所拖累,这两个女人在他看来争风吃醋又神经兮兮——只是他绝不允许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去妨碍他完成这幅此生最重要的作品。
“如果他把实情告诉了埃尔莎,这幅画就要泡汤了。或许在最初的那股冲动之下,他确实说过要离开卡罗琳。恋爱中的男人的确会说这样的话。或许他当初也只是放任别人去猜想,就像他后来依然放任别人去猜想一样。他并不在乎埃尔莎心里会有怎样的憧憬,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只要能让她再保持安静一两天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他就会告诉她实情,告诉她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他从来都不是个会为此感到良心不安的人。
“我想,他一开始确实努力过,不想和埃尔莎纠缠不清。他警告过她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她不肯听,反而还迎上前去,去迎接她的宿命。对于像克雷尔这样的男人来说,女人只是些玩弄的对象而已。如果你问他的话,他可能会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埃尔莎还很年轻——她很快就会缓过劲儿来的。这就是埃米亚斯·克雷尔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他的妻子才是他唯一在乎的人。他并不特别担心她,她只需要再多忍上几天就好了。对于埃尔莎口无遮拦地把什么事情都说给卡罗琳听,他感到很生气,但他依然很乐观地认为这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卡罗琳肯定还会像以前每一次那样原谅他,而埃尔莎呢——埃尔莎也就只能‘将就着忍了吧’。对于一个像埃米亚斯·克雷尔这样的男人来说,生活中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但我想,在最后那天晚上他真的开始担心了。是为卡罗琳,而不是为埃尔莎。也许他去了她的房间,而她拒绝和他说话。不管怎么样,经过一个不眠之夜,早饭后他把她叫到了一边,把实情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他确实迷恋过埃尔莎,不过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一等那幅画画完,他就决定不再见她。
“作为回应,卡罗琳·克雷尔气愤地大喊:‘你和你那些女人!’你们看,这句话把埃尔莎和其他那些女人,那些已经各走各路的女人们归为一类了。而且她又愤愤不平地加上一句:‘哪天我一定要杀了你。’
“她气坏了,对他的冷漠无情,以及他对那个姑娘的残忍深恶痛绝。当菲利普·布莱克在大厅里看见她,并且听见她自言自语嘟囔着说‘太残忍了’的时候,她心里想着的其实是埃尔莎。
“而说到克雷尔呢,他从书房走出来,看见埃尔莎和菲利普·布莱克在一起,于是就粗鲁地命令她继续下去摆姿势。他不知道的是,埃尔莎·格里尔刚才就坐在书房的窗户外面,把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她后来写给我的那份记录中关于那段对话的内容并不真实。别忘了,那只是她一个人的说法。
“想象一下吧,当她听到事实真相以那样一种残酷的方式说出来的时候,该有多么震惊!
“梅瑞迪斯·布莱克已经告诉我们了,在之前一天的下午,他等卡罗琳从实验室里出来的时候是背对着房间站在门口的。他当时正在和埃尔莎·格里尔说话。那也就意味着她是面向着他的,她可以越过他的肩膀看到卡罗琳正在干什么,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她也是唯一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她看见卡罗琳偷拿了毒药。她当时什么都没说,但当她坐在书房窗外的时候她回想起来了。
“埃米亚斯·克雷尔出来的时候,她借口说想要去拿件毛衣,接着就去了卡罗琳·克雷尔的房间找毒药。女人知道女人喜欢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她找到了装毒药的瓶子,把里面的液体吸到了一个钢笔的墨水囊里,同时非常小心地既没有蹭掉上面的指纹,也没有留下自己的。
“然后她再次下楼来,跟克雷尔一起去了巴特利花园。毫无疑问,她马上就给他倒了些啤酒,而他也一如往常地一饮而尽了。
“与此同时,卡罗琳·克雷尔的心里也是翻江倒海。一看到埃尔莎回屋去(这次是真的去取毛衣了),卡罗琳立即来到巴特利花园找她丈夫谈这件事。他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令她无法忍受!这对那个姑娘来说简直太残忍太无情了,让人难以置信!而埃米亚斯因为受到了打扰也烦躁起来,说事情已经定下来了——等画一画完,他就会让那姑娘收拾东西走人!‘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我会让她收拾行李的。我告诉你了。’
“然后他们听见了布莱克兄弟的脚步声,接着卡罗琳走了出来,稍微有些尴尬,嘴里嘟囔着一些关于安吉拉啊,学校啊,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之类的话,于是两兄弟很自然地就把这些联系起来,认定他们听到的谈话是和安吉拉有关的,而那句‘我会让她收拾行李’也就变成了‘我会帮她收拾行李’。
“此时埃尔莎手里拿着毛衣,沿着小路走下来,泰然自若,面带微笑,再一次摆好了姿势。
“无疑她已经料定卡罗琳会受到怀疑,因为毒芹碱瓶子会在她的房间里被发现。而现在卡罗琳带了一瓶冰镇啤酒下来,并且给丈夫倒了一杯,这让她觉得自己已经完完全全地胜券在握了。
“埃米亚斯一口喝了个精光,做了副苦相,说道:‘今天所有东西都这么难喝。’
“你们还没看出来这句话别有含义吗?所有东西都难喝?说明在喝下这杯啤酒之前他还喝过什么别的难喝的东西,他的嘴里还有余味。此外还有一点,菲利普·布莱克提到克雷尔有点儿踉踉跄跄,还纳闷‘他是不是已经喝多了。’其实这轻微的踉跄正是毒芹碱起效的最初表现,那也就意味着,在卡罗琳拿给他冰镇啤酒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已经服下了毒芹碱。
“接下来埃尔莎·格里尔继续坐在灰墙之上,一边摆着姿势,一边活泼自然地和埃米亚斯·克雷尔说着话。她必须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不让他起疑心,直到毒性发作无可挽回。不久她又看见梅瑞迪斯坐在上面的长椅上,于是向他挥挥手。由于他在那里,她必须表演得更加认真严谨了。
“而埃米亚斯·克雷尔,这个痛恨生病且不愿为之屈服的男人,仍然在固执地作画,直到四肢已经不听使唤,话也说不清楚的时候,才无助地瘫倒在长椅上,但此时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
“从屋子那边传来了午饭的铃声,梅瑞迪斯从长椅上站起身,走下来到巴特利花园。我想就在那片刻之间,埃尔莎离开了她坐的地方,跑到桌边,把最后的几滴毒药加进了最后那杯原本清白无辜的啤酒里。(她在回屋的路上把那个滴管处理掉了——把它弄了个粉碎。)然后她在花园门口迎上了梅瑞迪斯。
“刚刚从树荫里走出来的时候总是会有些晃眼。梅瑞迪斯并没有看得很清楚——他只看到他的朋友四肢伸开地躺在那个熟悉的地方,看到他的眼睛从画上移开——用梅瑞迪斯的话来形容就是目露凶光。
“埃米亚斯到底能知道或者猜到多少呢?他的意识中究竟明白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手和他的眼睛是忠实的。”
赫尔克里·波洛指着墙上的那幅画。
“我第一眼看见这幅画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因为这是一幅非同凡响的作品。这是一幅被害者为凶手画的像,画的是一个姑娘看着她的爱人在眼前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