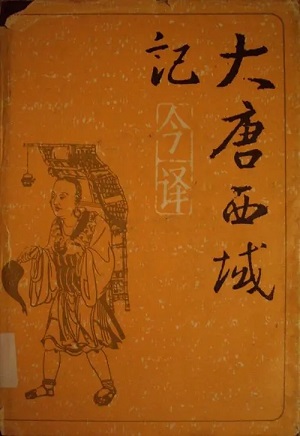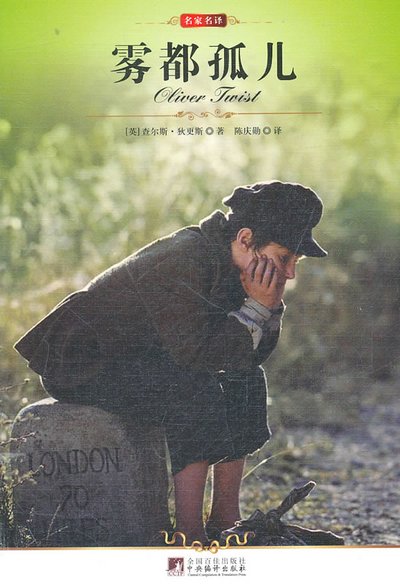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曾国藩就有了实权。
传统时代,人活着最大目的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四个字,升官发财。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源兖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56页。]
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刚刚升为侍郎,曾国藩工作也更加卖力了。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家信中汇报自己初任礼部侍郎的工作情况:
二十五日午刻上任,属员共百余人……从前阁学虽兼部堂衔,实与部务毫不相干。今既为部堂,则事务较繁,每日须至署办事。八日一至圆明园奏事,谓之该班。间有急事,不待八日而即陈奏者,谓之加班。除衙门官事之外,又有应酬私事,日内甚忙冗,几于刻无暇晷。[《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0页。]
也就是说,以前虽然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完全不管部里的事。现在正式做了“副部长”,情况不同了。每天都要坐班,下属一共一百多人。每八天要去一次圆明园向皇帝汇报事务,叫作“该班”。如果有什么急事,不到八天就要去见皇帝,叫作“加班”。除了工作,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一段特别忙,几乎没有片刻闲暇。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我们从中抽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初二日,看看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
[读书]:
未刻读《汉书·韩王信传》。申刻读《会典·宗人府》十四页。
[静坐]:
申正在坐曲肱枕坐三刻。
[办公]:
早入内,刑部值日。旋至部。午初到家,灯后清折底。
[课子]:
背经五页,讲鉴三条。
[对客]:
早自署归拜客三家。未初会二客。
[回信]:
回余菱香信,自写一片。[《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3页。]
大抵是每天上午都要赴署办公,其他时间要课子读书见客应酬。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自己在礼部工作顺利,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
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寅亦极协和。男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6页。]
就是说,他已经很熟悉现在部门的工作了。下属官员也都很佩服他,所以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如果一辈子这样在礼部当官,平平顺顺、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办事,他也很愿意。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十分留意,按类别“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8页。]
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虽然致力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246页。]。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他又加上经济一门。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86页。]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理性,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679页。]
由此可见,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的。
但是,做了一段时间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我们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诗文反映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灰色的。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咍。[《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76页。]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
…………
径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5页。]
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
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5页。]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任礼部侍郎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76页。]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8页。]。咸丰元年(1851)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68页。],在官场上如同废物。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89页。]就是说,我打算一年左右时间内就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自问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在这里混日子,实在对不住这份工资和地位。
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
主要是曾国藩升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
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身上打满补丁,早餐舍不得多吃一个鸡蛋。说是有一次,他和一个大学士聊天,问大学士,你早餐吃什么?大学士说,臣很俭朴,只吃三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吓了一大跳,说你真阔气啊!朕早餐一个也舍不得吃。为什么呢?因为内务府官员骗他,说外面鸡蛋三十两白银一个。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笑话往往会反映一些历史事实。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我们看故宫现存的道光画像,道光皇帝确实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用的大臣,又都是穆彰阿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眼看着国家一天不如一天,却都不敢向皇帝直言。
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这个人慷慨激烈,将来肯定会死在战场上。“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9页。]当时天下太平,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而曾国藩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所以曾国藩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13页。]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饱知官场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
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太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