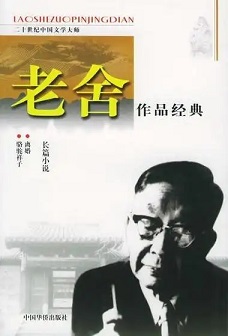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二十(这是虚岁,实足年龄十八周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九岁,也就是说,新皇帝比他小了差不多二十岁。
这一下,曾国藩先不提回家了,他要看看这个新主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年纪很轻,“主少国疑”,但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他工作非常勤奋,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谕旨,而不像老皇帝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
一般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台后,也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我们前面提到,穆彰阿这个人名声不太好。还没当皇帝之前,咸丰就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很多结党营私蒙蔽君主之类的负面传闻。所以上台之后,立足刚稳,就拿他开刀了。
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850年12月1日),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他说: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叙用。[《清实录》第40册,第294~295页。]
也就是说,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达极点。吏治败坏,人心浇漓。穆彰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职位,为私利而损害国家。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主,逢迎上意。我念他是三朝老臣,不忍置之重法,革去其职务,永远不再任用。
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还说:
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清实录》第40册,第294~295页。]
也就是说,从今而后,大小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公忠体国,把以前那些因循糊弄的积习都迅速改掉。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
这道谕旨一下,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像穆彰阿那样继续“弥缝”“糊弄”下去,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真是不凡,很可能是一个英主。
上台之后,咸丰皇帝另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初八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上谕,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表现出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
曾国藩心情太激奋了。
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契若符节”,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
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在这份上疏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官员们“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5页。]。他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就是说,京官,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很用心。但是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多少人敢想。
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是一个字,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推给下一任。第二个是颟顸,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了,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管。
在奏折结尾,曾国藩更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8页。]
就是说,十来年间,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负责进谏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过皇帝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这说明,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
所以,曾国藩说,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
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4页。]
这道奏折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已经让咸丰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
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他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
所谓郊配,就是皇帝祭天时,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唐张九龄在《请行郊礼疏》中说:“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
不许郊配,不进太庙,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严重到几乎无法遵守。特别是不进太庙,那么后世子孙怎么祭拜他呢?但是道光皇帝的这道遗嘱是“朱谕”,也就是亲笔书写的,无疑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不是谦虚之词,咸丰不能不重视。可是,刚刚上台的年轻皇帝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只好让大臣们集体讨论。
朝廷大臣进行集议,大多数人都从保险出发,说套话,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必行”。就是说,道光皇帝功业辉煌,怎么能不进太庙,不用郊配呢?所以这个遗嘱根本没法执行,还是按惯例办了了事。
按说,大家集体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曾国藩顺水推舟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曾国藩回去之后,感觉不妥。他是礼部侍郎,他认为自己要责无旁贷地拿出更合适的意见来。所以经过十余天的思考,他提出了不同意见。正月二十八日,他上了一道奏疏,说大行皇帝的遗嘱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为什么呢?他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页。]道光这么正式地留下这道遗嘱,一定有他特殊的考虑。曾国藩说,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死后不进宗庙之理。但“毋庸郊配”一项,道光皇帝说得也有一定道理。第一,道光这是从天坛祭坛的尺寸角度考虑的。因为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现在,死去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就要新修一个祭台,现在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道光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有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久远之图”,怕以后放不下,“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所以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这一点我们不可轻忽。
第二,“古来祀典,兴废不常。”祀典历代、历朝都有调整,并非丝毫不可变动之事。
第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对死去皇帝皇后的意见,一定要重视,不能视同无物。比如康熙时,太皇太后孝庄死了,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孝陵,陪着自己的儿子顺治。按理说这“不合袱葬之例”,因为皇后死了,按理要安葬到自己的丈夫身边,所以她应该埋到沈阳的清太宗昭陵去。但是康熙还是不敢违遗命,将太皇太后梓宫安放在孝陵旁边,雍正时就在这里正式下葬了。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就是说,不许后世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乾隆皇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按以前之例,完全可以称“祖”。但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所以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也。”[《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抑自身,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家法。
曾国藩的这道奏疏辨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一看,十分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论辩,他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曾国藩的这道奏折也说服了满朝大臣,大家一致同意这么办。所以,这件事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为对曾国藩的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户部之外的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一下,曾国藩就更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他写家信说:
余至刑部,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长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92页。]
也就是说,我到了刑部,可比以前更忙了。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同,事情太多了。要是长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了。
如此勤奋,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皇帝的欣赏和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咸丰元年(1851)三月,曾国藩上了《议汰兵疏》。曾国藩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二是军队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社会动荡,四处用兵之际,军队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臃肿软散,不能作战。他说,广西有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但是现在遇到农民起义,“竟无一人足用者”[《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0页。]。所以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提出裁兵五万,这样每年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用来练兵。应该说,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抓住了当时军队问题的关键,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
之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他在奏疏中提出现在百姓生活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势。”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强盗土匪“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三是冤狱太多,司法腐败严重,民气难申。[《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1~42页。]
曾国藩认为,这三大问题关乎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如果不从现在起就全力以赴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
配合这道民间疾苦疏,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疏》,其中,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具体办法。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应该说,这些文字是非常精彩、也非常有深度的。曾国藩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这样,国家大幸,民众大幸。他也可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做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然而,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
咸丰皇帝摆出了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
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
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