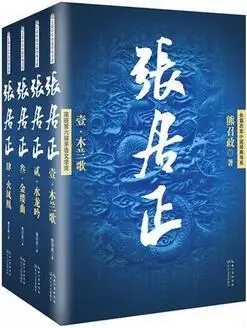荀磊告诉冯婉姝说:“我父亲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笑嘻嘻地说:“别臭吹了!你有什么资格自比安徒生?”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是鞋匠的儿子。冯婉姝确确实实没有丝毫鄙弃修鞋匠的意识,无论是丹麦的还是中国的,修鞋匠在人格上与她,与所有的人,都是绝对平等的。但她过去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她觉得就凭荀磊那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他父亲起码也得是个中学教师。
荀磊重复地说:“我父亲真的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一看荀磊眼神,就明白他并不是开玩笑。于是她收敛了嬉笑,把靠在他肩膀上的脑袋调整得更舒适,闭上眼睛说:“你爱他吗?把他的情况细说说吧!“
荀磊便抚着她一头柔软的长发,徐徐地对地说:“我父亲叫荀兴旺。我们老家是河北博野。我爷爷早就去世了,奶奶带着我两个姑姑和我爸过日子,苦得不得了。爸爸后来就加入了八路军。那时候他才十四岁,枪比他人还高半头。后来他是解放军里最普通的战士,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你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前些时候拍过一部故事片,就叫《解放石家庄》吗?你自然不知道。你照例不看这样的电影。我也一样。主要是这样的片子艺术上贫血贫得太厉害了,对吧?可电视上放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爸爸看得津津有味。他坐在我们家他自己打制的沙发上,手里攥着他那麻栗疙瘩旋成的大烟斗,脑袋前伸着,聚精会神地从头看到尾,一边看还一边评论着:“对!就是那样!......不对!瞎掰!当时哪是那样!”电视上好象不止播过一次,他次次都是这么个看法。说来也怪,跟他一块儿打仗的战友,牺牲了不知多少,他却连重伤也没落下。他还拼过刺刀哩。你不信吗?我信。因为我爸嘴笨,说实话都费劲,说瞎话那就非把他难死不行。他有一回跟我们讲他拼刺刀的事,就那么三两句话,听得我心里怦怦直跳。不是真拼过的人讲不出那话来。他说到那时候眼里只有敌人的肚子,那肚子东躲西闪,可他非把刺刀插进那肚子里不行,扎进去拽出一嘟噜肠子来,他就高兴了。他就那么出生入死地在第一线战斗。我奶奶和我两个姑姑,那一阵整天站在村口守着,一有担架队过来,他们就挨过去,一个一个掀开被子认,始终没有见着我爸爸。她们就哭了。人家问她们为什么哭,两个姑姑说:“高兴的。俺弟弟杀了敌人,可他没挂彩。”
奶奶却说:“糟了。怕是牺牲在那儿,抬不回来了。”仗打完了,爸爸回到家里,奶奶和姑姑让他脱光了膀子,见他果然一点没残,高兴得了不得。爸爸左肩窝、右腰根、左腿肚子上各有一处弹片划出的伤痕,左腿肚子削去的肉最多,可那毕竟算不了什么。爸爸要是留在部队,继续南下,说不定就当上南下干部了。那就不知道会娶个什么样的老婆,养出些什么样的孩子来,反正没有我了。可土改以后家里没有劳力,他就解甲归田了。种了几年地,我两个姑姑先后出阁了,城里招工,我爸就进城当了工人,后来把奶奶也接进了城。我爸先学木工,后学钳工,他这人手巧,想做什么能成什么,后来一直升到了七级。八级工到头,他只差一级。他们厂也没有八级的,他算技术最高的了。
“你一定觉得奇怪,我爸爸成分、经历这么好,可他怎么会不是党员?他不是。据说他出师的时候,厂里党委书记挺动感情地对他们车间党支部书记说,荀兴旺你们不发展,你们究竟想发展谁?可车间支部书记为难。我爸是个出名的孝子,奶奶爱吃豆面糕,近处没有,歇礼拜那天我爸就骑车跑遍全城,不买到豆面糕绝不罢休。这当然不会成为问题。可后来奶奶去世了,当时北京市已经大力提倡火葬,党团员都要带头,家里死了人要送去火葬,可我爸无论别人怎么劝,也不忍心把奶奶火葬,到底他还是买了棺材,想法子把奶奶送回老家土葬了。党支部书记觉得这事很难辩解,确实是落后的表现,所以不同意发展我爸入党。再有我爸原来是个文盲,进厂后进扫盲班,费了老大力气,认字也不多。后来补文化课,补到初小程度就再提不高了。他不爱看书,只爱鼓捣东西,比如打个家具、安装个管道、编个渔网、修理个自行车、修个鞋、旋个烟斗什么的,弄出来样样让行家佩服,可一叫他看书他就头疼。他一生只精读过两本书,一本是《苦儿流浪记》,这本书我听他讲过,不是法国那个马洛写的那本,好象是解放初印的一种诉苦材料;另一本是《鲁班学艺》,据他说他得到的那本书页已被撕破,他是一页页拼拢一起,一字一字读下来的。他一生最佩服的是两个人,一个古人一个今人。古人就是鲁班,今人就是彭德怀。
因为我爸文化始终提不高,党支部认为是学习不够努力造成的,所以后来也就一直没有发展他入党。我爸这个人人缘特好,但人人又都认为他绝不是入党、做官的材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他哪派都不是,哪派也都不积极找他。往外派工宣队,没他的事儿。“支农小分队”他也没参加过。他就是在车间干活。车间停产了,他也去,甚至只剩他一个人了,他也在那儿呆着,擦擦这儿,扫扫那儿。他就是那么个木头人似的模样。真实他心里很有主见。他平生最喜欢看的一出戏就是《白毛女》。他说还在部队里的那阵,参加土改,他天天在文工团演《白毛女》的时候站在台上“压台”,只要一演到逼死杨白劳那场,他就忍不住流眼泪。有一回有坏人捣乱,在场子里喊反动口号,我爸从台上一个雄鹰展翅扑下去,追了半里路,抓住了那个坏人,要不是别的人起来劝阻,我爸当场就会把他毙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告诉他,说江青说了,歌剧《白毛女》是毒草,他连惊讶和愤慨都没有,因为他根本不信。后来知道真把歌剧《白毛女》否定了,他也并不激动,他认定那不过是一时的说法,他坚信歌剧《白毛女》是好的。后来组织大家看芭蕾舞剧《白毛女》,看到喜儿被抢,他照样感动,他跟人家说:“《白毛女》还是好的吧?我就知道打不倒它。”人家便跟他解释:这个《白毛女》同那个《白毛女》有质的不同,那个反动,这个革命,比如那里头的杨白劳软弱无能,这里头的杨白劳英勇不屈,等等。他却全然听不进去,人家费老大劲说完了,他却表态说:‘我看差不离,就是这里不用那脚尖子跳,兴许更顺眼。’你说拿他有什么办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演歌剧《白毛女》,他在电视里看了,照样流眼泪。我跟他说:‘如今芭蕾舞跳的那种不能演了。‘他不以为然,对我说:‘干吗不演了?我看也挺好。就是少用脚尖子走路,兴许更好。’
你看,他什么时候都保持他个人的看法。我爱我爸,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稳定的、厚实的、淳朴的人格。他用他的这种人格力量,启示了我,使我的灵魂善良、纯净。
“那么,你要问我了,他不是七级钳工吗?怎么又当了修鞋匠呢?
那是前年的事。他才五十四岁,可他提前退休了,为的是让我二姐进厂去顶替。这就要说到我家里别的人了。先说我母亲。她就是咱们北京郊区顺义县的人,是我爸的师傅把她介绍给我爸的。他们也是一见钟情,认识不久便结婚了。后来我妈妈也进厂当了工人。我们家开头就住在工厂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中。一排一排的那种简易平房,一间屋子住一家人。我家人口最多的时候是六口人,我奶奶,我爸我妈,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那哥哥七岁的时候得病死了。全家挤着睡,连个收音机都没有。过春节的时候买张年画贴到墙上,一年里头把画上的每个细节都看熟,那大概便是我家的文化生活了。后来奶奶去世,姐姐们长大,三年困难时期,我妈生下了我。说起来要多亏一场意外的火灾,不知哪家生炉子不小心,把屋子引着了,结果牵三连四,救火车又一时开不过来,把厂里那片宿舍区烧光了。作为善后的结果,我们家和另一家被安排进了如今住的这个小偏院。头年厂里盖了新楼,我们两家都属住房困难,我爸把进楼的权利让给了那家,我们留在了小偏院中,那家的那间屋归了我们,我们现在总算有两间屋了。我妈渐渐从一个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她现在显得比我爸年轻很多(其实她比爸爸只小三岁),每天回到家头一件事是大洗大涮,用立体梳子梳她那烫过的头发,抹银耳珍珠霜。她有两身西装,一身是专门到王府井蓝开服装店做的,逢到休息的那天,她便穿得整整齐齐,有时候手上还戴个粉红的假宝石戒指,沏茶喝水以前要把杯子洗涮得很仔细。尽管她这样,你一眼看上去,还是有股天然的土气。我也爱我的妈妈。我觉得她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把我们姐弟三个拉扯大不容易,现在喘过气来了,讲究一点,是一种自我意识复苏的表现,是可喜的。别看她有这种似乎俗气的一面,干起家务事来,她还是那么能吃苦,那么麻利。你一看见她干活,便能感觉到她天性便是热爱劳动,并且渴望通过劳动来达到她的理想境界的。她把屋子总整理得特别利索,一尘不染。床单、被褥、窗帘、沙发上铺的浴巾等等并不见脏,她便把它的取下来,泡进洗衣盆,挽起袖子,露出两条比我还粗壮的胳膊,愉快地洗涤起来,望着那些溢出盆外的肥皂泡,她仿佛格外感到幸福。据大姐回忆,当年我们家是乱作一团的,妈妈也顾不得收拾,如今有两间屋子可以供她细心拾掇了,难怪她那么心满意足。她的审美观当然是受她成长的环境和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制约的。你到我家一看就能明白。每一样东西都是她精心挑选来的。
其实我们家附近的百货商场什么都能买到,但她为了买一块窗廉布,却宁愿跑到西单、大栅栏去,细细地比较、挑拣,然后汗淋淋地回来。
现在挂在我们家外屋窗户上的窗帘就是她的作品:布料是浅蓝底子的,上头有深蓝的松树和褐色的白鹤图案,下头用爱丽纱细心地镶上了花边。而沙发上铺的浴巾呢?棕红色的底子上是两个鲜红的散花的仙女。还有盖在酒柜和饭桌上的塑胶布......你一看就会感到“怯”(土里土气的意思。),但我以为你应当和我一样尊重我妈的审美趣味,看久了,你甚至会体验到一种质朴的以浓烈的色块和明快的配搭取胜的民俗美。现在里屋是我的世界。我那些从英国带回来的东西,我妈看不惯,就象我看不惯她选择的窗帘布一样,可她也尊重我。我把一只绘有抽象派图画的挂盘挂在床头上,每回妈妈收拾屋子的时候都要发笑:“天哪,这能叫画儿吗?”但她并没取下它,而是用鸡毛掸子小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尘。我妈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也快退休了。她说她退休以后,要好好养一点花。我想那时候,我们家小院一定能变成了美丽的花园。
“我两个姐姐的情况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大姐插队回来当了售货员,大姐夫也是售货员。二姐从兵团回来待了一阵业,后来当临时工,顶替我爸进厂以后,在十四层的宿舍楼里开电梯,去年她也结了婚,我二姐夫是厂里的电工。
“怎么样,你都听进去了吗?听腻了吗?”
冯婉姝把脑袋从荀磊肩上挪开,两手梳理着披肩长发,感叹地说:“听得津津有味。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我过去所不了解的世界。一个我即将踏进去的神秘的世界。”
不久,她的确迈步进入了这个世界。
那天,她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骑车前往荀磊家。路过后门桥时,她看到了鞋摊,看到了荀师傅本人。那头一眼的印象,便使她对这位未来的公公无比敬爱。
一般的人,看到冯婉姝的打扮做派,总会把她划入所谓“现代派”青年一流,似乎她所欣赏的,只能是洋味儿的人物,比如电影演员,一定只欣赏法国的阿兰·德隆和日本的山船敏郎,其实不尽然。冯婉姝自小在心目中,就崇敬、爱戴两个银幕形象,一个是《平原游击队》里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阳,一个是《上甘岭》里高宝成扮演的张连长,除去别的因素之外,她觉得那两个人物从外形上看也是最美的。当她长大并且当了翻译以后,她仍然保持着那样一种看法,并且对自己经久不息的鉴赏激情上升到了理性——那两个银幕形象凝聚着一种和中华民族古老历史以及苍茫大地相联系的,经过世世代代的劳动者审美意识筛选的男性美。有一回她同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褐发女郎交谈,惊讶地发现,那位偶然看过中国影片《平原游击队》的女郎,竟然也坦率地承认:“李向阳真可爱!我爱这样的男人!你要见到那位扮演李向阳的演员,请你转告他,我是多么崇拜他!我要热烈地吻他!”她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热情可鄙可笑。美的事物,人们总是欣赏的。
当她骑着小轱辘的自行车接近那鞋摊时,呈现在她眼里的荀师傅,便兼有着李向阳和《上甘岭》中张连长的神韵。那荀师傅脸上皮肤因为长久露天作业,近乎酱黑色,但轮廓线极刚劲,眉毛浓黑,印堂宽阔,眼睛极其有神,鼻子高矮适中,人中长而明确,嘴唇厚实,下巴上还有个浅浅的窝儿。满街有多少明眸皓齿、衣衫华丽的俊俏男子,可谁注意到这后门桥一隅的鞋摊主人,远比他们都更富有阳刚的魅力呢?冯婉姝从荀师傅身上,认出了荀磊那之所以使她一见倾心的素质——别看荀磊细皮白肉,宛如出生在另一种家庭的翩翩少年,他那结实的骨架,那眉宇间透出的自尊感,那下颚和下巴线条体现出的阳刚之气,分明都来自他父亲的遗传基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