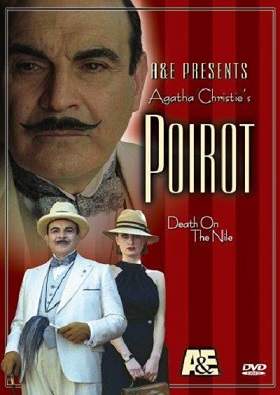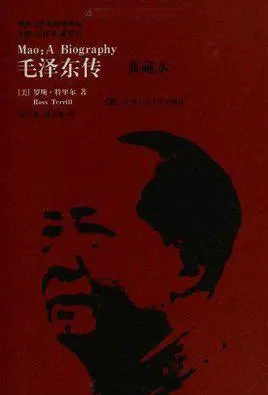26
钟鼓楼下的“老人俱乐部”。
一过下午三点,照射到鼓楼东墙根的阳光,便显得格外宝贵,因为至多还有半个来小时,这冬日的阳光便不再具有暖意了。
在鼓楼东墙根下“负暄”(晒太阳。)的老人们,一到这时辰,心情便不免沉郁起来。他们留恋带有暖意的阳光,不那么愿意,甚或很不愿意回到那属于晚辈统治的家里。即便在家里得到尊重和孝敬的老人,一想到又要同谈得投机、玩得默契的友伴分手,心里也怅怅的。
胡爷爷自然是最怕“老爷儿”(“老爷儿”,即太阳。)偏西的一位,因为“老爷儿”一偏西,便是“老人会”的散场,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之后,见到的将是儿子那张冷漠的脸,儿媳妇那对白果一般的眼球,以及在饭桌上的这类遭遇:孙子将一块肉挟起来,对他说:“爷爷,给!”而儿媳妇将那块肉接过去,喂进孙子口中,假笑着说:“爷爷好吃素,爷爷要你吃!”他呢,便连自己挟一块肉吃的勇气也没了......
胡爷爷同海老太太坐在一起,犹如小孩子嘴里含着一块几乎化成了薄片儿的糖果,舍不得让它消失一般,你一言我一语地竟相咂摸着这钟鼓楼边的往事,仿佛在这样一种炽烈的怀旧中,他们便能够让时间停住似的。
咂摸得最久,并且百提不厌的,自然是那关于一百多年前的“豆汁姑娘”的传说。论起来,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还是那传说中有关人物亲友的后裔呢。
胡爷爷的祖上,原是银锭桥畔那经营豆汁铺的老夫妇的近邻,老夫妇的独生女儿被恶贝子抢走的情景,胡爷爷祖上是亲见的,因此多年来讲起这段事,胡爷爷总用着权威的口吻。据胡爷爷说,那贝子自从被神秘地剜去双目后,惧怕连性命也失去,便放还了那被抢的姑娘。
姑娘的父母,后来果然给她招进了一名白衣女婿,是个瓦工。庚子年间,那年老的夫妇都已去世,这对夫妇连同他们的五个子女,都成了“义和团”的团民。每当有人说那昔日被抢过的妇人,入“义和团”后当了“红灯照”时,胡爷爷总要予以纠正:“不是红灯照,是蓝灯照。我爷爷当年跟他家熟得不能再熟,他家的豆汁我家随便喝,我家的芸豆窝头蒸得好,他家也随便拿;所以究竟是怎么个情景儿,得听我爷爷的——我爷爷说,义和团的女团民,只有那年轻没出阁的,才叫红灯照,结了婚的妇人就叫蓝灯照,还有寡妇们,叫青灯照。“ 后来呢?
据胡爷爷说,“义和团”失败后,那瓦工被捕去杀了头,英勇牺牲了,那妇人便带着子女逃往了外地。究竟逃到了哪儿?他就说不清了,因为他爷爷没告诉他。不过,至今胡爷爷仍能到银锭桥畔,指认当年那家豆汁铺和他家祖上居室的位置——自然早已成为了别姓的住屋。
海老太太呢,却是与那传说中的反面角色有亲缘关系。据说那恶贝子的一个庶出的妹妹,便是海老太太的姥姥。这样论起来,那被义士剜去双目的贝子,海老太太还该叫他舅姥爷呢。这种关系倒并未使海老太太在参与讲述那传说时有什么羞愧之感。因为据她说,那舅姥爷岂止是欺压府外的良民,就是府内,他也不仅是虐待奴婢,对海老太太的姥姥——他庶出的妹子,也是想骂就骂,说打就打的。因此,每当讲到她那舅姥爷在那个月黑夜里,门窗未动而双目被剜的情节时,她甚至比胡爷爷等人更觉解气,还每每要发一通“恶有恶报”的议论。
再说,与海老太太有亲缘关系的满清贵族及其后裔还很多,有的支持过辛亥革命,有的解放后成为政协委员,还有那论起来得叫她舅妈、表婶的,人家都成了共产党员了。因此,海老太太的亲戚关系里是既有坏蛋也有好人——这也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的状况,不足为怪的。人们自然常向海老太太打听她那舅姥爷的下场,她总是凿凿有据地说:“出了那档子事没多久,他就得疯病死了。临死的时候,他直嚷:”烫!烫!“问他:”炕烫,火盆烫?“他说:”豆汁烫!豆汁烫!“敢情他总觉得有人端着热豆汁往他身上泼......”对这类描述,人们自然只是姑妄听之。
那传说中笼罩着神秘色彩的侠义少年,他究竟从何方而来?又往何方而去?他何以能够不动门窗而潜入恶贝子寝室,从容地将其双目剜去?这些问题,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便只能同大家一样,凭着想象去猜测了——他们都失去了权威性。但几种传说的“版本”中,都有这个细节:在恶贝子双眼被剜的那天傍晚,那骑马的美少年,曾光顾过鼓楼大街上的“北豫丰”烟庄。“北豫丰”烟庄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
这个问题,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以前就争鸣过,这天不知怎么搞的,聊着聊着,他俩又抬起杠来。
海老太太说:“那”北豫丰“烟庄,就在如今”炊事用具供应部“那儿,门脸正对着烟袋斜街。买妥烟料的主儿,一迈出“北豫丰”的门坎,抬头就能望见烟袋斜街把口的“双盛泰”烟袋铺,那门口挂着好大的烟袋幌子——您忘啦?足有四、五尺长,底下坠着红布......“
胡爷爷说:“那咋不记得?幌子上还箍着铜箍儿,小风过来不带晃摇的......可”北豫丰“蒂根就不在这鼓楼南大街上,它是在鼓楼东大街,如今”民康回民小吃部“斜对过......瞧您那点子记性!”
海老太太便扬起嗓子说:“我记性差?凡我经过的事儿,拾起来全能全枝全叶的......我倒试试您吧——当年烟袋斜街里的”忠和当“,门脸在哪块儿?”
胡爷爷脖子都直了:“街中间,庙对门,门脸朝北——我能忘了它?早年可没少跟它打交道!“他忽然回忆起,民国十三年夏天,紫禁城里建福官遭回禄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考问海老太太:“您记性好,您该记得早先故宫里头着大火的事儿吧?......”
海老太太不等他问完便用劲地说:“敢情(”敢情“与别的词语构成句子时,相等于”原来是“、”真叫是“、”可不是“......一类意思,单用时是一种表示充分肯定的语气词。)!那一年春上我出的阁,那场大火,记得是阴历五月十四晚半晌着起来的。第二天我跟我们掌柜的逛”荷花市场“,一进大堤,满耳朵听见的全是那大火的事......”
海老太太一提起“荷花市场”,胡爷爷便把那建福宫大火的事撂一边了。“荷花市场”!这四个字勾起了他多少既酸辛又甜蜜的回忆。他不由得又同海老太太一问一答地议论起当年的“荷花市场”来。海老太太在这话题中,同样也既回味到青春的乐趣,又反刍出人生的苦涩。
所谓“荷花市场”,是民国初年到三十年代末那二十几年里,在这钟鼓楼西南的什刹海出现的一种临时市场,每年从阴历五月初五开市,至阴历七月十五收摊。当时的什刹海前海遍植荷花,海西是一条颇宽的土堤,堤东是一片稻田,“荷花市场”的中心区便在这土堤之上,所谓“东边荷花西边稻,棚架半在水中泡”——市场的商棚,大都用杉篙木板扎搭,一半搭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中,上面或罩以席顶,或铺着可展可收的苇帘,当然也有因陋就简——覆以旧布缝缀的伞篷的。
胡爷爷当年也曾一度在著名的“德利兴”棚铺中学徒,到那“荷花市场”中给人搭过棚架;而海老太太的掌柜的,得意时却是“荷花市场”中携眷游逛的人物,潦倒以后,一度又在“荷花市场”中摆摊给人测字相面......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回忆了一番“荷花市场”的盛时景象......那“八宝莲子粥”,用糯米和上好粳米煮成,煮得腻笃笃的,盛在小碗里,中间混着鲜莲子、鲜藕、鲜鸡头米,上面再堆上雪花棉白糖、青丝红丝......小碗又搁在冰桶里,用那从窖中取出的天然冰块偎着,取出来的时候,凉飕飕的,称作“冰盏儿”,你说该有多么爽口!
还有“苏造肉火烧”,是拿花生油、鲜鸡蛋和细罗面烤成的,皮儿一层又一层,层层不乱,薄薄的皮儿下,露出里头的萝卜丝瘦肉末馅儿,一两算你两个,真勾人的“哈喇子”(口涎。)!......吃的如是丰富多采,那些耍货(玩具。)更让人眼花缭乱!上头泥塑、下头猪鬃扎脚的“鬃人儿”,搁在铜盘子里,一敲盘边,它们就连转带舞,别提有多么逗哏;还有各式各样的风筝,“黑锅底”、“沙燕”、“蜻蜒”、“蜈蚣”、“孙悟空”、“美人”......都不稀奇,最有趣的是“蝴蝶送饭”——它附在大风筝之上,大风筝放起老高以后,把它挂在风筝线上,能眼见着自动升上去,上去老高了,拴着线香头的小爆竹一响,绷线震断,它那翅膀便能一合,“嗤溜”滑将下来——你说巧也不巧?......
他们又回忆到当年“荷花市场”上售卖的几种灯:“荷花灯”,并不真用荷花制作,而是用高粱秸破蔑,圈成一个小西瓜大的圆圈,上面贴一圈用粉纸剪好压凹的花瓣,下面再贴一圈用绿纸剪成的六七寸长的流苏,中间点上一支小蜡烛,孩子们入夜后用一根小棍挑着,边玩边唱:“荷花灯,荷花灯,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他们小时都点过,也都扔过的;“荷叶灯”,用真荷叶一张,当中插蜡烛,点上举过头玩;“河灯”,用一小块厚厚的圆木头,周围糊一圈纸,中间放一个泥捏的小油灯盏,点上后,搁进什刹海,任其漂流;最令人难忘的是“蒿子灯”,拔一棵青蒿,把许多点燃的线香头一一系在青蒿的枝叶间,手举根部,摇来摇去,在昔日昏暗的庭院里、胡同中,点点红星晃动着,袅袅香烟飘散着,引出正当青春年少的他们多少非分的幻想!......
“啊,二位说时,不就是当年”雨来散“里的玩意儿吗?”一位一手提着鸟笼、一手揉着核桃、身板比他们硬朗的主儿,听他俩聊得起劲,凑过来搭话。
“雨来散”?对!当年的“荷花市场”逢上下雨,自然散摊,所以确有“雨来散”的俗称。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一听见“雨来散”这仨字儿,心中顿时充满了无限的怅惘。“荷花市场”逢雨便散,人生呢?
缘分呢?......唉唉,往事真不堪回首!
那过来插话的,便是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他比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要小十来岁,对于他来说,“荷花市场”实在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
他记得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在轿行里等着当随行的执事——他们丐帮中的小伙子常去干这个,当然轮不到他们打伞、打扇,只能是在执事行列的尾部打打旗。旗有几种:青龙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他受雇时只能是打那绣着龟身蛇尾的“玄武神”的玄武旗,走在最后。那年夏天他天天去轿行等候,天天落空,也不知怎么搞的,那年夏天阔主儿们都不娶媳妇!于是他头一回跟着父辈去“荷花市场”搞“硬乞”。他把一个大铁钩子钩迸锁骨,拖着个坠铁球的铁链,从堤南走到堤北,竟然只有人指点观看,而并无人施舍一枚铜板!从那以后他就恨上了什刹海,每从湖边过,他总忍不住要往湖里啐一口痰!
现在他听见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坐在那儿你一句我一句地赞美“荷花市场”,心中好不以为然,点出那“荷花市场”不过是“雨来散”之后,他又把右掌心的核桃揉得哗啦哗啦乱响,大声地说:“当年那什刹海有什么好的!别看海心里有那么点荷花装样子,海边上堆着多大一圈垃圾杂物?那住海边的人家,有的还见天地往里倒屎尿盆子,那股子味儿!打那里头窜出来的蝇子蚊子就别提有多少了!你们二位岁数都比我大,该比我早看见过”鼓楼冒烟儿“?......”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一听,一齐点头呼应:“可不是,有一回这鼓楼顶上蹿起一丈多高的”黑烟“,街面上的人都当是里头着火了,嚷的嚷,跑的跑......”“是有那么档子事儿!后来不是把那消防队都叫来了吗?
消防队的人爬上去一细看,咳,闹了半天,哪是什么“黑烟”,是成团的蚊子搅成了那么个“通天柱”!“
“瞧,那时候咱们这块儿有多埋汰(脏、丑。)!说那路面是”无风香炉灰,有雨墨盒子“,真是一点也不假!”卢胜七突然焕发出一种忆苦思甜的热情,指着斜对面街上的店铺说,“要是当年,甭说别的字型大小了,就那”泰麟菜蔬商店“,那”和成楼生熟肉铺“,咱们敢进去吗?”
海老太太接上去说:“敢情!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那物价就光见涨不见落!我还记得日本人来了以后印的那票子,一边有个孔夫子像,一边有条龙,瞅着就跟豆纸(手纸。)似的,”毛“得厉害!......”胡爷爷抢着说:“可不!那是”华北准备银行“的票子,外号”小被窝“嘛。当年大伙不都这么说吗:“孔子拜天坛,十块当一元!”......再后来那国民党的“法币”,就更不能提了,日本投降以后,“光复”的头一年,一百块“法币”还能买俩鸡子儿,过了没两年,一百块“法币”合算只能买上一个煤球儿!那是些什么日子啊!......“
说到这儿,恰好一辆长车身的8路公共汽车从他们面前的街道上驶过,海老太太便见景生情地接着进行新旧对比:“那时候打咱们这块儿出门有多难!都到民国多少年了,这街上才有了当当车(当当(音dang一声)车:当年北京人对有轨电车的称呼。),那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踩铃儿,当当地响,真吵人!......”胡爷爷跟上去说:“可不,我记得司机踩出的那调调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