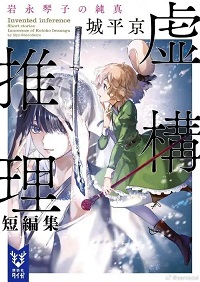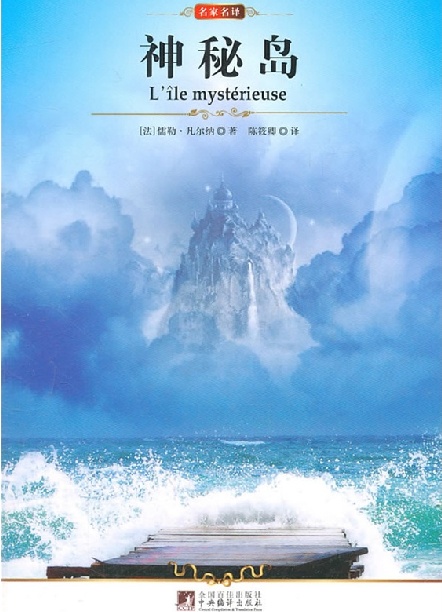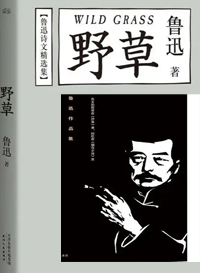正值孙文众人奔返于香港、广州两地,重阳起义的筹备正如火如荼之际,北洋舰队覆灭的噩耗传至京师,士大夫阶层无不震动。
国内舆论对此次战败分作两种极端,扼腕、愤慨自然有,然而暗自庆幸者,亦不在少数。
孙文是个典型的现有制度反对派,他总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孙某自孩童起,便常闻太平天国的英雄事迹,至今,仍视天王为偶像,立志成为第二洪秀全。”
太平天国可称得上是清统治两百余年中的头号反叛集团。孙文这席话,可证明他从小骨子里就流淌着革命的血液。与陆皓东结伴损坏村头北帝庙佛像一事,更体现了他那胆大妄为的性子。
甲午战争前夕,孙文之所以苦苦谏言李鸿章,是由于他对体制内改革还抱有期望。然而冰冷的现实让他不得不与陆皓东踏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相对于上书宰相却受挫的孙文,康有为的做法更为直截了当——上书当今圣上。
康有为带头发起“公车上书”,却因“庶民不得上书”的原因,被拒紫禁城门外。
世人只知“公车上书”,怎知康有为早在七年前便已只身尝试上书朝廷。“公车上书”且重重受阻,遑论七年前的康有为仅是区区举人之身,自然是被当作疯子般打将了出去。
位及进士后,康有为发起过三回上书,但均受官吏百般阻挠,最终石沉大海。
第四回上书有幸敲开金銮殿,却因“妄议议会设立,有污圣听”的理由,被内阁给沉了。
经受多次挫折,康有为对朝局心灰意懒,转头致力《万国公报》的创立,并委任梁启超、麦孟华等一干门人为主笔。首刊于同年8月17日[指1895年。]在北京出版,并首先分发给王公重臣。此举的目的在康有为所著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得很清楚:变法须始于京师,始于王公大臣。
西太后慈禧,掌控清廷最高权力的女人。
“东”与“西”,照理说,应该是“东”的地位更为尊贵。在日本,相扑选手的排名也是以“东”为大。
咸丰帝在位十一年(1850—1861年),皇后却未诞下子嗣,但好歹是正宫,咸丰驾崩后,皇太后之位自然非她莫属。然而,慈禧身为新帝同治的生母,母凭子贵,也不可能继续屈居为贵妃,于是便有了“东”“西”两宫太后的特例。
正宫东太后无心弄权,加之当今圣上并非自己生子,便将政务与权力一并托付于西太后,史称“西宫专政”。
同治未至弱冠便早早夭折,西太后只得扶持胞妹与醇亲王之幼子载湉继位,即光绪帝。光绪帝四岁继位,至甲午海战,已二十有三,却仍为西太后的政治傀儡。
康有为对这位年轻的君王寄予厚望,孜孜不倦地上书谏言。
广州暴乱的内幕,康有为早已了然于胸。两广总督极力隐瞒,甚至捏造出子虚乌有的闱姓大盗,但就算能瞒得过朝廷,瞒得过别省,广州本地人可不吃这一套。出生于广州南海县、大名鼎鼎的“南海先生”,更不可能被蒙在鼓里。
起义军里包括告密的朱淇与越洋而来的陈清,南海县人不在少数。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康有为对此番起义的轻蔑:“一帮乌合之众在广东小打小闹,能成何气候?”“可笑,军中竟无一举人。”
改革应自京师而起——这是康有为的信条。虽同乡众多,但康有为生性高傲,不愿结识市井之辈。唯一谈得上略有耳闻的也只有电报实习生陆皓东,另外就是在澳门与葡萄牙医生抢生意的孙逸仙了。
综上所述,康有为对广州起义做出了如下评价:竟无一人有功名者在列。乌合之众,妄图谋国,兴不起多大风浪。
康有为一手创办的日报《万国公报》顺利在北京出版。其实,上海早年便有与其同名的月刊了。这份刊物的原身为西方传教士出版的周刊《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为月刊,并更名为《万国公报》。
康有为明知撞名,却执意以此为名的理由,如今已不得而知了。或许是以为两地相隔千里,没那么多顾忌。亦或许“万国”二字,为当时随口即来的大众词汇。
但上海方面显然没他这样想得开,北京《万国公报》创刊不足三月,便遭到老牌《万国公报》的投诉,不得已更名为《中外纪闻》。发行此报的载体“强学会”也在康的领导下应运而生。
中国自唐起,各路节度使与地方长官便在国都长安设藩邸(出差办事处),方便实时掌握京都情报。此机构亦有个独特的称呼——邸报。
此后几经改朝换代,此机构仍然得以沿用。至清时,更名为“京报”,数十所“报房”遍布京师。康有为在“报房”中略有相识,得以让在京官员每日一早便阅读到自己的报纸。
《中外纪闻》在京城反响极大,每刊印刷数均在千份以上。究其原因,那年月的京报,说白了仅是官方辞令与要闻的公开栏,不涉及任何评论言语。而《中外纪闻》却能毫无顾忌地在报上议论朝廷所为。
部分不明真相的京官对这份“反常”的京报还抱着欢迎态度:“咦?这些日子京报改版了?加了个解说栏,倒比之前的有看头。”
而消息灵通的官吏则避之不及:“报房那头怎有胆子发布这样的文章?这是‘小臣’康有为创办的个人刊物……这事可悬,咱还是少看为妙,省得摊上干系。”
“小臣”一词,最近在朝野中愈发流行开来。即有“大臣”,相应,自然也得有“小臣”。这“小臣”可小觑不得,称得上“大臣”的官员有千万,但“小臣”一词为乙未年会试及第的康南海[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故而人称“康南海”。]的专称。
当时的朝廷中,西太后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光绪帝年幼时,太后摄政倒也罢了。但一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光绪帝年至十七,西太后明为隐退颐和园,还大手操办了亲政大典,实则却仍然大权在握,垂帘听政。甚至甲午惨败,朝局动荡,西太后仍稳坐第一把交椅。
于是乎,朝野中呼吁皇帝掌权的部分官员便被划为“帝党”,帝师翁同龢、文廷式首当其冲。甲午兵败,北洋统帅李鸿章遭翰林院三十五人联名上书弹劾,文廷式便为上书发起者。
严格来说,“翰林院”并非参政机构,而算是教育机构。成绩优秀的科举考生在正式入朝为官前会被派到这儿来实习,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翰林院编修”。说白了,他们就是一群只会纸上谈兵的政治雏儿。
“帝党”中最不缺的就是这类群体,这帮人的政治诉求也是单纯至极:西太后已年迈,中兴大清之重任最终还得落在“帝党”肩上。西太后麾下李鸿章一众踟蹰误国。皇上必须从翰林院中另择贤臣,匡扶社稷!
然而实际上,“后党”一称从未正式出现过,即便是“帝党”成员,也不敢公开叫嚣“后党”如何如何。毕竟两者实力太过悬殊,着实无法以“党”并称。
就这般朝局,怨不得康有为兵着险招。改革已刻不容缓,每耽搁一刻,便多一分亡国之虞。
这般想来,“保皇派”康有为与一意倒清的孙文,虽同为救国,所处立场却截然相反。
康有为将“强学会”会长一职托付给文廷式。文廷式身为“帝党”,有充分的理由和资格。若由康有为本人出头,难免惹上“变法派”的嫌疑,而“变法”与“改革”仅有一线之隔,动辄便是谋反大罪。
英吉利传教士李提摩太,为呼吁上海信教自由而来京城时,便一度奉劝康有为尽早远离京师这是非之地:“听说,大学士徐桐与御史褚成博等一干帝党正密谋镇压变法派。我建议康先生这阵子到上海避避风头,就说要去设立强学会上海分会。”
康有为接纳了这位洋人好友的忠告,于农历九月一日(10月18日)离京,此时距九九重阳,仅八日之隔。
李提摩太,英文名Timothy Richard,出生于英国南威尔斯,为新教传教士。日清战争进行正酣之时,李提摩太曾向朝廷重臣张之洞谏言富国强兵之策。
李提摩太的情报网可不容小觑,他率先察觉到京师的异动。康有为离京前不忘将自己的首席弟子梁启超,推荐给他作为秘书。初闻情报时,康有为半信半疑:“李先生是否过虑了?朝廷诸臣至今仍将小可蔑称为‘小臣’,如何会起镇压之意?”
“这可是康先生您妄自菲薄了。可知,您操办的《中外纪闻》已被视为洪水猛兽,被多数官邸拒之门外。他们这是在脱干系呀。一纸报刊尚且如此,创办人岂能全身而退?多说无益,您明日便动身吧。”
《中外纪闻》是混在官方京报中传递到政府要员手中的。既为免费刊物,按理说,接受方亦没有理由拒绝。但《中外纪闻》内容敏感,早在朝野间流传开了。接受方若仍照单全收,他日事发不免会受牵连。考虑到前程与身家性命,也不能来者不拒。
西太后虽隐居颐和园,但满朝文武却仍以她马首是瞻。西太后对朝局动态更是了如指掌。上至大臣,下至宦官,甚至是外国使节,俨然将颐和园当作紫禁城。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光绪帝大婚。皇后为副都统桂祥之女,亦就是西太后的侄女。
然而,十九岁的光绪早有两名意中人,侍郎长叙之女的瑾、珍两姐妹。西太后也不欲棒打鸳鸯:“皇上既中意那俩女娃,便一并纳作侧室就是了。”
西太后金口玉言,姐妹俩当即由“嫔”升格为“妃”。但问题亦接踵而至,光绪帝一颗心系在瑾、珍两姐妹身上,反倒将正宫皇后晾在一旁。这让其舅妈西太后情何以堪?对此,西太后却貌似不以为然道:“男女情事,本非外人可干预。且静观其变,再另作打算吧。”
朝野上下心如明镜,依西太后的性格与权柄,“静观”之后是何等雷霆手段,可想而知。
康有为坚信光绪帝定会采纳自己的变法之策,怎奈只要有西太后一天,光绪帝便无法挣脱其桎梏。
见天子受小臣唆使,热衷于政治改革,西太后不敢苟同。誓死捍卫祖制的守旧派大臣倒深得她的欢心。照这势头,西太后迟早会给予守旧派兵权。届时,便是帝党覆灭之日。
守旧派早就疑心康有为勾结海外势力,企图激起变法运动,碰巧李提摩太在这节骨眼儿进京,无疑又加重了守旧派的疑念。
康有为采纳友人忠告,在上海避了数日,随之便转战南京。秉持“变法始于高层”的宗旨,他试图说服张之洞。
两江总督刘坤一身负钦差,远赴山海关,张之洞只是暂代其职。
当时朝野之中,张之洞算得上是少数有资格与李鸿章一较长短的权臣之一,但世人通常认为其个人魅力与政治手腕远不及后者万分之一。他自己亦深知这点,为青史留名,便全身心投入收买人心。
看了康有为带来的《中外纪闻》后,张之洞对康有为要出版周刊《强学报》表示支持,并承诺出资赞助上海强学会。于是乎,上海强学会便赶鸭子上架般开张了,创始成员仅有十六人。
康有为不忘拜访上海名士黄遵宪。后者对康有为的来访喜出望外:“阁下便是南海康先生吗?您的大作让黄某人受益匪浅,只叹无缘相见。”
“晚生亦拜读黄大师著作久矣。您对日本的了解,真可谓是我大清第一人!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康有为也热忱地看着面前这位长自己十岁的前辈。他们同为广东出身,黄遵宪的官话中混杂着一丝地方音,表明其客家身份。
黄遵宪作为“新兴文学”巨匠,在上海文化界颇具地位。另外,他曾从事外交工作,对海外的认知,在当时的清国数一数二。最重要的,他是变法派的先驱者之一。
黄遵宪二十九岁中举,同年便得了个驻日公使参赞(文员)的差使。但日本那时正闹“西乡隆盛之乱”,其拒绝初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来日。一直耽搁到1877年(光绪三年,明治十年)秋,使节一行才被允许赴日。
驻日四年里,外交公务之余,黄遵宪热衷于伊藤博文、榎本武扬、大山岩、森槐南、冈千仞、岩谷一六等诸多日本政界、文界名流探讨汉文。了解到日本本土教育的普及,源自民众对假名的兴趣,黄遵宪认为祖国的教育亦可以此鉴,自此便开始钻研日本历史文化,撰写《日本国志》四十卷。
康有为口中的“著作”,指的便是这部《日本国志》。而黄遵宪所言“大作”,乃是上文曾提过的《新学伪经考》。
既有同乡之谊,又互相仰慕对方的作品,怨不得两人会这般一见如故。
黄遵宪驻日四年期满,被提拔为旧金山总领事,其后被指派到英吉利、新加坡等地总领外交事务。直到在新加坡感染上疟疾,才得以告病还乡。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张之洞初见时的不羁态度。文献中有言:昂首阔胸,单足置于膝上,摇头摆脑,声震屋瓦。
文人一旦到达某种境界,处世待人难免孤傲,黄遵宪亦不可免俗。此后,张之洞每当出台一项为政举措,黄遵宪总少不了向旁人吹嘘:“张香帅[张之洞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所以叫张香帅。]纳我之建议尔。”
显然,张总督曾怠慢了这位学者。黄遵宪在后辈康有为面前表现出的谦逊,亦足可以体现出他那傲上媚下的性子。
于是乎,在上海“强学会”的运营下,北京《中外纪闻》的姊妹报纸——《强学报》不久后便在上海出刊。
另外,这个新兴会党为了摆脱“帝党”嫌疑,先后吸纳了张之洞、刘坤一、孙家鼐、徐世昌、翁同龢、袁世凯等一众朝廷要员入会。唯独李鸿章,捐赠两千元申请入会,却因赴日媾和一事被拒之门外,部分激进的会员甚至做出以下言论:“卖国之财,虽死不受!”
谁知一石激起千层浪,仅因这一句话,《中外纪闻》便遭在朝“保守派”官员一律抵制。张之洞也随之中断了对强学会的经济援助,理由很是牵强:首先,他对康有为那套孔子改制的思想尚心存疑虑;再者,《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标注日期,此举有不尊大清正朔的嫌疑。
另流传一种说法,康有为的那套“孔子改制”思想,仅是披着“尊孔守制”的外衣,试图“借古改今”的变法派理论。
也怪康有为所托非人,张之洞就是一株官场上的墙头草。
西太后的生子同治帝早夭,她做主,让醇亲王之子载湉过继到咸丰帝(慈禧亡夫,同治生父)名下并继位,是为光绪帝。时任刑部主事的吴可读不惜“尸谏”(上书后自尽)西太后,抨击此举“有违礼教护持,开朝以来未有先例”。光绪继位亦无不可,只不过前提是过继为同治帝子嗣,而非咸丰帝。
一言以蔽之,西太后的考量为皇太后有权摄政。若遵循礼教,将光绪过继为咸丰子嗣,西太后便不再是皇太后,而为“太皇太后”,到那时,她便只能深居后宫,再无参政资格。
临此紧要关口,拉了西太后,救西太后于苦境的,便是这张之洞了。他出面强行扭曲吴可读的正论,让西太后在立嗣之争上赢得上风。如此说来,满人入关至今二百六十余年,自太祖努尔哈赤以来坚守的“父死子继”祖制,倒是被他张之洞给打破了。
此后,张之洞的官位亦是扶摇直上。这归功于他对西太后的奉迎。
对上海强学会的态度急转直下,多半也是因为他先人一步地嗅到了西太后对变法派(自称维新派)的敌视。
不得不承认,这株墙头草的政治嗅觉确实敏锐非凡。上海《强学报》创刊于1896年1月12日,亦为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而3月29日,御史杨崇伊便以“聚众诽谤朝廷”为由,弹劾帝党之首文廷式。
文廷式虽仅为一介侍读学士,但其竟能在甲午战败与马关媾和后,号召三十五名翰林院学士联名弹劾李鸿章,足以见其威望。另外,他曾担任皇帝宠妃——珍、瑾姊妹二人的教书先生。有这层关系,想不被西太后怨恨都难。
西太后采纳了杨崇伊的弹劾,将文廷式发配至江西祖籍,单是发配还则罢了,不出几年,慈禧又下令两江总督将此人问罪处斩。好在基层官员没有吃透慈禧的意思,对这个流放官员爱答不理。而文廷式早已远赴日本,还与内藤湖南(日本学者)成为莫逆之交。
《中外纪闻》与《强学报》二报自然难免其咎,双双停刊。后来,黄遵宪利用被勒令解散的强学会余出的一千两百余元的资金,又自掏腰包赞助了千元,在上海另起炉灶,创立旬刊《时务报》[《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8月9日,是戊戌维新时期宣传维新思想最有力、影响最广的刊物。]。
至1896年,变法、保守两派之争愈发不可收拾。变法派自称“维新派”,蔑称对手为“顽固派”。
视角再次转回兴中会三人。与此同时,亡命日本的孙文动身远赴下一个战场——他的第二故乡——夏威夷。郑士良正伺机再度潜回广东。削了发辫的陈少白则留守日本,致力于巩固第二根据地。
“少白,我让你独自留守日本,是希望你能广结本地好友。不仅限唐人,日本人的人脉亦是重中之重。对了,我在夏威夷交际颇广,其中有一位名为菅原传的日籍好友,与你的性子甚是相近。他前段日子已回国,我们明日便去拜访他。”
“既是逸仙看中的人,定然错不了。我不善交际,恐怕还真得麻烦你在动身前帮我与这菅原兄弟做一做引见。”
于是,在孙文的牵线下,陈少白与菅原传相识。孙文远赴夏威夷后,这菅原传在拓展人脉方面给了陈少白极大的帮助,其中便有辛亥革命的大功臣——“大革命家”宫崎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