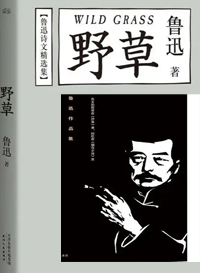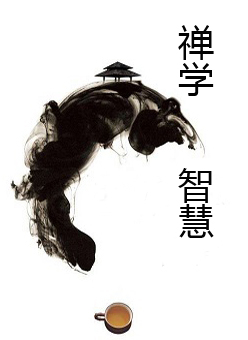周恩来躲不开,他是总理,而且必须配合毛泽东搞工作,为大局为团结,他只能作检讨。党内公认总理的组织观念最强,从不犯自由主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听到过他背后议论哪位同志的缺点,总是讲这个人有什么什么长处,那个人如何如何好,有什么什么贡献。对于缺点错误,他坚持当面提或公开讲。这次为了“反冒进”而挨批评的事,他也一样不议论不提别人有什么“错误”,只谈自己的“错误”,谈自己的担心和苦恼,找认识上的差距,设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
后来我们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毛泽东是想让总理自己动手,以便真正“提高”认识。
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检查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夹,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悯;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砧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
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定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住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起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俏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无奈在其中呵!
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痛的痛哭。
这一章结束时,我想附带再讲几句。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己。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
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
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
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一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陶大哭。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 七、五次发脾气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作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伯”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10点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