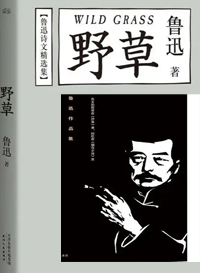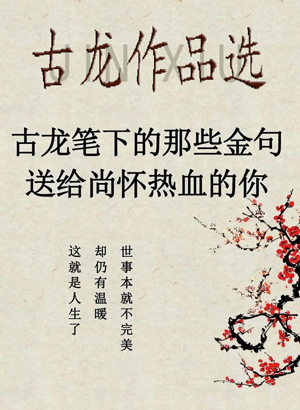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周恩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身的体会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