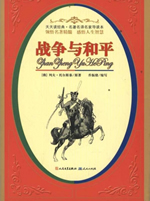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
这老子尝为众生做什么?
——王安石
御街行——秋日怀旧
纷纷坠叶飘香砌 ,夜寂静、寒声碎 。真珠帘卷玉楼空 ,天淡银河垂地 。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 ,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敧 ,谙尽孤眠滋味 。都来此事 ,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偎红倚绿,江湖酬唱,人情所难免。任何一个经历过得而复失,或思而难得的伤情痛楚的人,于无处话凄凉且无以舒怀寄托时,藉诗词说出自己未能抒发之情总是一种不错的方式,总好过于狂醉深宵。只是红巾翠袖,搵英雄泪,常是催得愁肠更断。诗词,兴起而发,蕴籍于委婉之中,常意在可说和不可说之间,如禅宗短偈,只渡可悟之人。
但当一个男人坐困于此番剪不断理还乱的愁城,最好翻起另一页,读读写下这首《御街行》的范仲淹于戍守西北时写的另一首词,或许能幡然醒悟,如禅师对自己当头棒喝一般,人生苦短,勿忝尔生,勇猛精进,信心必起:
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侠骨兼具柔情,内省以起激荡。苏轼的两首《江城子》亦有此番气象,一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二歌“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亦如Kurt Cobain可以在狂躁急促的鼓声中高歌“smell like teen spirit”,也曾低吟“something in the way,嗯嗯嗯……”。
公元 1044 年夏天,《岳阳楼记》中写的庆历四年,离开中枢相位改任河东陕西四路宣抚使的范仲淹于赴任途中,特意到河南南阳,拜访已退休多年的前宰相吕夷简。
此时仲淹与富弼,韩琦等人发动的庆历新政已如昙花一现般草草收场。见面时,夷简问仲淹:“你为何要去西部呢?” 仲淹答道:“因为要经营西北边事。”夷简笑着反问,“要经营西北边事,在朝中不是更好,何必去西部呢?万事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吧。”
我们难以知晓仲淹听到这位执政近二十年,政敌和提携者均有之的老上司在临终前不久和他说的这番话后是何感受,只是从他两年后写下的《岳阳楼记》可以读出,他心怀鸿鹏之志,即使面对冷酷的现实困境,依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而在二十多年后推动熙宁变法的王安石亦有类似故事。公元 1084 年夏天,从黄州改任常州的苏轼于赴任途中,去探望辞去相位后闲居于金陵的王安石。虽然过去作为晚辈苏轼曾激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新政,但当日两人见面时,仍是相谈甚欢。王安石是和范仲淹全然不同的性格,王氏一生尊崇孟子,于是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即使谤侮加身,理想不达,也在所不辞,以至于行事执拗不已。两人会面两年后,王安石病逝,才气纵横的但身为作为新法反对者的苏东坡执笔官方悼文,他赞扬王安石道:“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
中国历史上,不乏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商鞅借秦孝公之力发动变法,虽然后来商鞅悲剧般的身死,却为百年后秦国一统天下打下坚实的军政基础。而到了中国帝制的黄昏,戊戌变法昙花一现,惨烈地以六君子喋血宣外菜市口而告终。当谭复生引颈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之时,拥挤的看客,或许已经挡住了他寻望不远处的北半截胡同里的浏阳会馆的视线。
皓首穷经的中国读书人不会不懂《周易》里革卦所提示的“变”,也不会不懂诗经中吟唱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他们自小在学塾里读的第一段话或许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新民”二字,必常使得抱有齐天下理想的他们念兹在兹。可是,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的框架内,“变”总是一个动人却令人生畏的字眼。不像当年奥巴马竞选时提出“change!”的简单口号令选民兴奋,一呼百应。
在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相望于三十年间。这两次改革,虽然只是对于各个不足之处的微调,而不涉及根本,但是在改革前后士大夫们所展现出的精神,风骨是帝制里的中国历史所空前绝后的。他们对儒家的理想带着一种宗教般的真挚与狂热,“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有机会便起而行之的立身准则。
鼎故革新的理想终为现实所困顿,范王二人也许会痛惜自己未竟的事业,满襟余恨。范仲淹或会想起他在庆历新政前对仁宗说的:“我国家革五代之乱, 富有四海, 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疆场不靖,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王安石或许也会想起改革前他在《百年无事札子》中劝谏神宗的话:“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千年过后,借着画家李公麟在王安石罢相后闲居金陵时为他画的那副写实风格的半身像,我们可以看到当日安石身形矍铄,目光坚毅。只是那时,他的无奈心境,或许有如南宋碧山词所说的“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
你我听说的唐朝(618 -907 年)和宋朝(960 -1279 年)或许是从小学早读课中高声朗诵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或“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的诗句开始的。唐宋常常是被误解为连读的两个类似的朝代,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差异巨大。
历史进程如同江河的源头一般,开始时总是局限于狭小的区域,但是随着水道恣意纵横,不分畛域的前行,最终冲击成一片广大的三角洲。中国历史从秦统一中国后建立大一统的中央王权开始,历经一千多年,直到隋代和唐宋,才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平等且合理的统一政权下的文官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如选官制度,中央各部的分工和士大夫为主的政府管理等等都一直延续到清代,乃至于于细微处影响着今日。
特别是到了宋代,在皇帝的有意支持下,平民拥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科举进入文官体系,而士大夫阶层对于时政也有了更大的话语空间。于宋开国时,中国的帝制便逐步走出了贵族式的政体,平民智识分子开始走上政治前台。虽然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诞生更为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来启蒙民智,但是至少当时经济发展,思想活跃,社会有了合理的秩序。而如欧阳修,张载,苏轼,朱熹般的文学家,思想家灿若星河,所以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说:“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也就是这样宽松的环境里,宋代士大夫在面对时局的危机时,由于自发的担当而推动了宋代的两次改革,首次便是宋代立国七十余年后,即 1043 年前后的庆历新政。
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威权的衰微,造成唐中期开始的藩镇割据和唐亡后的五代十国的数十年的分裂。宋朝无奈地承袭了五代十国后留下的外部军事压力,即北方契丹和后来的西部夏国的威胁,特别是在宋中期仁宗在位期间,战事迭起,军政不张,加之财政入不敷出的巨大压力,使得当时的士大夫们开始了对于整个制度的反省,于是在庆历年间催生了庆历新政。
但庆历新政如昙花一现般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便以新政各主导要员辞职,新法大多被废而告终,这场新政的成果对弊端的改变影响甚微。但是,当我们今天回看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的庆历诸君子于国家危难之际的的言行,激论天下事的勇气,总会有一番感动。庆历新政的影响,其实更多的是从精神上撼动其后来者,而如此士大夫起身救世的豪情,于二十余年后继续催生了宋神宗与王安石发动的熙宁变法。
范仲淹和王安石的行事风格大相径庭,仲淹清楚地知道局势不可挽回时,早早萌生退意,明哲保身。而安石却执拗而为,即使罢免反对派贯穿了整个改革过程,他甚至和自己的兄弟,旧知因为政见不同而反目,也在所不惜。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其性格所导致的实际运作方式是关乎成败的细节,可是我们仍要思考的一点是,改革当日的主政者不管正反方,均是一时之选,但最终会失败?到底为什么?所提的政改的目的均是朝野认同的目标,最终在实行的过程中,为什么依然饱受阻碍,难见成效?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一句漂亮而空洞的口号,而是以殉道者般的激情而起而为之。如同九百多年后,腾冲国殇墓园里,“碧血千秋”石碑后小团坡上,深埋于土中的那些永远不会老去的年轻士兵一样,历史人物之于我们,不应视如寺庙里的偶像那般,信众的香火烟熏得这些偶像失却本来面目。岂不知,偶像存世的当日,亦是凡人,凡人应有的所有,他们亦曾有之。如罗大佑唱的“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庆历年间,距今大约 980 年,故事的主角里,我们藉由诗词古文而熟悉的欧阳修 36 岁,即使较为年长的范仲淹也才 54 岁,当时的皇帝宋仁宗 33 岁,而另两位重臣韩琦和富弼也是和欧阳修大致同年。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这样的年纪里的可能的思维,而不是如今日在画中看到的那种总是身着官服,留着长须的呆板模样。历史人物,并不是戏台上妆容相似的那些帝王将相。他们和此刻的我们一样,都曾经那样地活在那时的当下。如果简单地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观点,去武断地对过去时代的人们的言行进行判断是不公平的。我们对于过去的人,应该抱有一种批判性的同情和介入。我不赞同黄仁宇先生所认为的,历史人物对过往的愆尤失误是一种无奈,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抱着同情的眼光去理解他们当时面对的现实困境,便会发现此种艰难不易克服。我觉得这样的观点是在为当事人的不作为来制造理由。当时可以做,为什么不做?那么时代如何可以前进?正如庆历中的宋仁宗就是可为而不为。
今日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就事件的表面看,而应深入去探究这些人事与他所处的当日情境下方能尽量看清当日真实模样。但历史毕竟是过去的事情了,因此对待历史,就如同数学中极限的概念一般,我们或许可以无限接近,但是,夕阳已落,黄昏将尽,轻舟万重,不复重来。
当我们尝试要进入庆历的世界时,让我们先把眼光放更辽远一些,辽远如十多年后夜间忽然忆起,夜自修前,远远地传来操场外传来的福南堂剧院的乐声一般,清澈透亮,渐行渐远,绵延徐逝。让我们先看看庆历之前的一些故事,才能明白,庆历新政因何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