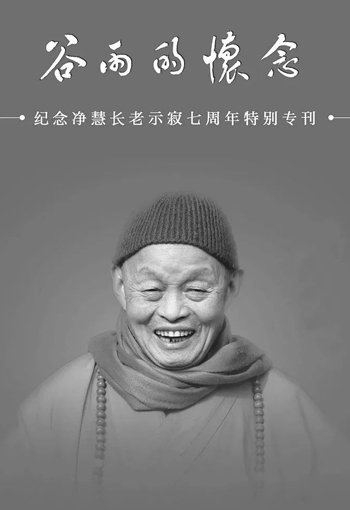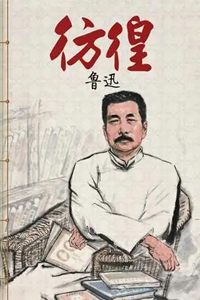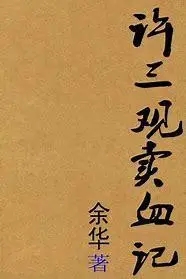晚唐文人的猥琐,从当日浮艳虚薄,淫冶曲歌的诗句中就可见一般。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 838 年,距唐亡只有 60 余年。裴思谦靠奉承宦官仇士良而状元及第后,周游狎妓,在夜宿平康里贪欢鱼水后,写下“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染桂枝香”一诗而气盛一时。而这样的情形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仁宗年间,即便柳永曾写出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等不逊于豪放词风的壮士悲秋,但也只是因为他落第后喝多的那夜,兴起后发牢骚般地写道,“青春都一饷,且把功名,换了浅酌低唱”便让仁宗给予这位于风月场中声名赫赫的柳七“且去填词”的绝弃,于是柳永直至终老也难觅功名,潦倒一生。
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字,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气质。如果一个时代还疯狂的在为淫词艳曲而叫好的时候,那么你就不能期待这个时代能有什么让人感觉有希望的愿景产生,即使少数志士也难以影响当日风气。毕竟这都是非主流的微弱声音,更何况,非主流一词已沦落哗众取宠者惯用的耍酷标签。
一个时代的审美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南唐后主李煜在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哼唱“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的淫靡之音时,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样颓废无力,秾艳拘狭的小文艺无法撑起时代前进的需求。晚唐到五代社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社会,从晚唐坚实难摧的世家门第到五代跋扈的武夫,在那样的时代里,奋起疾呼是一种异端,随波逐流才是最好选择。
而宋朝的建立,改变了这浮云蔽日的一切,其诸多举措,也让赵宋不至于成为五代后的第六代短命王朝。
作为一位从五代这样纷乱的时代中成长起来军事精英,宋太祖敏锐地意识到,为防范武人对皇权的威胁,着力提高文人的地位,使士人阶级成为皇权的最大支持者才是长久之计。而从更现实与极端的角度看,太祖曾经认为,即使有一百个的昏庸的文官在地方执政,也胜过一个跋扈的武人。所以他在立国之初,就着手分派文官夺地方武人实权并开始崇文抑武的国策。
而从行政治理效能层面考虑,太祖当然知道马上夺天下而马下治天下的简单道理。因此他着手建立选拔文人才俊的制度,自中央到地方逐次建立一个有序的文官行政体制,另一方面鼓励武人读书,努力扭转五代的无序的社会形势和颓唐的风气。
当东京在公元 1127 年陷于金人后,被掳走的宋徽宗特意从北方托人带话给在南方即位的宋高宗。来人告知高宗,太祖皇帝曾立一块誓碑在太庙的密殿之中,这里只有皇帝和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允许进入。誓碑中有誓词三行,第一条是要求保护优待后周皇族柴氏的子孙,第二条是不可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第三条便是要求子孙遵守这两个誓言,“渝此誓者,天必亟之”。
这个誓碑在开封城破后已不可再寻,只留于典籍的记录中,于是成为诸多学者的研究之课题。我们从宋代皇帝优待士人的作为中,可以相信这个誓碑存在的极大可能性。而这不仅仅是宋代历代君王对于祖宗之法的一种尊重,而是从太祖,到太宗,真宗逐次树立的朝政气氛,这种气氛体体现在言论包容与对士人的尊重。
赵宋立国一百余年后的神宗年间,由于陕西用兵失利,神宗欲斩一位漕臣。宰相蔡确坚决反对。他对神宗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表示可以做出让步,但要将这位漕臣如对待犯人一样刺面发配时,蔡确再次反对此举,他认为在脸上刺字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忿忿地发牢骚说道,“快意事做不得一件”。而在神宗后继位的哲宗曾在新旧党争时,对得势的新党首领的宰相章惇说,“我尊从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所以不可穷治旧党。”相较于明代的皇帝专制,动不动官员就遭羞辱般的廷杖,宋代的崇尚文治,使得时时处于外族军事强压下,立国三百余年的宋代,得以成为中华文化最灿烂的时光。
士人们必定都读过西周厉王暴政下,无奈的国民只能“道路以目”的故事,还有当时大臣劝谏厉王时说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而终宋一代,并无此顾虑。而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宽松的氛围,直至今日,我们才能在宋代的文献中,读到大量诸大臣臧否时事的奏折,特别是在宋朝面临危机的仁宗康定到庆历年间和神宗熙宁变法前后这两个时间段。如果在危机中,整个执政集团内是人人心知,却噤声不语,那么即使刻下没有爆发点,将来可能发生的一件小事会如堤防上的小孔一样,成就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功。如同托克维尔回忆在 1848 年工人阶级革命前夜的警告,“此时此刻,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欧洲的大地又震颤起来了”“暴风雨正在地平线上隐现”这样的话,也如同庆历四年谏官余靖说的:“天下之势,如人坐积薪之上而火已燃,虽火焰未及己身,但是可谓危矣”。
虽然在民国前,中国历史属于帝制的时代,可是,在大多数时间内,君主并非绝对独裁的。比如唐代,任何决定,必须要通过中书省确定,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如果门下省不同意,便可退回中书。而如果皇帝违反流程直接下达,这样的做法就叫做“斜封墨敕”,这是受行政官员所鄙夷的。即使在武则天高压强权之下,时任凤阁侍郎(即中书侍郎)的刘祎之曾说,不经凤阁(即中书省)签署同意,怎能叫敕令呢?而回望中国历史的黎明的春秋时代,则是一种贵族共治的情况。那时,各诸侯国王更似一个部落酋长,而地位已衰的周天子只是一位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已。而这样的君主与大臣共治的形态到了宋代,特别是在北宋中期,达到了一个巅峰。中国的帝权专制实际更多地是从明代戕害士大夫文人开始,直到清代用狭隘的部族思维来限制士大夫的作为。
英剧《王冠》第一季里,当伊丽莎白二世说菲利普亲王去学驾驶飞机是属于他的私事时,首相丘吉尔厉声对这位刚继位的女王说,你和亲王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私事!而类似的言语,在士气高涨的宋代,屡见不鲜。
宋真宗有意立出身卑微的刘氏(即仁宗朝垂帘的章献皇太后)为贵妃,手诏送到宰相李沆处,李沆直接“引烛焚诏”以示反对。而嘉祐元年正月,风闻四十七岁的仁宗中风时,文彦博等执政大臣赶忙召集内侍史志聪等人询问身体情况,史志聪表示这是大内禁中事务,属于秘密而不予告知,意图搪塞诸大臣。文彦博叱责道,“天子违豫,海内寒心,彦博等备位两府,与国同安危,岂得不预知也!”
欧阳修在为故相杜衍写的墓志铭中记载,仁宗曾按所谓内降或恩泽,即绕过正常任命程序,意图直接下令任命向自己关说的近宠为官员。时任吏部侍郎的杜衍对此一概不理,均退回给仁宗。仁宗也只好苦笑着称赞杜衍,说这是在帮他解人情之围。再比如在熙宁变法时,王安石虽然权倾朝野,亦得神宗的权利支持,但是,当他决定破格提拔李定时,反对派苏颂等人拒绝为此起草任命文书,并以辞职相胁。
而更早前,在仁宗幼冲时,垂帘的章献太后想掩盖仁宗的生母李贵妃去世的消息,吕夷简不同意草草办理其后事。期间,他对章献太后说,“我身为宰相,内外事无不当预”,也就是说,皇帝的生母去世虽是皇家的“内事”,但作为宰相,也有权过问。
再如,仁宗去世后,英宗初立。按制度,应由亲王先来道贺,当时允弼是宗室内最尊之人。由于允弼与仁宗同辈,比新皇英宗高了一个辈分,而且允弼曾被封为北海郡王,而英宗最高的官衔也只是团练使而已。因此,辈分和官阶都要高于英宗的允弼傲慢地质问宰相韩琦:“岂有团练使(指英宗)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指允弼)?”傲慢不服气的他在韩琦的淳淳劝导下仍不愿祝贺新皇登基。韩琦只能大声叱道,“大王,你是人臣,不得无礼”,这样的情况下,加之甲兵在殿,允弼才无奈从之。
如果类似的话放在明代,或是清代,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位所谓的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当他听到北宋思想家程颐说的“天下治乱系宰相”的话时,便愤怒地斥责这是“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就此可见宋儒的气象和与后来者的区别了。
而更早前,西汉昭帝身后,把持朝政的大将军霍光废黜刚继位为皇帝的昌邑王刘贺,但此时丞相杨敝事先并未被告知,事后杨敝为霍光未告知他的原因,霍光回答道,“这是内朝事,与你统领的外朝无关”。
有以上两事便可知宋代的士人地位当为空前绝后了。
宋代士人如此对朝政抱持的主人公般的态度,对治道的憧憬往往带着一种宗教般的狂热执着而不为利益所撼动的气魄,除了春秋战国时的贵族和游士外,也只有宋代才普遍有这番气象。这也是宋初的开始养士的国策,历经半个世纪后,到了仁宗年间,催生了士大夫们挺身而出,匡扶救世的作为。
太宗朝的宰相吕蒙正被罢,太宗轻鄙地揣度蒙正此时的心态说,“蒙正本是一介布衣,被擢升为宰相,可现在被罢,估计他对于自己何时能复位应该是望眼欲穿啊”。但钱若水驳斥说道:“当今岩穴高士不求荣爵者甚多,我并不觉得他会有如此有郁悒之态”。
亦如同司马光在熙宁变法时,他清楚地知道在那时的现实中,即使就任高职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政见,于是好不眷恋,弃位而去。所以程颢才会对神宗说,“如果陛下能听从司马光的建议,光必来,如不能用其言,光即使招之也不会就职的”。而王安石的好友韩维也曾评价王安石说,“安石素有经世之志气,非甘愿终老于山林。”
虽然朝廷里不免有曲阿之人,但是宋儒不管在位或是在野,他们对自己坚持的价值理想的坚毅果决,自信于一旦据鞍上马,那必然是慨然有澄天下之志,这份精神令后学者仰之弥高。
在南宋朱熹的时代里,看似朱学大谈所谓的内圣之学,但是骨子里,他们所期望的也还是要内圣而外王,就是有机会便要得君明志,齐天下。这就是如孟子说的:“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是孔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因此,当朱子理学的内圣的外衣被剥去时,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正带着理想的士大夫,他们没有因为种种困难而退缩在个人修身的世界中,而是在等待时机。如果不是这般,那么他们又和宋儒所驳斥的佛老之说何异?
南宋陆九渊说:“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朱熹在感怀诗里说:“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素期,几年霜露感,白发忽已垂”。相较于处于中年危机里的李商隐吟唱的“晓镜但愁云鬓改,月吟应觉月光寒”,或是如李宗盛唱的:“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陆朱两人的气魄显得更大。朱熹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朱熹并非保守的,他激烈地反对为君权张目,他提到南宋朝廷变得君臣关系愈渐疏远时,感叹道,“据说北方的金朝在最初的时候,其酋长和部落首领并无分别,同坐同饮,相为戏舞”,此时南渡之后的赵宋朝廷,却变得“人主极尊严,宛如神明,而人臣极卑屈,望拜皇帝于庭下,君臣不交一语而退”。或许南宋高祖赵构早忘了宋太宗的话,他对大臣说:“天下之大,卿等与朕共理”。
我们不能去苛求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要能有如七百年后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否定专制王权,提升民权等观念。可是,这种君主和士大夫共治的观念一旦继续发展下去,我们能不想象,这样的启蒙思潮不会出现吗?可是,这只是想象。就如同后世学者讨论如果当年是楚国统一中国而非暴秦,那么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范仲淹的后辈程颐说,“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如果天下为皇帝独私一人所有,非君道也”。一切得益于宋代宽松开放的思想环境,这样的环境,激发了智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更加鲜明的理想主义,而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士大夫们才有机会和信念去主动建树功勋。而若有各类桎梏,则恣意想像,丈夫功业便不可能。
神宗熙宁三年三月(1071 年),王安石的反对者文彦博,在讨论士大夫们对变法的反对情绪时,对神宗说:“祖宗法制都在,不须轻易更张变革而失去人心”。神宗回答道:“更张法制,于士大夫间确实多有不悦,但并没有给百姓太多的不便啊?”文彦博不免偏激地回答道:“朝廷是与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而王安石更是曾石破天惊地说:“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也就是说,对于道行品德高尚之人,即使是天子,也要转过身来虚心请教,而尊其为主。
当我们读到这些言论时,难道无法有如岳武穆的“壮怀激烈”的感动吗?
中世纪欧洲,巴黎大学的教师们与教会匹敌,他们就像是这黑暗世界的另一道光,在神学家托马斯· 阿奎那,来自帕多瓦的政治思想家马西略和英格兰圣方济各会士奥卡姆的威廉等思想巨擘的授课下,学院如磁石般的吸引着无数学子。如芭芭拉·塔其曼在《远方之镜》一书中讲述的,由于这样的崇高的学术地位,以至于巴黎大学在论及基督教权威时依然桀骜不驯,总是和主教和教皇发生冲突,“你们这些坐在自己桌边的巴黎大师们似乎觉得,世界应当由你们的论证来统治”,罗马教皇的使节本尼迪克特·卡埃塔尼大光其火地说,“世界被委托给了教会,而不是你们”。但是未被此言说服的大学教授们却认为自己在神学方面像教皇一样具有权威,是世界的两道光。
所以只有带着更高远的理想信念,拥有极具开创性,时代进步性的思想体系的支撑,方能成就宋代士大夫能展现出与过去唐代,五代士人完全不一样的气象。宋初开始的文治并非只是影响到执政的层面,而是与民间的风气相互交融的。当政府的文治风气一开,经数代之教育,明识者自然而出,而欲上进者自然也会从学问中寻求出路,而在此过程中,他们会思考,他们会放开眼界,因为知而行之是在宋代智识分子的追求。他们不会如清代学人一样,担心文字狱祸及己身,可又无处宣泄才华,只能很可怜,可惜地皓首穷经般的在故纸堆里堆砌才识。
宋初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索理论的要义,寻求建立他们所处的新时代的思想行动法则。于是,新儒家出现了。
五代时的读书人在武夫的压迫之下,大体只得一个物的功用,直至北周朝方见宽松,但是,仍难洗猥琐之气,所以才有赵普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才有宋太祖催促官员,武将要多读书,从另一个角度讲,可见宋刚建国时人才的缺乏和学问风气的不张。
宋代新儒学不似过往,局限于老一套的人生指南,鸡汤调了几百年还是那些陈腐滥调,而是积极地在儒学的外衣下,尝试重建整个社会的秩序。
宋儒的思想源流可追溯到唐代的韩愈,即使韩愈生活的年代离宋初诸子的年代有两百年之遥。但韩愈尝试重塑儒学权威,以匡扶他认为已经偏离正常轨道的唐代社会的企图,如同一道高山雪水,绵延流淌至宋初后,被宋代文人所继承,发扬,成为新儒家的时代洪流。
韩愈生于安史之乱平息后十年,正是唐代从盛唐开始转向没落的时代。在韩愈的世界里,他痛心儒学之不振,而此时从民间到政府,均崇尚佛老之学。所以他激进地提出要对道佛“火其书,庐其居”,即要销毁这些宗教经典和寺观,他愤懑于众多僧道不劳而食,且占据大量经济资源,希望明儒家之道而治之,才能挽救社会危机,使贫弱者有养。所以他说要“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传统农业社会中发展而来的中国的思想体系自春秋以降就富含着现实主义,《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左传春秋》也说过,“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主事者在决断大事时犹豫想要占卜知吉凶,被随从砸坏占卜的器具,并痛斥对方大事当前不应听信鬼神的故事,在中国历史里出现多次。因此,虽然中国的文人往往杂糅着出世和入世的气质,比如苏东坡。但在社会治理层面,中国的文人们从来就不相信清静无为可以改变什么。所谓修身,只是为了将来可以平天下。所以魏晋的清谈除了是一种如阮籍般的无奈地逃避,或如王羲之般雪夜访客的自我陶醉,千百年后,一切留下的至多是一个白衣飘飘的背影。就如同狄奥根尼可以冷对亚历山大帝,恨其挡住了自己眼前的灿烂阳光,但是他犬儒的思想,并无法支撑起一个雄浑的时代。
人世的艰难和对玄妙般自在的渴望,使得在宋初,佛老依然是占据了思想界的高峰。而当政权稳定,思想,社会亟待再造,于是宋初诸子便接过韩愈的火炬,继续批判当日风行的佛学。
佛家有完整的一套宇宙理论和修身理论,为了和佛学抗争,宋初的儒家只好也拼凑起他们的宇宙理论,而通过这样的宇宙理论,才能建立起理论的高度,以便成为最终强调修身治学平天下的津梁,虽然在很多方面,他们也藉由佛学的思维方式,词语来重塑儒学。因此在这个所谓宋儒的思想体系中,不免还是留着佛学痕迹。比如,禅宗讲究师法传承,从初祖龙树到六祖慧能,而宋儒也相应地把儒学的传承创造了一个谱系。早在韩愈的思想中,他就认为,所谓儒家的原道,即思想真谛,就是从尧舜禹,商汤,周文武王,再传到孔子孟子。而宋儒便将这所谓的“道”的传承延续为从孟子传到韩愈,再到宋儒。或比如到了南宋的陆九渊,他提到一个士大夫内圣修养的最高境界时,说“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经世”,这样的话完全就是禅宗气象。欧阳修甚至因此而厌恶易经,拒绝谈论心性,他痛斥佛法那一套,要求读书人回到儒家经典中济世经邦的理想去,因为他相信,儒家经典里,才有治国修身之法。所以他说“性非学者之所急,六经之所载,才是急切于世事的知识”。
石破天惊的革新思想往往是不易使人接受,但如果可以借助一个已经被肯定的前师来保护自己的新思想,往往是一件更安全的事情。所以,如同欧洲的宗教改革一样,圣人之道便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去充实它,解释它的范畴。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解释,使得这些名士占据了思想的高地,这便不是权威的力量容易否定的。宋儒的革新在于,他们不困于这些复杂的理论,而是要反观内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如同南宋的朱熹,格物致知等等,骨子里甚至更希望以儒家的天下代替皇权的天下。
维摩经中说,“有法门,名无尽灯,譬如一等燃白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宋代新儒学经宋代两百多年的传承,发展,衍生出诸多流派,但是,即使他们论点不一,但最基本的目的还是该如何经世济,以求儒家“内圣外王”的高远理想。但是,他们的起点还是要从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开始。
胡瑗等三人都是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学者型人物,岁数也与范仲淹都相仿。他们的活跃的年代,都处在庆历变法时期前后,和庆历诸子有许多的交集,比如,胡瑗就曾在在范仲淹任苏州知府时做苏州府学教授,后在离苏州不远的湖州任教授长达 20 年。而石介亦曾在庆历新政中任职类似今日国立大学的国子监内的讲师。
他们如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自然哲学家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一样,思想清澈,直接。他们没有如宋中期后的儒家学者提出的一大堆格物致知,涵泳气象等复杂说法,或如德国古典哲学一样让普通人看得云里雾里的理论。他们成长于宋初优待士人,提倡知识的年代里,而在宋代数十年养士的收获时期,他们重新高举儒家的经典,尝试重新诠释儒家的经典,而不是如过去朝代里的读书人一样,或是在章句中皓首穷经,玩弄文字游戏,或是把经典当做求富贵的工具。
在唐末五代宋初,学术思想大多转入佛学的大势下,他们利用学院教习的机会,不囿于传统儒学经典章句的束缚,而是在其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前进需求的理论。他们号召为人应该“明体”,为事应该“达用”,试图重新拾起最早的儒家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们的理论和文字,一洗晚唐五代风俗轻薄之士风,摒弃音律浮华之辞藻,驳佛老出世无为之浮伪。他们寻求真正的义理之学,就是要达到他们的后学张载所总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这样的精神,也直接影响了同时代的欧阳修所倡导的古文运动。
欧阳修强调说,学习经典,是“不只是学古,而是必求可以施于今日”。也就是在“君子学以致其道”的精神感召下,胡瑗的弟子,后来成为理学大师的程颐,才会在二十余岁还在太学读书时,敢于上书仁宗,大胆地质问道:“臣请议天下之事。不识陛下以今天下为安乎?危乎?治乎?乱乎?怎可知危乱而不思拯救之道呢!?”。
由此,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是他们那辈士大夫群体的精神总结。
每个时代都有读书人,宋代却更为士气高涨。这个时代的士人风范,或许只有战国时期的游士与五四时期的新知识分子可以类比。但是战国时期的谋士虽各具个性,可他们多游离于各诸侯间,寻求可能的壮志可酬,只为功利,常不守原则,所以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机会主义更多于理想主义。为了服务于此诸侯国的利益,他们可以算计老东家,往往是图利的心态高于遵循普世价值之上。
但宋代的士人是幸福的,而一个时代的气氛便是这样生成了。当学者可以在自由著述而得到学界景仰,当耿直的朝士可以无所顾忌地在朝中相互据理力争,无畏于皇帝的态度。这种的气氛,根本不需要去在乎传说中的太庙密殿里的那块写着不杀言事官的大石碑。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就有虽天下人吾往矣的豪气。明代的言官在当时那么高压的气氛中都敢直言,更何况言论宽松,风险系数不大的宋朝。因此,在这样的气氛下,有机会从政的知识分子,只要有心,更是不会放过“得君行道”的机会。
陈寅恪先生评论宋代文治时说,“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这样辉煌的根本即在于宋代的士大夫精神,其精神之不朽,亦如先生于 《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评价王静安先生的话,“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