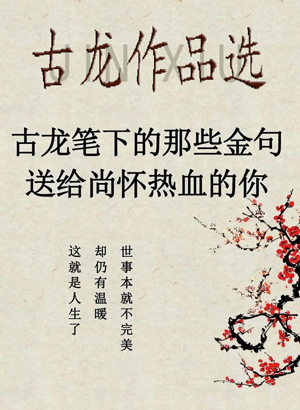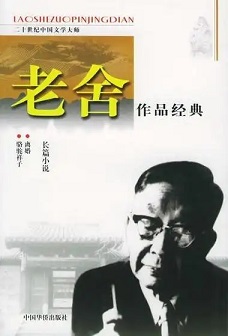1
梅特卡夫医生是丹尼茅斯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对病人谦和有礼,总能让病房里的气氛轻松愉快。是个嗓音温和悦耳的中年人。
他仔细聆听哈珀警司说话,并且平和准确地回答他的问题。
哈珀说:
“梅特卡夫医生,这么说,我可以确定杰弗逊夫人的话是真实的?”
“是的,杰弗逊先生的健康状况不稳定。近几年,他一直在无情地驱赶自己。他要和其他人过一样的生活,因此生活节奏比健康的同龄人快得多。他拒绝休息、放松、慢节奏——完全不接受我和他的医疗顾问提出的任何建议。结果,他成了一台过度使用的机器。他的心脏、肺、血压全都超负荷。”
“你是说杰弗逊先生完全听不进别人的话?”
“是的。我没有责备过他,我从不对病人说这样的话,警司,但是一个人与其荒废,确实还不如忙得筋疲力尽。我的很多同事都是这样,而且我知道这个方法并不坏。在丹尼茅斯这样的地方,人们看到的大都是另一种情况:患病的人牢牢地抓住生命,他们害怕让自己过于劳累,害怕流动的空气和四处散落的细菌,甚至连吃一顿饭都会犹豫不决!”
“我觉得确实如此。”哈珀警司说,“这就是说,从身体方面来看,康韦·杰弗逊还很健壮——或者应该说肌肉强壮。对了,他精神好的时候可以做什么?”
“他的手臂和肩膀力量很强。空难之前他就是个很强健的人。他可以灵巧地操纵轮椅,依靠拐杖可以自己在房间里活动——比如从床挪到椅子上。”
“像杰弗逊先生这样受过伤的病人不能安假肢吗?”
“他不行。他的脊椎骨被损坏了。”
“原来是这样。我再总结一下。从体格方面来看,杰弗逊健康强壮。他自己感觉很好,是这样吗?”
梅特卡夫点点头。
“但他的心脏状况不好。任何紧张或劳累、震惊、惊恐都可能导致他猝死。是这样吗?”
“基本是这样。过度的劳累正在慢慢杀死他,因为他疲劳的时候也不休息。这让他的心脏病更加恶化。疲劳不可能导致他猝死,但突如其来的震惊或者惊恐则很容易导致这种结果。因此我已经明确提醒过他的家人。”
哈珀警司慢慢地说:
“然而,事实上震惊并没有夺走他的生命。医生,我的意思是,他还活着,不可能有比这更令人震惊的事了,对吧?”
梅特卡夫医生耸耸肩。
“我知道。不过,警司,如果你有我的经验,就会知道很多病例确实无法准确预测。本该死于震惊和寒冷的人,却没有因震惊和寒冷而死等等,不胜枚举。人体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坚韧得多。而且,从我的经验来看,身体上的打击通常比精神上的打击更加致命。简单地说,与得知自己喜爱的女孩死于非命相比,突然的摔门声对杰弗逊先生来说更加致命。”
“这是为什么呢?”
“突如其来的消息通常都能引起听者的防御性反应,让听者麻木。起初,他们无法接受。需要一点儿时间彻底弄清事情的原委。可是砰的摔门声、从壁橱里突然跳出一个人、过马路时一辆车疾驰而过——这些都是即发行为。用外行的话讲——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哈珀警司慢慢地说:
“不过每个人都知道,那女孩的死所带来的震惊或许会轻易要了杰弗逊先生的命?”
“哦,很容易。”医生好奇地看着对方,“你不会是想——”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哈珀警司恼怒地说。
2
“然而你必须承认,长官,这两件事非常吻合,”稍晚时候他这样告诉亨利·克利瑟林爵士,“一石二鸟。先是那个女孩——她的死同时会带走杰弗逊先生——在他有机会更改遗嘱之前。”
“你认为他会更改遗嘱?”
“这个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长官。你认为呢?”
“我不知道。鲁比·基恩出现之前,我无意中得知他已经把钱留给了马克·加斯克尔和杰弗逊夫人。我不理解他现在为什么要改变主意,不过当然有可能这样做。也许他会把钱留给某个动物收容所,或是捐助给年轻的职业舞蹈演员。”
哈珀警司表示同意。
“你永远猜不到一个男人的脑子里究竟装了什么——尤其是他处理钱财而不必考虑道德义务的时候。这件事的背景是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亨利爵士说:
“他喜欢那个男孩——小彼得。”
“你觉得他把彼得视为自己的孙子吗?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长官。”
亨利爵士慢慢说:
“不,我不这么认为。”
“还有一件事想问你,长官。我个人无法判断。可他们是你的朋友,所以你知道。我很想了解一下,杰弗逊先生到底有多喜欢加斯克尔先生和小杰弗逊夫人。”
亨利爵士皱起眉头。
“我不能确定你究竟是什么意思,警司?”
“呃,是这样的,长官。抛开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谈,如果他们是普通人,他有那么喜欢他们吗?”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
“是的,长官。没有人怀疑他非常依恋他们两个——但是,在我看来,他依恋他们是因为他们分别是他女儿的丈夫和儿子的妻子。不过,如果他们之中有谁再婚呢?”
亨利爵士想了想,说:
“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不知道。我倾向于怀疑——这只是一种看法——这会使他的态度有很大改变。他会祝福他们,不会心存怨恨,不过我认为,他也不会对他们有更多的兴趣。”
“对两个人都是这样吗,长官?”
“我想是的。对加斯克尔先生的态度几乎可以肯定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对杰弗逊夫人也是如此,不过不这么肯定。我觉得他很喜欢她。”
“这和性别有关。”哈珀警司故作聪明地说,“对杰弗逊先生来说,把她当女儿比把加斯克尔先生当儿子更容易。反过来也一样。女人很容易接受女婿,而很少把儿媳看成女儿。”
哈珀警司继续说:
“长官,你介意和我一起沿着这条小路去网球场吗?我看见马普尔小姐坐在那里。我想请她帮个忙,事实是,我想请你们两个都来。”
“什么事,警司?”
“弄到一些我弄不到的消息。我想请你代我去查问爱德华兹,长官。”
“爱德华兹?你想从他那里知道些什么?”
“任何你能想到的事!他知道的一切以及他的想法!关于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对鲁比·基恩这件事的看法,内部信息。他比任何人更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肯定知道!他不会对我说,但他会跟你说。我们也许能因此发现什么。当然,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亨利爵士严肃地说:
“我不反对。我匆忙赶到这里就是为了弄清真相。我会尽最大努力。”
他又补充道:
“你想让马普尔小姐怎么帮你呢?”
“是几个女孩,女童子军。我们已经找来了六个左右,都是帕米拉·里夫斯生前来往最密切的好友。她们很可能知道些什么。你看,我一直在想,如果那女孩真的要去伍尔沃思,她应该会找另一个女孩和她一起去。女孩通常喜欢一起结伴购物。”
“是的,我想确实如此。”
“所以我觉得伍尔沃思可能只是个借口。我想知道这个女孩真正去了什么地方。她可能会无意中透露了什么。如果是这样,若是有人能从这些女孩身上问出来,那人应该是马普尔小姐。我得说,她比较了解女孩——比我了解。再说,这些女孩害怕警察。”
“听起来,马普尔小姐最善于处理乡下的地方性案件。你知道,她非常敏锐。”
警司笑了,他说:
“你说得对。几乎没什么事能逃过她的眼睛。”
马普尔小姐看见他们过来,抬起头热情地打招呼。听了警司的要求,她答应了。
“我非常愿意帮忙,警司,而且我觉得我应该能做点儿什么。凡是关于主日学校、小女童子军和我们的女童子军,附近的孤儿院的事——你知道,我是委员会的成员,经常和主妇交流——还有仆人——通常是非常年轻的女佣。我一眼就能看出一个女孩什么时候在说真话,什么时候在说假话。”
“你是真正的专家。”亨利爵士说。
马普尔小姐责备地看了他一眼,说:
“哦,请不要取笑我,亨利爵士。”
“我做梦也不敢取笑你,相反,你取笑我的时候倒是很多。”
“在乡下,见到的邪恶之事确实很多。”马普尔小姐低声解释。
“顺便说一句,”亨利爵士说,“我查清了上次你向我提出的问题。警司告诉我,鲁比的废纸篓里有剪下的指甲。”
马普尔小姐一边思考,一边说:
“是吗?那么就是……”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件事,马普尔小姐?”警司问。
马普尔小姐说:
“是这样——呃,看到尸体时,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不知怎么的,她的手看起来不对。起初我想不出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明白了,习惯浓妆艳抹的那种女孩通常都会留长指甲。当然,我知道女孩们喜欢咬指甲——这个习惯很难改。不过虚荣心常常能起作用。我当时还以为这女孩还有这个毛病。后来那个小男孩——就是彼得——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了以前她是留长指甲的,只不过因为钩住了东西而断裂了。这样的话,她应该会把其他的指甲都剪齐。所以我问起指甲的事,亨利爵士答应去查一查。”
亨利爵士说:
“你刚才说:‘看到尸体时,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还有别的吗?”
马普尔小姐用力点了点头。
“哦,是的!”她说,“就是那件衣服,实在太不对劲儿了。”
两个男人都好奇地看着她。
“这又是为什么?”亨利爵士问。
“嗯,你看,那是件旧衣服。乔西说得很肯定,我也亲眼看到了,那件衣服很廉价,很旧。这完全不对劲儿。”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对劲儿。”
马普尔小姐的脸有点儿红了。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认为鲁比·基恩换了衣服是打算去见某个人,也许就是我的小侄子们所说的‘心上人’?”
警司的目光闪烁了一下。
“那是推测。她有个约会——和人们常说的男朋友的约会。”
“那么,”马普尔小姐追问道,“她为什么穿了一件旧衣服?”
警司挠了挠头,说: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她应该穿一件新衣服?”
“我认为她应该穿上她最好的衣服。女孩们都这样。”
亨利爵士插话道:
“是的,不过你看,马普尔小姐。我们假设她是出去约会了。她或许会乘敞篷车,或许会选一条不太好走的小路散步。她不想把新衣服弄坏,于是穿了件旧的。”
“这是明智的做法。”警司表示同意。
马普尔小姐转向他,立刻反驳道:
“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换上长裤和外套,或者花呢衣服。这个(当然,我不想太势利,不过这次恐怕很难避免),这是女孩——我们这个阶层的女孩的正常做法。”
“一个有教养的女孩,”马普尔小姐继续这个话题,“总是会特别注意在适当的场合穿适当的衣服。我的意思是,无论天气多热,一个有教养的女孩决不会穿着丝绸花裙子出现在赛马场。”
“那么和恋人约会时合适的打扮应该是什么?”亨利爵士追问道。
“如果是在酒店或某个穿晚礼服的场合见面,她会穿上她最好的晚礼服。当然,如果在外面约会,穿晚礼服会显得滑稽,所以她会穿上她最漂亮的运动装。”
“那是时装模特的做法,但是鲁比这个女孩——”
马普尔小姐说:
“鲁比,当然——坦率地说——鲁比不是个淑女。她那个阶层的女孩在任何场合都会穿上她们最好的衣服,不管合不合适。你知道,去年我们去斯克兰特尔礁野餐。女孩们的打扮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丝绸的花衣裙,与众不同的鞋子,精致优雅的帽子。她们穿着这些衣服爬上山石,穿梭于金雀花和石南属植物之间。年轻的先生们则穿着他们最好的西服。当然,徒步旅行又不同,这种场合的着装是有规定的——女孩们却似乎没意识到,除非身材非常苗条,否则穿短裤是非常不雅观的。”
警司慢慢地说:
“而你认为鲁比·基恩——”
“我认为她会一直穿着她之前穿的那件——她那件最好的粉红色裙子。除非有更新的,否则她应该不会换掉。”
哈珀警司说:
“那么,你的解释是什么,马普尔小姐?”
马普尔小姐说:
“我没有解释——目前还没有,不过我总觉得这事很重要……”
3
在四周安着围栏的网球场里,雷蒙德·斯塔尔的网球课快结束了。
一个矮胖的中年妇女说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拾起天蓝色的羊毛开衫,向酒店走去。
雷蒙德对着她的背影嚷了几句轻松的客套话。
他转身朝长凳上坐着的三个观众走来。手中网球袋里的球摇晃着,球拍夹在腋下。现在,他脸上那欢快的表情像被擦掉一样忽然消失了。他看上去疲惫而焦虑。
他走近长凳,说:“结束了。”
笑意在他脸上绽开,迷人、孩子气、富有表现力,与他晒黑的脸庞和轻巧自如的优雅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
亨利爵士不禁在心里猜测他有多大年纪。二十五、三十、三十五?无法判断。
雷蒙德轻轻摇着头说:
“她永远也打不好,你知道。”
“这对你来说一定很乏味。”马普尔小姐说。
雷蒙德说:
“是的,有时候是这样。特别是夏末。想起酬金会让你振奋一下,但即使钱也不能激发你的想象力!”
哈珀警司站了起来,忽然说:
“我半小时后再来找你,可以吗?”
“没问题,谢谢。我会准备好的。”
哈珀离开了。雷蒙德站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说:“我能在这里坐一会儿吗?”
“坐吧。”亨利爵士说,“抽烟吗?”他拿出烟盒递过去,同时想着自己为什么对雷蒙德·斯塔尔存有偏见。只是因为他是一个职业网球教练和舞蹈演员?如果是,那也不是因为网球——而是跳舞。亨利爵士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认为舞姿太好的男人都不可靠。这个家伙的舞姿太优雅了!雷蒙——雷蒙德——哪个是他的名字?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对方似乎觉得这很有趣。
“雷蒙是我最初工作用的名字。雷蒙和乔西——看,很有西班牙风情。后来,因为这里对外国人有偏见,我就成了雷蒙德——非常英国化——”
马普尔小姐说:
“你的真名完全不同吗?”
他对她笑了笑。
“事实上,我的真名是雷蒙。我祖母是阿根廷人,你知道——”怪不得他臀扭得那么好,亨利爵士想,“但我的第一个名字是托马斯。平凡得令人乏味。”
他转向亨利爵士。
“你是从德文郡来的,是吗,先生?从斯塔内?那边有我认识的人。在阿尔斯蒙斯顿。”
亨利爵士兴奋起来。
“你是阿尔斯蒙斯顿的斯塔尔家族的?我真没想到。”
“是的——我知道你不会想到。”
他的声音里有一丝苦涩。
亨利爵士尴尬地说:
“运气不好——呃——诸如此类的。”
“你是说那块地在属于家族三百年之后被卖掉了?是的,非常不幸。不过,我想,我们这样的人还是得生存。我们的生命比自身的价值更长。我哥哥去了纽约,从事出版业——干得不错。我们其他人分散到了各地。现在,如果你只接受过公共学校的教育,要找一份工作是很难的。运气好的话,有时候可以在酒店做接待员。领带和礼貌在那里是一种资本。我能得到的唯一工作是在一家洁具部做展示员。那里售卖高档的桃子色和柠檬色的瓷浴缸。那个用于展示的浴室非常大,可是我对那些该死的东西的价格或发货时间一窍不通,于是我被解雇了。”
“我只会跳舞和打网球。”我在里维埃拉的一家酒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收入不错。我想我干得也不错。后来,我听说一个老上校——非常老,老得让人不敢相信,是个地道的英国人,总是在谈论浦那[浦那(Poona),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城市。]——找到经理,大声喊道:
“‘那个跳舞的男人呢?我要找他。我夫人和女儿想跳舞,你知道。那家伙在哪里?他敲诈了你们多少钱?我要找那个跳舞的男人。’”
雷蒙德继续说:
“这事说起来很傻——但是我干了。我辞掉工作,来到这里。虽然挣得比以前少,但工作很愉快。我的工作主要是教那些永远、永远、永远都学不会的胖女人打网球。还有和那些富有的顾客的女儿跳舞。她们在舞会上往往是没有舞伴的姑娘。嗯,我想这就是生活。请原谅今天这不走运的倒霉事!”
他大笑起来,露出雪白的牙齿,眼角向上扬起。他突然看起来健康、快乐、充满活力。
亨利爵士说:
“很高兴和你聊天。我一直想和你谈谈。”
“关于鲁比·基恩?我帮不了你,你知道。我不知道谁杀了她。她的事我知道得很少。她从来不跟我说心事。”
马普尔小姐说:“你喜欢她吗?”
“不是特别喜欢,也没有不喜欢。”
他的声音透着无所谓和不感兴趣。
亨利爵士问:
“那你没什么话要说了?”
“恐怕没有了……如果有的话我早就告诉哈珀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是那种不值一提的、卑鄙的小犯罪——没有线索,没有动机。”
“有两个人有动机。”马普尔小姐说。
亨利爵士锐利的目光看向她。
“真的?”雷蒙德似乎很惊讶。
马普尔小姐目不转睛地盯着亨利爵士,他极不情愿地说:
“她的死可能给杰弗逊夫人和加斯克尔先生带来五万英镑的利益。”
“什么?”雷蒙德似乎真的大吃一惊——不仅仅是吃惊——而且很不安,“哦,可是这太荒唐了——绝对荒唐——杰弗逊夫人——他们两个谁都不可能——和这件事有关。这样想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马普尔小姐咳了一声,轻轻地说:
“我觉得,恐怕是你太理想主义了。”
“我?”他大笑起来,“不是我!我是个没心没肺、玩世不恭的人。”
“金钱,”马普尔小姐说,“是个非常强烈的动机。”
“也许吧。”雷蒙德激动地说,“不过他们两个谁都不会冷酷地勒死一个女孩——”他摇了摇头。
然后,他站了起来。
“杰弗逊夫人来了,来上课。她迟到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有趣,“迟到了十分钟!”
艾黛莱德·杰弗逊和雨果·麦克莱恩正沿着小路匆匆向他们走来。
杰弗逊夫人微笑着为迟到致歉,接着走向球场。麦克莱恩在长凳上坐下。他礼貌地问过马普尔小姐是否介意,征得同意后点燃了烟斗,默默地抽了几分钟,有些不满地看着网球场上的两个白色身影。
然后他说:
“不明白艾迪为什么要上课。好玩,是的。没有人比我更喜欢玩,可为什么要上课呢?”
“想玩得更好。”亨利爵士说。
“她打得不错。”雨果说,“总之够好了。见鬼,她又不参加温布尔登比赛。”
他沉默了一两分钟,又说:
“这个叫雷蒙德的家伙是谁?这些职业教练是从哪儿来的?那家伙像个意大利人。”
“他是德文郡斯塔尔家族的人。”亨利爵士说。
“什么?不可能吧?”
亨利爵士点点头。这个消息显然让雨果·麦克莱恩非常不快。他比刚才更生气了。
他说:“不知道艾迪为什么让我来。她似乎丝毫没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气色从没这么好过。为什么叫我来?”
亨利爵士有些好奇地问:
“她什么时候叫你来的?”
“哦——呃——这些事发生以后。”
“你是怎么听说的?电话还是电报?”
“电报。”
“出于好奇——请问电报是什么时候发的?”
“呃——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你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其实我没有收到,事实上——是她打电话给我的。”
“哦,你当时在哪里?”
“事实上,我前一天下午就离开伦敦了,当时我在戴恩伯里角。”
“呃——离这儿很近?”
“是的,很滑稽,是不是?听到消息时我刚打完一场高尔夫,立刻就赶来了。”
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后者显得焦躁不安。她说:“我听说戴恩伯里角这个地方相当不错,而且还不算太贵。”
“不,不贵。贵了我也支付不起。那是一个漂亮的小地方。”
“我们一定要找个时间开车过去看看。”马普尔小姐说。
“嗯?什么?哦——呃——是的,我会的。”他站起来,“运动一下是很好的——能有胃口。”
他说完便僵硬地走开了。
“女人,”亨利爵士说,“对她们忠实的仰慕者太不公平了。”
马普尔小姐笑了,但没有搭腔。
“你是不是没想到他这么乏味?”亨利爵士问,“我很有兴趣知道。”
“也许想法比较保守。”马普尔小姐说,“但很有潜力,我认为——哦,确实很有潜力。”
亨利爵士也站了起来。
“我该去办我的事了。我看见班特里夫人正走过来,要和你们做伴。”
4
班特里夫人气喘吁吁地走来,坐下喘了口气。
她说:
“我刚才一直在和酒店女仆聊天。可是一点儿帮助都没有。我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你觉得那个女孩真的能暗地里和人来往,谁都不知道吗?”
“这一点很有意思,亲爱的。我觉得显然不可能。如果她确实在和什么人来往,就肯定会有人知道,但是她的做法一定很聪明。”
班特里夫人的注意力转向网球场,她赞赏地说:
“艾迪的球技很有长进。那个职业网球手是个迷人的年轻人。艾迪也很漂亮。她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如果她再婚,我一点儿都不会惊讶。”
“杰弗逊先生死后,她还会成为一个富有的女人。”马普尔小姐说。
“哦,简,不要总是心存恶意!为什么你还没解开这个谜团?我们似乎一点儿进展都没有。我本以为你很快就能解决它。”班特里夫人的语气里有责备之意。
“不,不,亲爱的。我并不是立刻就知道的——而是过了一段时间。”
班特里夫人吃惊地转过身,用不敢相信的眼神看着她。
“你是说你现在知道是谁杀了鲁比·基恩?”
“哦,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知道!”
“可是,简,是谁?快告诉我。”
马普尔小姐坚决地摇摇头,紧紧闭上双唇。
“对不起,多莉,可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你很不谨慎。你会告诉每一个人——即使不说,你也会暗示。”
“不,不会的。我谁也不说。”
“说这话的人总是最后一个遵守诺言。这不好,亲爱的。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事情还不清楚。你记得我当时那么强烈地反对让帕特里奇夫人负责为红十字会收账,但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那只是因为她鼻子抽动的样子和我的女佣艾丽丝出去付账时抽鼻子的样子完全一样。艾丽丝总是少付给别人一先令左右的钱,还说‘可以记在下个星期的账上’,帕特里奇夫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只不过数额大得多。她挪用了七十五英镑。”
“先不提帕特里奇夫人了。”班特里夫人说。
“但我必须向你解释。如果你真的在意,我会给你个提示。这个案子的问题在于所有的人都太轻信、太相信别人。你不能听到什么就信什么。只要有任何可疑之处,我就完全不会相信!你看,我太了解人性了。”
班特里夫人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换了一种语气:
“我告诉过你,是不是?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不应该从这个案子里获得乐趣。发生在我家里的一起真正的谋杀!这种事绝不会再发生的。”
“希望不会。”马普尔小姐说。
“是的,我也希望不会。一次就够了。但是,简,这是我的谋杀案,我想自己能从中获得乐趣。”
马普尔小姐看了她一眼。
班特里夫人挑衅似的问:
“难道你不相信吗?”
马普尔小姐温和地说:
“当然,多莉,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是的,不过你从不相信别人对你说的话,是吗?你刚才就是这样说的。好吧,你是对的。”班特里夫人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辛酸,她说,“我并不是个傻瓜。简,你或许以为我不知道圣玛丽米德的人都在议论什么——整个郡!所有的人都在说,无风不起浪,既然那个女孩是在亚瑟的藏书室里被发现的,那么亚瑟肯定会知道些什么。他们说那女孩是亚瑟的情妇——还有人说是他的私生女——她在勒索他。他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会继续这样说下去!开始时亚瑟没有意识到——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是个可爱的老傻瓜,从来不认为人们会这样看待他。人们会冷淡他,对他侧目而视——无论那是什么意思——最后他会渐渐明白,然后会突然变得惊恐万分,伤心不已,他会像只蛤蛎一样紧紧封锁自己,日复一日在悲伤中度过。”
“正因为这一切会发生在他身上,我才来到这里搜寻任何我能找到的蛛丝马迹!这起谋杀案必须查清!如果侦破不了,亚瑟这辈子就毁了——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
她停了一会儿,继续说:
“我不会让亲爱的老伴儿为他没做过的事而遭受地狱般的痛苦。我离开丹尼茅斯,把他独自留在家里就是为了这个——查明真相。”
“我知道,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