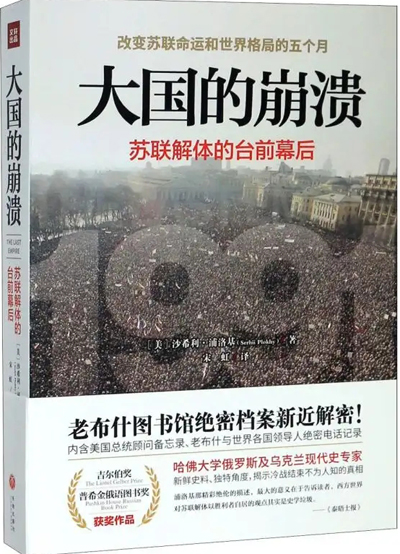阿尔乔姆·波波夫垂下发烫的枪管。他想用手背擦去汗水和泪水,却摸不到眼睛——有防毒面罩挡着呢。也许该把那劳什子摘下来,去他的?事到如今,早死晚死又有什么分别呢……
感染者的哀号声似乎压过了自动步枪的射击声。不然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病人迎着子弹从车厢里冲了出来?难道他们就没听到枪响,就不明白他们会吃枪子?他们在指望什么呢?还是说他们已经无所谓了?
月台打开的出口几米之内堆满了臃肿的尸体。有些还在抽搐,尸堆里传来呻吟。留在车厢里的人惊恐地挤成一团,躲避着子弹。
阿尔乔姆扫视了其他士兵一圈,想知道是否只有他的手在抖,膝盖在颤。所有人都一言不发,连指挥官也保持缄默。只能听见塞满的车厢发出的呼哧声,似乎在极力压抑咳血。死人堆里的濒死者发出怨毒的咒骂:“起开……浑蛋……我还没死呢……真他妈沉……”
指挥官锁定了目标,上前一步,对准濒死者射光了弹匣里的全部子弹。随后他站起身,瞅着自己的手枪,莫名其妙地在裤子上擦了擦枪管。
“保持安静!”指挥官嘶哑地大喊,“擅离隔离区者,杀无赦!”
“尸体怎么办?”有士兵问。
“塞回车厢。伊万年科、阿克谢诺夫,你们俩负责!”
秩序恢复了。阿尔乔姆回到了铺位,想尽可能眯上一会儿,距离起床号只剩下一两小时了。哪怕睡上一小时也好啊,这样明天才不至于晕倒在值班室……
但到底还是没睡成。
伊万年科迈着大步回来了,摇晃着脑袋,不肯去碰那些腐烂发臭的死尸。指挥官举起手枪对准他,忘记弹匣里的子弹已经打光了,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拉上枪膛。伊万年科尖叫一声,撒腿就跑。
就在这时,一个不时咳嗽的士兵举起自动步枪,笨拙地将枪刺捅进了指挥官的后背。指挥官撑住身子,慢慢扭过头,瞪着偷袭他的士兵,惊怒地叱骂:“你他妈的反了?浑蛋!”
“这样下去你会把我们全都害死的……站台上所有人都会感染!今天我们这样对他们,明天你就会这样对我们!”偷袭的士兵朝他喊着,既没有将枪刺拔出来,也没有开枪。
无人出面制止。即便阿尔乔姆也只是朝二人跨出了一步,便僵在了原地。枪刺终于抽了出来,指挥官像搔痒一样,打算把手探到后背去摸伤口,随即跪倒在地,双手撑住湿滑的地板,使劲儿摇晃着脑袋——他是想恢复神智,还是想从梦中醒来?
没有人胆敢结束指挥官的性命。那个偷袭的士兵畏惧地后退一步,一把拽下防毒面罩,扯着嗓子大喊起来:“兄弟们!不要再折磨他们了!放他们出来吧!他们反正是个死!我们也逃不掉!我们还是不是人?!”
“你敢……”指挥官跪在那里,有气无力地说。
士兵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处车厢门口的栅栏被拆开,紧接着又一处……随后有人朝偷袭的士兵迎面开了一枪,他的身体晃悠着后退一步,倒在死人堆里。但为时已晚:感染者们已经咆哮着挤出车厢,笨拙地挪动着两条臃肿的大腿拥向大厅,夺过了被吓破胆的哨兵们的枪,四下散开。有些士兵还在向感染者射击,有些士兵则跟感染者混在一处,离开站台,跑向两侧的隧道——有的向北通往谢尔普霍夫站,有的则向南通往纳加金诺站。
阿尔乔姆站在原地,呆呆地盯着指挥官。指挥官还不想死,他起初四肢着地朝前爬,随后吃力地站起身,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嘴里嘟囔着:“现在就给你们一个惊喜……你们以为我没有准备吗……”
他那游离的目光定在了阿尔乔姆身上,微微一怔,突然恢复了平素不容置喙的神态,命令道:“波波夫!带我去无线电室!必须通知北部哨卡封锁出口……”
阿尔乔姆用肩膀架住指挥官,二人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空旷的列车,避开撕打的人群,越过尸丘,向无线电室走去,电话就安在那里。指挥官的伤势看来并不致命,但他失血过多,勉强撑到无线电室,力气已经耗尽,昏迷过去。
阿尔乔姆将桌子挪过来挡住门,跳到无线电台旁,开始呼叫北部哨卡。话筒里响起一阵肺痨病人似的咳嗽声,随后便哑巴了,像个死人一样。
假如隧道出口已经来不及封锁了,至少要向多勃雷宁站示警!阿尔乔姆一步蹿到电话旁,按下了控制台上两个按钮中的一个,等了几秒钟……电话还没坏:话筒里起初只能听到回声,随后便听见了嗒嗒声,最后响起了嘀嘀的提示音。
一,二,三,四,五,六……
上帝啊,快点叫人接电话吧。如果他们还活着,如果到现在还没有被感染,就让他们赶紧接电话,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千万不要等到感染者闯入他们的站台。阿尔乔姆情愿抵押自己的灵魂,只要有人接电话!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七声提示音响到一半就被打断,隐约听到哼哼声和遥远的喧哗,一个紧张得发颤的声音急切地喊道:
“这里是多勃雷宁站!”
****
囚室里一片昏暗,但即便如此吝啬的光线也足以使荷马看清楚囚禁者的剪影了:过于瘦弱、萎靡,不可能是队长。那好像是个稻草人,死气沉沉的……是卫兵,而且是死掉的!猎人去哪儿了?!
“谢谢,我还以为等不到了。”一个粗重低沉的声音从背后远处传来,“我在里面……太憋闷了。”
梅尔尼克转动轮椅的速度竟比荷马扭头的速度还快!在通道处,一个魁伟的身躯堵住了通往站台的去路。猎人的十指紧紧扣在一起,仿佛两只手互不信任,在防备对方逃脱一样。他侧身站着,用正常的半张脸孔对着众人。
“是……你?”梅尔尼克面部的肌肉剧烈抽搐着。
“眼下还是。”猎人说着,怪异地咳了一声,若非荷马知道猎人从来不笑,一定会将那声音错当成笑声。
“你这是怎么了?……你的脸?……”梅尔尼克真正想问的显然与脸无关,他大手一挥,将卫兵们全轰了出去,只留下了荷马。
“你看上去也不咋的。”队长又咳了一声。
“这不算事。”梅尔尼克嘴一撇,“只可惜,没法拥抱你了。真是见鬼……你死哪儿去了……我们找你找得好苦!”
“我知道。我必须……一个人独处。”猎人吞吞吐吐地说,“我……我不想接近人群。我想永远地离开,但我害怕了……”
“当时发生了什么,黑暗族怎么了?这是它们弄的吗?”梅尔尼克朝猎人脸上的疤痕抬了抬下巴。
“不碍事。我没能消灭它们。”队长伸手摸了摸伤疤,“我斗不过它们,它们把我……摧毁了。”
“当年你是对的。”梅尔尼克的语气突然激动起来,“原谅我,我起初没当回事,没信你的话。我们当时也确实……你自己也知道……但后来我们找到了它们的老巢,把它们全炸飞了。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以为你被它们……我之所以炸它们也是为了给你报仇。我把它们一个不剩全炸死了!”
“我知道,”猎人哑着嗓子,同样激动地说,“它们早就料到了会是这种结局,就因为我。它们知道一切。它们能预知每个人的命运。你根本想不到,我们对抗的是谁……是他最后一次冲我们微笑……派来了它们……为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可我们……我开了头,你收了尾。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因为怪物……”
“你在说什么?……”梅尔尼克听得一头雾水。
“当我去找它们时……它们向我展示了我自己。我就像照镜子一样,看见了一切。我完全看懂了自己,也看懂了人们,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梅尔尼克惊恐地盯住自己昔日的同伴,迅速瞅了一眼门口——他是否在后悔自己喝退了护卫?
“听我说。我用它们的眼睛看见了自己,不是外表,而是内心……在皮囊之下……它们把我的内心召唤了出来,放在镜子里,好让我看见——一头食人魔,一头怪物,总之绝不是人。我被它吓坏了,我醒了过来。我以前一直在欺骗自己……我对自己说,我在保卫,在拯救……但那都是谎话。我只是一头饥饿的野兽,甚至还不如野兽。镜子消失了,可它……却留在了我心里。我醒过来了,从此再也无法入睡。它们本以为,我会把自己杀死,不然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我没这么做。我觉得自己应该抗争,起初是一个人,远离人群……以免被任何人看见。我原本以为,我可以通过自我摧残,用疼痛将那头怪物逼出来……”他说着,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脸上的伤疤,“但后来我发现,如果周围没有人,怪物就会苏醒,我就会忘记自我,于是我就回来了……”
“你这是被它们洗脑了!”梅尔尼克焦急地喊。
“但没关系,都过去了。”队长将手从伤疤上拿开,声音重新变得僵死低沉,“差不多都过去了。那个故事已经翻篇了,干了就干了。我来不是为了这个。图拉站发生了疫病,完全有可能传染到塞瓦斯托波尔站和环线,是靠空气传播的病,致命的传染病。”
“还没人向我汇报。”梅尔尼克疑虑地看着猎人。
“他们没向任何人汇报,他们在撒谎、隐瞒,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想让我做什么?”梅尔尼克驱动轮椅靠近猎人。
“你知道的,威胁必须清除。给我身份铭牌,给我人手,还有喷火器。必须封锁并清洗图拉站,如果必要,也包括谢尔普霍夫站和塞瓦斯托波尔站。但愿不会波及更广。”
“一下子灭掉三个车站,就为了以防万一?”
“这是为了拯救其他车站。”
“这样的屠杀会让游骑兵成为众矢之的……”
“任何人都不会知道的。我不会留下任何一个可能的感染者……以及目击者。”
“这么大的代价?!”
“你难道还不明白?如果我们再犹豫不决,任何人都用不着救了。我们知道得太晚了,再过两个星期,整个地铁就会全部感染,再过一个月,所有人都要死光。”
“我必须亲自确认……”
“你难道不相信我?你以为我疯了?你当年就不信我,现在还是不信?”猎人冷哼一声,“没关系,我一个人去,跟上次一样。至少我自己良心能安。”
猎人转过身,推开呆若木鸡的荷马,朝出口走去。但他抛出的最后一句话却像一柄大鱼叉,紧紧地咬住了梅尔尼克,将他拽在自己身后。
“等等!拿上你的铭牌。”梅尔尼克左手探入制服口袋,掏出一块毫不起眼的金属牌,递给站住的猎人,“我……批准了。”
猎人从梅尔尼克瘦骨嶙峋的手掌中抓过铭牌,揣进口袋,默默地点点头,久久地凝视着梅尔尼克。
“你一定要回来,”梅尔尼克说,“我累了。”
“我却正好相反……充满了力量。”猎人又咳了一声,很快便消失了。
****
很长一段时间,萨莎都不敢再次按响门铃,生怕吵恼了翡翠之城的守卫。他们肯定已经听到了,没准已经看清了她的长相,之所以到现在仍没开门,大概是在商议,该不该放这个蒙对暗号的陌生人进来。
假如门开了,她该怎么对他们说呢?
说图拉站发生了疫病?他们会援救吗?他们肯冒这个险吗?万一他们所有人都像列昂尼德一样,能够看穿她的内心呢?是不是应该主动向他们坦白自己感染的心病,向他们坦白自己至今都不敢对自己坦白的事情?……
萨莎能打动他们吗?如果他们早就找到了战胜可怕疫病的方法,为何坐视不管,为何不派人给图拉站送药?难道仅仅是出于对地铁居民的成见?还是巴望着疫病将地铁居民全部消灭?甚至于……病毒会不会正是他们释放的呢?
不!她怎么可以这样想呢!列昂尼德说过,翡翠之城的居民是正直仁爱的,他们甚至没有死刑和监禁。在那样无限美好的环境中,任何人都绝不会心生恶念的。
可既然如此,他们为何不去救人呢?为何不给她开门呢?!
萨莎又按了一次门铃。又一次。
铁门后面一片死寂,仿佛铁门只是个幌子,门后除了数千吨泥土和瓦砾,什么都没有。
“他们是不会给你开门的。”
萨莎猛然扭过头,十步开外站着乐手,面色凝重,神情忧伤。
“那你来试试!也许他们已经原谅你了呢?”萨莎疑惑地看着他,“你不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吗?”
“已经没有人能够原谅了,里面没人。”
“可你不是说……”
“我骗了你,这不是翡翠之城的入口。”
“那入口在哪儿?”
“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双手一摊。
“那你为什么到处都能通行?难道你不是观察者……可你……环线、红线……你现在才是骗我的,对不对?你不小心说漏了翡翠之城的秘密,现在又后悔了,是不是?”她眼巴巴地望着他的眼睛,试图找到对于这一猜测的佐证。
“我自己也一直想到那儿去,”列昂尼德直勾勾地盯着地面,“我寻找了很多年,收集了所有相关的传说,阅读了所有相关的图书,光这个地方就来过不下一百次。我找到了这个门铃……有一回连续按了一天一夜,但都是白费。”
“你为什么要骗我?!”萨莎愤怒地朝他走过去,右手不由自主地去摸匕首,“我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因为我想把你从他们身边骗走。”乐手看见萨莎手里的匕首,一下子慌乱起来,后退了一步,一屁股跌在了铁轨上,“我想,假如能跟你独处……”
“那你为什么又回来?!”
“说不好。”他温顺地自下而上看着萨莎,“也许是我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把你打发到了这儿……我一个人留在那儿,想了很久……人的心肠并非生下来就是黑的,起初是透明的,后来才一点点变黑。人总会为自己找到借口,姑息心中的恶念,但慢慢地,黑斑会越来越大。很少有人能感觉到这点,从内心是看不到的。但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越过了那条界限,由此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我才跑过来对你坦白,因为你不该受这种对待。”
“那为什么所有人都怕你?巴结你?……”
“不是因为我,”列昂尼德叹口气,“是因为我老爸。”
“什么?”
“‘莫斯科温’这个姓氏你听说过吗?”
“没有。”
“那你在地铁里真的算是独一无二了。”乐手苦笑一声,“简单说吧,我老爸是个很大的官,整个红线的统帅。他给我办了个外交官护照,所以我才哪儿都能去。我这个姓氏太特殊了,没人敢冒险开罪我,除了那些无畏的无知者。”
“那你在这干什么……”萨莎后退一步,满带敌意地盯着他,“你有秘密任务?”
“我老爸把我抛弃了,他看透了我,知道我烂泥扶不上墙。这不,我正在慢慢地败坏他的名声。”列昂尼德撇撇嘴。
“你跟他吵架了?”萨莎眯起眼睛。
“谁敢跟他吵架呢?他可是丰碑、至高无上!是他把我赶出来了,任由我自生自灭。我从小就是个呆子,就喜欢图画、钢琴、书——受我老妈影响,她原本想要个女儿的。老爸却一门心思想让我爱上枪炮和阴谋权术,结果都是白费力气。老妈教会了我吹笛子,老爸却用皮带抽我,不让我吹。他把教我学问的教授全赶跑了,派了个军官来调教我,但也是枉费心机。我不喜欢压抑和古板,我渴望灿烂的生活,想搞音乐、绘画。老爸有一回逼着我砸坏了马赛克雕饰,以此教育我,美的事物都是易腐烂的。但我一边砸,一边把所有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能够照原样拼出来。直到现在我都恨他。”
“不能这样说自己的父亲!”萨莎生气地说。
“只有我可以说他。”乐手笑笑,“换作别人,会被枪毙的。至于翡翠之城……最早是我的一位教授偷偷告诉我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暗下决心,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找到入口。我相信,世界上肯定有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为之存在的那些东西是有意义的,所有人都是为了它们而存在的。在那里,我将不再是百无一用的低能儿,不再是养尊处优的统帅之子,而是平等的一员。”
“结果却没能找到,”萨莎将刀重新揣好,冷冷地说,“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
列昂尼德耸耸肩,站起身,走到按钮旁,按下了门铃。
“那里有没有人听到我并不重要,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地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相信它存在,相信有人会听到我,只是现在的我还不值得他们为我开门而已。”
“你就这点追求?”萨莎不屑地问。
“人类自古如此,我自然也是。”乐手又耸了耸肩。
****
荷马追着队长跑出月台,仓皇四顾,但哪儿也见不到他的人影。梅尔尼克也从通道中摇着轮椅驶出,面色苍白,无精打采,仿佛掏给猎人的不仅仅是那块神秘的铭牌,还有自己的灵魂。
猎人跑哪儿去了?为何抛下了自己?不能问梅尔尼克,必须趁早远离这个人,趁他还没有想起自己。于是老人作势追赶队长,匆匆跑开了,唯恐被梅尔尼克叫住。但后者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他。
猎人对老人说他需要他,以免忘记自我,难道只是在撒谎?也许,他只是担心在波利斯就彻底失控,卷入一场胜算不大的战斗。尽管他杀人的本能和本领超乎寻常,但毕竟没法单枪匹马跟波利斯斗,如此一来他就无法到达图拉站了。若果真如此,在陪猎人到达波利斯之后,老人就演完了自己的戏份,该领盒饭回家了。
如此说来,故事的结局也有荷马的功劳,是他亲手推动了结局按照队长——或者代替队长发声的那个怪物——的意愿发展。
那块铭牌是什么?通行证?调兵符?还是赎罪券——用于免除猎人将要犯下的全部罪恶?无论如何,在从梅尔尼克那里获得铭牌和准许之后,队长就彻底放开了手脚。他不打算向任何人坦白。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坦白呢,在他内心占据上风、时不时便会逃出囚笼的那个怪物,根本连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
当猎人赶到以后,图拉站会遭遇什么?一个站台、两个站台、三个站台的鲜血能否止住他的饥渴?还是恰恰相反,这样的祭祀会令猎人心中的怪物胃口大开?
究竟是谁叫荷马与他同行的呢?是吃人的怪物,还是与怪物搏斗的人?在林地站的诡异搏杀中倒下的那个又究竟是谁?在此之后跟老人谈话,请求帮助的又是谁?
也许……也许荷马当时应该射杀他,这才是荷马的真正使命?也许原先那个队长残存的意识之所以拽上他做这次远征,就是为了让他目睹这一切,从而出于恐惧或者怜悯,在黑黢黢的隧道从背后将他一枪射死?队长没法自我了断,于是找了个帮手,这个帮手能够自己猜出一切并果断采取行动,终结队长体内那个日益强悍、不愿死去的怪物?
然而,即便荷马鼓足了勇气,抓住时机将猎人一枪毙命,又能如何呢?单凭他自己是没法阻止疫病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注定的败局之中,老人只有旁观和记录的份。
荷马大致能猜到队长去哪儿了。那个神乎其神的游骑兵团——看来,梅尔尼克和猎人都是其中一员——据说就驻扎在斯摩棱斯克站,波利斯的腹地。游骑兵团宣誓保卫地铁及其全体居民,为其消除其他军事力量无法应对的威胁……这就是游骑兵团允许外界人知晓的一切。
但斯摩棱斯克站戒备森严,老人想偷混进去门都没有。不过,他也没必要去那儿。想再次碰见猎人,只需回到多勃雷宁站,等在那里即可。猎人的轨道车势必会途经那里,然后才会驶向犯罪现场——整个可怕历史的终点站。
怎么办?难道任由他处置感染者,清洗图拉站,然后……完成队长未曾说出的意愿?老人想,自己另有使命:写作,而非打枪;给予不朽,而非夺取生命;不审判、不干涉,让小说主人公自行其是。可是,当站在齐膝深的血泊中时,想不沾染血污是不可能的。谢天谢地,他把萨莎放走了,虽然是跟那个小魔头一起。至少,萨莎不必亲眼见证可怕的屠杀,一场她注定无法阻止的屠杀。
他跟站台的挂钟对了对表,如果队长严格按照时间表进行,自己似乎还有一些时间。
但也只有一两个钟头而已。在这段时间,他还能独处,然后邀请波利斯跳最后的探戈。
****
“那你打算怎样获得进入的资格呢?”萨莎问。
“嗯……听起来也许可笑……用我的笛子。我想它也许能起到作用。知道吗,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昙花一现的。它只存在于乐器奏响的时刻,乐器一停,音乐便随即消失。然而,没有什么能够像音乐这样迅速地感染人,深深地触动人心,令人久久无法平静。触动你的那些旋律将永远留在你心里,这就是美的疗效。我想,可以用它来治愈心灵的畸形。”
“你真奇怪。”萨莎说。
“可现在我突然明白,畸形是无法治愈其他畸形的。假如我不向你坦白一切,这扇门将永远不会向我敞开。”
“你以为我会原谅你吗?原谅你的谎话和戏弄?”萨莎严厉地盯着他。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列昂尼德突然对她笑了一下,“你不是说了吗,我们都有权利拥有最后一次机会。”
萨莎谨慎地点点头,不想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几乎已经相信乐手了,相信了他的忏悔,可万一他又故技重施呢?
“我对你所说的所有话里面,有一句是真的,那种病真的有药可救。”
“解药?”萨莎精神一振,情愿再次上当受骗。
“其实不是药,不是药品或者血清之类的。这种疫病几年前在红线的革新广场站就暴发过。”
“那为什么猎人不知道?!”
“因为没有传染开来,病毒自己消失了。这些病毒对辐射十分敏感,射线会让它们发生变化……好像会停止分裂,这样病也就治好了。需要的辐射剂量并不大。这也是无意中发现的。这就是解药,只需把感染者送到地表即可。”
“真的?”萨莎激动地握住了列昂尼德的手。
“真的。”列昂尼德用自己的手掌盖住了萨莎的手,“只需要跟站台取得联系,告诉他们……”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段时间又死了多少人啊……”萨莎将手甩开,瞪了列昂尼德一眼。
“在一天之内?未必。因为……我不想让你跟那个杀手在一起。”他喃喃地说,“我本来一开始就打算告诉你的,但我想用这个秘密来交换你。”
“你是在拿其他人的命来换!”萨莎恨恨地说,“这连一条人命都抵不过!”
“我情愿拿自己的命来换!”列昂尼德眉毛抖动着。
“这不是你说了算的!起来!我们得赶紧回去……趁他还没有赶到图拉站。”萨莎指着手表,低声盘算了一会儿,惊呼一声,“只剩下三个小时了!”
“不必,我可以动用关系……他们会打电话给汉萨,说明一切。我们不必亲自跑去那里,再说我们有可能赶不及……”
“不!”萨莎摇着头说,“不行!他不会相信的,他根本不会听,除非我亲口对他说,向他解释……”
“然后呢?”列昂尼德酸溜溜地说,“跟他双宿双飞?”
“关你什么事?”她没好气地说,但随即,像凭借女人的本能悟到了支配痴情男人的诀窍似的,柔声加了一句,“我根本不需要他,现在我需要的是你。”
“你也跟我学会撒谎了……”乐手心酸地一笑,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走吧。”
他们花了半个小时才回到运动场站,哨兵已经换岗了,列昂尼德只好重新对他们一一说明,这个没带证件的姑娘是可以进入红线边境的。萨莎紧张地盯着手表,而列昂尼德则紧张地看着她,看得出来,他仍在犹豫,仍在自我斗争。
月台上瘦弱的新兵正往老旧的轨道车上装一些货包,醉醺醺的工匠正装模作样地忙活着,一队穿制服的孩子正在学唱不输于儿童的歌曲。五分钟之内,萨莎和列昂尼德就被查了两次证件,第三次查验——当他们几乎走进通往伏龙芝站的隧道时——尤其仔细。
时间不等人。就连仅剩的两个多小时萨莎都不敢确定,毕竟,猎人是没人敢拦的。检查还没结束,当兵的已经装好了车,轨道车呼哧呼哧喷着气,加速朝他们赶来。这时,列昂尼德做出了决定。
“我不想放你走,但我也拦不住你。我本想尽量拖延,这样你就没必要赶过去了。但我知道,这样的话,我照样得不到你。诚实是泡妞大忌,但我已经厌倦了撒谎,跟你在一起令我羞愧。你愿意跟谁在一起,还是由你自己来选吧。”
列昂尼德说罢,一把从慢吞吞的哨兵手里夺过自己的万能护照,以出人意料的灵巧一拳打在哨兵的颌骨上,将他打翻在地,随即抓住萨莎的手,迎着轨道车走去。轨道车恰好驶到他们面前,目瞪口呆的轨道车手刚扭过头,便看见了左轮手枪黑洞洞的枪口。
“爸爸肯定会为我骄傲的!”列昂尼德哈哈大笑起来,“他对我说过无数次,我做的都是些没用的,整天像个姑娘一样抱着笛子,不会有出息!可现在,我终于像个爷们儿了,可惜他不在我身边!真是遗憾!下车!”他对高举双手的轨道车手喝令道。
车手不顾轨道车还没停稳,顺从地跳下车,嘴上连连求饶,连滚带爬地消失在了黑暗中。列昂尼德将车上的货包一股脑扒下来,随着货包一袋袋掉落在铁轨上,轨道车马达的轰鸣声越来越强劲。列昂尼德和萨莎跳上轨道车,向前驶去。轨道车暗弱的车头灯眨巴着,仅能照亮前方几米远。吱吱吱吱一阵尖叫,像有人用指甲刮擦玻璃似的,从车轮下方钻出一群耗子,四散逃窜。刚才被列昂尼德打倒的那个哨兵慌张地躲到一旁,后方远远传来警报声。弧形拼板越来越快地向后退去,列昂尼德将轨道车飙到了极限。
伏龙芝站一闪而过,猝不及防的哨兵像刚才那群耗子一样惊惶四散,直到轨道车驶出一百米开外,伏龙芝站的警报才跟运动场站应和起来。
“来吧!”列昂尼德兴奋地大喊,“只要能闯过环线坡道就行!那里有个大哨卡……谁都休想拦住我们!”
他知道威胁来自哪里:从通往红线的支线,一盏小型内燃机车的探照灯迎面扫射过来。两车距离只剩下几十步,再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列昂尼德索性将油门踩到底,萨莎眯起了眼睛。现在只能祈祷前面的道岔已经扳开了,两辆车不会迎面相撞。
对面车上的机枪怒吼起来,弹雨呼啸,擦着萨莎的耳朵飞过去。一阵热浪袭来,两辆车奇迹般地错开了,小型内燃机车在轨道车驶入岔道后的一瞬间,飞入了他们原来的轨道。轨道车震颤着继续向文化公园站疾驰,而小型内燃机车则朝相反方向驶去。
他们得到了一个喘息之机,而这足够让他们安全到达下一站了。接下来呢?轨道车速度放缓,开始缓慢爬坡。
“文化公园站离地表很近……”列昂尼德四处环顾着,对萨莎解释说,“地势要比伏龙芝站高得多,只要能上去这个坡,后面就能提速了!”
临近文化公园站,轨道车的速度果然又提起来了。文化公园站陈旧而傲慢,高高的拱顶死气沉沉,半明半暗,几乎不像有人居住。警报正扯着生锈的喉咙嘶喊。砖砌工事后面探出几颗脑袋,后知后觉地在轨道车后面胡乱射击。
“我们也许能保住小命!”列昂尼德大笑起来,“只要再多一点运气……”
就在这时,身后的黑暗中亮起一盏灯光,越来越亮,越追越近——是小型内燃机车的探照灯!探照灯的强光如一杆标枪朝轨道车抛来,两车之间的距离迅速拉近,机枪再次狂吠起来,子弹呼啸而出。
“再撑一会儿!马上就到克鲁泡特金站了!”
克鲁泡特金站的站台被分割成一个个方格,摆满了样式统一的帐篷,因无人打理,像是已经荒废许久。墙壁上画着某人的画像,显然是不久前才漆上去的,油漆有些流了下来。到处插满了旗帜,连成一片。
后面射出一发枪榴弹,墙壁上的大理石碎片瞬间如冰雹一般砸落在轨道车上,其中一片割伤了萨莎的腿,幸好伤口很浅。前方哨兵手忙脚乱地放下拦路杆,但轨道车丝毫没有减速,直接将其撞断,轨道车也差点被甩出轨道。
小型内燃机车越追越近,它的发动机比轨道车强大数倍,能轻易驱动包着铁皮的庞大机身。萨莎和列昂尼德不得不矮下身子,靠轨道车的金属车帮来隐蔽……
几秒钟后,小型内燃机车跟轨道车车身平齐,一场近距离激战在所难免。列昂尼德突然疯了一样,开始脱衣服。
前方又出现一个哨卡,沙袋垒成的胸墙,钢铁菱形拒马,没路了。萨莎和列昂尼德被夹在了两盏探照灯之间,两挺机枪之间,铁锤和铁砧之间。
再过一分钟,一切就全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