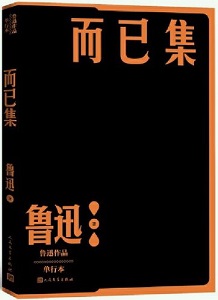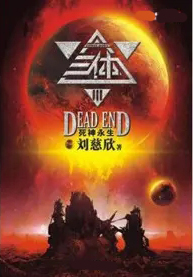被赶走的居民陆续由通道返回阿尔巴特站,负责维持审判会现场秩序的警卫队也卷入了大混战。起义的游骑兵从站台向不同方向退却,阿尔乔姆被汉萨游骑兵夹在中间带走了。但他仍然在充耳不闻的黑衣人身后冲所有人高喊:“世界还活着!我们不是唯一的幸存者!你们被骗了!你们可以离开地铁!你们上当了!不要相信他们!”
于是他的嘴又被封住了。
继续效忠梅尔尼克的汉萨游骑兵向着阿尔巴特站的司令寓所退却。他们将狼狈不堪的上校抬上微微变形的轮椅,送到了他的合法位置——那间张贴着阵亡名单、祭着酒杯的办公室。
阿尔乔姆和同样被当成暴动分子的伊利亚被关在梅尔尼克接待室的隔间,由陌生的士兵看守着,不时有人走进上校的办公室,询问是否立即处决俘虏,但梅尔尼克迟迟没有下令。
走廊里游荡着寒冷的穿堂风,从门板底部缝隙捎来断断续续的谈话:一些来自站台,一些来自上校的办公室。阿尔巴特站听上去似乎聚满了惶惑的人群,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游骑兵的变故,此起彼伏地重复着阿尔乔姆方才的呐喊。
好在用自己换回了阿妮娅,阿尔乔姆想。
至少让她跑出去!
伊利亚瞪大眼睛看着黑衣人,双股战栗,裤裆里散发出一股尿骚味,也许是设想到了子弹射穿脑门的情形。但他没有哀号,只是低不可闻地嘟囔着:“当然了,他自己怎么样都行。他女儿没有指头,他把她交出来了吗?没有,他护着。他能看着她长大,陪她玩耍,他妻子也还活着,没有用连裤袜上吊,身子没有在横梁上晃荡,舌头没有吐在外面,发黑的舌头……”
一位看守右腕带着手表。阿尔乔姆盯着倒立的指针,注视着时间的缓慢流逝。他一遍遍掐算,荷马需要多长时间抵达帝国,想象着跟他一起搞定印刷机,找到干燥的纸张,向老人口述文稿。传单并不需要在全地铁散发,只需把它们送到波利斯和花卉站,全地铁就都能传开了。
除了荷马和廖哈,再没有人知道计划。所有的汉萨游骑兵都聚在这里,聚在梅尔尼克身边。他们正在阻拦一群逐渐逼近的好奇者。
从办公室传来梅尔尼克的咆哮:“给别索洛夫打电话!再打一次!我要跟他通话!跟他本人!”
惊慌失措的、从双轮战车跌落的上校,正急切地给自己的主人拨打电话,却一直接不通。这么说,廖哈还有机会在梅尔尼克通风报信之前找到别索洛夫。
阿尔乔姆再次灵魂出窍,跟廖哈一起,在把荷马送到契诃夫站之后,划船来到妓馆。在游骑兵老战友们的掩护下,穿过嘈杂,像隐身人一样封锁住萨莎的小屋,完成上次失败的刺杀任务。不,不是刺杀,而是将其劫为人质,带领战士们进逼地堡。
“再拨!再拨一次!”
倒立的分针不断后退,过去了半小时,四十五分钟,一小时。站台的喧哗声愈发嘈杂,波利斯管理层派来的代表偶尔虚张声势地喊上两声,但人群并不准备散去,他们追问封锁部队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个疯子嘴里喊的其他城市的幸存者又是怎么回事。
“而我的女儿呢?只不过长了一条短尾巴而已,完全可以剪掉,在产房里就可以。她那么可爱。纳丽奈说,要是女孩,就让她跟亲爱的奶奶叫同一个名字——马林娜,马林娜·伊利尼奇娜,马林娜·伊利尼奇娜·什库尔金娜……”
阿尔乔姆这才反应过来,伊利亚并非自言自语,而是在对他讲述,尽管没有看他的眼睛。他摇摇头表示同情,继续想自己的事。
“你给我闭嘴!”看守扯着嘶哑的嗓子对伊利亚喊,“我脑袋都快被你嘟囔爆了!闭嘴!不然老子现在就把你毙了!反正你们俩早晚都得死!”
“马林娜·伊利尼奇娜……”伊利亚将音量调到守卫听不见但阿尔乔姆能听得出的程度,“小小的马林娜·伊利尼奇娜,她奶奶肯定会高兴坏了……”
廖哈能成功劫持别索洛夫吗?
他又能否带着人质穿越半个地铁?他可是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他只是一个经纪人,而非战士或杀手。在无线电中心他勉强应付过来了,但当时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什么都不用想,唯一的目的就是活下来,可现在……
没事的,他一定能行的。
游骑兵的弟兄们会帮助他的,只要他来得及向他们说明一切。
他肯定能行,毕竟他是第一门徒,跟着阿尔乔姆一路走过来的。他无需劝导,无需证明,自己就能记住一切,感知一切。
“我不管有没有人接!继续打!”
也许廖哈已经抓住了别索洛夫?已经给这个混蛋罩上口袋,拖着他向通往地堡的秘密通道进发了?只要荷马及时地印发传单……不过,即使没有传单……他不是知道一切吗?就算印刷机用不了,他也可以亲口向人们讲述,就像那个真正的荷马一样……
有人在外面挠门。
三个忧心忡忡、愁眉苦脸的人走了进来:一个是身着长袍的婆罗门,一个是头戴双头鹰大沿帽的军官,第三个身着便服。他们敲开梅尔尼克的门,在屋内争先恐后地吵嚷着什么,同样在要求就某些问题给予答复。
站台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发酵,成形,鼓胀,终于酝酿成熟了。这三位使者试图敦促梅尔尼克立即弹压骚动,以免形势失控。
梅尔尼克则不时恶狠狠地骂几句作为回应。
办公室的门微微开启了一条缝。
“我们将召开波利斯议会会议。我们无权保持沉默!让所有人在会上畅所欲言好了,会后再通知居民会议结果。至于游骑兵的分裂……您自己想办法解决!”
“如果整个帝国当真是伪造的,”伊利亚兀自说道,“如果元首本人也是傀儡和叛徒,如果我们那儿的一切都是虚假的,那我算什么呢?为什么那样对我?为什么就因为一条小尾巴就把马林娜杀死?为什么逼纳丽奈上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对我说,写下来,可你叫我怎么写,这些东西该记到哪里,用什么话……”
阿尔乔姆的嘴被破抹布堵着,既没法回答他,也没法请他安静。
久未理发的婆罗门用长袍扫着地上的灰尘,踽踽走到门外,散发着汗臭味道的军官大步跟在身后,不明身份的便衣男子随后也匆匆走出。会见结束了。
“再接着打!”
三位使者的身影逐渐变小,最终穿过走廊尽头仅有火柴盒大小的门洞,走向民众。
“真相!”从外面向敞开的门内爆发出枪炮般的轰鸣。
伊利亚身子贴着墙壁,微微站起身,慢慢朝喊声探过身去。就在整个人都要探过去的时候,他被浑身长毛的看守一拳擂到小肚子上。
门外的人群又爆出一声轰鸣。
看来,人们终于在要求真相了,可阿尔乔姆的嘴又一次被堵住了。但没关系,现在其他人可以替他说了,不仅有人替他说,还有人替他行动。他已经向地铁各个方向派出了信使,即便死也可以瞑目了。
三位使者轮番对醒来的民众哼唱摇篮曲,但民众不吃这套,仍在高声质问。
阿尔乔姆想:谢谢你,飞鼠。
可惜你死了。
不敢相信你死了。
难道说,从今往后你再也不会斜愣着眼瞪我了吗?再不会给我讲笑话了吗?今后你叫我找谁去输血?原谅我,在最后时刻怀疑了你,飞鼠,可是你对我不也是将信将疑吗?
但你仍然说出了那些话,就为了将我救下绞索。
可惜,你听不到站台上的人们在怎样呼唤着真相。
我们正在合力为他们开启气密门,我和你。我们将一起带他们走出地下,重返地面。
其余地方还有我们的人,我们的同志,正在行动。荷马在印发传单,廖哈正用枪抵住别索洛夫的太阳穴,逼他开启地堡。就让梅尔尼克在这儿上蹿下跳、气急败坏吧,这只丧家犬。
他们在波利斯议会上会说些什么?是商量怎么把盖子盖得更紧,还是如何迅速弹压各地的骚乱,将暴动者全部清除,以免关于重生世界的消息在地铁扩散开来?
“继续打!往哪儿打都行!往花卉站打!”
想镇压所有人是不可能的。
“真相!”外面喊声如雷。
“你说的都是真的?”伊利亚一再向阿尔乔姆确认,“你对荷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阿尔乔姆郑重地对他点点头。这位教员脑袋里有什么东西被熔化了?又被重新熔铸成了什么形状?
手表的主人眼睛滴溜乱转,越来越频繁地看表。地铁正在酝酿一场不可逆转的风暴,这一预感透过门缝,从上校的办公室向接待室前厅传来。
他再次想到了阿妮娅。
他想,她爱得多么倔强。
阿尔乔姆则不然,当他最初感受到阿妮娅的冷淡,就开始以冷淡作为回应。似乎他本身无法散发爱,而只能以自己内心的凹面反射阿妮娅的爱。起初,当他感受到阿妮娅投射到自己身上的漫不经心的爱意时,便将其集中成光束,反射回去。她的爱意愈浓,他的爱情也就愈发炽烈。可一旦阿妮娅的爱开始暗弱,他也就随之冷却,直至最终熄灭,失去信念,直至他们的将来在自己内心完全干裂,化为碎末。
而阿妮娅的心脏似乎是完全相反的,表面看去,似乎她已经不再需要他了——因为他那撞上南墙也不回头的死倔,因为他完全不肯妥协于自己的愚蠢幻想,对她的合理诉求则毫不理会。也许,她的确想过率先放弃阿尔乔姆,灯捻上的油眼看就要枯竭。可是,当他一离开,她立刻又燃烧起来,炽热而决绝,以至于阿尔乔姆的眼睛承受不住这样的炽烈,不自觉地想用手掌去遮挡。但即便如此,他终究还是被焐热了,阿妮娅把爱再次投射到他内心,而且比之前更加清晰,更加明亮。
爱情,真是奇特的燃料。
“还是没人接?”
现在也许已经永远打不通了,我的岳丈。时间已经过去了足够多。如果第一门徒行事顺利,如果一切任务都被不打折扣地完成,地堡也许已经被攻破占领,硕鼠们已经在塔甘卡车站被排成一列,穿着自己愚蠢的制服,像小学生回答教员提问一样,接受人民的审问。
“安佐尔!”
安佐尔应声而入,用敌对的眼光打量了一下阿尔乔姆和伊利亚。他听完梅尔尼克的狂吠,将在歪歪扭扭的轮椅上躁动不安的上校推出门外。
“这两个咋办?”戴手表的人问。
“还没决定,等议会开完再说吧。”梅尔尼克连头也没扭,从牙缝里挤着说。
他到底还是没有打通电话。
“把他们留在这儿?”
“对……不,慢着。带上他们,没准儿会用得上,但要仔细看好他们的嘴。”
被堵住嘴的阿尔乔姆和被吓尿了裤子的伊利亚被夹住两腋,从地板上揪起来,被带到了敞亮的阿尔巴特站站台。一行人呈楔形编队,分开人群,不容侵犯地穿过整个站台。他们被周围人的喊声震聋了耳朵,但听不清喊的是什么。
波利斯议会就坐落于此,梅尔尼克的办公室也正因如此才设在这里。
一行人在议会门口停下。游骑兵站成人墙,荷枪实弹,将入口封锁。梅尔尼克和安佐尔走进去,接着又来了几个迟到的婆罗门,然后大门就关闭了。
“听说,有人收到了什么信号……”周围人在嘀嘀咕咕。
“我们好像不是唯一的幸存者……”
“哪儿还有人?什么人?谁说的?”
“等他们出来就清楚了,正开会呢。”
“这怎么可能……那么多年没有消息……可一下子就……”
“游骑兵获知了消息,他们还起了内讧,要不要公之于众。”
“那两个人是谁?坐在长凳上,被铐起来的那两个?”
“恐怖分子。很快就会宣布了。”
阿尔乔姆看不到犯嘀咕的人们,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黑色背影和防弹背心的武装肩带,毛茸茸的后脑勺,叉得很开的黑色足球鞋。但他能够感受到那些人,他们的好奇心使得空气在嗡鸣,氧气在燃烧,墙壁在相互靠近。他们足有上百人。且看梅尔尼克怎样让他们老实地等待答案。
人群忽然喧哗起来。
有人灵巧而坚决地从人群中间挤到前排:“我要去议会!让路!”
警戒线也骚动起来,警卫起初将彼此抓得更紧,但接着似乎有些波动。
听这声音,难道是铁木尔?飞鼠和阿尔乔姆共同的兄弟,他是站在阿尔乔姆这边的,铁木尔……
他不是已经跟廖哈、荷马还有被救出的阿妮娅一起撤退了吗?为什么会在这儿?他不是应该正在进攻地堡么?还是说地堡已经拿下了?给议会送来了别索洛夫的项上人头?
“让开!我受议会邀请!”
警戒线破了一个洞,放进了铁木尔,后面还跟着杜克和卢卡,两人都是游骑兵老成员。铁木尔看见了长凳上的阿尔乔姆,冲他点点头,但没有帮他说情。他只身走进门内,卢卡和杜克留在门外护卫。
阿尔乔姆想:他们在谈判什么?在交易什么?是在拖延时间?发布最后通牒?央求宽恕?还是在研究盘子里的人头?
门内一片寂静。
难道是全部中毒身亡了?
“让路!让路!去议会!”
这次又会是谁?
人群这次的让路不再那么情愿,不大尊重地抱怨着:凭什么我们就该在这儿戳着?阿尔乔姆伸长脖子,黑色包围圈也没有立即给来人让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到来人。
第一个穿过警戒线的,赫然竟是别索洛夫本人。
他还活着!面色苍白,表情凝重,沉默不语。在其身后是第一门徒廖哈。别索洛夫目光阴沉地审视了阿尔乔姆一眼,但没有说话,廖哈则冲他点了点头。两人一同走进门内。第一门徒将他作为人质押过来了?跟他们同来的还有两个游骑兵,留在了外面。
阿尔乔姆从长凳上跳起来,试图隔着破抹布喊出心中的疑问。他的膝盖被人从后面蹬了一脚,一下子跪倒在地,卢卡和杜克向出手的那个人低叱了一声,双双抓住了手枪套。
过了一会儿,手又松开了。
眼下决定一切局势的是门后,而非此地。
空气变得无比沉闷,就像在共青团站的机枪前一样。人们向前拥挤,封锁部队慢慢收拢,但他们无权放弃阵地。青铜枝形吊灯,足有两米长、半吨重,但似乎在迎风摇摆——这么多人在朝着同一方向呼吸。
突然——
一个声音响起,有人在清嗓子。封锁线的战士们顿时紧张起来,人群陷入沉默,所有人都开始向四周环顾。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来自很多个扬声器。原来,这里也有自己的通告系统。
“喂喂,喂喂。”
一个深沉、悦耳的声音传遍了整个站台。
“尊敬的公民,请大家注意,即将发布重要通知,请勿散开。”
“告诉我们真相!说出真相!”人群朝着看不见的讲话者喊。
但那人在清完嗓子之后,就再没了动静。
“重要通知……”
“难道是真的……”
“天哪……”
直至时间完全停滞,大门才终于敞开。一个身穿褐色制服、精明强干的胖子走了出来,他心灵的窗户被装上了玻璃,宽阔而隆起的脑门像拱桥一样伸到后脑。助手帮助他爬上了阿尔乔姆身边的大理石长凳,这样人们就能看见他了。
“是议会主席!……”
随后出现在门口的是梅尔尼克和安佐尔,在他们身后是铁木尔。双方各自走到了长凳两侧。
胖子主席用手帕擤了把鼻涕,接着又用它擦了擦汗渍渍的脑门,然后又用它擦了擦眼镜片,将眼镜架回鼻梁上。
“公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起因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事件。在以保护我们大家为使命且备受尊敬的游骑兵内部,发生了……怎么说好呢,分歧。关于这点我们稍后再讲。”
“别兜圈子了!照直说吧!”
“好,当然,开门见山。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已经确定,当然,这的确不可思议,但我们有不容置辩的证据,我们将对其及时公布,请不用怀疑。总之,我们完全确定,莫斯科不是在最后战争中唯一幸存的城市,我们用无线电拦截到了广播信号。”
人群鸦雀无声。只剩下褐色制服的胖子那令人厌烦的带霉味的声音。
阿尔乔姆沉默地自下而上地注视着他,如同仰视着降示的神明、遇刺前的飞鼠、一位圣人。
“我们会放给你们听,但在听之前,先容我说两句。这对于我本人,跟诸位一样,是真正的震惊,因为这段广播来自大西洋彼岸。亲爱的公民,同志们,兄弟姐妹们,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毁灭我们国家的敌人,将我们一亿四千万同胞埋进坟墓的敌人,杀害我们的父母、子女、妻子、丈夫的敌人,还活着。敌人还没死,战争还没结束,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再也无法感觉到安全。新的致命打击随时可能出现,只要我们以任何方式暴露自己的存在。”
阿尔乔姆拼命挣扎号叫,从长凳上滑下,摔到冰冷的地板上。
“这么多年来,拯救我们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铁。因为我们确信,地表并不适宜居住,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幸存。而如今,这仍是我们继续活下去的唯一机会。我明白,这听起来很奇怪,很难相信。但我请求大家相信,波利斯议会请求大家相信。你们自己听听吧,这是我们今天截取的录音,来自纽约。”
扬声器再次响起,打起了喷嚏。
“咳咳咳……咿咿咿呜……咝咝咝咝……”
接着,响起了歌曲,奇特的异域歌曲,外语歌,伴着鼓点和呜嘿声,伴着军号和喇叭声,一个男声以支离破碎的节奏哭号着,不知是流行乐还是进行曲。女生齐声合唱,与其应和。整首歌曲宣泄着不羁的力量,透露出挑衅、恶魔的欢乐,以及野蛮的生命力。
伴随着这首歌曲可以扭动、跳舞,放荡不羁,随心所欲。
但偌大的白色大理石大厅里,在半吨重的枝形吊灯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动弹哪怕一下。
枝形吊灯在摇晃,如同遭遇了地震。人们吸入鼓点的敲击,呼出纯粹的恐惧。
“你们自己看见了,不,听见了,这是怎样野蛮、禽兽的音乐……换言之,当我们在忍饥挨饿的时候,他们仍在恣意放纵。而且,据可靠消息,他们还留存着核弹。这个敌人是百倍危险的,对此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很可能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了,新的时代开始了。因此……我们有一个通报发布。请过来。”
铁木尔——黑发中夹杂白丝,瘦削细长的身材——走到了褐色制服的主席跟前。他先弯腰拉起阿尔乔姆,帮他在长凳上坐好,然后自己站到了长凳上。
“游骑兵元老不满于前司令梅尔尼克上校的独断独行,我们的同志未经公正审判就被他的奴才残忍杀害。我们为由此引发的骚乱向波利斯公民表示歉意。特此宣布:我们将退出游骑兵编制,拒绝服从梅尔尼克上校的命令。”
铁木尔的话说得断断续续,声音嘶哑,显然是抽烟过多。他是游骑兵团最优秀的侦察兵,飞鼠的老战友和导师。他想干什么?
“斯摩棱斯克站的游骑兵基地由我们接管。我们将公平选举,产生新的司令部。但我们认为,在新的局势之下,不可放任冲突继续。因此,作为新的建制,我们将直接效忠于波利斯议会,我们将誓死捍卫波利斯,抵御任何敌人,无论明暗。”
他转身面向褐色主席,敬礼。
某处响起孤零零的掌声,接着是别的地方,继而,暴雨般的掌声扩散开来,沙沙,咚咚,哗哗。
“好!”“万岁!”“乌拉!”
“白痴!”阿尔乔姆用被堵住的嘴巴冲铁木尔大喊,“糊涂蛋!根本就没有什么波利斯!也没有什么议会!你只不过是效忠于另一个脑袋而已!不要相信他们!”
铁木尔朝他看一眼,点点头:“我们会把你救出来的。我们还要并肩作战,对付美国佬呢!”
梅尔尼克坐在有些变形的轮椅上,沉痛地说:“我不同意对当前局势的处理,但我不会予以追究。我不认为这是哗变,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分歧而已。祖国正处于危难,我们无权内讧,我们将依靠谈判解决。我们的游骑兵已经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我同样代表游骑兵宣誓,效忠波利斯议会。我认为内讧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今后绝不应该再自相残杀。红线、帝国、汉萨……但我们首先是俄罗斯人,对此必须牢记。我们面对的威胁来自我们的宿敌,敌人可不会考虑我们的信仰问题。一旦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活着,他们就会将我们赶尽杀绝,一个不剩!”
人群安静地倾听着,没有一个人敢于反驳,甚至连交头接耳都不敢。阿尔乔姆身子整个前倾,跪倒在地上,挣扎着站起身。紧接着,没等听入了迷的警卫反应过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用脑袋撞在梅尔尼克的太阳穴上,将其连人带车撞倒在地。
“抓住他!抓住他!”
警卫开始拳打脚踢,而阿尔乔姆则拼命用双腿夹住那个老混蛋的脖子,想把他勒死、闷死。阿尔乔姆的一颗牙齿被打掉,破抹布也掉了下来。
“你撒谎!你们都在撒谎!混蛋!”
挤过密密匝匝的人群是不可能的,黑衣人于是将阿尔乔姆拽向门内。梅尔尼克被扶上轮椅,拍掉身上的灰尘。
“狗杂种,神经病!我要把你化成灰,碾成粉!混蛋!你,还有那个忘恩负义的女人!我要把你们两个都绞死!胡说八道,一派胡言!”
铁木尔替梅尔尼克宣布:“被逮捕者是破坏分子,有理由怀疑他是间谍,企图暴露我们。我们正在调查。”
上校被扶回了轮椅,而阿尔乔姆被拖进了门内。门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有很多出口。阿尔乔姆被扔在地上。
他趴在地上竖起耳朵谛听。
“很好,斯维亚托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胖子主席摇晃一下沉重的谢顶的脑袋,“您说的话是金玉良言,您深知人命的可贵,对此我深表赞同。我建议,即刻向红线、汉萨和帝国分别派出我们的外交官,将各方召集到谈判桌上,结束这么多年来我们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我们并没有本质性差异。如今我们应该精诚团结,勠力同心,共同保卫地铁,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是未来数十年间我们唯一的家园,是我们幸存的唯一希望,我们永久的神圣家园!”
“并没有本质性差异,”伊利亚恐惧地重复着他的话,“我们并没有本质性差异,我们和他们……我们首先都是俄罗斯人,团结起来……为什么?为了什么?他们要向帝国派出外交官……我的纳丽奈……”
但人群将他的絮叨吞没。人群起初被突如其来的声明搞得不知所措,现在逐渐缓过神来,开始理解、思索他们所获知的:“美国佬……这么久以来……音乐……吃饱喝足……唱歌跳舞……野蛮……但感觉总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吃屎,而他们连屎也要抢走……我们仅剩的东西……我早就知道……他们不会让我们有安生日子过的……没关系,我们会挺过去的,比这还糟的我们都挺过来了……没关系,也许还会和以前一样……”
“你们知道的,眼下时局本来就不太平。”胖子主席盖过所有人的声音,“蘑菇白腐病将我们的食物储备消耗殆尽,我们得勒紧裤腰带了。但是,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不屈的民族!”
人群的喧嚣不断上涨,他不得不随之调高音量。人群终于嚼碎、吞下了他们所期待获知的真相。
阿尔乔姆无可奈何地坐在墙边,专注地咂摸嘴里难吃的温热血液,用舌头舔舐被打掉的牙齿留下的豁口。
走廊某处突然出现了别索洛夫的身影——他是从会议室出来的?——其后跟着第一门徒廖哈。
“杀了他!”阿尔乔姆冲着廖哈嘶喊,“都是他搞的鬼!”
“这是谁?”别索洛夫没有认出阿尔乔姆,“这里还有其他出口吗?我不想再一次挤过人群了。”
“您的大衣忘拿了,”廖哈对他说,“我回去帮您拿。”
“廖哈!廖哈!你……你在干什么……你不是……你应该……”
“跟上!”别索洛夫大步流星,朝相反方向走去。
廖哈用略带抱歉的语气扭头对阿尔乔姆说:“听我说……我决定……如果我们把他杀了,我们什么都得不到……秩序要从内部改变!循序渐进。起义不是办法,明白吗?……他让我做他的顾问,做他的助理。我会逐渐地……从内部……从地堡里……”
“你这个吃屎的!”阿尔乔姆气急败坏,“你投靠地堡了?为了那些吃的?你为了食物背叛了我?背叛了我们?背叛了所有人?!”
“什么‘我们’?”廖哈翻了脸,“哪儿来的‘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我们’!没有人需要你的变革,除了你!你马上就要死了,而我还要当官呢!”
“廖哈!”别索洛夫传唤他说,“还要我等多久?这就是你刚开始工作的态度?”
廖哈再没看阿尔乔姆一眼,转过身,跑去追赶别索洛夫了。
门哐当一声被撞开,铁木尔闯了进来:“能走路吗?”
“我不想走。”
“快起来!趁他们在演讲,赶紧走!”
铁木尔揪住阿尔乔姆的白色服务生衬衫领口,将他拽起来,把他的胳膊环到自己肩膀上。
“把我也带上吧!”伊利亚低声哀求,“我不想留在这儿!求你们了!”
“这里还有一个出口,我们先去那儿。等老头子回过神来,你就完蛋了,我也救不了你了。”
“要去哪儿?……”
“博罗维茨基站,阿妮娅在那儿等你。从那儿前往林地站,然后再去别的地方。你有地方藏身吗?”
“我可以回家。阿妮娅……她现在还好吗?”
“她在等着你呢!该送你们去哪儿?”
“展览馆站。我不要去林地站,我要去契诃夫站,去帝国。”
“你还去契诃夫站干什么?!”
“荷马在那儿,我要去找荷马。”
“喂!”一个头发蓬乱的婆罗门从会议室探出头来,“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铁木尔,你总该明白吧?……隐形观察者,他们把我们关在这里,你们所有人都被骗了。他们在欺骗我们!”
“听着……你别想忽悠我。我不想掺和政治,我只是一名士兵,就这样。我不能把你扔在这儿不管,但你也别想着给我洗脑。我们最好还是做朋友吧。”
该怎么跟他解释?该怎么向所有人解释?
还有一个机会向人们证明:趁他们用自己的狗屁广播散布谎言的工夫,赶到契诃夫站,帮助荷马印发传单。
三人撞开一道道油漆大门,穿过曲折的走廊通道,不时有人迎面走来,看见阿尔乔姆身上的服务生制服和鼻青脸肿的样子都吃惊了一惊。伊利亚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身后,头顶的灯光忽明忽暗,老鼠在脚下吱吱乱窜。终于,一股消毒剂的味道扑面而来,一派温馨之感——博罗维茨基站到了。
“我们先找到阿妮娅,然后去林地站。”
“我不去林地站,我要去契诃夫站,去帝国。”
“你自己跟她商量吧,你先坐这儿等着,千万别被我们的人看见,明白了?”
“明白,我会小心的。谢谢你,铁木尔。”
他在长板木桌前坐下,将伤痕累累的胳膊交叉放在身前,四下环顾。这是全地铁他最心仪的车站。
暗红色砖墙,空气中弥漫着松香般的消毒剂味道,微甜而清香。一个个小单间,布制灯罩,不知从哪里传来悠扬的弦乐,身着滑稽长袍的人们小心翼翼地翻动陈旧破烂的书本,低声谈论着读到的内容。他们活在自己的书本世界,无论对地上世界还是地下世界都漠不关心。
阿尔乔姆曾经向丹尼尔借宿的那个小房间在哪儿呢?丹尼尔,这位一日之交,却是他铭记一辈子的朋友。他的房间如今也许早被别人占了。
“荷马?”
他站起身。
那个身影很眼熟。
“荷马!”
他是从哪儿到这儿来的?怎么来的?为什么?他不是应该在帝国吗?
阿尔乔姆跛着脚走过去……他揉了揉眼睛。老人正全神贯注地查看一处空房间。一位长着滑稽小胡子的年轻婆罗门正在向他展示房间,交代注意事项,并交给他一把钥匙。
难道是认错人了?
“实在是没地方放桌子了,但您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好在这里有书架……规矩只有一条,不许带宠物,您得跟您的母鸡说再见了。”
“必须这样吗?”
“必须。”
“既然如此——”
“荷马!”
老人转过身。
“大爷……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怎么会在这里……是我们的人把你藏在这儿的?你做到了吗?……印发传单?成功了吗?印刷机还能工作?纸张没泡水?”
荷马像看死人一样看着阿尔乔姆,眼神忧郁而隔膜。
“你为什么不说话?做好了吗?给我看看!”
“阿尔乔姆……”
“你想干吗?”小胡子婆罗门出面干涉。
“传单呢,大爷?你去契诃夫站了吗?”
“需要叫守卫吗?”
“不必。”荷马摇摇头。
“等等,你为什么没去那儿?那些人在阿尔巴特站召开了发布会,对人们撒谎……还是老一套,但所有人都信了……”
“那不是我该干的事,阿尔乔姆。”
“什么?”
“我做不来那些事。”
“哪些事?”
“宣传,印发传单,起义……相对于这些事,我已经太老了。”
“你压根就没去契诃夫站?”
“没去。”
“为什么?”
“我不相信,阿尔乔姆。”
“不相信什么?干扰器?隐形观察者?地上世界?到底是什么?难道你不相信,地铁里的一切都是枉然的?!”
“我不相信人们需要这些。”
“可这才是真相!真相!人们——需要——真相!”
“你别喊。我该向他们讲述哪种真相?”
“一切!你所见到的一切!我所见到的一切!那个脑壳被钢筋敲碎的女人!那个生存空间!”阿尔乔姆使劲摇晃着脑袋,指着一路跟来的伊利亚,“还有他们是怎样朝自己人后背开枪的!怎样因为一条小尾巴就把婴儿杀害的!怎样因为几句话就把人枪毙的!怎样把毫无防护措施的人赶到地面修建风力发电机的!就为了给干扰器供电!还有干扰器!还有野狗吃死人的事!”
“难道这就是真相?”
“不然是什么?!”
“这是胡扯,阿尔乔姆。你以为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吗?他们就生活在这里,他们只是不愿意想起罢了。难道会有人愿意阅读这种东西?那样的话,食人族是怎么吃人的要不要讲?势力高层——不管是汉萨,还是红线——是怎么猥亵孤儿的要不要讲?”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要知道,这也是真相。人们会喜欢阅读这个吗?他们需要这个吗?他们根本不希望了解这些屁事。他们需要的是英雄,是神话。只有在别人身上发现美,他们才能保住自身的人性。我该对他们说什么呢?难道说,有那么一小撮官僚,一直以来都在统治他们?他们完全没有必要窝在地铁里?待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这只能制造混乱、黑暗,阿尔乔姆,而他们需要的是光明!他们在寻找光明,哪怕是蜡烛的火光,哪怕是微弱的火光。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说他们都是奴隶?蝼蚁?绵羊?没有一个人会听你的!他们会把你绞死!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你打算告诉他们什么?用什么来替代真相?”
“我?我会告诉他们……一个传说,一个关于阿尔乔姆的传说。他原本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他生活在一个名叫展览馆站的边远车站,他的家园跟全地铁一样陷入了可怕的险境。危险来自梦魇般的恶魔,它们居住在地表,企图剥夺龟缩在地底的人类最后的庇护所。这个小伙子穿越了整个地铁,在战斗中得到锻炼,最终从一个愣头青成长为大英雄,拯救了全人类。这样的故事人们才会喜欢,因为这是关于他们的、关于每个人的故事,因为它美好而单纯。”
“你想讲述这个?那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呢?……”
“这是政治、鼓动宣传,阿尔乔姆,这是权力的游戏,这一切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我不想写抨击文章,它们活不长久。”
“那你想要什么?永恒吗?”
“永恒……这个倒不敢奢望……”
“我不许你写我,不许,明白吗?!”
“这已经不再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全人类了。”
“我不想在你那胡说八道的故事里做一个跳梁小丑!”
“人们会阅读它,知道你的故事。”
“我根本就不在乎人们知不知道我!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你还年轻,阿尔乔姆。”
“跟年轻又他妈有什么关系?!”
“你别这样……跟我讲话。你是英雄,人们会了解你,你将为人们所传诵。你还会有孩子的,也许会有。而我呢?我怎么办?我能留下什么?默默无闻的传单?无人问津的豆腐块?”
“等等……他们给了你……这间房子……是不是?”
“他们为我提供了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你会为了他们写作?为了别索洛夫?写我?他们把你收买了?!”
“究竟是他们收买了我,还是我收买了他们呢?会有书问世的,一本关于你的、真正的巨著,以及可观的印量。我想不通,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阿尔乔姆!”——是阿妮娅。
“你可以问问伊利亚,他会告诉你的。谁会拒绝这个呢?真正的巨著,署着我的大名!不是为食人魔编写的教科书,而是神话、传说,它将永世流传。”
“他们把我们踩在泔水里,把我们当牲口,当建筑材料,根本不把我们当人……而你,你在为虎作伥……你……”说到这儿,他像突然被爆炸波击中了一样,一下子被震醒了,再也说不出话,只是翕动着嘴唇,喃喃自语道,“该死。他说的对,他说的全对,那个败类。根本就没有什么‘我们’和‘他们’,有的只是九头蛇怪,我们自己就是,他们就是由我们组成的。贵族阶级其实早就没了,所以地堡那些人又是从哪儿招募来的呢?就是从我们中间。这怪谁呢?谁也不怪,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这样干的。事到如今,你,廖哈……我怎么可能打败这个九头蛇怪?没有任何人真心打算跟它搏斗,每个人都梦想着向它献上自己的头颅,成为它的一个脑袋,每个人都对它说:来吧,要我,带我走,我想成为你,追随你。屠蛇的勇士一个都没有,而蛇头却排成了长队。这是怎样的政权……不过,这跟政权又有什么关系……上帝啊,我真是蠢蛋……好吧,大爷,你写吧,印吧。祝你长命百岁。上帝啊,该死……”
他爆发出一阵大笑。
他原本害怕自己会号啕大哭,结果笑声却从嘴角汩汩涌出,像抽羊角风的人口吐白沫一样。
“阿尔乔姆!”
他看见了阿妮娅,跪倒在她面前。
“原谅我。”
“阿尔乔姆,你怎么了?”
“你真要去契诃夫站?”铁木尔问,“帝国很快就要返回那里了,不然还是去林地站吧?”
“不。把气密门打开,我要上去,从地面上走。”
“你疯了?!”
“打开气密门,打开!”
“阿尔乔姆,出什么事了?”
“我们从上面走,阿妮娅,从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