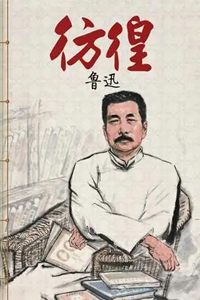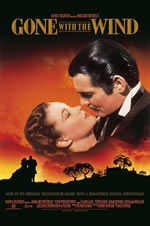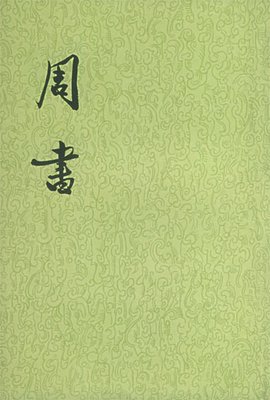我从不敢轻视的两种行业“小人物” ,文化界有两个行当,从业人员很不起眼,也基本都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高手如云卧虎藏龙,实在是不可小觑:一个是中学教师,另一则是报刊出版社编辑。他们这些人,可能终其身都在“潜水”,名不见经传,可才学并不比大教授名学者流差。所以,我常常觉得,中学、报社、出版社,是很埋没人才的三个地方,简直是西湖梅庄的地牢。让任我行陷在里头,也极难出头。
先说中学老师。对于他们,我晓得很多人是怀有偏见的。由于待遇差,一直有一种很流行的意见在说,国内的中小学老师,都是“不入流”的学校里“班级倒数前几”的人,才会分流去的,自然很容易看轻。这个也不好说是诋毁胡说。比如我上学那会,一般来说,211以上大学毕业生要是“沦落”到中小学当老师,似乎都是奇闻,普通大学里成绩不错的也基本跑去考研考公甚至做生意去了,剩下的才是中小学教师主力,除非是贫困生上了免费师范签了合约不得已的。当初郭德纲解释相声界为啥整体水准不行,原因在于“门槛太低”,尴尬是类似的。再加上这些年中小学恶性内卷,很多教师本身也的确德与学不配位,导致社会对他们总体观感说不上好,多的是“脸上笑嘻嘻心里mmp”。老实说,我有时看家长群里老师的发言,也会不想让小孩再去上学了。 这个复杂的“观感”里面,自然也还有这么一项:对这个群体才学的否认。觉得你就是个领着四五千可怜薪水、没啥能力的“孩子王”,懂啥呢?这是很根深蒂固的偏见。话说我有一位朋友,还是某著名省重点的语文老师,有次看一位名教授公众号文章,发现不少似是而非的失误,一时技痒私信过去“商榷”,而且出于礼貌还表明了自己身份,哪知那位“望重士林”的教授直接回怼,大意是“你一个中学老师,考我研究生都不收,别不懂装懂”,顺带还把他拉黑了。可实际上,那位朋友潜心研究这个问题很多年了,功底不下专家,评议很切当,措辞也很得体,就因为是“区区中学老师”,没法平等对话,得不到丝毫尊重。流俗的毁誉一旦固化,会犹如条件反射,也是很可怕的。
这个复杂的“观感”里面,自然也还有这么一项:对这个群体才学的否认。觉得你就是个领着四五千可怜薪水、没啥能力的“孩子王”,懂啥呢?这是很根深蒂固的偏见。话说我有一位朋友,还是某著名省重点的语文老师,有次看一位名教授公众号文章,发现不少似是而非的失误,一时技痒私信过去“商榷”,而且出于礼貌还表明了自己身份,哪知那位“望重士林”的教授直接回怼,大意是“你一个中学老师,考我研究生都不收,别不懂装懂”,顺带还把他拉黑了。可实际上,那位朋友潜心研究这个问题很多年了,功底不下专家,评议很切当,措辞也很得体,就因为是“区区中学老师”,没法平等对话,得不到丝毫尊重。流俗的毁誉一旦固化,会犹如条件反射,也是很可怕的。
可中学老师里就是有很多厉害的人。钱锺书生前就感慨说,“中学教师里真正有学问的人是很有一些的”,这是有的放矢。不说如今“钱学”里头,成绩最好的就有几位是中学老师,钱当年刚出版那几部“天书级”著作时,能给他写信指出错误的高手里,也有好几位正是中学教师,所以连钱这等不世处的博学宏儒都是不敢小觑这个群体的。我还记得我上中学时,班主任是一位女物理老师,平日不显山露水的,看不出任何过人之处。可是,毕业很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晓得,早些年她就是一家旧诗词网站的“名角”,还以化名出版过旧体诗词集,在业内小有名气。后来阅历渐多一点,就慢慢明白这样大隐隐于中学的“民间高手”所在多有。比例也许不大,千里挑一吧,但总量很可观。
文字编辑就更不用说了。我自己就亲身见识过不少。平日里,附庸风雅舞文弄墨惯了,偶尔也会在报刊上蹭点版面,和不少编辑打过交道,体会很深:每每自觉已经很完善的稿子,见报后一看,如果有所改动,那必然都是妙招,有的简直鬼斧神工,心悦诚服!这些人可说是文字行的老师父,寥寥几笔,当做颊上三毛,武功深不可测。所以,平素见到文字编辑,咱都是很恭敬的。名教授大学者浪得虚名的多了去了,这类“小人物”反多沉潜有道的高明,理应高看一眼。
说来也是挺辛酸挺不合理的,中小学教师是为小孩子俯身作“孺子牛”,文字编辑则是默默“为他人作嫁衣裳”,都带有低报酬高奉献,而且躲在幕后的性质。这样的行业性质,决定了即便是高手,想要冒头也是极难。甚至,我听说,像出版社编辑这个行当,在港台地区和西方世界,“责任编辑”按规则名字都是不出现在书里的,不管你为之出了多少力,订正了多少内容,都只能彻底隐身,简直是不公平到顶点。我熟悉的一位朋友,就供职于海外某大学出版社,仅我所知的某部近年来很受追捧的学术名著(前段时间还看到豆瓣有人如此评论这本书:“本科同学说,不嫁没读过这本书的人”),她就跟进了一年多,期间大到提供资料,小到修缮词句,贡献几埒作者本人,但是书出来后,她的大名是找不到丝毫踪迹的。按我这俗人的看法,她饶是能力如齐天大圣,似乎都只能乖乖做“扫地僧”,深可叹欤!这样低调且不得不低调的“幕后英雄”,报刊界、出版界,委实是不少的。
记得以前中华书局有位编辑名叫曾次亮,一生精研历法,熟稔到明清哪天下雨哪天下雪都了若指掌,日后研究《红楼梦》判断出曹雪芹生卒日,就是从气候角度断定的,有若神明。可如此能人,俨然大师,就是没几个人知道,有个别人听说他,还端赖他有个著名女婿——国内大学中文系文学理论统编教材的作者童庆炳。怪不得,我听说编辑基本都不希望儿女“承继父业”,来个“克绍箕裘”啥的。
来源:留愚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