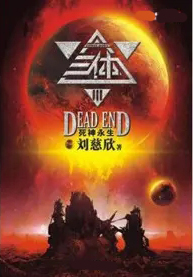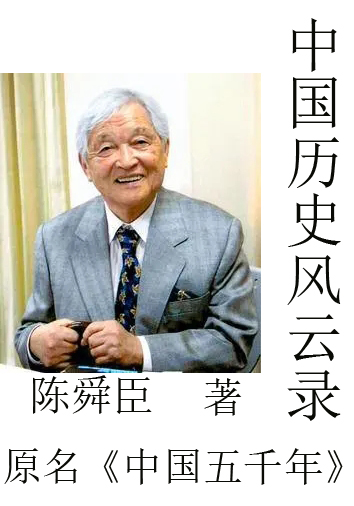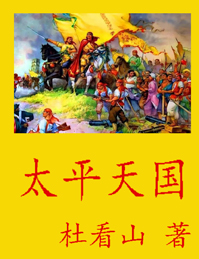香港那一波起高楼的巨富,绝大部分靠的是投机思维和钻营政商关系,利用了资本主义的特许和社会主义的准许,完成的巨额财富的积累,其中尤以四大家族为代表。

最近企业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李嘉诚向贝莱德资本出售巴拿马运河的港口,被指为离了心的企业行为;另一件则是李兆基的去世,由于其重仓在香港和内地,被很多人称为李嘉诚另一面。
目前四大家族,或者说香港巨富的第一代,基本就剩下李嘉诚了。
严格意义上说,他们这一代进入我们内地视线,大概是与我们改革开放同步,当时各个大佬都是携款几十亿的资金,“驰援”祖国,于是在北京和上海的核心地段,几乎都被他们占据。可能现在说几十亿,差不多就是一个大项目的投资,当年约等于很多省份一年的财政收入。估计当时刚毕业的许家印也不敢想,有朝一日能成为他们的牌友。
事实上80、90年代我们内地对他们的崇拜,几乎于造神了,于是经营之神、股神、船王基建之神等等,神话至妖魔化了。毕竟当我们还在使用最大币值在10元的年代,几十亿的冲击力,至今都缓不过来。
现在想想当年的造神或许是场合谋,政府需要投资、企业家需要标杆、媒体需要吃饭、群众则需要慕强。当时企业界最流行的做法就是去香港朝圣,朝圣最多的就是李嘉诚和李兆基。
既然造神,那么神的话,我们很多也照做了,对后世影响最深远就是我们的金融改革和房地产改革,这两个行业深化改革,基本都是采用的香港模式。尤以地产为甚。
听最早经历过海南地产泡沫的老地产人讲,其实当时我们有两个模式可以选择,一个是香港模式,一个是美国模式,通俗的说,一个是期房模式,一个是现房模式。再进一步说,一个是可能烂尾的模式,一个是不会烂尾的模式。
最终在这几位大神的“参谋”下,我们选择了香港模式,同时也匹配了该模式下的金融改革,从此我们有了三座大山中的最大的那座。

钢琴曲掩盖枪声VS干就完了
如果你明知道一个地产商是通过政商关系,获取的优质土地,你会怎么想这个地产商;
如果你背负的高房价,就是几家大地产商合谋的产物,你会怎么想这些群体;
如果你的按揭贷款还是他们提供的,而且利率不低,你会怎么想这些企业家;
如果你的菜篮子,也由他们提供,你会怎么想他们;
如果你的养老保险,还是他们提供,你会怎么想;
如果你用的天然气、汽油,又是他们提供,你会怎么想;
当然这还不包括你去的购物中心,你办公的地方,甚至你终极的陵园,都是他们提供。
说实话,这些动作,不就是十几年前的地产商、十年前的银行、五年前的电商、一直的两桶油嘛,这些企业或者企业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几乎是我们“申讨”最多的企业或者群体。他们毕竟还处于垄断的初级阶段,手段并不高明,而且我们还可以用最激烈的语言去反击,甚至投诉。
然而这些,就是香港四大家族做的事情,当然他们还垄断了电力、码头等等民生设施。学过政治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这些在内地也是国家层面解决的事。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控制了媒体,甚至包括内地的媒体,让这一切的发生似乎是理所应当了,他们把钻营政商的黑金史偷换成个人奋斗史,在内地宣传。
每个家族都有一战封神的历史。只是不能深挖,深挖约等于刨祖坟了。
不只是李嘉诚的有“超人”称号,四大家族每个人都像是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实则是个冷笑话。他们最擅长的不是造房子,而是造“政商永动机”——上世纪70年代囤地,80年代炒楼,90年代玩金融,这些动作,在90、00、10年代,在内地又玩了一遍,即便到海外也是路径依赖。他们的第三代都已经进入了各皇室成员的朋友圈,他们的商业哲学就八个字:“买下一切,然后涨价”。这和内地许老板们的“高杠杆盖楼,快周转套现”有什么区别?
四大家族创造了独特的“三维制导”模型:通过垄断土地供给制造空间稀缺(第一维度),操控金融市场进行资本增殖(第二维度),渗透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控制(第三维度)。比如新世界发展旗下周大福集团控制着香港26%的巴士线路和15%的电力供应,这种产融结合的统治术,将市民的衣食住行都变成利润源泉。
他们的徒子徒孙内地地产商则发明了“高周转腾挪术”。我的前东家碧桂园"456"模式(4个月开盘、5个月回款、6个月资金再周转)将商品房预售制推向极致,疫情前Top50房企平均回款周期压缩至6.8个月。当香港开发商用百年地契收割时间价值时,内地同行正在用金融杠杆制造空间折叠。
一定有人说,香港地产商他们建的房子不烂尾,他们的负债率低。其实这个你需要看看他们在内地的开发企业,股权穿透后的情况,也可以看看他们建的产品质量和成本。甚至可以看看他们在税收方面是否于内地开发商享受同样的待遇。
总之能给你看到的,都是别人精心设计的。两种模式本质都是对时空价值的极致压榨,区别只是刀叉与筷子的用餐礼仪。
不过一个用钢琴曲掩盖枪声,一个用干就完了。

文明外衣下“合法抢劫”
香港四大家族最厉害的不是盖楼,而是造梦。他们掌控的电视剧里永远有住在半山别墅的豪门恩怨,却从不拍廉租房里的蟑螂爬过婴儿奶瓶。前几年当内地自媒体在扒万科的精装修猫腻时,香港报纸正在吹捧郭炳江出狱后“回馈社会”——没人追问新鸿基在金融危机时如何用“呼吸Plan”让10万家庭破产。
同时他们的公关术深得殖民统治真传:用专业术语制造认知壁垒,用慈善光环转移阶级矛盾,用司法程序消解民众抗争。2016年我们内地长沙业主因学区房维权被拘留,同年香港海景豪宅虚假宣传被判罚200万,看似法治差距,实为统治策略差异——一个用警棍维稳,一个用法律当镇静剂。
现在看来我们对内地开发商苛刻了,原本被我们申讨的内地开发商嗜血的一面,在四大家族面前,属于太“实诚”了。恒大足球俱乐部烧钱120亿时,连广场舞大妈都知道许家印在搞政商投机。可当李嘉诚投资Facebook、Zoom时,香港市民真以为“李超人要带我们科技转型”——其实他不过是把从香港楼市吸的血,换成其在硅谷的政治资本筹码。
更讽刺的是“地产霸权+金融镰刀”的组合收割。我们的地产商再无情,再想做作,他们也不可能操作银行,只是会行贿而已,只能小范围之内,想为所欲为,几乎不可能。因为金融端在产业鄙视链的上端,不是那么好配合的。
而香港四大家族则不同,都是左右手的关系,比如新世界,一边把香港国际机场商铺租金涨到3000元/㎡/月,一边通过旗下周大福金融发行年化8%的理财产品。小摊贩白天交完租金,晚上就把积蓄送进郑家的钱柜。这种“闭环收割术”,内地P2P看了都直呼内行。
两种模式本质都是“割韭菜”,区别在于工具选择。四大家族用信托基金把资产转移到开曼群岛,内地老板用VIE架构在美股上市;香港用《土地收回条例》强征丁权地,内地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推平城中村。当李嘉诚说“我们永远看好香港”时,他家族78%的资产已在欧洲基建里生了根。
我估计一定有人说,这是商业模式问题,也有人说这是商业的选择,他们战略的高明之处。
还记得当京东、淘宝进入社区生态时,我们申讨他们:与民争利。我们当时理所当然的把他们应该对标的对象是马斯克、贝佐斯、扎克伯格、比尔盖茨,最次也是巴菲特。
那么香港人民,是不是也该这么想呢。别忘了,这些大佬很早就赚取了第一桶金。
其实我们评判一个企业家是不是牛逼,就是看他赚取第一桶金后的表现,如果还痴迷于投机和钻营,那充其量只是一个巨商,似乎达不到企业家的层面。
巨商是挖掘和垄断存量市场,进而需要有文明的外衣来包装。
企业家则是增量市场的创造者,不需要太浮夸的包装。
最近刚看完《李光耀传》,李光耀在书里评价过四大家族,大致意思是他们很有钱但从未打造过一款畅销世界的产品,投资的生意主要是房地产,码头,电信,电力,超市等基础和民生领域,依靠垄断和结盟赚钱,他们无疑拥有低买高卖的超级交易能力,但实际上对经济却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这虽然不妨碍他们仍是商业教科书的经典案例。
不得不说还是同时代的人了解他们。
来源:高谈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