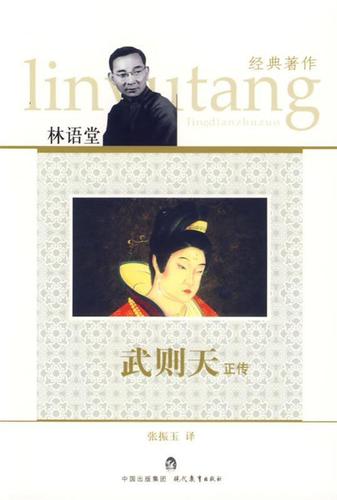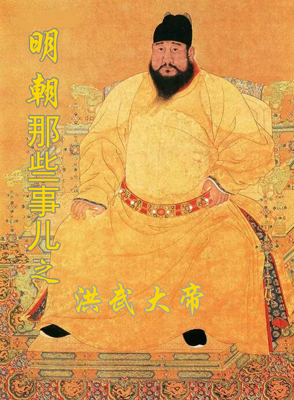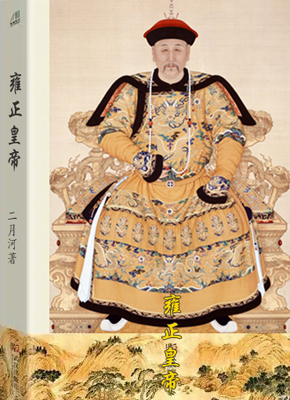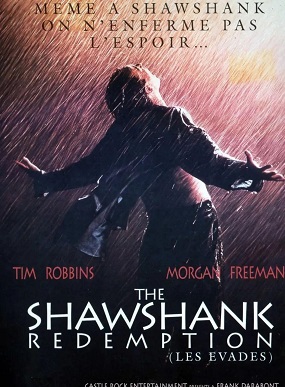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三汲乡王厝墓出土“中山三器”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白狄族的鲜虞部落在太行山东麓建立的一个国家,它地处燕赵两国之间,是秦、齐、楚、燕、韩、赵、魏之外的一个小国。中山国的历史文献所载仅有片言只语,人们对王室世系并不清楚。
20世纪70年代,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汲乡发掘了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了大批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其中铁足铜鼎(大鼎)、夔龙饰铜方壶和(子次)圆壶3件青铜器上都有长篇铭文共上千字,仅大鼎铭文就有469字,创战国时期青铜器长铭之最,此件青铜器被人们称作“中山三器”。
这3件青铜器,大鼎为铁足铜身,通高51.5厘米,腹径65.8厘米,重60公斤。自鼎钮以下至腹足部以上,有铭文469字。记载了相邦司马贾(“贾”,早期释为“赒”)领军伐燕,开疆扩土的事迹,告诫后代吸取燕国“子之之乱”的教训,警惕周边诸国。方壶通高63厘米,腹径35厘米,重28.72公斤。壶身四面有铭文450字,颂扬了中山国伐燕的战绩,讲述了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和安邦定国的道理,铭文中提到了国君的名号。圆壶通高44.9厘米,腹径32厘米,重13.65公斤。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铭文歌颂了的慈爱贤明,赞扬了相邦司马贾率军伐燕取得的战果。此外,圈足还有铭文23字,记录了壶的重量和制壶工匠的名字等。

铁足铜鼎铭文(局部)
中山三器铭文的发现,为研究战国时期中山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三器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的历史,补充了文献中的缺佚。如方壶铭文中的“皇祖文武、桓祖成考”,就记录了4位先王的庙号,连同制作器者王厝,制作圆壶者(子次),再加上最后的国王尚(也称胜),这就衔接起了前后共7代中山王的世系,对文献所载中山武公前后的历史作了重要补充。
中山三器铭文(圆壶铭文前22行除外),不同于以往所见的先秦文字,仔细观摩就会发现,它首先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每一篇铭文在各自的器身上,都经过精细的计算,布局匀称,疏密有致,行间分明,不仅和器物的造型和谐统一,还增加了器物的美感;铭文字形修长,古朴典雅。宽与高的比例约1:3,并且,每个字的重心都偏上,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铭文结构清晰,有的字还加了饰笔,相互之间有呼应,也注意了避让,看上去很生动,富有动感;铭文运笔果断,流畅自然,运笔纤细沉稳,笔画多为尖入尖出,横画多藏锋,竖画若悬针,弯如蛇弓,富有美感。笔画直线挺劲,弧线圆润遒逸,富有弹性,弯曲的弧度彰显了生命的力量,显得非常有活力。

郝建文老师中山篆书法作品
中山三器铭文,可以说是庄重书体,它大气端庄,富有庙堂之气,在战国文字中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国最美古文字”,人们也将这种书体称为“中山篆”。目前,中山篆爱好者遍布全国各地,日本也有一些研究中山国文字,并用中山篆搞书法创作的学者和书法爱好者。
关于中山三器铭文是刻还是铸的问题,近几年有一些讨论,而且关注度也很高。中山三器出土后,发掘者认为那些文字是古人在青铜器上镌刻的。发掘报告写道:“刀法娴熟,横竖刚直,圆弧匀畅,刀锋细锐,构字秀丽,粗细、深浅匀称,是工匠高超技艺和锐利金属工具相结合的产物。刻字前先轻轻地划出横竖格线。格线细如毫发,时隐时现。”刻铭之说被广泛引用。但是铭文上少见凿刻痕,又无法解释。

铁足铜鼎局部特写
2017年,我用微距镜头仔细观察,发现圆壶铭文有的字口边缘微微隆起,凹槽底部平缓圆滑,没有一丝的刀痕。为此我咨询了从事铜雕工艺的朋友,他告诉我青铜器硬度很高,质脆,在上面刻字字口边缘难以形成隆起,而且,更不会没有凿刻的痕迹,尤其是笔画转弯处圆润自如,还看不到刀痕,这是不可能的,应该是铸铭。另一位搞铸造的专家告诉我,铜水有收缩性,只有铸造的铭文才会有看不到刻凿痕的现象。
2021年夏天,我通过微距镜头,又在方壶器身下半部一些铭文发现有二次加工(补刻)痕迹。有的是对某一铭文进行过补刻,也有的是对铭文某一部分笔画进行补刻,有的补刻的笔画外面还留有铸铭痕迹。补刻和铸造的笔画有明显错位,且笔画质量很差。在大鼎铭文上我发现笔画被残留物堵死的情况,如“否”字,在灯光从侧面照射的情况下,上部“不”字的竖笔画被填充物断为两段(在拓片上可看到竖画是断的),我怀疑那填充物可能是铸造的残留物。更有意思的是,铭文圆点像是用圆头工具摁上去的,底部平缓,光滑,并非刀刻能完成。方壶铭文中有两个补刻的圆点,一个是沿着圆点的外轮廓刻线,另外一个是在圆点里刻了一个小坑。由此看来,古人并没有什么“神器”。
另外,古人在“写”这些铭文之前,曾用“硬笔”起稿,所以留下了一些痕迹。还有一些不是铭文笔画的线条或划痕,可能是古人手中的“笔”不小心留下的,这些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些铭文是在比较软的泥模或蜡模上用“硬笔”书写或者刻的。由此看来,中山三器铭文从整体上是铸铭,只是对没有铸好的个别铭文进行过补刻。
2021年秋天,苏荣誉、李耀光发表《论战国中山王厝鼎及其铭的铸造》的文章,他们通过X光成像技术对鼎(大鼎)进行了探究,认为铭文“绝大多数字和绝大多数笔画都没有錾刻痕迹,应铸造成形,个别笔画的某些痕迹,应该是对个别笔画的加工痕迹”。这也印证了我的观察和分析。
文 / 郝建文 (河北博物院研究员 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原载《思维与智慧》2024年第02期
注:“厝”“子次”等生僻字以学界通用读音字代替。
来源:中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