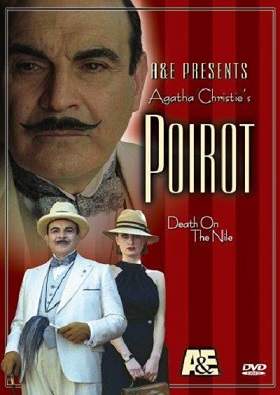阳石公主这些日子就像刚刚绽放的月季,眼角眉梢都洋溢着喜气。
霍去病班师回朝的消息,让她觉得冬天的脚步似乎还很远,长安的每一缕阳光都比往年这个时候更加温暖,惬意。
可是,她却有些心不在焉了。
她不时地抬头看着天空,就埋怨时间过得太慢。她看着眼前穿甲戴盔、全副武装的宫娥们也开始不顺眼了。
“看看!你们都成什么样子了?稀稀松松的,还像个士卒么?”阳石公主朝指挥演兵的宫娥喊道。宫娥们的招式顿时乱了,有的干脆傻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阳石公主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上前就给了宫娥一马鞭:“知道卫大将军和霍将军是怎样演兵的么?如果在他们那里,你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宫娥手中的剑“当”的一声掉在地上,眼泪也哗哗地挂在腮边了,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求饶道:“公主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
“起来!”
阳石公主让宫娥们站成一排,挥舞着手中的宝剑道:“霍将军征讨河西,现正率十万降卒班师回朝。他是本宫的表兄,本宫是要请他来观看演武的,你们这个样子不是给本宫难堪么?你们继续练习,如果敷衍应付,小心本宫的鞭子!”
她想了想自己这会儿的心情,暗自笑道:自己心里不平静,心猿意马,却拿宫娥出气,这和表兄差远了吧?
她又开始想着法儿来缓和紧张的气氛:“本宫就为你们做个示范。”
说罢,她一人独自拔剑起舞,用心去塑造着自己在表兄心中的形象,她的舞剑让宫娥们看得眼花缭乱。
领头的宫娥知道公主的心事。唉!女人心中装了男人后,不管是痛苦还是折磨,都是幸福愉悦的。这大概就是爱情的魔力吧!
舞完一遍,阳石公主轻轻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对宫娥们道:“你们去练吧,本宫休息一会儿。”
于是,宫娥们重新拉开阵势,每两人结成一对,各自以对方作为目标,开始演练剑法。
她赧颜地笑了,也许只有皇帝的女儿才能如此蛮不讲理吧?
霍去病回朝的日子越临近,她的心绪就越复杂。她希望早日看见他,却又怕因为没有准备好而使他失望。她希望父皇出面帮她玉成婚事,但却从心底里期待这事由霍去病亲口说出来。
阳石公主收回心神,瞧见从花园的偏门进来一个人影——原来是皇后身边的春香,后面还跟着椒房殿的舆轿,说是皇后召见。
阳石公主的脸上立时笑开了花,问道:“莫非是表兄有什么消息了?”
“这……皇后娘娘没有说,只是奴婢看见长公主好像进宫来了。”
阳石公主的脸就立时拉下来了,她知道姑母去见母后,一定离不开她与表弟的婚事。
“不去!”
阳石公主说罢,转身就要往回走。春香上前拦住道:“既然是皇后口谕,公主不去不仅违制,而且娘娘心里也不好受。”
“可去了之后,本宫能说些什么呢?”
“奴婢知道公主为这事烦恼,其实皇后也一样。”春香近前一步,说话的声音明显就低了,“骠骑将军不日即可到京,公主可要拿定主意哦!”
“谢谢姐姐提醒,本宫这就进宫去。牵马来!”
春香忙在一旁道:“皇后娘娘为公主准备了舆轿呢!”
可阳石公主就在春香的呼唤声中跨上了马,就直奔椒房殿去了。
阳石公主的身影一出现在殿门口,长公主的眼睛就顿时亮了,说话的声音也抬高了许多:“哎哟!看看,几天不见又长高了不少,出落得清荷玉立,真是好看!”
“你姑母今天来……”
“姑母有话不妨直说,孩儿洗耳恭听。”阳石公主说着便坐在卫子夫身边,摆弄着手中的玉蝴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长公主见此心里很不舒服,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大大咧咧的了?可当着卫子夫的面,她又不好发作。
她这回来与其说是为了儿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自己。所以她把这一肚子不快暂且忍着,用宽容的语气道:“虽说长得青笋逢春,枝叶翡翠,可毕竟是个孩子,贪玩图新也是常理,譬如伉儿……”
阳石公主斜睨了一眼姑母,不以为然道:“姑母可不能这么说,蕊儿可与伉儿不一样。蕊儿就羡慕表兄,率军征战,建功立业。”
长公主被噎了一句,胸口堵得慌,便把目光投向卫子夫。
卫子夫怎会不明白女儿的心思呢?可她是皇上的姐姐,惹恼了她,后宫也不得安宁。
“你姑母拿来藩国进贡的珍奇宝物,是专门给你的,你看看喜不喜欢?”
“是啊!是啊!”长公主忙令丫鬟捧上一个银盘,上面盛了一簇玉雕的鱼儿,紫中泛红,红中带绿,与真的一般,“女孩子就喜欢这些精致什物,想着便给你带来了。”
阳石公主看了一眼盘中的鱼儿,笑着道:“看来姑母还不了解蕊儿的秉性,蕊儿自小生就一个男孩子的性子,从不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再说这样珍贵的东西,蕊儿怎敢领受呢?”
卫子夫在一旁眼见长公主脸上已阴云密布,正要说女儿几句,却被长公主抢在了前头:“你这孩子怎么如此不懂长幼有序?本宫好心来看你,你却是如此轻慢,看来是本宫高攀了!”
长公主说着,又把矛头对准了卫子夫:“皇后是怎么教的女儿,没大没小的。伉儿哪一点不好,怎么就配不上她呢?好了,就算本宫自作多情,此事不劳皇后,本宫直接面奏皇上好了,告辞!”
卫子夫忙起身挽留,阳石公主却笑了,上前挽住长公主的胳膊道:“弄了半天,姑母是为了伉儿的事啊!既是如此,姑母何不早说?为何还要转这么大一个圈子?”
卫子夫也劝道:“都是蕊儿无礼,还请公主入座,不跟她一般见识了。”
长公主见此也就重新坐下了,她说话的口气也平和了许多:“本宫想玉成这桩婚事,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大汉江山啊!”
“姑母所言之事,母后已对蕊儿说了多次,蕊儿也不是没有想过,只是……”
“有话可尽管讲出来!”长公主身体向前倾了倾,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阳石公主。
“只是蕊儿有个不情之请,还请姑母谅解。”阳石公主顿了顿,“蕊儿自小尚武,倘若表弟能像表兄那样,越祁连,过居延,蕊儿……自然……”
“罢了!”长公主再也忍不住了,“你这不是拿霍去病来呛本宫么?霍去病有什么了不起的?本宫最瞧不起的就是这些只会打打杀杀的男人。”
阳石公主比起姑母的尖刻毫不逊色,她反唇相讥道:“既然最瞧不起霍去病,那让表弟也弄个冠军侯来当当呀!”
“不稀罕!不要说一个霍去病,就是你卫氏一门,哪个当年不是本宫府上的奴才?”
这话一出口,卫子夫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平日里柔情似水的眼睛冷若冰霜,说出口的话也带着明显的愠怒:“公主说够了没有?公主有恩于子夫姐弟是不假,可也不能总拿往事伤人啊!左一个打打杀杀,右一个浅薄之至,公主是不是嫁给卫青也后悔了?公主若再如此无理,恕妹妹就不奉陪了。”
卫子夫说着,就朝外面招了招手喊道:“春香!送客。”
这一来长公主的面子更挂不住了,她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撇了撇朱唇,鼻子里哼出几许轻蔑:“哼!当了皇后又能怎么样……”然后愤愤出殿去了。
卫子夫惊呆了,这就是当年那个送自己进宫时温婉可亲的长公主么?她竟然在椒房殿里撒起泼来,这成何体统?
卫子夫黯然神伤地坐在榻上,也不说话,眼泪顺着两颊哗哗直流。这样子让春香好生伤心,她忙跪在卫子夫面前劝道:“娘娘玉体要紧,千万不要为此事伤心。”
“唉!本宫这是……”卫子夫咬了咬嘴唇,颤抖着肩膀抽泣。
阳石公主杏眼里喷出愤怒的火光,叫道:“好一个泼女人,椒房殿是什么地方?竟在这里撒野!孩儿这就去杀了这个女人,替母后出气!”说话间她就从腰间拔出宝剑,追了出去。
卫子夫看着姑侄两个先后出了殿门,心想坏了,若真的动起手来,弄出人命怎么得了……天……
她心中焦急,可嘴唇只打哆嗦,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着急地指着殿外。
守在门外的黄门和宫娥见状,立时拥进椒房殿,春香抱着卫子夫一边呼唤,一边喊道:“还不拦住公主,还愣着干什么?”
“母后!”只听殿外一声叫喊,阳石公主跑了进来,扑进卫子夫怀里。
她憋在胸间的那口气,到这时候才缓了过来,只是脸色还是一片苍白,对跪在面前的女儿道:“你呀!还是不懂事。此事你父皇早已说过,由他来管,你急什么啊!”
“母后!孩儿知错了。”
卫子夫觉得手背上热乎乎的,她睁开困倦的眼睛一看,却是阳石公主的泪水落在了手指间。
在场的黄门、宫娥们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岁初,朝野都在为迎接霍去病班师而忙碌着。
从长安北门到京畿咸阳,两地之间长达十里的道路旁,每隔一里就搭建起一座门楼,上面挂满了各种饰物,每一座门楼上面都飘扬着“汉”字彩旗,它们被冬日的寒风吹得哗哗直响。
横门外搭建起一座很大的平台,上面铺着红色的地毡。平台的中央,以皇上为核心,两边依次布置了大将军、丞相、御史大夫的座位,两边各插着四面“汉”字大旗,上面绣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图案。
由羽林军精壮士卒组成的仪仗队,每天在横桥北端反复演练,四排五列的队伍由各路司马带着,从步伐到阵列,从行注目礼到高擎刀剑,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整个过程都有军正署的令丞监督,士卒一不留神鞭子就会落在头上。
“皇上圣明”、“大汉威武”的喊声在咸阳原上荡起此起彼伏的回声。
刘彻即将在横门外举行盛大的仪式,随着河南、漠南与河西战役的大胜,匈奴元气大伤,不仅汉朝的疆域向北方和西北大大延伸,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边境都将赢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
在去年九月底的朝会上,刘彻提出要发车两万乘组成车队仪仗,彰显大汉的军威;还要赏赐浑邪王及其部属三十万金。
两万乘车辆,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李蔡和张汤都无言以对。当年强秦也不过号称兵车万乘,带甲百万。现在到哪里去筹措如此庞大数量的车辆呢?
可李蔡明白皇上的性格,也明白此役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外朝只有遵旨执行。
他立即想到,这事也属于内史府的职责。哼!那个汲黯不是总以敢说真话,犯颜直谏而自居么?那就让他去得罪人吧!
“陛下!臣以为此举正可大张我大汉国威,至于车辆征集,可以长安为主,不足之数可在京畿各县调集。”
张汤不待其他大臣说话,就立即出列表示赞同:“两万乘车辆摆在咸阳原上,那将是多么宏伟的场面,这正好可以煞煞匈奴人的威风。”
刘彻立即打断了张汤的话:“爱卿这说的是什么话?匈奴降将有何威风?浑邪王归顺大汉,就是我大汉臣民,何需震慑?朕这是要做给伊稚斜看的,朕要让他知道,在大汉域内,匈奴人同样可以封侯拜将。好了!此事就不用议了,车辆之事就由汲爱卿负责督办。”
散朝以后,走到司马门外,卫青向汲黯问道:“大人也以为可以筹措这么多车辆么?”
汲黯摇了摇头:“只是苦了百姓了。只是如果今天在下要是当面顶撞皇上,就正中了李蔡等人的下怀,在下要用事实感化皇上。”
连日来,汲黯起早睡晚,昼夜奔忙,简直到了“一饭三吐哺”的地步。他又是召集京畿各县令到署中,交代朝廷的旨意,又是派遣属下到街巷、乡村督促进度。
朝廷出钱在百姓中征集车马,叫作“贷贳”,由长安市令具体负责支付“贳金”。可朝廷给的钱到了乡间,往往被层层克扣,到百姓手中就所剩无几了,于是百姓就不买账。
市令征不到车辆,就派人强行征集,百姓纷纷藏匿车马,导致官民关系十分紧张,常常看到官府抓了车主,吊在树上拷打。求饶声,痛哭声不绝于耳。
汲黯听了汇报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把内史丞和长安市令找来,对他们说道:“朝廷要的是车马,而不是百姓的愤怨,如今官兵到处抓人,弄得鸡犬不宁,若是激起事变,你我就是十个头颅,也经不住东市的快刀。”
长安市令苦着脸道:“下官何尝不知道此间的利害,可现如今百姓中的刁钻之人,藏匿车马,到时怕贷贳不齐,皇上怪罪下来……”
“糊涂!荀子有言,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亲爱己,不可得也。皇上要我等贷贳车马,可没有让你们强取的意思。”
“大人,下官……”
长安市令还想说话,可内史丞却拦住他道:“就按照内史大人的吩咐去做吧。”
汲黯怎会不理解属下的苦衷呢?他明白只有自己把责任承担起来,属下才不至于提心吊胆。
“本官明白你的意思,朝廷命内史府征集车马,此乃事关大计,当尽力而为,不可懈怠。万一无法复旨,本官自会奏明皇上的。”
汲黯还叮嘱他们道:“百姓不可乱抓,贳金不可少给,职责不可懈怠。每日必须向内史府禀报一次征集计数。”
话虽这样说,可谁又能保证糟践百姓的事情不会发生呢?
这一天,刘彻在卫青、李蔡、张汤、汲黯、周霸等人的陪同下,到咸阳原上来查看盛典筹备事宜了。
他身着银色盔甲,衬红色战袍,腰挎宝剑,骑着一匹当年卫青在河南战役时缴获的赤色战马。因为皇上这身装束,所以陪同人员除张汤和汲黯外,曾上过战场的卫青、李蔡、周霸也都一身戎装。
一路走来,沿途彩楼高耸,仪仗威武,这让刘彻心中大悦,连连褒扬周霸办事得力。
刘彻的马鞭轻轻地打在战马身上,轻松惬意地走过横桥,他向卫青问道:“如果朕没有记错,周卿在漠北之战时,曾随在大将军左右吧?”
“皇上好记性,周大人当时在微臣军中任议郎,秉公执法,军中传为美谈。”卫青赞道。
“就是苏建那件案子吧?朕记得。”
周霸看了看卫青,没有说话。原来此事他曾改变过看法,他觉得自己在苏建的案子上有些偏颇,曾私下向卫青和苏建表示过歉意。现在皇上旧事重提,他倒有些尴尬。
说话间,他们就到了横桥的北端,应该是车马的阵列了。一万五千辆从京畿征集来的车辆,被少府寺的大匠们涂上了清一色的黑漆,每一辆车上站着戎装一新的四名士卒,一名驾车,三名持戟。他们看见皇上到了,一个个肃然挺立,行注目礼。
当刘彻从车阵中穿过的时候,车上爆发出有节奏的喊声:
“皇上圣明!”
“大汉威武!”
……
刘彻被这雄壮的喊声震得热血沸腾。
这车马、这气壮山河的军队、这广袤无垠的土地,使他对战争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他忽发奇想,如果这个时候匈奴突然来犯,他就会御驾亲征,体验战场搏杀的快感。他甚至生出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慨,历来开国君主,没有不马上取天下的,像他这一代的君主,就很少出征了。
刘彻勒住马头,满意地看了看汲黯问道:“两万车马都备齐了么?”
汲黯并没有打算隐瞒难处,直接说道:“勉强征集到一万五千辆车马,还有五千正在征集中。”
刘彻皱了皱眉头:“大军已过了西县,不日将进入虢县,爱卿如此慢慢腾腾,岂不要误了大事?”
对汲黯的责备,刘彻向来是很有分寸的,他并不像对其他人那样声色俱厉。但汲黯就这个脾性,有话从来不憋在肚子里。看着在一边冷眼旁观的李蔡和张汤,他反而提高了说话的声音:“皇上……”
话还没有出口,却发现皇上、卫青和李蔡等人的目光“刷”的一下都朝西转去了。天啊!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多么惨烈的画面。
两个士卒把一辆马车赶得飞快,鞭子在空气中发出“叭叭”脆响,马蹄自远及近,“嘚嘚嘚”的响过莽原,车驾后面卷起团团烟尘,从烟尘中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不好!出事了!”汲黯心头一沉,也不管身边的皇上和朝廷的大员,在坐骑屁股上狠抽一鞭,朝前冲去。
车驾在莽原上疾驰,汲黯的马迎着车驾奔去。
车驾上的士卒显然已经发现了对面来的奔马,高举鞭子大喊道:“闪开!竟敢阻挡朝廷的车辆。”
汲黯并没有回答,也举起了手中的马鞭。
士卒见来人并不惧怕威吓,心也虚了,想减慢速度,却不能奏效。而汲黯的马已到了面前,他扬手就给了士卒一马鞭,那士卒的额头眼见得就涌出一股热血。
士卒捂着头喊道:“好呀!你竟敢殴打官府差役,不要命了?”
但他这话刚一出口,头上又是一鞭子。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本官是谁?”
士卒定睛一看,并不认识,但凭他身上的官服,便明白此人官职必在长安市令以上,他仓皇地滚下车,跪倒在地连道:“小人有眼无珠,求大人饶命!”
这时候,车驾后面的惨叫声已转为微弱的呻吟。
汲黯一脸怒气转到车后,才发现车尾拴着一个人,浑身被车驾拖得衣衫褴褛,皮肉裸露,血迹斑斑。
“这是怎么回事?”
士卒口中嗫嚅,支支吾吾。汲黯又是一鞭子下去,他脸上又多一道血印。
“说!否则本官要了你的性命!”
“大人饶命,小人马上就说!”
原来他们一大早就到京畿的乡村去征集马车,这次他们去的是安陵邑,他们发现这家农户把车马藏在了柴火堆里,又坚决不给马匹,双方发生冲突,他们干脆抢了车马,将人拖在车后一路回京。
汲黯没有听完,就怒不可遏了,他雨点般的鞭子落在两个士卒的肩头,他们抱着头在地上打滚。汲黯一边打,一边骂道:“百姓乃衣食父母!殴打百姓,如同虐待双亲。本官今日就教训你们,免得你们以后不忠不孝!”
两个士卒不敢再求饶,只任汲黯抽打,不一会儿,身上的戎衣都被打得褴褛不堪。
这时候,长安市令急忙赶来,吩咐差役将车主扶上车,到京城疗伤。然后又来到汲黯面前,满怀歉疚道:“都是下官疏于职守,致使士卒目无法度,请大人治罪!”
“你不要命了?此事就发生在皇上眼皮底下。”
汲黯虽然能够体谅长安市令的难处,可“贷贳”车马虽由内史府经办,但市令却是负责支付“贳金”的;抗旨不遵,藏匿车马的嫌犯由廷尉府负责,士卒是由中尉府调遣的。今日之事,论理应由周霸处理,还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而留下一个故意找茬的印象呢!
“记住本官说的‘三不’,违令莫怪本官鞭下无情。”
汲黯说罢,正要翻身上马,却见皇上和大家都到了。他赶忙下来,来到皇上面前。
“刚才发生了何事?爱卿如此着急前来。”刘彻问道。
“陛下,是两名士卒因征集车马而残害百姓。”
“竟有如此作为?”
“不瞒陛下,这样的事自征集车马以来,屡有发生。”汲黯说着,看了看卫青和周霸。
卫青和周霸交换了一下眼色,点了点头。
“那个农户呢?”
“已经派人送到城中疗伤去了。”
刘彻“哦”了一声道:“传朕口谕,令淳于意前去看看。”
汲黯道:“只是外伤,无须惊动太医。”
刘彻收回目光,往汲黯身后看了看,眼神立时冷却了。
“长安市令何在?”
六百石的长安市令平日里都在汲黯的署中公干,哪有机会见到皇上?只有在皇上出行时才能远远地望着威威赫赫的警跸、浩浩荡荡的护卫。
他做梦都想聆听皇上的旨意。可现在,他却胆怯了。
刘彻语气很重的问话,让他的心里战战兢兢的,连“小臣在”这几个字都说得结结巴巴。
仓皇间,刘彻的斥责下来了:“班师在即,朝廷命你督办‘贷贳’事宜,你却玩忽职守,怠惰松懈,该当何罪?”
“陛下,小臣……”
“这两个差役是从哪里回来的?”
长安市令嗫嚅支吾了半天才道:“从安陵邑来。”
刘彻一听气就来了,怒道:“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先帝眼皮下残害百姓、渎职敷衍,朕不办你,律令威严何在?”
口谕一下,李蔡和张汤的眼神暗地向汲黯和卫青这面移动,那笑看似不经意,却是冷冷停留在他们的嘴角。
他们知道,现在最难堪的就是这两个人。
可接下来的情景却让李蔡和张汤张大了口,半天合不拢嘴。
当刘彻跨上坐骑准备离开时,汲黯冲上去拽住了马缰奏道:“皇上慢行,微臣有话要讲。”
汲黯脸上的肌肉没有一丝松动,双手由于用力而暴起一条条的青筋。那马见有人拦挡,一时起了性子,前蹄在地面上磕出阵阵声响,高扬的头发出阵阵嘶鸣,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卫青一看急了,生怕惊了马会危及皇上的安全,他上前去拉汲黯的胳膊,要他放开马缰。
若是放在平日,以汲黯的力气哪里是卫青的对手,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有气在胸中激荡,汲黯一把拦住卫青:“大将军且退后,下官现在就需奏明皇上,否则我将欠下一条人命,无颜面对皇上恩德。”
只要汲黯出头,李蔡和张汤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们相信皇上今天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对这个迂腐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了。他们觉得现在要做的就是在皇上的怒火上再加一点油。
李蔡立即收起刚才还挂在脸上的微笑,高声喊道:“汲黯,你到底要干什么?要造反么?”
而张汤也对着身边的警跸怒道:“还不将这反贼拿下!”
卫青愣住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情急之中他扯了扯周霸的衣袖。
周霸并不糊涂,李蔡等人借机清除异己的图谋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接着张汤的话吼道:“你们不可乱来,误伤了皇上,本官要你们性命!”
待警跸们住了手,周霸又道:“汲大人手无寸铁,一介书生,不过意气用事罢了。”
这是一个多么合理的理由,李蔡和张汤只能看着事情僵在那里。
这又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缓冲时刻,每个人似都在高速调整自己的情绪,都在寻求事情的转机。
刘彻勒住马头,扬起手中的马鞭,只要这一鞭子下去,汲黯的一只胳膊大概就得废了。可就在马鞭即将要落下的时候,他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给震撼了。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它平静得如同水波不兴的湖面,坚毅得像一块站立的石壁,真实得使你无法回避它的光芒。
多少年了,朝上朝下,君臣往来,刘彻只有从汲黯的眼里才读得出这么多意味。
马鞭慢慢放了下来,他在自问刚才的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的同时,一句宽容的话便说出口了:“好呀!朕很久都没有见你发驴脾气了,朕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把话说完。”
一听这话,汲黯便感动了,他立即跪倒在地谢道:“谢皇上。”
刘彻甩了甩战袍的袖子道:“刚看你的样子,好像非要把朕拉下马不可。你有话就直说吧!”
“臣斗胆启奏,长安市令无罪,请皇上独斩汲黯,民乃肯出车矣!”
“朕已恕你无罪,你站起来说话。”
汲黯站了起来道: “皇上,浑邪王一路东来,朝廷安排沿途各县盛情款待,已是前所未有,以致令天下骚动,为何疲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乎?”
“这……”刘彻心中暗笑:真是个可爱的书生,他怎能深解朕的远虑呢?就冲这点,就不与他计较了,“朕喜欢爱卿的率直,然此事牵涉到治国方略……”
“皇上之言差矣。”汲黯此话一出口,在场的卫青和周霸大吃一惊,眼见得李蔡和张汤又要发难,却又被刘彻拦住了,“朕已恕他无罪,索性就让他把话说完。”
汲黯抓住这个机会,立即把最近明察暗访所得消息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据臣所知,仅是京畿各县因藏匿车马坐当死者就达五百人,如此下去,百姓必怨声载道,皇上亦失德于天下,臣为社稷计,故……”
汲黯说到这里,李蔡就不答应了。他冲出人群,指着汲黯的鼻子骂道:“好你个汲黯,你渎职敷衍,又为长安市令开脱罪责,皇上不予追究已属仁慈宽怀,孰料你不知进退,竟敢妄言皇上失德于天下,分明欺君犯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臣也认为不可对汲黯姑息,乱了君臣之序。”张汤帮腔道。
卫青见刚刚平息的风波又险象环生,心想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是唯恐天下不乱么?
他觉得作为中朝的核心人物,在这个时候必须站出来。他与周霸交换了一下眼色,双双来到刘彻面前。
“皇上,虽然汲黯出言犀利,然胸怀坦荡,从无二心。倒是有人挟嫌报复,指是为非,心怀叵测!”
周霸也道:“今日残害百姓一事,臣负有失于管教之责,臣愿领罪。只是请皇上宽恕汲大人耿介,让他一心督促征集车马。”
朝廷大臣之间这些龃龉,长安市令何曾见过?只听说署中小吏们朋党比周,尔虞我诈,孰料这些大人物也……
他不敢深想,觉得要不是强行征车,也不会有汲大人鞭笞那两个士卒之举;要不是皇上责问自己,也不会殃及汲大人。自己死何足惜?要是没了汲大人,李蔡之流不更加肆无忌惮了么?
这样一想,长安市令倒也坦然。他爬到刘彻面前,那复杂的心绪变成喉头的哽咽:“皇上!以小臣的卑微,能够一瞻龙颜,今生再无遗憾。贻误皇命,咎在小臣,与汲大人无关。小臣一死,轻若鸿毛,可大汉不能没有汲大人啊!皇上!”
他的头在初冬坚硬的土地上磕出了血。
“请皇上降臣死罪。”
……
他看到路旁有一块巨石,上书咸阳界三字,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撞了上去,不一会就气绝身亡了。
“市令大人……”汲黯紧紧地抱着市令,悲怆地呼唤道,“你怎可如此糊涂啊?”
汲黯抬起头,愤怒地盯着李蔡和张汤,从牙缝里挤出冷笑:“哼……两位大人这回满意了吧?”
刘彻很吃惊,长安市令的举动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汲黯流着泪道:“兄弟!皇上就在面前,你有何话不能说?却要走此绝路?兄弟啊!你自跟随我以来,多有辛劳而少有安逸,是在下对不起你啊!”
这种超越幕僚之间的情感,让刘彻感动和震撼。他缓步走到汲黯面前,低声道:“人已去矣,爱卿还要节哀。长安市令恪尽职守,追封为勤勉侯,秩千石,以制厚葬。卿等位列三公九卿,当以市令为范,同心同德,上下协力,迎接骠骑将军凯旋!”
中朝和外朝之间的冲突,因长安市令的自杀而渐息烽火,他们在刘彻的安抚下各怀心事地站在了一起。
刘彻一回到未央宫,包桑就禀奏道:“大农令郑当时和长公主前来求见,现在塾门等候。”
“何时来的?”
“大约一个多时辰了。”
“真会找时间,你去回他们,就说朕累了,不见!”
“这……”包桑迟疑片刻,还是劝道,“看郑大人忧心忡忡的样子,一定是有要事禀奏。”
“那就传郑当时来见,让公主回去。”
“可听公主那意思,好像是从椒房殿那边过来的,说是皇后和阳石公主合起来欺负她怎么的……”
“女人们就是事多。”刘彻厌烦地皱了皱眉头,“好!快宣公主来见朕,说完了好回去。”
长公主一进殿,就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皇上!你可要为臣妾做主啊!母后去了,皇上再不替臣妾说话,臣妾就没有活路了。”
刘彻一听心中就烦了,可这毕竟她是自己的亲姐姐,也只能耐着性子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包桑递上一盏热茶,长公主喝了之后心情就平静多了,然后她断断续续地讲完了在椒房殿的遭际,末了还气愤地说道:“皇上!您说说,蕊儿竟拿霍去病作比较,说伉儿如果能带兵打仗就嫁给他,这不是欺负人么?”
刘彻“哦”了一声,原来皇姐至今仍没有放弃结亲的想法。唉!也是皇后太柔弱了,总是碍于过去的情面,不敢直说。而朕的这个大姐呢?偏又喜欢拿过去说事,皇后就越发地开不了口了,看来这话还真需要朕当面告诉她。
“此事皇姐无须再奏,这与皇后母女无干。”
“皇上说什么?臣妾不明白。”
“朕有意将蕊儿许给霍去病,等他从河西回来,朕就要当面对他说这件事情。”
“哦?是这么回事。”
长公主愣住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弟弟的主意,她怎么就一直认为是卫子夫做的呢?
她知道弟弟个性,又是皇上,哪能拿了自己的话当儿戏呢?何况霍去病眼下在他心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卫青,又岂能是她几滴眼泪所能改变得了的。自己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攀这门亲事,原本就是奔着太子去的,现在连皇上都不同意这件婚事,就算勉强做成了又有何意义呢?
长公主的心乱了,她不知道该怎样继续与皇上的谈话,泪水再度模糊了她的眼睛,口张了几次,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就在她的迟疑中,刘彻说话了:“满朝的王公大臣如云似雨,朕回头与大将军商议一下,绝不会委屈了伉儿。皇姐要没有事,就先回府去,朕还有事呢!”
这不是下逐客令么?长公主觉得再待下去也没有意思,于是站了起来,准备离去。她眼里写满了哀怨:“皇上把母后的临终嘱托都忘了,臣妾这就告退。”说罢一甩袖子,就出殿去了……
“朕的这个姐姐啊!”刘彻叹一口气,对包桑道,“宣大农令来见。”
自韩安国之后,郑当时是在大农令位置上履职最长的。与他一起的许多老臣,升迁的升迁,致仕的致仕,去世的去世,只有他还在为朝廷奔忙。
当年那个干练的大农令早已不在了,他老了,眉毛、须髯都变白了,走进宣室殿的步子也都是缓慢的。
在倾京都之力举行班师受降大典的时候,他会带来什么消息?
刘彻对这位建元以来的老臣表示了不同他人的尊重,他免去了参拜礼节,要郑当时坐到自己的对面说话。在问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也提高了许多,好让郑当时听得清楚些。
可郑当时一开口,就把一个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陛下,去秋以来,山东诸郡水灾频仍,民多饥乏。陇西、北地、上郡戎役繁重,田多荒芜。臣忧思重重,早起晚睡,千方百计,筹措财粮,以保军费之用度。然饥民日增,聚保山泽,堪为其忧。臣不敢欺君罔上,只能据实奏报,恳请圣裁。”
怎么所有的难事都在这时候聚到了一块呢?刘彻从咸阳原上带回的烦恼又增添了一层,要不是看在大农令高龄的分上,他早就发脾气了。
可现在,他只好耐着性子问道:“那依爱卿之见,该如何应对呢?”
“啊!粮食贵?”郑当时听得很费力,“物以稀为贵。现在遭了水灾,粮食当然贵了。”
“朕说该如何应对?”刘彻提高了声音。
“哦!老臣明白了。依臣观之,民生艰难,皆因豪强兼并,囤积居奇,欺行霸市,贫者益贫而富者益富。请皇上下旨,派遣谒者到各地劝民多种宿麦,凡富豪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另外,凡遭遇水灾之郡,尽开郡国仓廪,赈济灾民……”
“还有呢?”
“皇上说齐鲁?齐鲁不就是山东么?”
刘彻尴尬地皱着眉头道:“朕问的是还有没有其他事情!”
“有!当然有。还请皇上下旨,减陇西、上郡、北地一半戎卒,如此则三郡之民略可休养生息。”
看来!此老尚算明白。刘彻的心里获得了少许欣慰,如此年迈老臣,尚思虑如此周密,这一点就比公孙弘强多了。
“好!”刘彻提高了声音,“就依爱卿所奏。朕立即下旨给各郡,令其照办!”
眼见天色不早,刘彻对包桑道:“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安排人送老爱卿回去。”
包桑来到郑当时面前,附耳高声道:“皇上请大人回府呢!”
“回府?公公那么大声干吗?老臣耳朵还没有聋呢!”
可郑当时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大农令还有话说么?”
郑当时犹豫了片刻道:“臣还有一言,不知道该不该奏明皇上?”
刘彻点了点头。
“依臣观之,民生艰难,皆因战事频仍,连年不断。故臣斗胆奏请皇上在河西之战后,暂息兵戈,令民得以休息。”
这怎么可能呢?仗打到这个分上,匈奴已成强弩之末,怎么能停下来呢?近来不少人都这样说,刘彻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话。他觉得大农令也和汲黯一样的固执。
此时此刻,刘彻满脑子都是胜利,都是受降,都是霍去病的影子,都是浑邪王拜在阶陛之下的享受。看来,老爱卿也该颐养天年了。班师大典后,这事就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刘彻站起来,亲自搀扶着郑当时道:“时间不早了,爱卿所奏之事朕都准奏了,剩下的事情爱卿不必操心了,还是回府休息去吧!”
他又命包桑拿出一些滋补品,赐给了郑当时。
郑当时立即就涌出了浑浊的泪花,借着冬日的阳光看去,皇上的温暖就像这太阳一样让他从身上暖到心里,他那庄严的责任感被皇上脸上的笑容感化为一种勇气。
“皇上!臣还有话说,为了民生,息战……”
但是,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包桑送出了宣室殿。
“老而昏聩。”刘彻看着郑当时的背影,默默道。
“陛下,他已经走了。”
“嗯,走了好。”说完这句,刘彻不解地向包桑问道,“从一大早起来,朕就不断遭遇烦恼事,朕是不是真的错了?”
包桑尴尬地笑了笑,然后又把一道奏章递到刘彻手上,说是赵禹送来的。
刘彻打开奏章,那是对在河西战役中贻误战机的公孙敖、李广和张骞的审理结果。他说三人对所犯罪责供认不讳,依律当判斩刑,请皇上定夺。
刘彻的笔在空中停了半天,终于落下几行字:
罪虽当斩,前功可追,准予赎为庶人。
写完这些,刘彻忽然觉得很累,便躺在了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