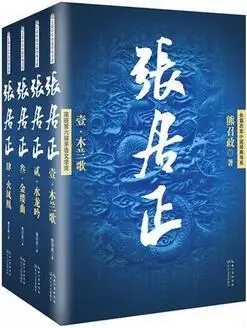原文
豫人张氏者,其先齐人。明末齐大乱,妻为北兵掠去。张常客豫,遂家焉。娶于豫,生子讷。无何,妻卒,又娶继室,生子诚。继室牛氏悍,每嫉讷,奴畜之,啖以恶草具。使樵,日责柴一肩;无则挞楚诟诅,不可堪。隐畜甘脆饵诚,使从塾师读。诚渐长,性孝友,不忍兄劬,阴劝母。母弗听。
一日,讷入山樵,未终,值大风雨,避身岩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馁,遂负薪归。母验之少,怒不与食;饥火烧心,入室僵卧。诚自塾中来,见兄嗒然,问:“病乎?”曰:“饿耳。”问其故,以情告。诚愀然便去。移时,怀饼来饵兄。兄问其所自来。曰:“余窃面倩邻妇为之,但食勿言也。”讷食之。嘱弟曰:“后勿复然,事泄累弟。且日一啖,饥当不死。”诚曰:“兄故弱,乌能多樵!”次日,食后,窃赴山,至兄樵处。兄见之,惊问:“将何作?”答曰:“将助樵采。”问:“谁之遣?”曰:“我自来耳。”兄曰:“无论弟不能樵,纵或能之,且犹不可。”
于是速之归。诚不听,以手足断柴助兄。且云:“明日当以斧来。”兄近止之。见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归,我即以斧自刭死!”诚乃归。兄送之半途,方复回。樵既归,诣塾,嘱其师曰:“吾弟年幼,宜闭之。山中虎狼多。”师曰:“午前不知何往,业夏楚之。”归谓诚曰:“不听吾言,遭笞责矣。”诚笑曰:“无之。”明日,怀斧又去。兄骇曰:“我固谓子勿来,何复尔?”诚不应,刈薪且急,汗交颐不少休。约足一束,不辞而返。师又责之,乃实告之。师叹其贤,遂不之禁。兄屡止之,终不听。
一日,与数人樵山中,歘有虎至。众惧而伏。虎竟衔诚去。虎负人行缓,为讷追及。讷力斧之,中胯。虎痛狂奔,莫可寻逐,痛哭而返。众慰解之,哭益悲。曰:“吾弟,非犹夫人之弟;况为我死,我何生焉!”遂以斧自刎其项。众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许,血溢如涌,眩瞀殒绝。众骇,裂之衣而约之,群扶以归。母哭骂曰:“汝杀吾儿,欲劙颈以塞责耶!”讷呻云:“母勿烦恼。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创痛不能眠,惟昼夜依壁坐哭。父恐其亦死,时就榻少哺之,牛辄诟责。讷遂不食,三日而毙。村中有巫走无常者,讷途遇之,缅诉曩苦。因询弟所,巫言不闻。遂反身导讷去。至一都会,见一皂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代问之。皂衫人于佩囊中检牒审顾,男妇百余,并无犯而张者。巫疑在他牒。皂衫人曰:“此路属我,何得差逮。”讷不信,强巫入内城。
城中新鬼、故鬼,往来憧憧,亦有故识,就问,迄无知者。忽共哗言:“菩萨至!”仰见云中,有伟人,毫光彻上下,顿觉世界通明。巫贺曰:“大郎有福哉!菩萨几十年一入冥司,拔诸苦恼,今适值之。”便捽讷跪。众鬼囚纷纷籍籍,合掌齐诵慈悲救苦之声,哄腾震地。菩萨以杨柳枝遍洒甘露,其细如尘。俄而雾收光敛,遂失所在。讷觉颈上沾露,斧处不复作痛。巫仍导与俱归。望见里门,始别而去。讷死二日,豁然竟苏,悉述所遇,谓诚不死。母以为撰造之诬,反诟骂之。讷负屈无以自伸,而摸创痕良瘥。自力起,拜父曰:“行将穿云入海往寻弟;如不可见,终此身勿望返也。愿父犹以儿为死。”翁引空处与泣,无敢留之。讷乃去。每于冲衢访弟耗;途中资斧断绝,丐而行。
逾年,达金陵,悬鹑百结,伛偻道上。偶见十余骑过,走避道侧。内一人如官长,年四十已来,健卒怒马,腾踔前后。一少年乘小驷,屡视讷。讷以其贵公子,未敢仰视。少年停鞭少驻,忽下马,呼曰:“非吾兄耶!”讷举首审视,诚也。握手大痛,失声。诚亦哭曰:“兄何漂落以至于此?”讷言其情,诚益悲。骑者并下问故,以白官长。官命脱骑载讷,连辔归诸其家,始详诘之。初,虎衔诚去,不知何时置路侧,卧途中经宿。适张别驾自都中来,过之,见其貌文,怜而抚之,渐苏。言其里居,则相去已远,因载与俱归。又药敷伤处,数日始痊。
别驾无长君,子之。盖适从游瞩也。诚具为兄告。言次,别驾入,讷拜谢不已。诚入内,捧帛衣出,进兄,乃置酒燕叙。别驾问:“贵族在豫,几何丁壮?”讷曰:“无有。父少齐人,流寓于豫。”别驾曰:“仆亦齐人。贵里何属?”答曰:“曾闻父言,属东昌辖。”惊曰:“我同乡也!何故迁豫?”讷曰:“明季清兵入境,掠前母去。父遭兵燹,荡无家室。先贾于西道,往来颇稔,故止焉。”又惊问:“君家尊何名?”讷告之。别驾瞠而视,俛首若疑,疾趋入内。无何,太夫人出。共罗拜,已,问讷曰:“汝是张炳之之孙耶?”曰:“然。”太夫人大哭,谓别驾曰:“此汝弟也。”讷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适汝父三年,流离北去,身属黑固山半年,生汝兄。又半年,固山死,汝兄补秩旗下迁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乡井,遂出籍,复故谱。屡遣人至齐,殊无所觅耗,何知汝父西徙哉!”乃谓别驾曰:“汝以弟为子,折福死矣!”别驾曰:“曩问诚,诚未尝言齐人,想幼稚不忆耳。”乃以齿序:别驾四十有一,为长;诚十六,最少;讷二十二,则伯而仲矣。
别驾得两弟,甚欢,与同卧处,尽悉离散端由,将作归计。太夫人恐不见容。别驾曰:“能容则共之;否则析之。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于是鬻宅办装,刻日西发。既抵里,讷及诚先驰报父。父自讷去,妻亦寻卒;块然一老鳏,形影自吊。忽见讷人,暴喜,怳怳以惊;又睹诚,喜极,不复作言,潸潸以涕;又告以别驾母子至,翁辍泣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蚩蚩以立。未几,别驾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见婢媪厮卒,内外盈塞,坐立不知所为。诚不见母,问之,方知已死,号嘶气绝,食顷始苏。别驾出赀,建楼阁;延师教两弟;马腾于槽,人喧于室,居然大家矣。
异史氏曰:“余听此事至终,涕凡数堕:十余岁童子,斧薪助兄,慨然曰:‘王览固再见乎!’于是一堕。至虎衔诚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愦愦如此!’于是一堕。及兄弟猝遇,则喜而亦堕;转增一兄,又益一悲,则为别驾堕。一门团圞,惊出不意,喜出不意,无从之涕,则为翁堕也。不知后世亦有善涕如某者乎?”
聊斋之张诚白话翻译
河南有个姓张的人,祖籍是山东人。明朝末年山东大乱,他的妻子被清兵抢走了。张某常年客居河南,后来就在河南安了家,娶了妻子,生了个儿子取名张讷。不久,妻子死了,张某又娶了一个妻子,也生了个儿子,取名张诚。继室牛氏性情凶悍,常嫉恨张讷。把他当作牛马使唤,给他吃粗劣的饭食。又让张讷上山砍柴,责令他每天必须砍够一担。如果砍不够,就鞭打辱骂,张讷几乎无法忍受。牛氏对亲生的儿子张诚,则像宝贝一样,偷偷给他吃甜美的食物,让他到学堂去读书。
后来,张诚渐渐长大了,性情忠厚、孝顺。他不忍心哥哥那样劳累,暗暗地劝说母亲,牛氏不听。一天,张讷进山砍柴,还没砍完,忽然下起暴雨,他只好躲避在岩石下。雨停了,天也黑了,他肚子太饿,只好背着柴回家。牛氏看到砍的柴不够数,就发怒不给饭吃。张讷饥饿难忍,只得进屋躺下。张诚从学堂回来,看见哥哥沮丧的样子,就问:“病了?”张讷说:“饿的。”张诚问他原因,张讷把实情说了。张诚悲伤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张诚怀里揣着饼来送给哥哥吃。哥哥问他饼是哪来的,他说:“我从家中偷了面,让邻居做的。你只管吃,不要说出去。”张讷吃了饼,嘱咐弟弟说:“以后不要这样了!事情泄漏了会连累弟弟的。况且一天吃一顿饭虽然饿,也不会饿死。”张诚说:“哥哥本来身体就弱,怎么能多打柴呢!”
第二天,吃过饭后,张诚偷偷上山,来到哥哥砍柴的地方。哥哥见到他,惊奇地问:“你来干什么?”张诚回答说:“帮哥哥砍柴。”张讷问:“谁叫你来的!”他说:“是我自己来的。”哥说:“别说弟弟不能砍柴,就是能砍,也不行。”催促他快回去。张诚不听,手脚并用扯着柴禾,还说:“明天要带斧头来。”哥哥过去制止他,见他的手指出血,鞋也磨破了,心痛地说:“你不快回去,我就用斧头割颈自杀!”张诚才回去了。哥哥送了他一半路,才又回去。张讷砍完柴回家,又到学堂去,嘱咐弟弟的老师说:“我弟弟年龄小,要严加看管,不要让他出去,山里虎狼很多。”老师说:“上午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已经责打了他。”张讷回到家,对张诚说:“不听我的话,挨打了吧?”张诚笑着说:“没有。”第二天,张诚怀里揣着斧头又上山了。哥哥惊骇地说:“我再三告诉你不要来,你怎么又来了?”张诚不说话,急忙砍起柴来,累得汗流满面,一刻不停。约摸砍得够一捆了,也不向哥哥告辞,便回去了。老师又责打了他。张诚就把实情告诉老师,老师赞叹张诚的品行,也就不禁止他了。哥哥屡次劝阻他,他始终不听。
一天,张讷兄弟俩同其他一些人到山中砍柴。突然来了一只老虎,众人都害怕地伏在地上,老虎径直把张诚叼走了。老虎叼着人走得慢,被张讷追上。他使劲用斧头砍去,正中虎胯。老虎疼得狂奔起来,张讷再也追不上了,痛哭着返回来。众人都安慰他,他哭得更悲痛了,说:“我弟弟不同于别人家的弟弟,况且是为我死的,我还活着干什么!”接着就用斧头朝自己的脖颈砍去。众人急忙救时,斧头已经砍入肉中一寸多,血如泉涌,昏死过去。众人害怕极了,撕了衣衫给张讷裹住伤口,一起扶他回家。后母牛氏哭着骂道:“你杀了我儿子,想在脖子上浅浅割一下来搪塞吗?”张讷呻吟着说:“母亲不要烦恼!弟弟死了,我绝不会活着!”众人把他放到床上,伤口疼得睡不着,只是白天黑夜靠着墙壁坐着哭泣。父亲害怕他也死了,时常到床前喂他点饭,牛氏见了总是大骂一顿。张讷于是不再吃东西,三天之后就死了。
村里有一个巫师“走无常”,张讷的魂魄在路上遇见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难,又询问弟弟在什么地方。巫师说没看见,但反身带着张讷走了。来到一个都市,看见一个穿黑衣衫的人,从城中出来。巫师截住他,替张讷打听张诚。黑衣人从佩囊中拿出文牒查看,上面有一百多男女的姓名,但没有姓张的。巫师怀疑在别的文牒上,黑衣人说:“这条路属我管,怎么会有差错?”张讷不信张诚没死,一定要巫师同他进城。城中新鬼旧鬼来来往往,也有老相识,问他们,没有人知道张诚的下落。忽然众鬼一齐叫:“菩萨来了!”张讷抬头看去,见云中有一个高大的人,浑身上下散放光芒,顿时世界一片光明。巫师向张讷贺喜说:“大郎真有福气!菩萨几十年才到阴司一次,给众冤鬼拔苦救难,今天你正好就碰上了!”于是拉张讷一起跪倒。众鬼纷纷嚷嚷,合掌一齐诵慈悲救苦的祷词,欢腾之声震天动地。菩萨用杨柳枝遍酒甘露,水珠细如尘雾。不一会儿,云霞、光明都不见了,菩萨也不知哪里去了。张讷觉得脖子上沾有甘露,斧头砍的伤口不再疼痛了。巫师仍领着他一同回家,看见村里的门了,才告辞去了。张讷死了两天,突然又苏醒过来,把自己见到和遇到的事讲了一遍,说张诚没有死。后母认为他这是编造骗人的鬼话,反而辱骂他。张讷满肚子委屈无法申辩。摸摸创痕已全好了,便支撑着起来,叩拜父亲说:“我将穿云入海去寻找弟弟。如果见不到弟弟,我一辈子也不会回来了。愿父亲仍然以为儿已死了。”张老汉领他到没人的地方,相对哭泣了一阵,也没敢留他。
张讷离家出走后,大街小巷到处寻访弟弟的下落。路上盘缠用光了,就要着饭走。过了一年,来到金陵。一天,张讷衣衫褴褛佝偻着身子,正在路上走着,偶然看见十几个骑马的过来,他赶紧到路旁躲避。其中有一人像个官长,年纪有四十来岁,健壮的兵卒,高大的骏马,前呼后拥。随行的一个少年骑一匹小马,不住地看张讷。张讷因为他是富贵人家的公子,不敢抬头看。少年勒住马,忽然跳下马来,大叫:“这不是我哥哥吗!”张讷抬头仔细一看,原来是张诚!他握着弟弟的手放声大哭。张诚也哭着说:“哥哥怎么流落到这个地步?”张讷说了事情的缘由,张诚更伤心了。骑马的人都下来问了缘故,并告知了官长。官长命腾出一匹马给张讷骑,一同回到他的家里。张讷这才详细地问了张诚后来的经过。
原来,老虎叼了张诚去,不知什么时候把他扔在了路旁,张诚在路旁躺了一宿。正好张别驾从京都来,路过这里。见张诚相貌文雅,爱怜地抚摸他。张诚渐渐苏醒过来,说了自己的家乡住处,可是已经相距很远了。张别驾将他带回家中,又用药给他敷伤口,过了几天才好了。张别驾没有儿子,就认他作儿子。刚才张诚是跟随张别驾去游玩回来。张诚把经过全部告诉哥哥,刚说完,张别驾进来了,张讷对他拜谢不已。张诚到里面,捧出新衣服,给哥哥换上;又置办了酒菜叙谈离后经过。张别驾问:“贵家族在河南有多少人口?”张讷说:“没有。父亲小时候是山东人,流落到河南。”张别驾说:“我也是山东人。你家乡归哪里管辖?”张讷回答说:“曾听父亲说过,属东昌府管辖。”张别驾惊喜地说:“我们是同乡!为什么流落到河南?”张讷说:“明末清兵入境,抢走了我的前母。父亲遭遇战祸,家产被扫荡一空。先是在西边做生意,往来熟悉了,就在那儿定居了。”张别驾惊奇地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张讷告诟了他,张别驾瞠目结舌。又低头想着什么,急步走进内室。不一会儿,太夫人出来了,张讷兄弟两人一同叩拜。拜毕,太夫人问张讷说:“你是张炳之的孙子吗?”张讷说:“是。”太夫人哭着对张别驾说:“这是你弟弟啊!”张讷兄弟俩不知是怎么回事。太夫人说:“我跟你父亲三年,流落到北边去,跟了黑固山半年,生了你的这个哥哥。又过了半年,黑固山死了,你哥哥补官在旗下,做了别驾。如今已解任了,常常思念家乡,就脱离了旗籍,恢复了原来的宗族。多次派人到山东打听你父亲的下落,没有一点消息。怎么会知道你父亲西迁了呢!”于是又对别驾说:“你把弟弟当儿子,真是罪过!”张别驾说:“以前我问过张诚,张诚没有说过是山东人。想必是他年幼不记得了。”就按年龄排次序:别驾四十一岁,为兄长;张诚十六岁最小;张讷二十二岁为老二。别驾得了两个弟弟,非常欢喜,同他们住在一间屋里,尽述离散的端由,商量着回归故里的事情。太夫人怕不被容纳。张别驾说:“能在一起过就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就分开过。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人呢?”于是就卖了房子,置办行装,定好日子起程。
回到家乡,张讷和张诚先到家中给父亲报信。父亲自从张讷走后,妻子牛氏也死了,孤苦伶仃,对影自叹。忽然见张讷回来,惊喜交加,恍恍惚惚;又看到了张诚,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流泪。兄弟俩又告诉说别驾母子来了,张老汉惊呆了,也不会哭,也不会笑了,只呆呆地站着。不多会儿,别驾进来,拜见父亲。太夫人抱住张老汉相对大哭。看见婢女仆人屋里屋外都站满了,张老汉不知如何是好。张诚不见母亲,一问,才知已经死了,哭得昏了过去,有一顿饭功夫才苏醒过来。张别驾拿出钱来,建造楼阁。请了老师教两个弟弟读书。槽中马群欢腾,室内人声喧闹,居然成了大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