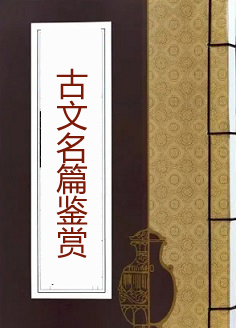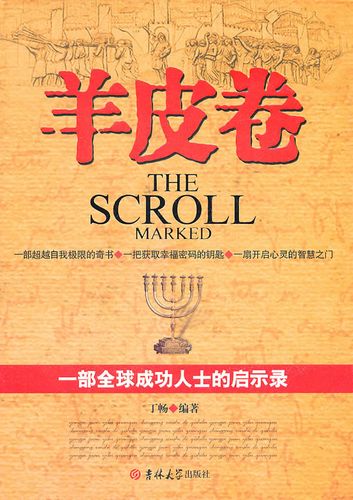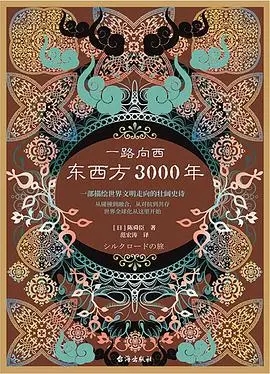三三 春秋刺客列传
今天我们讲一讲春秋的著名刺客。
说到刺客,人们首先会想到《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那几位著名刺客,即在柯之盟上劫持齐桓公姜小白的鲁将曹沫、刺杀吴王僚的专诸、舍身就义的豫让、白虹贯日的聂政,以及出名到爆的刺秦荆轲。
民间也盛传着中国暗杀史上的四大天王,即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号称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按民间的说法,还要增加一位著名刺客,就是刺杀吴公子庆忌的要离。
不过由于现在讲的是春秋史,所以战国时代的聂政和荆轲在此就不多讲了,下面讲一讲曹沫、专诸、要离的精彩暗杀人生。实际上,如果按曹沫的刺杀标准,大名鼎鼎的至圣先师孔子也应该厕列其中,在著名的夹谷之会上,孔子差点就拎刀砍下齐景公姜杵臼的人头……
说到曹沫,史学界一般认为他就是《左传·庄公十年》记载的那位在长勺之战大败齐桓公的鲁国名将曹沫,只有少数观点认为曹沫和曹沫是两个人。
曹沫的知名度不用多说,著名的《曹沫论战》早就写进了中学生的历史课本,想不出名都难。至于曹沫,人们对他远不如对专诸、荆轲熟悉,但司马迁把曹沫位居《史记·刺客列传》头把交椅,自有他的道理。
如果说曹沫就是曹沫的话,曹沫在长勺之战将初出江湖的姜小白打得鼻青脸肿,由此一战,曹沫一跃成为鲁国的一线名将。而曹沫也做过鲁国将军,结果对阵齐军三战三败,差点没把鲁庄公姬同吓出屁来,还被迫献城向齐国求和,丢人丢到爪哇国了。
曹沫只需要一场战争就扬名立万,曹沫用了三次机会,结果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当将军的材料。姬同用将的标准也有问题,一般用将者,会选择大脑发达的,而不是四肢发达的,比如齐景公用田穰苴,阖闾用孙武。而曹沫恰恰是四肢发达,“以勇力事鲁庄公”,天生就是当马仔打群架的好料子。
曹沫的官场身份,更像是禁军统领,鲁公身边的头号大保镖。但著名的三战三败后不久,姬同再次用曹沫为将,原因不详,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鲁国没有可用之将,姬同不用曹沫,难道要请他老娘文姜披挂上阵吗?
从身份职务上讲,在春秋战国的刺客中,曹沫的地位是最高的。不过严格来说,曹沫不算是标准的刺客,别人都在搞暗杀,曹沫直接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
事情发生在鲁庄公十三年(前681),姬同和姜小白在柯(今山东东阿东南)举行双方元首会议。鲁国刚刚在与齐国的战争中被打爆,姬允被迫割让遂邑(今山东肥城南),姜小白此次来柯,是敦促姬同履行割地条约的。
齐国是鲁国最大的邻国,而且姜小白初即位,管仲初执政,锋芒毕露,专骑在姬同头上吃大户。再这样下去,姬同早晚会被舅舅姜小白(姬同母亲文姜是姜小白的异母姐姐)吃成穷光蛋。
姬同在考虑如何才能避免割地赔款,并给姜小白一点下马威。如果用武力,鲁国根本不是齐国的对手,想来想去,被逼无奈的姬同只能使一些盘外招了。姬同把自己的秘密计划暗中交代给曹沫,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曹沫阴险地笑了。
在柯之盟会上,姜小白让姬同快点签割让条约,否则齐国的刺刀是不认你这个大外甥的。姬同的身边正站着曹沫,姜小白可能认为曹沫只是姬同的随行人员,哪知道这居然是个刺客。
还没等姜小白反应过来,身怀刺杀绝技的曹沫将军已经猫一样蹿到了姜小白眼前,一把亮晃晃的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架在了姜小白的脖子上。
站在一边的管仲应该没想到曹沫会来这一手,战战兢兢地问曹沫,你想干吗?曹沫倒是痛快,干吗?你们齐国连番侵占鲁国国土,你说我能干吗?今天你们必须把侵占的土地还给鲁国,如若不然,我一刀下去……
年轻气盛的姜小白已经成为曹沫手上的人质,但他依然展现出一个诸侯长才有的霸气,有本事给我一刀,让我还地,想都不要想!但对管仲来说,如果按曹沫的意思做,把地盘还给鲁国,齐国能在江湖上树立悲情的政治形象,同时也能搞臭鲁国。如果一味强硬,曹沫这个傻叉万一下手重了,要存折还是要命?你自己选择吧。
堂堂大齐国君,光天化日之下成了肉票,是非常没面子的事情,但姜小白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先让曹沫把匕首拿下来,万事好商量。姜小白答应曹沫愿意归还鲁地,曹沫笑了,收回匕首,准备回到鲁国的臣位上,欣赏由自己主导的这场伟大外交的胜利。
姜小白岂是省油的灯,曹沫刚坐下,姜小白就要下令武士上台,格杀曹沫!大不了鱼死网破。幸亏管仲眼疾手快,及时制止了姜小白的鲁莽,先忍下这口恶气,以后再找姬同算总账,好汉不吃眼前亏。
出于齐国称霸大业的考虑,姜小白强忍着屈辱,和一脸坏笑的姬同签订了新条约。新条约规定,齐国将全部归还之前三次暴打曹沫后侵占的鲁国地盘,曹沫在下边也得意地笑了。
表面上看,姬同和曹沫赢得了战术上的胜利,几乎兵不血刃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但从战略上看,鲁国此次完败于齐国。齐占鲁地是再正常不过的国家间战争行为,只能怪鲁国实力弱。而曹沫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胁迫齐人还地,对鲁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柯之盟后,“桓公之信著乎天下”,《史记·齐世家》也记载:“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从此拉开了齐国称霸天下的大幕。鲁国用几乎是政治自杀的行为衬托出了齐国的高大形象,实在是愚不可及。从政治角度讲,曹沫的刺杀是完全失败的。
讲完了临时客串的刺客,下面讲一个真正的刺客,就是大名鼎鼎的专诸。
单从知名度上讲,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暗杀事件中,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荆轲刺秦王,排在第二位的一定是专诸刺王僚,要离、豫让都要逊专诸一筹,更不要说强盗曹沫了。
如果从故事的精彩程度上讲,专诸刺王僚和荆轲刺秦王的惊心动魄相比,毫不逊色,从阴谋杀僚到堀室藏兵,再到扮厨学鱼,鱼中藏剑,兄弟二人钩心斗角,最后由专诸从鱼中抽剑,一击杀僚的过程,让后人叹为观止。
而且这场著名宫廷政变涉及了春秋史上的一线人物,有阴谋策划者伍子胥、阴谋得利者公子光、阴谋受害者吴王僚,甚至还有天下第一大贤人季札。傍上了这么多名人,专诸想不出名都难。专诸,在《左传》中记载为设诸,但这个名字太拗口难记,所以下文一直沿用专诸。
如果不是一个人的出现,专诸会一直生活在棠邑(今江苏六合),做一个职业斗殴者,专门以和地方上的猛男格斗为生,虽然辛苦,但也快乐,这个人就是楚国逃臣伍子胥。
伍子胥在逃亡入吴的路上,偶然发现了专诸正在和一群猛男打架,大块头的专诸很快就把那群猛男打得抱头鼠窜。而当专诸的老婆叫专诸回家吃饭时,专诸乖乖地跟在老婆后面。
伍子胥觉得非常奇怪,问专诸为什么怕一个女人?专诸瞪起牛眼说,你到底识不识货,我这不是怕老婆,而是屈一人之下,必居万人之上。伍子胥很惊讶地看着专诸,发现此人“碓颡深目,虎膺熊背”,是当今难得的勇士,伍子胥到了吴国发展,以后很有可能用得上专诸,就和专诸交了朋友。
等到伍子胥投靠公子光后,发现公子光要密谋除掉王僚,但苦无合适的人选。伍子胥突然想到了专诸,便暗中派人把专诸请到公子光府上。
专诸四肢发达,但头脑也不简单,他当然知道公子光请他来是做什么的,但见到公子光后,专诸装傻充愣。专诸说王僚继位是符合法定程序的,公子为何还要做掉他?公子光也不傻,立刻摆出一副苦大仇恨的模样,说我才是先君寿梦的嫡长孙,最有资格继位,而王僚的父亲夷眜只是庶出,他凭什么鸠占鹊巢?
公子光也懒得和专诸兜圈子,请专诸是来动手的,不是来磨嘴皮子的。公子光给专诸做出承诺,一旦事成,他就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上卿可了不得,再大的诸侯国也没有几个上卿,而专诸只是区区底层百姓。如果儿子做了上卿,那就是一夜暴富,进入上流社会,这也是专诸答应接这单买卖的主要原因。
王僚可不是轻易能接触到的,为了能让专诸近距离接触到王僚,公子光决定在府上设一场“鸿门宴”,趁厨子上菜的时候,伺机动手。因为王僚最喜欢吃烤鱼,而专诸又不太会做鱼,一旦在宴会上穿帮,后果不堪设想。在公子光的建议下,专诸特地去了一趟太湖,在湖边的渔家潜心学习三个月,果然学得一手好鱼技。
不过有一点值得怀疑,史料记载专诸学鱼的这一年是王僚九年(前518),而公子光准备刺杀王僚的时间是王僚十二年(前515),中间相隔整整四年!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公子光迟迟不动手,当然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但问题是,难道这四年间,专诸什么事也不做,天天在湖边练烤鱼吗?专诸也不怕倒了胃口。
动手的日子选在了王僚在位第十二年的四月丙子日,公子光事先在举行宴会的大厅下部挖了一个大洞,将几百名武士塞了进去,随时准备跳出来接应专诸。
公子光的计划很周密,但王僚对公子光突然举行莫名其妙的宴会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但又说不出来问题在哪里。王僚的母亲是个老江湖,一眼就看穿了公子光的花花大肠,老娘劝儿子去赴宴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安保,千万别中了公子光的花招。
王僚为了防止公子光行刺,特意穿上一具由棠谿上等好铁制作的精制铠甲,几乎是武装到了牙齿,这才敢放心地赴宴。随同王僚前往的有大批精锐甲兵以及自己的贴身亲信,甲兵全部接管公子光府的安保工作,每人手执一杆大戟,戟尖交叉,将王僚严密保护起来。
在正常情况下,公子光的人马是绝无可能强突刺杀王僚的,好在他还有不要命的大侠专诸。专诸已经做出了味香色俱佳的烤鱼,就等着王僚传召,上这道天下绝无仅有的美味。
公子光借口说脚疼,需要到内室换履,溜回厨房,趁周边没人,附在一级大厨专诸耳边嘀咕了几句。公子光的妙计,大家都知道,就是让专诸把一柄寒雪见光的利剑放进烤鱼的肚子里,这就是著名的鱼肠剑。吴越的炼剑技术非常发达,公子光提供的这柄剑,极有可能是专门打制,用来对付王僚的棠谿甲的。
按照礼节,作为身份低下的厨子,专诸必须跪在地上,捧着鱼盘膝行。正因为如此,专诸跪在地上的角度正好有利于他抽剑刺王僚,如果专诸站着端盘子,等抽出鱼肠剑再往下刺,角度和时间都有利于王僚更好地躲闪。
专诸膝行至王僚面前,虽然两边有武士执戟交差护卫,但毕竟还闪出一个不大但可以至少容纳专诸的缝隙,这就足够了。专诸假装调整鱼盘的方向,在电光火石之间,专诸突然把手伸进鱼里,抽出那把命运之剑,一跃而起,直插进王僚穿着三层铠甲的胸膛。
王僚惨叫一声,痛苦地倒在地上,眼角还死盯着地上那盘已经被专诸用手掏烂的烤鱼。等侍卫反应过来,用大戟刺死专诸时,一切都晚了。
专诸敢做这笔惊天的大买卖,就是求死不求活的,只要王僚死了,他就圆满完成任务了,他死不死无足轻重。何况公子光在地下室还有一支伏兵,趁厅上血光四溅时,公子光一打口哨,数百甲士破土而出,将王僚的人马一扫而光,“尽灭之”,也算为专诸报了仇。
王僚确实死不瞑目,他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公子光会在一个不知名的厨子身上动歪脑筋。而对专诸来说,以一条“烂命”换来至尊王者的生命,改变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同时又给自己的儿子挣来上卿的位置,这场以命易命的危险游戏,值得。新任吴王阖闾(即公子光)也没有食言,“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当初专诸豪情万丈地对伍子胥说:“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现在看来,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很幸运地把自己的名字铭记在历史深深的记忆之中,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专诸刺王僚,主要还是图名利,以一死换铭碑不朽,子为上卿。而且从专诸怕老婆的细节看,专诸是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男人,至少他爱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专诸性格的弱点并不影响他人生中散发着人性化的光辉。
而和专诸相比,另一位同时代的著名刺客要离就显得相当可怕了,要离为了所谓的君臣重义,替阖闾杀掉了王僚的儿子庆忌,居然用了死间计,让阖闾杀死自己的妻儿,以骗取庆忌的信任。
妻儿何罪?罹此大难!要离于心何忍,何况阖闾向来没有恩重于他。而且刺杀庆忌成功后,要离自杀殉妻儿,只求一名永垂不朽,不图利只图名的人是非常可怕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司马迁对要离的行为极不认同,在《刺客列传》中根本没有提到要离这个名字,甚至连庆忌都没有提到。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把庆忌的一些事情交代清楚,要离刺庆忌这个经典刺杀桥段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有人说确实发生过,有人说纯属江湖臆造。
不仅《史记》只字不提庆忌和要离,《左传》只在鲁昭公二十年提到过一次吴公子庆忌,这个庆忌在为夫差效力,因为庆忌劝谏夫差不听,庆忌逃到楚国避难,随后庆忌听说越王勾践伐吴,又回到吴国,不久被吴人所杀。
“要离刺庆忌”中的这个庆忌,出现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而且点明此庆忌就是王僚的儿子,最终被要离刺死。后人所熟知的这个刺杀故事,就是出自《吴越春秋》。综合来看,王僚之子庆忌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夫差同时出现的那个庆忌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要离刺庆忌,其实是专诸刺王僚的姊妹篇,王僚被刺身亡,阖闾夺位,开始对王僚的势力进行清洗,作为王僚最优秀的儿子,庆忌自然成了阖闾的眼中钉。庆忌的厉害,阖闾是亲眼见过的,用阖闾自己的话说,“庆忌之勇,世所闻也。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走追奔兽,手接飞鸟,骨腾肉飞,拊膝数百里”。而最要命的是,庆忌躲过了阖闾的追杀,逃到了卫国,客观上对阖闾在吴国的统治构成了致命威胁。
如何才能除掉庆忌,这是一个让阖闾寝食难安的问题。如果出兵进攻卫国,要跨过诸侯地界不说,远离本土与卫军交战,胜算不大。阖闾把问题抛给专诸刺王僚事件的总编剧伍子胥,让他给出个主意。
伍子胥天生就是搞暗杀的,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再找一个像专诸那样的刺客,去卫国把庆忌灭了。阖闾是很认同这个办法的,聘请一个刺客花不了几个大头银子,总比劳师远征经济实惠。
问题是专诸已经死了,上哪去找不要命的刺客?伍子胥适时推出了专诸二代——要离。和专诸一样,要离也是一个打架不要命的主儿,当时江湖上盛传着要离当众羞辱第一勇士椒丘䜣的传奇故事。至于伍子胥是如何认识要离的,估计也是入吴的路上结识的,然后结为好友,以备日后不时之用。
阖闾在王宫接见了要离,但阖闾很快就泄了气,要离瘦得跟火柴棒子似的,出门都不要坐车,一阵风就送到目的地了。要离事先应该是在伍子胥那里得到了他所要执行的任务,拍着胸脯告诉阖闾,把信任交给我,我把庆忌的人头交给你。
从阴谋刺杀王僚开始,到再次准备刺杀庆忌,阖闾(公子光)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而要离却非要把刺杀庆忌的行为上升到一个道德高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臣,说什么“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
要离所理解的忠义,实际上还是没有脱离绿林江湖的小忠义范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忠义。且不说王僚在位期间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庆忌更是人中之龙,为人和善,刺杀这样的父子,去满足一个野心家的政治快感,看不出忠义何在。
更让人发指的是,要离为了践行他所谓的忠义,居然丧心病狂地提出一个要求,让阖闾把自己的妻儿杀死在闹市之中,焚骨扬灰。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庆忌相信要离,从而让要离接近庆忌,伺机下手。
阖闾无恩于要离,妻儿无仇于要离,要离害死和自己血脉相连的妻儿,却帮助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外人。除了变态,真不知道还能用什么词来形容要离。
阖闾不管你这些,只要你答应刺杀庆忌,反正烧死的又不是自己的妻儿,没人会心疼。要近距离接触庆忌,阖闾只能按这个路子去走。还有一点让阖闾放心的是,要赢得庆忌的信任,要离必须巧舌如簧。
要离不但能打架,而且嘴功极为了得,当初椒丘䜣不服要离,来辱骂要离,结果被要离三句话轻松驳倒。要离有身手,有嘴功,是刺杀庆忌的不二人选,要离提出什么要求,阖闾都会答应。
但让阖闾抓破头皮也想不通的是,要离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只要求阖闾现在就烧死他的妻儿,并悬赏千金购买他的人头。天下还有免费的午餐,阖闾的嘴都笑歪了,你自己冒傻气,可别说我一毛不拔。
就在要离北上投奔庆忌的同时,他无辜的妻儿被阖闾烧死在闹市,扬骨弃灰。不过从要离和阖闾对话的字面意义上来解释,要离只是让阖闾先杀妻儿后扬灰,并没有要求直接烧死妻儿。
阖闾为了把戏演得更逼真一些,让庆忌彻底相信要离,这个阴冷的国王在要离离开后,私自更改剧本,将要离的妻儿烧死,可见阖闾为人之阴狠毒辣。这种心理极度阴暗的人物当权,实在是历史的莫大悲哀,一如以假仁假义欺骗历史三百年的赵匡胤。
要离同样无耻,他在路上散播谣言,说因为他得罪了吴王,阖闾就烧死自己妻儿,以换取别人廉价的同情,庆忌自然也上当了。庆忌待人真诚,性格阳光,不像他堂叔阖闾那样阴暗龌龊,要离在庆忌面前哭诉阖闾的暴行:“阖闾无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于市,无罪见诛。吴国之事,吾知其情,愿因王子之勇,阖闾可得也。何不与我东之于吴?”
庆忌和阖闾有杀父之仇,要离和阖闾也有杀子之仇,所以要离的“悲惨遭遇”很容易拨动庆忌内心深处那根最柔软的同情之弦,引要离为心腹,“庆忌信其谋”。
这场暗杀计划要想获得成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离必须得到庆忌的充分信任。要离用他的精湛表演艺术骗到了庆忌,接下来要做的,只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送出那致命的一刀。
根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记载,三个月后,庆忌组织了一支精锐的复仇军,杀回吴国找阖闾讨回血债。就在这支军队准备渡江的时候,要离与庆忌同坐在一条大船上,要离趁庆忌不备,抽剑刺向庆忌。
阖闾派要离来刺庆忌是非常冒险的,因为要离的身高不符合标准。庆忌高大威猛,要离费了很大的力气,几乎是原地弹跳,才将冰冷的长矛送进庆忌的胸膛。即使如此,庆忌还是把矛从体内拔了出来,强忍剧痛,把要离放倒在甲板上,把要离的小脑袋摆在水里,差点没把要离憋死。
但让要离惭愧的是,庆忌并没有杀他,而是坐在甲板上,把要离拎到自己的腿上,并告诉身边甲士:“此人是勇士,不可杀。”直到临死的那一刻,庆忌还称要离是勇士,这实在是高看要离了。专诸勉强还算半个勇士,要离不是,他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暗杀机器。
先不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为一名侠客,要有最起码的正义感和辨恶能力,而这一点恰恰是要离所不具备的。要离不是不知道阖闾的厚黑无耻,还甘做阖闾的走狗,这和忘恩负义的石守信之流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故事就这么结束,要离永远也不配称为勇士。但庆忌在人生最后时刻对要离的欣赏,却像一支点燃的火柴,温暖着要离依附于别人利益而存在的自我,要离灵魂深处的潜善意识开始复苏。
要离痛哭流涕地怀念被阖闾烧死的妻儿,甚至开始怀念庆忌当初对自己的推心置腹。按《吕氏春秋·忠廉篇》的说法,要离回到姑苏后,阖闾果然大悦,要封要离为一字并肩王,被要离拒绝。
要离的回答带有很强烈的忏悔,“杀妻子焚之而扬其灰,以便事也,臣以为不仁。为故主杀新主,臣以为不义。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庆忌为之赐而不杀耳,臣已为辱矣。不仁不义,又且已辱,不可以生”。遂伏剑而死。
吕不韦的门客说要离自杀是因为“临大利而易其义”,只说对了一半,在庆忌大度地饶恕要离之前,要离是不知义为何物的。真正的义,不是给强权者当走狗,是捍卫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自我约束。
阖闾做的那些丑事本身就是不仁不义,他的鹰犬又怎么可能会大仁大义?但当要离猛然醒悟之后,伏剑自杀,上报庆忌之义,下报妻儿之仁,拒绝与阖闾同流合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洗清了自己人生中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