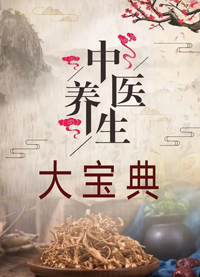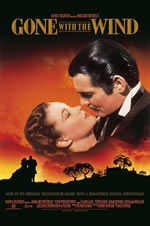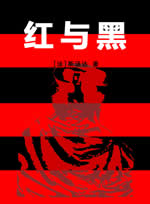三六 季札和豫让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被一代鬼才金圣叹称为第五才子书的《水浒传》的核心价值观,这个字只能是“义”字,虽然大多数梁山好汉的所作所为和“义”字没有任何关系。
人在江湖上行走,必须遵守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义规矩——义,即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谁都不能越界,梁山如此,春秋也是如此。孟子常说春秋无义战,这恰从反面角度证明了春秋以仁义为基础的道德价值体系并没有完全崩塌,否则也就不存在义不义战了。
江湖中人都自诩义士,不过真正能“践义”的并不多,梁山好汉中也只有鲁智深、林冲数人而已。春秋风云人物如过江之鲫,但要么诡诈多奸,要么迂腐可笑,算来算去,真正可称义士的,而且又大名鼎鼎的,只有两位:吴国季札、晋国豫让。
之所以把季札和豫让单列出来讲“义”,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季札和豫让截然相反的出身。季札出身于吴国王室之家,深得父王宠爱,天生就是混社会上层的,而豫让出身社会最底层,以做智伯之家客为生。
季札和豫让,一个高富帅,一个矮穷丑,却从两个社会极端层面完美地解释了人性中的“义”。具体来说,季札的义,更接近于“信”,豫让的义,更接近于“忠”,下面先讲季札。
说到季札,我们首先想到那个践行诺言的著名典故——季子挂剑。“义”的基础是“信”,无信则无义,季札因徐君一言,相赠宝剑,被传为千古美谈。唐人李白有首著名的诗篇——《陈情赠友人》,前八句写得非常动情,如下:
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懦夫感达节,壮士激青衿。
这个感动千古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4年,这一年春,季札奉吴王之命北上出使鲁、齐、郑、卫、晋,开始了这场著名的文化外交之旅。季札的第一站是鲁国,而从吴赴鲁,就必须经过徐国(今江苏泗洪附近)。
出于外交礼仪,徐国国君亲自设宴款待季札,在席间饮酒时,徐君看中了季札随身佩带的宝剑。徐君很有眼力,季札的这柄剑是吴国最上等的好剑,史称“吴之宝”。和季札不熟,徐君不好意思开口索剑,倒是季札看出来了,只是由于他有公事在身,外交场合须臾离不开佩剑,也就没说什么。
按季札的想法,等他处理完外交事务后,再路过徐国,把剑送给徐君。没想到等季札再次回到徐国时,徐君已经去世了。季札做出了一个很惊人的举动,把吴国的镇国之剑挂在徐君墓旁边的树上。
从人劝季札不要拿宝剑随便赠人,何况人都死了,还送给谁?难道送给树上的乌鸦吗?季札的回答让人很感动,“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伤心,廉者不为也”。做人不能欺心,欺心者必被天欺,这就是季札朴素的人生观。
因为信守承诺,挂剑而去,季札深深感动了历史,其实这只是季札“义”生中的一个经典镜头。季札的“义”,还体现在他对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恪守,绝不越政治雷池一步,保国保家,两得其美,被后人称赞伯夷再世。
“义”在季札身上体现为两层性,即个人大义和国家大义。挂剑赠徐君属于前者,以非嫡长子之由拒绝继位,属于后者。《后汉书·丁鸿传》对国家之义的理解是:“《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在这一点上,季札几乎是道德完人,鲁国圣人孔子对季札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季札能在春秋绚烂的舞台上呼风唤雨,首选不得不承认他有一个好祖宗。这一点不能说不重要,谁不想有个金爹银妈?后天的拼命奋斗那都是被残酷的命运逼出来的。
季札是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如果从辈分上讲,季札是吴王僚和阖闾的亲叔父,夫差的嫡亲叔祖。这一点决定了后来季札在吴国王室“族长”般的地位,有些类似北宋野史演义中那位著名的八贤王赵德芳。
季札之所以在王族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这和他以自己非嫡子为由拒绝继承王位有直接的关系。季札是个恪守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只是庶四子,上头还有三个兄长,从来没有窥视过那个位子。
季札不是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为了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位子杀得头破血流,问题是老爹寿梦最喜欢季札,一再扬言要越次立季札为君。形势非常简单,只要季札点一下头,那个位子就是他的,长兄诸樊、次兄余祭、三兄夷眜都得靠边站,他们半点机会也没有。
其实在季札之前,庶子继承君位的例子并非没有,他完全可以不背这个心理负担。只是季札始终无法说服自己背叛心中的“大义”,正如他对父亲临终前要求他即位时所说:“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
季札知道父亲疼他宠他,而且这个位子不是他耍阴谋手段抢来的,坐上去也心安理得。但如果他坐上去了,置三个兄长于何地,特别是长兄诸樊。在季札的坚持下,寿梦不再为难他,改立长子诸樊为嗣。
讲到季札的义,就要讲一下他侄子阖闾的不义。在有史料所载的吴国王室中,抛开阖闾的能力不谈,阖闾的人品是最有问题的,为了最高权力,阖闾耍尽了阴谋诡计,弑君杀兄,置春秋大义于不顾,和季札是没法比的。
阖闾的人品还不如他的父亲诸樊,当初季札坚辞让位,把诸樊感动得一塌糊涂。诸樊知道这个位子本来是属于四弟的,他如果坐上去,会觉得心有不安。在先王寿梦的葬礼结束后,诸樊就惴惴不安地要把王位还给季札,被季札拒绝。
以诸樊此时的身份,季札已经固让,他完全可以顺水推舟爬上高台。但让人感动的是,“吴人固立季札”,这个吴人,指的只能是诸樊。不能说诸樊是在演戏,因为他没有必要这么做,季札不接单,能有资格接单的只有诸樊。
季札的大义,体现在他对诸樊一根筋似的行为的反应。“季札弃其室而耕”,向诸樊以及国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是不会即位的。在万般无奈之下,诸樊只好心怀愧疚地做了吴王。
都说季札有大义,其实诸樊同样有大义,诸樊始终为自己的即位心感不安,他只有把位子传给季札,才能卸下这块心结。诸樊在临终时(前548)把王位传给二弟余祭时称赞季札有“义”,为了能让季札有机会即位,王位将兄终弟及。至于自己的儿子姬光,诸樊根本没有任何考虑。想必诸樊传位时,姬光就站在父亲身边,看到父亲舍子立弟,姬光心中肯定打翻了醋坛子。
十七年后,余祭病死,把位子传给三弟夷眜,为的就是将来夷眜死后把位子名正言顺地交给季札,了却父亲和长兄的遗愿。四年后,也就是公元前527年,夷眜病死前请求季札接位,但季札铁了心要恪守传统,宁死不即位,“逃去”。
是季札对功名利禄没有兴趣吗?不是,他并没有退出官场,继续做他锦衣玉食的延陵公子,同时又是吴国的外交部长,可谓位高权重,名满天下。
季札认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末,没有资格做吴王。让他做吴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三位兄长没有一个子嗣,在这种情况下,季札才有可能接位。仅仅因为他的排行不合旧制,坚持不以坏礼为代价,来博取个人名利。
后人对季札的义歌颂不绝,实际上包括诸樊在内的三兄弟让贤所体现出来的大义同样值得歌颂。兄弟和睦,不败其家,吴国在寿梦之后突然强势崛起不是偶然的,其内在推动力就是兄弟四人友爱礼让,团结就是力量,这是历史的真理。
季札的贤与义,不仅感动了历史,也给他那位野心比西瓜还大的侄子姬光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姬光在请专诸做刺客时,针对专诸的疑问,姬光就抬出了季札做挡箭牌,说天下本就不是王僚的,就算杀之,等季札出使诸国回吴后,也不会废掉我。
从姬光的这句话可以反映出季札在吴人心目中的地位,姬光要想在舆论上处在有利的位置,就必须在政治上继续尊崇季札,丝毫不敢少礼。等姬光弑君后,因为季札已经回到姑苏了,所以姬光不敢造次即位,还假惺惺地,说要把王位还给季札。
季札不接受三位兄长的传位,自然更不会接姬光的盘子,季札说得很清楚,“尔杀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乱也。”你姬光杀人,却让我即位,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傻子才会接招。这个侄子是什么货色,季札再清楚不过了。
虽然姬光礼待季札,但季札从心底是不认同姬光的。在季札拒绝姬光虚情假意的让位之后,季札就来到王僚的坟头痛哭一场,这分明是在否定姬光的弑君恶行。在此之后,季札并没有再次“逃去”,而是留在朝中,这让姬光很不自在,从另一个侧面再次对姬光的王位继承进行否定。
从现在的眼光看,季札的选择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姬光通过非法手段上位,却实现了吴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灭楚,这是王僚没有做到的。季札应该以吴国大业为重,出山辅佐姬光。但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总要有人出来维护,季札不捍卫传统,社会就少了一杆道德标尺,这才是季札心中最大的义,这也是后世老夫子们对季札赞不绝口的主要原因。
在季札死后,据说齐天大圣孔仲尼派学生子游去季札墓前,写下两个字,“君子”。孔子非常看重“义”,和季札一样,都在努力维护主流价值观念,从这层意义上讲,孔子和季札是同志,所以孔子称赞季札是再正常不过的。
司马迁在《史记·吴世家》卷尾史评中用了七十五个字,其中王僚、阖闾、夫差等大头王一字也未提及,却用了三十字称赞季札:“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众所周知,司马迁非常认同儒家的思想理论,实际上季札也是一个儒家,他传承的是自周公以来的旧儒,而孔子的新儒也是从周公旧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从年龄上来看,季札长孔子二十多岁,当季札于公元前544年来鲁国观乐时,孔子只有七岁。当孔子成名时,季札早已名满天下,是周公之后,孔子之前的旧儒家的代表人物。季札一生重“义”,以身作则,推行旧儒家的思想理念,这对孔子新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
讲完了季札,再来讲豫让。
豫让本来是应该放在《春秋刺客篇》中的,专诸、要离都是豫让的前辈同志。之所以把豫让和季札同篇,主要是因为虽然三人同为刺客,但性质完全不同。
专诸是贪图姬光许给他的封其子为上卿的大富贵,他和姬光之间是典型的买卖合同关系。至于要离,纯粹是个神经病,什么都不图,用全家人的性命拼掉了和自己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庆忌,二人和“义”是扯不上关系的。
豫让行刺赵襄子赵毋恤,既非图名,也非图利,只是想为曾经对自己恩重如山的旧主智伯报仇,这才是大仁大义。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的那些刺客们,也只有豫让才有资格称为义士,其他人全是糊涂蛋子,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活。
司马迁在名篇《报任安书》中曾经提到一个著名成语,即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实际上这句名言的版权所有者就是豫让,司马迁只是免费借用了一下。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几十载春秋轮回而已,总要留下一点什么,才不会觉得遗憾。有人给儿孙留下了万贯家财,有人给后世留下了千古骂名,豫让留下的则是“义”。
豫让的义和季札的义不甚相同,季札维护的是主流精英为本位的社会价值观,而豫让则是在维护一种江湖中人特有的道德价值观。江湖最推崇的就是义,而不是仁,所以江湖中人拜把子,称为结义或义结金兰,没听说过结仁或仁结金兰的。
庙堂之上的义,讲究的是君君臣臣,天下社稷,万民安泰否。江湖草野的义,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个人化的正确价值观,做人要恩怨分明,受人一鹅毛,必以千金赠。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伍子胥和韩信在穷困落魄的时候受漂母一饭,他们发达后,立刻相赠千金,以报一饭之德。
豫让刺赵毋恤,本质和伍子胥、韩信一样,都是在报恩。不过略有不同的是,伍韩报恩是出于做人“以德报德”的道德本能,而豫让为旧主寻仇则是出于他心中的江湖大义。因为受智伯恩惠的并不止豫让一人,而只有豫让选择了和赵毋恤血拼到底。
前面讲过,豫让出身于草根,但他的家世并不简单。我们都知道吴国有一位著名的奸臣伯嚭,间接导致了夫差的灭亡和勾践的称霸,伯嚭的祖父是楚国大夫伯州犁,而伯州犁本来是晋国大夫伯宗之子。伯宗在晋国得罪人太多了,为了保护好儿子,伯宗在民间得到了一位奇士毕阳,由毕阳保护伯州犁入楚,不久后,伯宗就在晋国内乱中被杀。而这个义士毕阳,就是豫让的祖父。
对于毕阳的生平,除了《国语·晋语五》卷尾提到了送伯州犁入楚,再无史料记载。但从豫让一直生活在晋国来看,毕阳送伯州犁入楚后,很可能又回到了晋国,豫让也有可能在小时候就生活在祖父身边。毕阳的义举,以及家庭的草根地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豫让价值观的形成。
豫让生活在春秋末期,此时距离春秋最后一位霸主勾践的去世(前465)已经过去了十多年,齐桓、晋文争霸的时代早如过眼烟云。
齐国自简公姜壬被杀后,姜氏的权力就落入权臣田常手上,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相比于齐国,晋国的形势更加混乱不堪,齐国是田常一人执政,晋国则是六卿执政,即著名的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晋国姬姓公室早已被架空。
六大家族的祖上都是晋国勋贵大臣,背景个个硬得很,平时为了争夺权力没少暗中拆墙使绊子。从实力上来看,知氏最强,赵魏韩次之,范、中行最弱。在公元前458年,知氏的家主知瑶(即大名鼎鼎的智伯)联合赵魏韩三家吃掉了相对弱小的范氏和中行氏,四家共同瓜分,利益均沾。
《史记·刺客列传》说豫让曾经在范氏和中行氏门下当过差,时间都不太长,豫让接连炒掉范老板和中行老板,跳槽到了知氏公司当员工。豫让在智伯手下都做了什么事情,于名不详,可以肯定的是,智伯非常欣赏豫让,至少豫让在智伯那里得到了重用。而范氏和中行氏应该是对豫让不够尊重,豫让在他们手下看不到前途,才不得不改换门庭的。
蜀汉第一谋士法正曾经在益州牧刘璋门下做事,但不受重用,后来法正攀上了刘备这根高枝,并在刘备取代刘璋自为益州牧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奇功。后世一些人就以法正曾经给刘璋效力为借口,攻击法正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实际上法正和豫让是同一类人,恩怨分明,你投我以桃,我报你以李,都具有明显的江湖豪侠之风。刘璋不待法正以国士,法正又凭什么给刘璋卖命到死?豫让同样如此,范氏和中行氏待豫让如下人,豫让没有道理为这样的人物当一辈子小弟。
知瑶是晋国的正卿执政,没有两把刷子,他也爬不到这个位置。公元前472年六月,知瑶率晋师伐齐,在犁丘(今山东临邑)将齐军打得鼻青脸肿,生擒齐国大夫颜涿聚,可见知瑶的军事能力不是吹的。
豫让投奔知瑶麾下,并非是贪图知瑶的权势,否则在知氏被灭后,豫让有一万个理由拜在新执政的赵襄子门下,而不是去刺杀他。知瑶应该是知人善任的,豫让重情重义,能力想必也不会太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豫让)去而就知伯,知伯宠之。”能让文武兼备的晋国正卿宠爱有加,豫让岂是凡品?
这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刘备在亲征汉中时,在阵前冒箭雨拼杀,法正也不避危险地陪在刘备身边。以法正恩怨分明的个性,刘备待他如路人,他是断然不会以死相报的。
不能说法正是在刻意模仿豫让,但豫让的大忠大义确实感动了历史,故事的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公元前455年,野心已经极度膨胀、“欲尽并晋”的知瑶,以武力强迫魏桓子魏驹、韩康子韩虔,组成多国部队,向盘踞在晋阳,素来不服知瑶的赵襄子赵毋恤发起强蔟,这就是春秋史上著名的晋阳之战。
形势本来对知瑶非常有利,这场战争打了两年多,赵毋恤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但在最关键的时刻,赵毋恤利用“唇亡齿寒”的心理,说服韩、魏两家,对知家反攻倒算,实现了人生大逆袭,一代大卿知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战国三雄赵魏韩崛起的垫脚石,知家的地盘被三家瓜分。
撇开魏、韩两家打酱油的不谈,赵毋恤和知瑶有不共戴天的死仇。当年知瑶率军攻郑,赵毋恤为副将,知瑶有次在帐中饮酒大醉,对赵毋恤强行灌酒,当场让赵毋恤难堪。
最过分的是知瑶企图参与赵家的废立大事,要求赵毋恤的父亲赵简子赵鞅废掉毋恤。赵鞅当然不会听知瑶的满口柴胡,但赵毋恤由此恨知瑶入骨。这次灭掉知瑶,赵毋恤的复仇快感可想而知,他在极度的兴奋中把知瑶的人头砍下来,做成酒器,在人群中四处炫耀。
赵毋恤是复了仇,可他对知瑶尸体的污辱却深深伤害了豫让,知瑶得罪赵毋恤,那是他们之间的恩怨,和豫让无关。豫让只知道知瑶待他如国士,如今恩主死后被辱,作为知家最受宠的臣子,豫让岂有坐视之理?为子死孝,为臣死忠,这是为人的本分。豫让唯一能做的,就是复仇,用赵毋恤的一条命来报答知瑶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故事的过程很简单,豫让用易容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待罪的奴仆,怀揣一枚利刃,趁人不备,混进了赵毋恤家中正在装修的豪华厕所里。豫让假装在粉刷墙壁,等着赵毋恤自投罗网,没想到赵毋恤太过敏感,一眼就看出这个奴仆有问题,让身边人拿下,果然搜出了一枚利刃。
豫让要以死殉义,尽人臣之忠,其实心存大义的,还有他的敌人赵毋恤。豫让刺杀自己,赵毋恤有一万个理由杀死豫让,赵家门人也劝家主除掉豫让,但赵毋恤很大度地赦豫让不死。理由是“彼义士也,知伯已死无后,而其臣至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士”。当然,不能排除赵毋恤以赦豫让树立自己仁慈形象的嫌疑,但反过来说,豫让刺杀赵毋恤,也不是图一个江湖忠义之名吗?
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赵毋恤释放豫让后,豫让并不感恩,反而用自残的方式折磨自己,改变自己的外形、声音,准备再次刺杀赵毋恤。豫让把全身涂满了黑漆,导致皮肤溃烂,甚至把烧红了的炭放在嘴里,造成声带嘶哑。
豫让的朋友看到后,问他何苦自残,知瑶已死,你为他报仇又有什么实际意义?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在赵毋恤门下,必能得到重用,做人不能不识时务。豫让说得斩钉截铁:我明知事必不成,但我受知伯厚恩,必以死报之,让后世那些食主之禄却背主求荣的小人们羞愧至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豫让已经不是在为知瑶报仇了,而是纯粹地追求一种人生的存在价值观,即他心中的大义。或者从人性私的角度来看,豫让这么做,是在求死,准确地说,是在求名。只是问题在于,如果心无大义,一般人不敢以死求这样的名,文天祥是以死求名,但这样的求名,又有几人敢做?
豫让再次刺杀赵毋恤于桥下,结果又被赵家门人活捉,激怒了曾经放他一马的赵毋恤。赵毋恤有些愠怒地责问豫让:“你当年也在范氏和中行氏门下做事,范氏和中行氏被知瑶所灭后,怎么不见你为他们报仇,偏偏要为知瑶报仇,何故?”
“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以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以国士报之。”这是豫让对赵毋恤的回答,字字滴血,感人肺腑。范、中行氏待豫让如路人,豫让当然不必为他们复仇,知瑶待豫让如兄弟,恩宠有加。豫让连番刺杀赵毋恤,就是要以死报答知瑶当年对他的知遇之恩。
豫让向赵毋恤提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要求,他两次行刺赵襄子,论法当死,但如果不报于知伯,他死不瞑目。“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赵毋恤的回复同样感人,“义之”,赵毋恤是一代雄杰,如果这点度量都没有,干脆别在江湖上玩了。
豫让的忠诚感动了曾经对知瑶恨得咬牙切齿的赵毋恤,他脱下袍服,让侍从高高举起,权当是赵毋恤本人,请豫让举剑刺其衣,也算为九泉之下的知瑶报了仇。豫让泪流满面地挥舞着利剑,朝着袍服连刺三下,《战国策·赵策一》对豫让刺衣的桥段写得简洁而震撼人心,如下:
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同样是死,专诸和要离的死可以说轻如鸿毛,不甚值钱,但豫让的死却重于泰山。不过有种观点认为豫让为知伯报仇是愚忠,甚至是奴性的表现,此言大谬。豫让报的并不是主,范氏和中行氏被知伯所灭,豫让无动于衷。豫让报的是德,知伯待他如兄弟,他自然要还报兄弟之德,这是人世间最感人的大义之一。能说文天祥为宋殉国是不识时务吗?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殉国的将士呢?他们也不识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