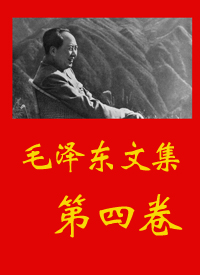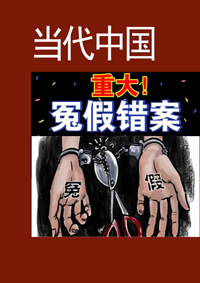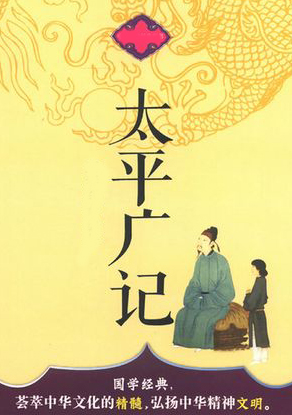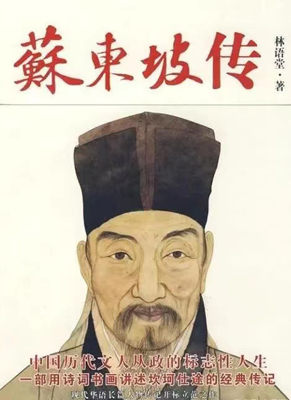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冯道生存之“道”(一)
五代十国兴亡百余年,史事庞杂,再加上五代十国历史不甚著名,需要讲清五代十国兴亡始末,即使写百万字也未必能详说其细。因为篇幅实在有限,所以只能择其主要帝王事迹来写,次要帝王以及相关大臣需要写的,都附在帝王篇中,不单独作传,但那位被世人骂了一千多年的“奸臣”冯道显然是个例外。甚至可以这么讲,不写冯道,不算写五代。五代少了冯道,也就不是五代了。
说到冯道,最著名的事迹就是以一身侍四朝五代,早上是唐臣,上午是晋臣,中午摇身一变成了契丹大臣,下午为汉臣,到了晚上又成了周太师。在一些道德家看来,不忠是冯道永远摘不掉的标签。自宋以来,对冯道不忠的批判连篇累牍,大骂者有之,嘲讽者亦有之。
“衣冠禽兽”“恶浮于纣、祸烈于跖”“名妓转世”“冯道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矣”。更不要说欧阳修、司马光两位大佬那两篇针对冯道的著名评语,而孤独的王安石称赞冯道的那句“菩萨,再来人也”反而觉得非常刺眼。
实际上,被当成道德靶子乱箭穿心的,并不是冯道本人,那只是一具名为冯道的道德尸体,成为后世政权号召人臣效忠的工具。真实的冯道,根本不是宋朝道德家们所谓的贰臣、佞臣、奸臣,如果按他们的逻辑,同样做过唐晋辽汉周大臣的宋初名臣张昭、名将符彦卿岂不都是“恶浮于纣、祸烈于跖”!更何况张昭、符彦卿等人比冯道还多侍奉一个朝代——北宋,从未见宋人骂过他们不忠,公平何在?
五代十国名流如云,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五代十国只是三个人的风云时代:柴荣、李煜、冯道。柴荣和李煜都是帝王,虽然李煜的南唐帝国早被柴荣砸得稀巴烂,而冯道作为大臣,他身上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所以用比较长的篇幅来讲一讲这个有趣的冯道。
冯道,字可道,河间景城人(今河北河间与沧州之间),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父亲冯良建,曾在唐朝末年出任秘书少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后来退休还乡家居。冯家虽然寒素,但却是唐中叶以来的儒门清流名家,家中藏有不少图书。靠山吃山,靠书吃书,冯道生长在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肚子里灌了不少墨水。
冯良建对这个儿子非常看重,希望他能光大冯家的儒门之业,从《道德经》中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冯道。
冯道读书非常用功,无论风吹沙尘,还是大雪压庐,冯道都端坐于房中,手捧书本,如饥似渴地诵读先王治政之道。冯道家庭背景一般,要想出人头地,不读书还有活路吗?但冯道成年时,天下大乱,枭雄遍地,去长安考取功名的路是行不通了。冯道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附军阀做幕僚,一步步往上爬。而当时控制景城的,是横跨幽州、横海(今北京、天津、河北北部与东部)的燕王刘守光,所以冯道出道后的第一个老板,注定是刘守光。
刘守光为人残暴荒悖,而且仇恨士人,“刘守光为燕帅,性惨酷,不喜儒士”,杀士人是家常便饭,“名儒宿将,多无辜被戮”。冯道投奔刘守光,也是硬着头皮去的。道德家攻击冯道靠阿谀奉承混日子,其实冯道在官场上的第一谏就是针对刘守光的,险些被刘守光杀掉。时任幽州参军的冯道可以选择避退,装哑巴谁不会?但即使看到同僚孙鹤在劝谏刘守光时被酷刑处死,年轻热血的冯道依然没有退缩,当众劝刘守光不要做昏君,激怒了刘守光,把冯道送进大狱。只因为冯道人缘好,为了拯救冯道,幽州文官们想办法捞出冯道。这次劝谏险些丧命,对冯道后来的人生观难免会产生一些不太积极的影响,胡三省就说:“冯道自此历事唐、晋、汉、周,位极人臣,不闻谏争,岂惩谏守光之祸邪?”但冯道并非没有再谏过君主,李存勖和柴荣两大英主都领教过冯道的强硬,只不过胡三省向来瞧不上冯道,对有利于冯道形象的,胡先生都装作看不见。
刘守光不能用冯道,冯道干脆炒了刘守光的鱿鱼,来到了与燕国相邻的河东晋国,继续追逐着他致君尧舜的理想。
晋王李存勖当时处在人生的鼎盛时期,是典型的明君做派,刘守光不用的人才,李存勖自然要重用。有个叫周玄豹的江湖术士横竖看冯道不顺眼,没少在河东大总管张承业面前说冯道天庭晦暗,不能当官,但张承业素来“重其文章履行”,告诉周玄豹,他推荐冯道的原因只有一个,“惟其有才”。
随着河东晋国开疆扩土,事职繁重,所以李存勖急需一名主掌晋国文翰的掌书记,而张承业郑重向李存勖推荐了冯道。掌书记,相当于办公厅主任,而河东掌书记则相当于最高党政机会的办公厅主任,地位之高可以想见。而正因为如此,盯上这块肥肉的大有人在,比如士族出身的河东推官卢程。但卢程是个饭桶,百无一用,而且“为人褊浅”,嫉贤妒能。
其实李存勖曾经给过卢程机会,让卢程写篇文章,可卢程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李存勖怎么可能用这样的饭桶?为了能让冯道上位,李存勖纡尊降贵,在一次特意安排的酒会上,李存勖站在冯道的座前,微笑着告诉冯道:“此樽酒,赏卿!自今日后,卿便为吾书记。一应文翰辞章事宜,奚付卿处置。”
傻子都知道,冯道将成为新一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的人选,但又出乎所有人意外的是,冯道竟然拒绝了晋王的任命。
冯道当然有些“油滑”,他初来河东,人生地不熟,他知道这个位置有很多人在争,他不想得罪人,特别是那个乌眼鸡似的卢程。面对这个足以使自己青史留名的位置,说不动心,冯道自己也不相信。冯道虽然以自己地位卑下为由婉拒,但他自始至终也没说过自己才不如人。
李存勖当然明白冯道的小算盘,在李存勖强硬坚持下,冯道最终还是接下了这个让人无比眼热的职务。得罪人的事让李存勖去做,反正李存勖也不怕得罪卢程。冯道很聪明,老板想用我可以,你先摆平公司里那些对我羡慕嫉妒恨的人。
冯道有些孤傲,但他出色的工作能力是绝对对得起李存勖给他开的工钱的。但冯道更是谨慎的,他不会在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让政敌如卢程等人抓住反击自己的机会。同时与同僚和睦相处,不会把自己骨子里的清高外现,平白得罪别人。至于卢程等人攻击冯道相貌粗陋,是个乡巴佬,“士人多窃笑之(冯道长相)”,这也不过是格调不高者的无聊攻击罢了。
冯道很会做人,但他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做人底线做交易,在工作上,即使你是晋王,你做错了,我照样当面顶撞你,半点面子也不给你。
李存勖有一次和河东军界头号人物郭崇韬发生了严重冲突。事情的起因是李存勖经常和将士们在大殿上喝酒吃肉,拍桌子骂娘,郭崇韬非常反感李存勖的江湖土匪习气。郭崇韬“以诸校伴食数多,主者不办,请少罢减”,结果激怒了李存勖。李存勖认为自己如果不这样做,弟兄们谁还肯给自己卖命?咱们就缺这几个饭钱?盛怒之下的李存勖赌气地说自己回太原养老,让郭大帅在军前掌兵权。实际上李存勖怎么可能把兵权交给外人,李存勖想到了冯道,便叫来冯道,让冯道写一篇攻击郭崇韬的文章,务必把郭崇韬抹黑成贪得无厌的政治小丑。
后世道德家经常攻击冯道不敢谏君王,但冯道刚来河东不久,就给李存勖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冯道要是奸臣,他会接过这个烫手山芋?听李存勖的话就是了,至于严重后果,关冯道何事?
冯道知道一旦君主与主将闹别扭,将会加重国内的政治生态,甚至引发军心动荡,岂不是外敌之福?河东江山是李存勖的,但同时也是冯道的事业。李存勖是明主,只要他不倒,冯道的未来就有了保障。就凭这一点,冯道也不会置郭崇韬于不顾。
李存勖让冯道写文章,冯道虽然提了笔,却一直没有落笔,任凭墨汁滴在纸上,洇成一个个大黑点。李存勖有些生气,而冯道却语气平缓地告诉李存勖:郭崇韬是国之重臣,大王自毁长城,是朱友贞之福。
一句话就足够了,李存勖再盛怒,也不会砸自己的衣食饭碗,李存勖逐渐冷静下来,他知道冯道这句话的分量。而且郭崇韬也主动向李存勖道歉,给足了李存勖面子,李存勖自然就坡打滚,大家和好如初。
不要认为冯道这次劝谏是和风细雨式的,在性格古怪的李存勖头上拔毛,那是极需勇气的。《旧五代史·周书·冯道传》说得清楚:“郭崇韬入谢,因道为之解焉,人始重其胆量。”可见这次劝谏如果弄砸了,很可能波及冯道的仕途,甚至是人身安全。
奸臣佞臣乌足有此!
冯道这次劝谏,深深打动了李存勖,彼时的李存勖英果贤明,他看中了冯道的治才,更欣赏冯道的胆量,这才是致君尧舜的公忠大臣。虽然当时冯道的资历还有所欠缺,但李存勖已经开始把冯道当成宰相培养了。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十月,李存勖百战灭梁,称霸中原,开始大封文武。宰相方面,李存勖用的是礼部侍郎韦说、尚书左丞赵光胤,外加之前的宰相豆卢革。而时任翰林学士赐紫(三品紫袍)的冯道,则被晋升为正四品下的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时人都知道,户部侍郎不过是冯道进入内阁的一个跳板,谁不知李存勖的用意?
正在冯道书写锦绣前程的时候,他的家乡突然传来噩耗——父亲冯良建病故。哀痛之下的冯道必须按官场规矩,回家丁忧守孝二十七个月,这一年应该是923年。其实冯道并不担心自己的前程,他知道李存勖是一定会给自己在内阁留出一个位置的,三年很快就会过去。
冯道没有想到,他这次回乡丁忧,反而是因“祸”得福。冯道在家乡做了两年农民,每天除了守在坟前,平时多在地里耕种,或者砍柴烧饭,与农夫无二。而在相同的两年里,曾经无比欣赏冯道的当代汉光武却以光的速度从天上坠落凡间,这位扬起十指自称“李天下”的圣明天子昏庸无道,天下怨愤,直到魏兵叛起,李存勖死在洛阳城门之上,一片冲天大火结束了一段伟大的传奇。李家天下,不出意外地落在了河北相公李嗣源手上。
可以想见,如果冯道这两年间一直留在李存勖身边,刀兵之下,谁敢保证冯道毫发无损?甚至变质的李存勖在恼怒之下,很有可能一刀杀掉冯道。
而贤明的李嗣源继位,改变了后唐政权的荒谬乱象,诚为百姓之福,亦是冯道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