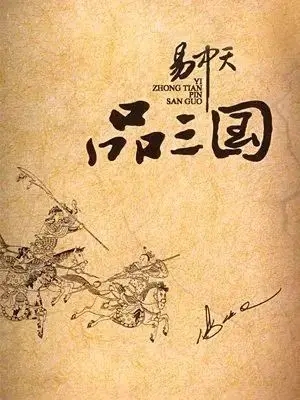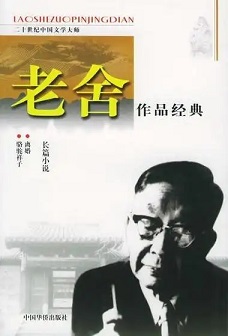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丁巳(499年5月7日)元恪在鲁阳(今河南鲁山)即位,是为北魏世宗宣武帝。宣武帝在位十六年(按古代标准,他在位时间跨了十七个年头,从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到延昌四年正月,499—515),使用过四个年号(景明、正始、永平、延昌),每个年号都是四年。《魏书·世宗纪》说他小时候“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雅性俭素”,做了皇帝之后,“善风仪,美容貌,临朝渊嘿,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矣”。这是对他个人品性风格的描述,格于史体,当然都是尽量说好话的。至于他统治时期的朝政状况,《魏书》的评价就不高了:“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夫汉世,元成安顺之俦欤。”[《魏书》卷八《世宗纪》,第257页。]以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安帝、顺帝来比附他,也就把后来北魏衰乱的责任部分地推给了他。
《魏书》称宣武帝“垂拱无为,边徼稽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总结性评价,说的是宣武帝本人不像他父亲孝文帝那样锐意制作,各方面都没有改革创新的努力,却意外地在南北军事对抗方面收获了巨大成功。这些成功中最重要的两项,即夺取南朝的汉中和寿春,并非北魏积极进取的结果,而是和献文帝时获得刘宋的淮北淮西大片土地一样,是收了南方内政破裂的大礼。只有夺取义阳,算得魏军主动进攻的重大成就。不过,不管过程如何,论疆境南扩的深度,宣武帝时期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孝文帝时期,而且这些重要战略要地的获得,注定了南北军事上强弱攻守的态势再无翻盘的机会。
也许这些军事成就反倒加深了北魏政治酝酿已久的内部危机。尽管一直有战事,但规模都不大,而且都在南方,可是在北方和西北,传统的军镇密集区和职业军人最多的地方,进入了太平盛世般无仗可打的和平时期。北魏以征服立国,军队在体制内最为尊崇,尤其是军力所赖的北方边镇,在朝廷财政支出中享有优先地位。孝文帝迁都,以六镇为首的北方边镇地位开始下降。对高级将领来说,无仗可打意味着无功可立和升迁缓慢,造成边镇官职的吸引力下降。对中下级军官来说,无仗可打意味着得不到正常财政支出之外的后勤补充,那也就意味着经济利益的不小损失。
来自朝廷的好处大幅下降后,军镇各级官贵势必加大对所领镇戍军民的盘剥,底层军民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战争提供的阶层流动性趋于冻结。再加上宣武帝时期北方连年大旱,严重削弱了边镇各戍耕牧自给的能力。此外,随着王朝大兴文治,越来越多的官职开放给华夏士人,相应的,能够供应迁洛代人的官职日见寡少。《魏书·山伟传》:“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魏书》卷八一《山伟传》,第1935页。]虽然说的是孝明帝时期的情况,其实主要是宣武帝时期造成的。
不过,以上话题都是传统政治史所关注的,与我们这里围绕王钟儿/慈庆所讲的故事,虽有联系,却不是那么直接。有直接联系的是宣武帝对权力、对宫廷、对身边各类人的看法和处理方式。
毫无疑问,元恪当上皇帝,年过六十的慈庆一定是高兴的。后来宣武帝把慈庆留在宫内,最紧要的时刻还想到请老太太出马,可见他们一直是有联系的。和北魏此前历代皇帝比,宣武帝崇佛最甚。《魏书·世宗纪》说他“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并记永平二年十一月己丑(509年12月12日)“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宣武帝在皇宫聚众讲经远不止这一次。《魏书·释老志》:“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可以想象,慈庆是一定会参与这类讲经活动的。在旧有的情感凝结之外,老尼慈庆与宣武帝又有了一层新的精神联系。

不过,对于宣武帝来说,从在鲁阳即位到自如地安坐洛阳宫,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经历了一番风雨艰险的。
孝文帝在南阳病重,自知大限已到,匆忙为继承人安排辅政班子时,彭城王元勰央求孝文帝不要选他,允许他在新君继位后退居闲散,还要求孝文帝立下字据。孝文帝共有六个弟弟,他一向器重的是最小的两个弟弟彭城王元勰和北海王元详,尤其是元勰,迁洛后深得倚重,兼综军国大务,声实俱隆。反倒是孝文帝的长弟咸阳王元禧,在军政事务中都无关紧要。元勰大概明白,孝文帝在世一切都好,只要孝文帝不在,自己的处境会非常危险(“震主之声,见忌必矣”),所以他坚定地请求孝文帝允许他“辞蝉舍冕,遂其冲挹”。孝文帝当然理解这一要求的合理之处,不仅答应他,还给太子元恪一份手诏,要他尊重元勰的立场,“汝为孝子,勿违吾敕”。
因元勰退出,孝文帝给元恪安排的辅政大臣一共六人,号称“六辅”。六辅之中,咸阳王元禧和北海王元详分别是孝文帝的长弟与幼弟,代表皇室;任城王元澄和广阳王元嘉在太和后期为孝文帝所亲重,代表宗室;尚书令王肃和吏部尚书宋弁是太和后期诸般改革的智库,代表朝臣,特别是其中越来越重要的文士。虽同为辅臣,六人轻重不同,元禧、元详分任太尉、司空,地位最高,宋弁只是吏部尚书,名位最轻,且死在孝文帝晏驾之前。余下三人都是尚书省长官,王肃是尚书令,元澄、元嘉分任左右仆射。照说王肃位高,不过他从萧齐逃难而来,虽受孝文帝宠用,在朝中全无根基,元澄等人自然不服。
恰好有南齐降人举报王肃与南边勾结谋叛,元澄立即抓捕王肃,同时上报朝廷。审查的结果是子虚乌有,这下子元澄就麻烦了。他因在太和后期特受孝文帝信任,元禧早已反感,于是借机与元详联名上奏,指责元澄“擅禁宰辅”,迫其“免官归第”[《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传》,第540—541页。]。王肃虽获昭雪,心气已挫;元澄虽不久再获任用,亦远离中枢[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认为元禧等畏惮元澄,借机把他逐出权力中心:“按史官称任城王澄之才略,魏宗室中之巨擘也。太和之间,朝廷有大议,澄每出辞,气加万乘而轶其上。孝文外虽容之,内实惮之,况咸阳王禧等乎!因王肃而斥逐之耳。主少国疑之时,澄之能全其身者,幸也。”见《资治通鉴》卷一四二齐纪东昏侯永元元年五月,第4443页。]。这件事发生在宣武帝即位之初。六辅格局还没开始就死了一人,刚刚开始再废去二人,意味着所谓的“六辅”,实际从未存在过。
即使在六辅格局中,真正有权威的也只是元禧和元详二王。在宋弁早死,王肃、元澄淡出后,广阳王元嘉以疏属(太武帝子孙)年老,“好饮酒,或沉醉”,本来就有装饰意味,现在更不会再摆辅臣的架子。这样真正发挥辅政大臣作用的只剩下元禧和元详,而元禧作为孝文帝长弟尤为崇重。即位之初的宣武帝,因居丧守孝(所谓“谅闇”),理论上不听政事,实际上也不被允许行使皇权,军国万机皆决于元禧、元详二人。北魏自道武帝以来虽不见兄终弟及之事,但可汗诸弟依次上位的古老内亚传统并未完全消失。美国学者艾安迪指出,北魏中前期许多皇弟死得不明不白,很像是被有计划地杀死的,目的大概是避免他们在皇帝死后参与皇位继承之争[Andrew Eisenberg, Kingship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Brill, 2008, pp.35-60.]。从这个角度讲,宣武帝元恪的潜在权力竞争者首先是他的六个叔父。
六个叔父中的赵郡王元干,死在孝文帝之前。剩下的五个叔父,名声最大的彭城王元勰在鲁阳时就把孝文帝的手诏跪呈给元恪,表现出告别权力的决心。而陪同元恪南来的元禧,和元恪的东宫诸臣一样,一开始并不信任元勰,元禧甚至不肯入城,而留在城外逗留观望。大概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元勰有夺位自立的野心,这是他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甚至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时机。当元勰把大军指挥权分享给元恪的东宫官属,让孝文帝的御前侍卫转而为元恪效力,和元澄一起在第一时间扶元恪即位,这才基本上洗脱了嫌疑,元禧也才放心入城。兄弟见面,元禧对元勰说:“汝非但辛勤,亦危险至极。”元勰知道他为何迟迟不入城,心下怨愤,回道:“兄识高年长,故知有夷险,彦和(元勰字彦和)握蛇骑虎,不觉艰难。”从鲁阳开始,元禧代表皇帝行使军国大权。回到洛阳,元详也加入进来,不过他作为幼弟,不能与元禧完全并立。就这样,元禧把自己推到新君头号畏忌对象的位置上。
这时宣武帝元恪已经十七岁,不是任人与夺的少年了,但他从无监国或带兵的经历,与朝臣缺乏个人联系,因而不知道可以倚靠或利用朝臣中哪些人来抗衡元禧。而他的成长经历,特别近四五年来过山车般的洛阳宫经历,让他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对宫廷内外以及朝廷上下几乎无法建立信任。这种情况下,他会本能地在自己身边寻求支持。所谓身边,就是物理距离最近的人,只能是侍卫武官和宦官。《魏书》辟有《恩倖传》,专记那些出身细微、以近侍身份大得皇帝(或太后)信赖因而飞黄腾达的人。《魏书·恩倖传》一共为九人立传,其中六人活跃于世宗朝,可见近侍贵宠的现象以宣武帝时期最为多见。
自在鲁阳即位,宣武帝接触最多的便是身边的侍卫武士,而这些侍卫武士又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原太子宫侍卫,另一部分是原孝文帝御前侍卫。宣武帝与他们日常厮混,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和亲密关系,其中乖巧者自然能够察知皇帝的心事,会主动为皇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魏书·恩倖传》所记的王仲兴本是孝文帝的贴身侍卫,宣武帝即位后继续担任近侍武官,职为斋帅,深得宣武帝信任,后来升为武卫将军,总领宫内禁卫军。另一个“恩倖”寇猛,孝文帝时任羽林中郎,属于禁军的下级军官。宣武帝“爱其膂力,置之左右,为千牛备身”,成了手执大刀紧贴皇帝的御前侍卫,后来也做到武卫将军。
不过宣武帝即位之初,最亲密最信任的还是太子宫的旧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赵修。据《魏书·恩倖传》,赵修“起自贱伍”,“本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可见是作为厮役小人在太子宫打杂,虽具“左右”之名,却是“白衣”,即不在正式编制之内,没有官方身份。赶上年轻的太子爷最喜欢拳脚功夫好、擅长骑马射箭的卫士,“颇有膂力”的赵修很快就成了心腹。宣武帝即位后,赵修转为禁中侍卫,继续贴身服侍宣武帝,“爱遇日隆”。可以说,赵修是宣武帝即位之初最重要的耳目和爪牙。从他后来与于烈兄弟关系特亲来看,宣武帝与于烈联手终结亲王辅政,居中联络的除了于烈之子于忠、东宫御医王显,赵修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可是王显也好,赵修也好,对朝廷政务都全无了解,在政治层面毫无经验。要对抗亲王宰辅,还必须有深通朝政的计谋之士。在年轻的宣武帝跟身边几个亲信满腹怨悱却无能为力时,真正能出谋划策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从偏远的流放地秘密潜入京城的高聪。据《魏书·高聪传》,高聪出自勃海高氏中随南燕渡河居住青州的那一支,作为平齐民被掳至云中镇,成了兵户(和建立东魏西魏的那些六镇人士的身份差不多),得同宗的高允提携,才在魏朝做官。高聪不仅长于经史,文才突出,而且“微习弓马”,向孝文帝自荐,愿意带兵打仗。可是到了淮水前线,率领二千军队的高聪“躁怯少威重,所经淫掠无礼,及与贼交,望风退败”,被抓到悬瓠(就是孝文帝曾长期驻扎并且生病的那个南方重镇),孝文帝给他的处分是“恕死,徙平州为民”。平州大致位于今河北省东北角燕山山脉以南的滦河流域(唐山与秦皇岛之间),那时属于边地。可能高聪刚刚抵达平州,就听说孝文帝驾崩,于是不顾禁令,悄悄南返,回到洛阳后观察形势,发现了机会。
虽然细节已全不可知,反正高聪秘密地联系上了宣武帝,献上了最重要的策略。所以《魏书·高聪传》说:“六辅之废,聪之谋也。”宣武帝亲政,立即任用高聪为给事黄门侍郎,职居秘要。
高聪为废六辅做了哪些谋划,事涉机密,当时知者必甚寥寥,他自己事后决不会说,外间自然无人知晓。我这里纯粹推测,很可能正是高聪替宣武帝发现了于烈这个可用之臣。
据《魏书·于烈传》,于烈是孝文帝末期非常信任的武将,他虽不赞成孝文帝迁都改革,但从不公开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且当穆泰、陆叡等在平城谋划反对孝文帝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预”,为孝文帝深所赞赏,把他提拔到禁军统帅领军将军的关键岗位上。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最后一次出征时,没有如前次那样让于烈从行,而是把他留在洛阳,执手告别,说道:“都邑空虚,维捍宜重,可镇卫二宫,以辑远近之望。”当时孝文帝对自己的健康已失去信心,凡事都从长远考虑,把于烈留在洛阳,就是防范意外。孝文帝死在荆沔前线,于烈是洛阳城中少数几个得元勰通报的人之一,他“处分行留,神色无变”,为皇位顺利转移立下功劳。不过,于烈很快就和实际执政者元禧发生了冲突。
据说发端于一件小事。《魏书·于烈传》:“咸阳王禧为宰辅,权重当时。”元禧和元勰的风格很不一样,一向盛气凌人惯了的,更何况此刻高居权力巅峰,哪里把文武臣工放在眼里。他派一个家僮去见于烈,要于烈从禁卫军选派一批羽林虎贲来给他当护卫,以便“执仗出入”。羽林虎贲职在宿卫,只从属皇帝,怎能随随便便跟着一个奴僮出去?于烈说,我作为领军将军,只知道保卫皇帝保卫朝廷,要我派羽林虎贲,必须得有诏书,断无私下奉送之理。家僮悻悻而归,一番报告。元禧动了气,让家僮再来见于烈。
家僮传元禧的话道:“我是天子儿、天子叔,元辅之命,与诏何异?”
于烈面色严峻,厉声回答:“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儿、叔,若是诏,应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
无论《于烈传》这段话是否可靠(显然在美化于烈的同时丑化元禧,更是为宣武帝的后续行为铺垫合理性),于烈与元禧之间一定出了大矛盾。执政与禁军统帅闹崩,当然是极大的问题。元禧“遂议出之”,就是要把于烈调出洛阳,安排他去旧都平城担任恒州刺史。于烈不接受,屡屡上表要求留在洛阳,而元禧控制下发布的“诏书”则一再不听。于烈气急败坏,找到彭城王元勰,怒道:“殿下忘先帝南阳之诏乎?而逼老夫乃至于此!”这时的元勰名望虽高,却不在辅政之位,无从干预。
有意思的是,元禧虽然知道于烈是个威胁,也打定主意把他赶走,却没有先解除他的领军职务。于烈到此地步,一不做二不休,只好悄悄联系皇帝,推动政变发生。元禧与于烈的冲突对于夹在其间的许多文武官员来说固然是灾难,不过,对于宣武帝和他身边那些亲信来说,则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可想而知,在宣武帝与于烈之间沟通联络的,除了于烈的儿子于忠,就是原东宫亲信如王显、赵修这类人物。于烈让于忠秘密地传话给宣武帝:“诸王等意不可测,宜废之,早自览政。”这话才是说到宣武帝心坎里了。
恰在这时,身居元辅却被元禧压了一头的元详也忍不住了。元详虽是幼弟,却深得孝文帝器重,只是太和末年被元勰抢尽风头,新君继位后又被元禧高居其上,自然憋闷含屈。他主动跟宣武帝说,元禧有些做法太过头了,不能再让他这样搞。很显然,元详的目的是扳倒元禧,不过去掉元禧,不等于宰辅之位自动归入元详。于是元详又跟宣武帝说,元勰名望太高,对于皇上总是个威胁,不宜担任宰辅。元详这些想法的一个前提,便是宣武帝自己不能执政,必须有个亲王宰辅。去掉了元禧和元勰,虽然还有两个哥哥在,但他们名声才器都不突出,担任宰辅只有元详最合适。
可是宣武帝考虑的却是终结亲王辅政,这当然是元详意想不到的。
到景明二年(501)正月,十九岁的宣武帝居丧守孝理论上已跨三个年头(其实还不到二十个月),可以结束“谅闇”状态了。《魏书·术艺传》:“罢六辅之初,(王)显为领军于烈间通规策,颇有密功。”王显以御医身份,有较大的便利往来于宫廷内外,特别适合充当宣武帝与于烈之间的联络人。这些参与密谋的一帮人(特别是其中最有头脑的高聪),选择的行动时机正是礿祭。正月间最大的国家祭典是礿祭,祭日,三公诸王要一大早到太庙旁边斋洁,预备入庙行礼。据《魏书·世宗纪》,宣武帝宣布亲政在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可见行动就在这一天。据《魏书·彭城王传》,元禧、元勰和元详(一定还有其他王公大人)在太庙东坊斋洁时,于烈带着六十余名“宿卫壮士”闯了进来,大概他们先已在外面控制了这三个亲王带来的贴身警卫。
《魏书·于烈传》对事件经过有浅白的描述,特别记有宣武帝与于烈父子的对话,显得是宣武帝一人一时的决策,于忠只是传话者,于烈只是执行者。比如宣武帝前一晚让于忠传话给于烈,说“明可早入,当有处分”。次日一早于烈入见,宣武帝说了一堆“诸父慢怠,渐不可任”的话,于烈随即表态“今日之事,所不敢辞”,颇有舞台效果。其实这么危险的行动,一定是宣武帝与于烈早就仔细筹划过的,这一天不过是依计而行罢了,哪里用得着他们二人事到临头一个找理由,一个表决心?
据《魏书·于烈传》,于烈“乃将直阁已下六十余人,宣旨诏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卫送至于帝前”。据《魏书·咸阳王禧传》,于烈把元禧、元勰和元详三人押送到光极殿,见到了宣武帝。宣武帝拿出准备好的说辞:“恪虽寡昧,忝承宝历,比缠尪疹,实凭诸父,苟延视息,奄涉三龄。父等归逊殷勤,今便亲摄百揆。且还府司,当别处分。”最后一句,不是让他们各回各家,而是“且还府司”,意味着要暂时把他们留在什么地方,等接管权力的部署安排完毕,才会放他们回家。消息传出,引起朝廷上下不小的震动,很多人担心会有大规模杀戮,殃及池鱼,于是有些朝臣躲避奔藏,有些甚至逃出洛阳。《魏书·张彝传》记担任尚书的张彝和邢峦“闻处分非常,出京奔走”。
同一天,宣武帝颁布了亲政诏书(可想而知,所有文件都是高聪早已拟好的),让魏朝上下都知道现在是皇帝自己行使皇权了。诏书一方面感谢几个叔父“劬劳王室”,另一方面宣布“便当励兹空乏,亲览机务”,同时给元禧、元详加些好听的官号。据《魏书·彭城王传》,宣武帝告诉元勰,将遵照先帝指示,允许他“释位归第”,元勰表示“悲喜交深”。
宣武帝亲政后,似乎与几个叔父特别是元禧的关系仍然紧张。据《魏书·咸阳王禧传》,元禧失去权位后,连见宣武帝一面也做不到,“赵修专宠,王公罕得进见”。咸阳王府的卫队首领(斋帅)刘小苟向元禧报告说,皇帝身边的一帮近侍(如赵修)扬言要诛杀元禧。元禧叹道:“我不负心,天家岂应如此。”嘴里这样说,心下却万分不安,“常怀忧惧”。四个月过去,觉得日子有点过不下去了,可能加上身边有人怂恿,元禧竟动了李逵那种“反了吧”的念头。正当这个念头愈来愈炽时,五月壬子(501年6月20日),元禧的弟弟广陵王元羽暴死。元羽之死并无政治背景,纯是一个不光彩的意外。《魏书·广陵王羽传》:“(元)羽先淫员外郎冯俊兴妻,夜因私游,为俊兴所击。积日秘匿,薨于府,年三十二。”孝文帝曾严厉批评元羽,说他“出入无章,动乖礼则”,似乎早就知道元羽在外偷鸡摸狗,只是想不到他会死在这种事上。元羽虽然死得不光彩,毕竟是元禧的长弟,我们不知道的是,元羽的死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元禧下决心?
十天后,宣武帝到黄河南岸的小平津打猎,元禧在洛阳城西的小宅召集亲信商议,计划“勒兵直入金墉”,关闭洛阳城门(如曹魏的高平陵之变)。元禧似乎早就确定了要在这一天采取行动,已通知他在禁卫军里安排的亲信(后来宣武帝说“直阁半为逆党”),让他们在北邙山伺机下手刺杀宣武帝,同时派长子元通奔赴黄河北岸的河内郡,在那里举事响应洛阳。不过奇怪的是,元禧在城西小宅的会议上竟全无控制力,参会者“众怀沮异”(就是对元禧的计划提出种种质疑,让元禧意识到无法操作),会议开了一整天,未能形成一个行动方案。等到会议拿不出个结论,元禧自己也考虑等等再说,才派人去追赶元通(当然是追不上的,也就断送了元通的性命)。会议不了了之,跟大家约好保密,然后元禧自己带着家人(“臣妾”)前往他在城东的洪池别墅。参会的武兴王杨集始一出门就飞骑直奔北邙山,把元禧谋反的事报告给宣武帝。
据《北史·咸阳王禧传》,宣武帝打猎归来途经北邙山,在一座佛塔的阴凉里午睡,侍卫们四下追逐猎物去了,身边只有元禧安排的几个武士,但他们担心刺杀皇帝会招致不祥(“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癞”),最终没敢动手,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杨集始赶来告变时,宣武帝身边侍卫不多,又不了解洛阳发生了什么,一时颇为惊惶,只好派于忠先去探探洛阳的情况。于忠驰回洛阳,见自己父亲于烈已布置好了安全警戒,这才到北邙接宣武帝回宫。这之后,自然是对元禧及其党羽的大搜捕,很快就在洛水南岸的柏谷坞抓住了元禧。元禧人生最后一两天的细节,《魏书》《北史》记之甚详,这里一律从略。
宣武帝亲自审问了元禧,结果当然是赐死,死后秘密埋在北邙山上。时在景明二年五月壬戌(501年6月30日)。“同谋诛斩者数十人。”元禧还活着的儿子们(长子元通被杀于河内),一律逐出宗室,即所谓“绝其诸子属籍”。元禧的女儿们,“微给资产奴婢”。元禧倾力积攒的庞大家产,主要部分都被宣武帝赐给他最宠信(意味着在反元禧的事业中功劳最大)的赵修,以及舅舅高肇,剩下的则由内外百官瓜分。元禧诸子衣食匮乏,只有叔父元勰愿意略加救济。走投无路之下,元禧的几个儿子先后都外奔萧梁。
咸阳王府的音乐伎人(所谓“宫人”)作为财产自然也被重新分配,她们重新进入音乐伎人的买卖市场,漂泊流离之际,有感于咸阳王府的昔日,编了这么一首歌:
可怜咸阳王,
奈何作事误。
金床玉几不能眠,
夜踏霜与露。
洛水湛湛弥岸长,
行人那得度。
《魏书·咸阳王禧传》:“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虽富贵,弦管奏之,莫不洒泣。”在江南听到这首歌而泪水涟涟的北人,一定有元禧的儿子们。
元禧死后刚刚两个月,七月壬戌(501年8月29日),原六辅中位次较高的王肃病死,六辅之说遂成往事。
以元禧之死为标志,宣武帝的夺权斗争以胜利告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几个叔父的疑忌已经完结。北海王元详在元禧死后巴结亲附宣武帝的近侍恩倖,因此一度获得宣武帝的信任,但随着这一近侍恩倖集团的分裂(确切地说,是这一集团内部发生了权势转移),元详被牵连其中,触犯了忌讳(比如他和某些禁卫军官有亲密关系)。到正始元年五月丁未(504年5月30日),宣武帝下诏废元详为庶人。据墓志,元详死于正始元年六月十三日(504年7月10日),地点在关押他的太府寺。
这样,宣武帝的六个叔父,只剩下彭城王元勰和高阳王元雍在世,其中元勰以名高望重,素为宣武帝及其亲信所忌。随着宣武帝几个弟弟长大成人,加上宣武帝自己一直未能生子,他非常担心皇叔元勰与皇弟们走得太近。“诏宿卫队主率羽林虎贲,幽守诸王于其第。”这不仅是针对宣武帝几个弟弟的,元勰也享受了同样待遇。《北史·外戚传》记高肇“又说宣武防卫诸王,殆同囚禁”。《魏书·彭城王传》说元勰“既无山水之适,又绝知己之游,唯对妻子,郁郁不乐”。永平元年三月戊子(508年4月20日),唯一的皇子、不到三岁的元昌突然夭折,对宣武帝造成强大心理冲击。偏偏同年秋天,他的长弟京兆王元愉在冀州称帝起兵,虽然一个月内就兵败被杀,深知皇上心意的亲信们(包括高肇)立即把元勰牵扯进去。《魏书·世宗纪》:“(永平元年九月)戊戌,杀侍中、太师、彭城王勰。”据此元勰死于戊戌(十八日)。可是元勰墓志称“永平元年岁在戊子,春秋卅六,九月十九日己亥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80页。],则记元勰死日为九月十九日(508年10月28日)。据《魏书·彭城王传》,元勰被逼饮毒酒而死,在十八日深夜,十九日清晨“以褥裹尸,舆从屏门而出,载尸归第”,对元勰家人说他是喝酒喝死的。
孝文帝六个弟弟,到宣武帝即位的第十年,死得只剩一个元雍了。而且那时宣武帝的四个弟弟中,他已经杀了一个,软禁了一个,剩下的两个也在严格监督之下。传统读史者会说,宣武帝元恪称得上刻薄寡恩。如今我们看元恪的成长经历和他即位后的权力格局,也可以说,他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强烈的不安全感。他生长其中的孝文帝时代,留在他记忆中的,主要是惊心动魄的宫廷倾轧和朝廷权斗,而少许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温暖记忆,就来自他的母亲,以及围绕母亲的那些人和事。正是这种心理特质,使得宣武帝对朝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宗王缺乏信任,而无限亲近他身边那些出身寒贱的侍卫人员。主要是靠着这些侍卫人员,他才从煊赫一时的王公们手中成功地夺回了权力。
同时,宣武帝元恪把对于母亲的温暖记忆,转化为亲近和信任那些与母亲有关系的人。这一点因与王钟儿/慈庆相关,因而为本书所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