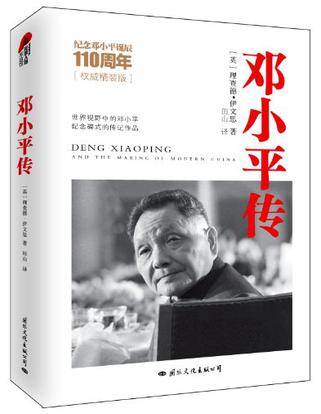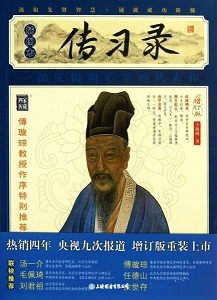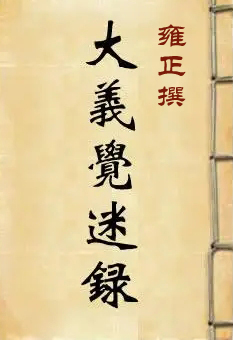高肇一死,执政诸臣看得很清楚,高氏势力中仍有潜在威胁的只剩下皇太后高英。按照制度与传统,在皇帝幼小、出现皇权停摆时,皇太后是唯一有制度性权力填补这一真空的。辅政者如果不能除掉皇太后(如孝文帝死后六辅之对付大冯),那么往往只好容忍她挟持幼君、以皇帝名义执政,从而分享或制衡辅政大臣的权力。对于延昌四年(515)春的辅政诸臣来说,他们最大的幸运是充华胡嫔的存在。在道武帝之后的北魏历史上,皇帝即位后生母仍然健在,这并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文成帝即位时[文成帝的生母是郁久闾氏,死后追尊为恭皇后。《北史·后妃传》说她“生文成皇帝而薨”《魏书·皇后传》说她“世祖末年薨”,都是不准确、不清晰的。据《魏书·高宗纪》,文成帝即位在正平二年(兴安元年)十月戊申(452年10月31日),郁久闾氏死在兴安元年十一月甲申(452年12月6日),十八天后的王寅(452年12月24日)追尊为恭皇后。]。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辅政诸臣的目标是抵制皇太后(文成帝即位时不存在这种情况)。把皇帝生母拉进这个角斗场,至少可以部分地打破皇太后主张自己制度性权力的可能。这一点,在宣武帝病死的那个夜晚,崔光和于忠就已经想到了。所以,他们为了哄骗高肇乖乖入城,就在高肇抵达洛阳西郊那天,尊高英为皇太后。
高肇死后,辅政诸臣立即整顿高层人事,重分蛋糕。据《魏书·肃宗纪》,二月癸未(515年3月10日),就是高肇死后第三天,按照资历拜命新的三公:高阳王元雍以太傅领太尉,班位最高,其次是清河王元怿任高肇腾出来的司徒,广平王元怀任元怿腾出来的司空。当然,接下来其他职务都有一番大调整。半个月后,大概权力分配和政治斗争战利品的分配告一段落,己亥(515年3月26日),“尊胡充华为皇太妃”。也许出于早已协商好的安排,胡氏尊为皇太妃五天后,三月甲辰(515年3月31日),“皇太后出俗为尼,徙御金墉”,彻底被排斥到权力场以外。高英出家为尼,法号慈义,墓志和《北史》都说她出家之地在瑶光寺。这里说“徙御金墉”,是指出家后她被移出北宫,先到了金墉城。出于安全考虑,执政者会先控制她一段时间,不知这段时间有多长,总之她后来进了瑶光寺。
铲除高氏之初,辅政大臣名义上以高阳王元雍为首,形式上是元雍与于忠二人分司内外的共治,其实是于忠大权独揽。元雍能力有限,自孝文帝至宣武帝都看不上他。《魏书·献文六王传》之《高阳王雍传》说他“识怀短浅,又无学业,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真正掌权的是于忠。《魏书·于忠传》:“忠既居门下(侍中),又总禁卫(领军),遂秉朝政,权倾一时。”手上握有禁军,同时又掌握了百官表奏的最终处理权和皇帝诏敕的颁发权,自然“权倾一时”。
《高阳王雍传》载元雍上表回忆于忠擅权时期,“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意思是诏书都由门下省发出,而于忠作为门下省第一号人物,实际上成了诏书的来源。他还说于忠以禁军统帅职务,阻断了小皇帝与辅政诸臣的联系,身为朝宰的元雍却见不到皇帝,“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内外,朝谒简绝”。正是因此,于忠掌握了最重要的人事任命权,用元雍的话说,就是“令仆卿相,任情进黜,迁官授职,多不经旬,斥退贤良,专纳心腹,威振百僚,势倾朝野”。
这样就引发了元雍所代表的外朝与于忠所控制的内朝之间的斗争。
于忠虽然握有实权,但班位还不算高。他对元雍说,宣武帝生前同意过给他“优转”,就是提高级别。《魏书·于忠传》:“(元)雍惮忠威权,便顺其意,加忠车骑大将军。”于忠过去只是二品上,现在提高到一品下,而且在一品下的官职中车骑大将军的位次排在仪同三司之前,可谓大大优转。满足这一点之后,于忠又表示自己在宣武帝去世后,“有安社稷之功”,明示暗示希望在爵位方面有点奖励,其实就是希望封公。封公的事要由三公提出来,当时的三公元雍、元怿和元怀不好驳他的面子(“难违其意”),“议封忠常山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于忠不太好意思一个人得这么大的好处(“难于独受”),又让人提出“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
《魏书·郭祚传》:“领军于忠恃宠骄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郭)祚心恶之,乃遣子太尉从事中郎景尚说高阳王雍,令出忠为州。”郭祚是尚书左仆射,曾做过太子少师,算是孝明帝的“师傅”,属于资历和名望都非常高的重臣。他认为应该警惕权力膨胀的于忠,于是派自己的儿子郭景尚去见元雍,建议把于忠调离洛阳,外出担任州刺史,这就意味着解除他的侍中和领军两个关键职务。同有此心的还有度支尚书裴植和都水使者韦儁,当然他们也代表一个不小的势力。元雍可能被他们说服了,但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却被耳目广布的于忠抢先下了手。《魏书·于忠传》:
尚书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以忠权势日盛,劝雍出忠。忠闻之,逼有司诬奏其罪。郭祚有师傅旧恩,裴植拥地入国,忠并矫诏杀之。朝野愤怨,莫不切齿,王公已下,畏之累迹。又欲杀高阳王雍,侍中崔光固执,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还第。自此之后,诏命生杀,皆出于忠。
前面说过,于忠跟宣武帝说“臣无学识,不堪兼文武之任”,宣武帝也承认他文化不高。那么,他怎么能熟练地应付朝堂上这些需要一点复杂技术的政治斗争?《北史·魏诸宗室传》之《常山王遵传》记拓跋遵的后人元昭在宣武帝死时,以黄门郎在禁中值班,发挥过重要作用,之后“曲事”于忠,“忠专权擅威,枉陷忠良,多昭所指导也”。于忠的另一个军师是名臣李崇的长子李世哲。《魏书·李崇传》说李世哲在高肇、刘腾当权时跟他们“亲善”,因善于钻营,世号“李锥”。《魏书·于忠传》说于忠当权,李世哲找关系靠近他,“遂被赏爱,引为腹心,忠擅权昧进,为崇训之由,皆世哲计也”。原来于忠有元昭、李世哲这样的人在背后出谋划策。既然元昭以及其他谋士能指导于忠“枉陷忠良”,自然也会指导他谨慎面对“朝野愤怨,莫不切齿”的局面。
一方面杀害形象好名望高的郭祚、裴植等人,另一方面还把宗室中“属尊望重”排名第一的高阳王元雍赶出朝廷,朝中已无人可以制衡于忠,这也意味着他突然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就是《魏书·于忠传》传末史论所说的:“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门族?其不诛灭,抑天幸也。”]。《魏书·于忠传》:“于氏自曾祖四世贵盛,一皇后,四赠三公,领军、尚书令,三开国公。”这种荣耀到于忠达到巅峰,但巅峰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可能出于元昭等人的策划,于忠明白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才能稍稍闪避朝野的怒视和狐疑,而皇太妃胡氏再一次成为他的方便工具。
据《魏书·肃宗纪》,于忠发出诏书诛杀郭祚、裴植等,逼迫元雍解除官职“以王还第”,发生在延昌四年八月乙亥(515年8月29日)。第二天,即八月丙子(515年8月30日),于忠就采取行动,“尊皇太妃为皇太后”。之前,杀高肇的权臣于忠、元雍、崔光等,为自身长远安全而逼迫高英出家。现在于忠排挤了辅政朝宰元雍,杀害尚书省高级官员多人,当必须向朝野表明自己全无危及皇权的野心时,又不得不抬出胡氏来填补高英的位置。他相信,以他在宣武帝死后从高英手下救过胡氏的大功,胡氏对他只有感激,全无威胁。
然而,也许他始料未及的是,胡太后远比高太后更有性格、更有能力。《北史·后妃传》:“(胡)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机,手笔断决。”经历了内宫十余年的艰难磨砺,她已从一个天真少女成长为颇有见识的成熟女性。高英出家,虽然获利最大的是胡氏,但这并不是她主动操作的。她那时初得解放,连亲生儿子都还没见到,自然没有能力排挤高太后。被尊为皇太后固然是她的一大梦想(或者是她过去都不敢梦想的),可是同样,这也不是她自己可以争取的,而是于忠和元雍争权、朝中政局发展的结果。如果于忠和元雍(及二人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之间)不生嫌隙,或至少维持某种平衡,那么胡氏可能会一直枯坐别宫,短时间内连儿子都见不到。从少年入宫到现在,她一直是被动的,逆来顺受,任凭命运摆布。不过,从被尊为皇太后开始,她终于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了,因为她知道如何利用制度赋予的自由空间,来为自己争利益。
胡太后要争的第一个利益,是和自己的儿子团聚。据《肃宗纪》,胡氏被尊为皇太后在八月丙子(515年8月30日),十二天之后的八月戊子(515年9月11日),“帝朝皇太后于宣光殿”。宣光殿是后妃所住的北宫的正殿,孝明帝从中宫的显阳殿经永巷门来到北宫,在宣光殿见到自己的母亲,对孝明帝来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自从五年半以前分娩成功,母子立即被分离,那时胡氏可能都没有机会,或没有力气认真看一眼孩子。重聚之时,按照那时的算法,孝明帝已经六岁半,可以说是七岁了。虽然史书不载,可以想象二人必是涕泪涟涟。
胡太后既然与儿子相聚,自然不会放他离开,从此母子要同吃同住了。这样,于忠与皇帝之间就出现了一道新屏障。尽管于忠作为侍中仍然出纳王言,但王言的具体内容却不再完全由他说了算,而要经过胡太后这一关。同日发布诏书,大赦天下,以庆贺皇帝与皇太后重聚。第二天(9月12日),颁布诏书,调整元雍去职之后的三公,元怿代替元雍以太傅领太尉,元怀以太保领司徒,元澄从尚书令升为司空。再过一天(9月13日),于忠得到元澄腾出的尚书令。据《魏书·于忠传》,于忠这一次新得到的职务是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同时“侍中、领军如故”。尚书令已是朝官之最,离三公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过也许在于忠看来这还只是正常升迁,而得到崇训卫尉一职就很不寻常了。胡太后在北宫住在崇训宫,她肯给于忠加崇训卫尉,是显示把自己的安全防卫完全交到他手里,显示了极大的宠信。
胡太后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的政治智慧,她对于忠的宠信是一种交换,要交换的是于忠支持她临朝称制。据《魏书·肃宗纪》,八月壬辰(515年9月15日),“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临朝称制,就是制度性的皇太后代替皇帝行使皇权。称制,是代表皇帝说话,特殊情况下大臣也可以称制。但在制度意义上,临朝称制的几乎只能是皇太后。看不惯或敌视于忠的内外朝官,当然希望以太后临朝称制来制约或削弱于忠的威权,所以一定会有很多大臣附和这一提案。但是,如果于忠坚决反对,他也一定能找到办法阻止这一提案得到批准。只不过,胡太后刚刚向他表达了无比的亲近姿态,显然听政后也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他有什么必要去冒险抵制呢?这大概是于忠那时的基本心态。
不知是不是于忠犹豫不决,或宫廷内外另有势力需要协调协商,具体情况已无从了解,但看起来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过了十三天才有结论。《魏书·肃宗纪》:“九月乙巳(515年9月28日),皇太后亲览万机。”这是胡太后在北魏政治史上崛起的时刻。今后许多年里,北魏政治的许多发展,至少在表面上,就要以她为中心了。跟以前相比,女主听政的最大不同,是太后要真正与百官见面,听他们汇报政务,当场作出决定。这是朝官都在场、都见证的,辅政权臣没有办法在中间制造一个可由自己控制的间隔。只要太后和皇帝在一起(这是太后临朝听政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人能够以皇帝的名义反对太后。太后的意志以诏敕的形式下达,胆敢违抗者就是与北魏国家机器对抗。
在冯太后于太和十年(486)结束听政之后,整整四十年过去了,现在再次出现了女主听政。
胡太后听政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于忠从权力中心赶出去。在朝廷,宣武帝的几个弟弟,特别是清河王元怿,可能会是太后的重要智囊。在内宫,曾救过她性命的宦官刘腾也会给她出主意。因此,胡太后对付于忠显得非常讲策略,是分阶段、分步骤的。第一步,解除他的侍中和领军职务,特别是后者,剥夺其军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隐患。《魏书·于忠传》:“灵太后临朝,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尚书令,加侍中。”解除了这些内朝职务之后,又给他“加侍中”,显然是为了宽慰他,可是加侍中不是侍中正员,且很可能只是一个名义,不能如正牌侍中一样在禁中上班。另外一个宽慰于忠的措施,是拜于忠的夫人元氏为女侍中,赐号范阳郡君。这位元夫人比于忠有文化,史称“微解诗书”。这可能发生在十月至十一月间。
当然,被解除了那么多职务之后,于忠还是尚书令,是行政执行机构尚书省的首脑,号称端右,是非常显要的。又过了十来天,才进入第二步。太后在崇训宫见门下省的侍官(侍中、黄门郎等),问道:“(于)忠在端右,声听何如?”众人都回答:“不称厥位。”于是下诏,外派于忠去担任冀州刺史。这个过程中,于忠基本上没有抵抗的机会,有的只是担心情况会更糟。好在胡太后念他救命有功,虽然后来元雍、元匡等请求加以重罪,太后都替他遮挡了,算是“软着陆”,后来竟得善终。
此后四年,都是胡太后临朝称制。
这四年间,与我们所关注的老尼慈庆相关的,主要是一些人物的死亡。对于这样一个上了年岁的人,她听到的消息中最能引发她关切的,总是那些在她生命中出现过、重要过的人的死亡。首先是胡太后的姑母比丘尼僧芝的去世。据僧芝墓志,僧芝在熙平元年正月十九日(516年3月7日)夜分,“终于乐安公主寺”,享年七十五岁。她总算看到了侄女荣耀时光的到来,侄女对她的报答只能是隆重安葬。但似乎下葬很快,墓志说“其月廿四日辛卯迁窆于洛阳北芒山之阳”。照说胡太后会参加丧礼,但也许只是其中某一个环节。慈庆也一定会前去吊丧。慈庆可能早在平城宫时就认识僧芝,后来在洛阳宫出家后一定与她联系更多。考虑到慈庆年事已高,未必能去送葬,另外我们知道的一些人物,比如一年前出家的宣武帝皇后高英(现在是比丘尼慈义),一定会去参加。还有孝文帝的废皇后小冯,以及王肃的前夫人谢氏,如果她们这时都还健在,也一定会参加,因为她们都是僧芝的弟子。
一年多以后,熙平二年三月丁亥(517年5月2日),广平王元怀病逝。元怀是慈庆抚育过的,应该一直都有一些联系。如果慈庆参加元怀的葬礼,她应有机会见到高猛和他妻子长乐公主元瑛。元瑛对慈庆,应该也有她哥哥宣武帝那种感情。如果高英也来吊丧,慈庆跟她当然毫不陌生。相见说起往事,必有万千感慨。
再过一年半,高英也去世了。
于忠等辅政大臣在延昌四年三月甲辰(515年3月31日),逼迫皇太后高英“出俗为尼”,一开始“徙御金墉”,后来进入瑶光寺。据僧芝墓志,高英出家后拜僧芝为师。高英墓志说她“帝崩,志愿道门,出俗为尼”。《北史·后妃传》:“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高英出家后,她的女儿建德公主就由胡太后抚养。《魏书·皇后传》:“建德公主始五六岁,灵太后恒置左右,抚爱之。”高英年纪轻轻(出家时大概只有二十五六岁,死时不到二十九岁),突然暴死,是胡太后安排的。
《魏书·肃宗纪》:“(神龟元年九月)戊申(518年11月14日),皇太后高氏崩于瑶光寺。”高英墓志:“以神龟元年九月廿四日(518年11月12日)薨于寺。”墓志记高英死日比《魏书》早两天,但两者都说她死于瑶光寺。其实高英死在自己母亲家里。高英的父亲高偃死于太和十年,母亲王氏辛苦带大了几个孩子。高英拜皇后的第二年,王氏被封为武邑郡君。据《魏书·皇后传》,那段时间(应该不是一天而已),高英离开瑶光寺回娘家看望母亲。偏偏这一天“天文有变”,出现了不利于后宫之主的天象。什么天象呢?《魏书·天象志》:“闰月戊午,月犯轩辕,又女主之谪。”《天象志》的这一部分不是魏收书原文,可能是用唐人书补的,时间错误很多。神龟元年闰月在七月[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73页。],但闰七月没有戊午日。随后的小字注占文也问题多多:“月犯轩辕,女主忧之。其后皇太后高尼崩于瑶光寺。……胡太后害高氏以厌天变,乃以后礼葬之。”概而言之,所谓“天文有变”就是月犯轩辕,占曰“女主之谪”。照说这种祸事会应在胡太后身上,她当然要想办法转移给别人。于是她想到了前皇太后高英、现在的比丘尼慈义。《北史·后妃传》:“灵太后欲以当祸,是夜暴崩,天下冤之。”
按胡太后的指令,高英在母亲家里被杀害,然后“丧还瑶光佛寺,殡葬皆以尼礼”。根据高英墓志,主持和参与丧事的是“弟子法王等一百人”。这里说的“弟子”,可能并不是高英/慈义的弟子,而是“佛弟子”的省称,指瑶光寺与高英有关联的比丘尼,当然她们中一定有不少本是宫女,是在高英出家时随她成为比丘尼的。高英下葬时间在十月丁卯(518年12月3日)。据《魏书·礼志》,当皇帝(其实是胡太后)问如何安排葬礼时,朝臣建议“内外群官,权改常服,单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讫而除。止在京师,更不宣下”。既不是正常的比丘尼葬礼,也不是皇太后葬礼,算是某种折中之后的简化。
前往北邙山送葬的一定有高猛夫妇。那时高家在世的人尽管还有一些,不过都成了明日黄花,只有高猛的妻子长乐公主元瑛以宣武帝同母妹的身份,尚能得胡太后礼待,仍然活跃在宫廷内外。老尼慈庆是否会去吊丧、送葬,已无从猜测。
接下来,是一个慈庆必定会参加的丧葬仪式,不过并非新丧,而是改葬。胡太后对一个早在二十三年前就已去世并安葬的人,举行隆重的改葬,这个人就是宣武帝的生母、孝明帝的祖亲高照容。《魏书·肃宗纪》:“是月(神龟二年正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高照容墓志残存文字也提到改葬时间在神龟二年(519),只可惜接下来的月日已严重残泐[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86—87页。]。有证据显示,至迟在前一年高英下葬后不久,胡太后就考虑要给高照容重新安葬。比如,《魏书·礼志》记神龟元年十一月尚书省祠部曹预备改葬事,就与典礼相关的皇帝、皇太后和群臣服制,发符给国子学士要求给出意见,崔光因兼国子祭酒,最后代表众学士上报他们讨论的结果。高英死后,殡葬皆以尼礼,不得配飨世宗,那么将来胡太后死后,是不是可以配飨呢?这次改葬高照荣,就是为将来做准备。
《北史·后妃传》:“(文昭皇)后先葬在长陵东南,陵制卑局。”高照容以普通妃嫔身份,陪葬于孝文帝的长陵陵园,时在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健在,大冯当道,当然不会隆重其事,所以坟墓规模较小,所谓“陵制卑局”。宣武帝亲政后,追尊为文昭皇后,配飨高祖,但并没有改葬,只是在原来封土之上扩大规模,增大了封丘,所谓“因就起山陵,号终宁陵,置邑户五百家”,做了表面功夫,实未涉及封土之下的墓室棺椁。
据《北史·后妃传》,到神龟二年正月,在胡太后主持下,“更上尊号太后,以同汉晋之典,正姑妇之礼,庙号如旧文昭”。据《魏书·皇后传》,这句话实际出自孝明帝的诏书:“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庙定号,促令迁奉,自终及始,太后当主,可更上尊号,称太皇太后,以同汉晋之典,正姑妇之礼。庙号如旧。”“姑妇之礼”,是指胡太后与高照容之间的婆媳关系,因胡太后在这次改葬大典中要自为丧主,所以须正其礼。可是,什么是汉晋之典呢?
孝明帝诏书还提到“废吕尊薄,礼伸汉代”,指的是汉文帝生母薄姬故事。薄姬虽在汉文帝时尊为太后,死后未入刘邦长陵,而在文帝的霸陵附近独营一陵,且未得配飨高庙。东汉初,光武帝刘秀建武中元元年十月甲申(56年11月15日),派司空冯鲂告祠高庙,称“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而“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于是,“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是为尊薄黜吕[《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83页]。光武帝“废吕尊薄”,显然是考虑为身后立规矩。这就是所谓汉典。所谓晋典,是指东晋的简文宣郑太后。郑太后是晋元帝称帝前所纳的妾,是简文帝的生母,虽然简文帝即位后并没有尊她为太后,而简文帝之子孝武帝却追尊祖母为简文太后[《晋书》卷三二《后妃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979—980页]。很显然,所引据的汉晋之典,都事关皇帝生母应该享有正宫地位。诏书倡言“废吕尊薄”,表面上取譬当今之抑黜大冯、尊崇高照容,实际上,是为将来胡太后自己终得配飨宣武帝,预做制度和理论的安排。
改葬高照容,就是在孝文帝长陵西北不远处(相距六十步),另挖墓穴,然后打开宣武帝时所增扩的终宁陵,向下挖了好几丈深,取出棺榇,移入新挖的陵兆。《北史·后妃传》:“迁灵榇于长陵兆内西北六十步。”因为极大地靠近了长陵,可以算是祔葬。然而,在终宁陵取棺榇时,棺上卧着一条大蛇:“初,开终宁陵数丈,于梓宫上获大蛇,长丈余,黑色,头有王字,蛰而不动,灵榇既迁,还置蛇旧处。”据此,移棺时必定先移开大蛇,棺榇迁入新陵之后,又将这条仍在冬眠状态、“蛰而不动”的大蛇,放回棺上。
这一盛大隆重的改葬仪式,自胡太后和孝明帝以下,内外百官、朝野僧俗,不知有多少人参加。高照容的儿女中现在只有长乐公主元瑛在世,她和丈夫高猛自然会参加。高家诸人一定也会参加。还有在高照容身边服务过的宫女宦官们,如宫内司杨氏,不用说也会参加,他们中就有老尼慈庆。当然,这一大典其实不是关于高照容的,高照容不过是文章的题目,文章的内容还是胡太后自己。胡太后“自为丧主”,在全部仪典中始终居于中心位置。只是,对于慈庆和长乐公主这样的老人、家人来说,她们大概多少会感激胡太后此举。无论如何,对于岁月未能弥平的伤害,这样的哀荣多少是个安慰。
这一年老尼慈庆八十一岁。至迟从孝明帝即位以来,她已隐入洛阳宫高墙华屋的暗影深处。只在很少的时刻,比如高照容改葬大典,我们知道她一定会出现,不过即使我们那时在场,也不大可能看得见她。一个团缩龙钟、昏眊重膇的老尼,在车水马龙、人山人海之中,不过是一片若有若无的轻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