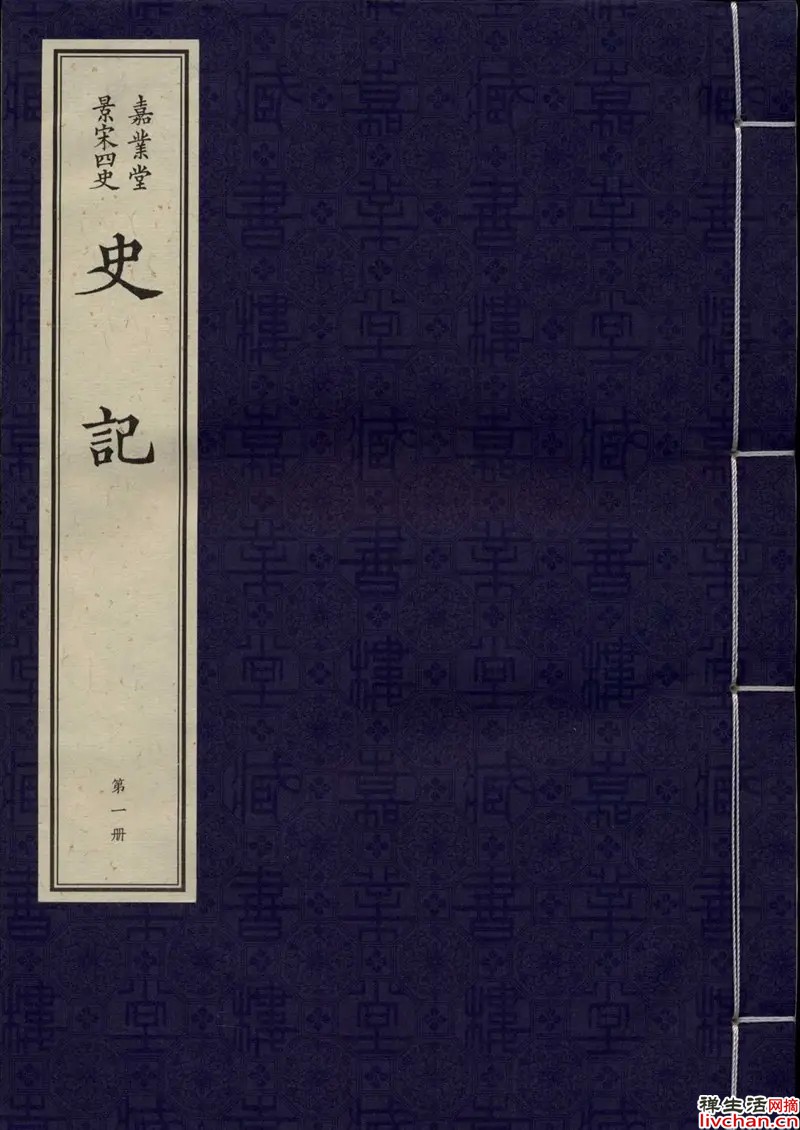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起了他们这一段十分清苦而又情趣盎然的生活状况。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旁边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且说萧子升到北京不久,就接受了蔡元培和李石曾的邀请,出任华法教育会的秘书,他同时还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共同主持着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
在北京等候赴法的湖南青年,很快就达到了四五十人。湖南成为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份。由于华法教育会工作比较松懈,尚没有创造好出国的条件,那些准备赴法留学的青年一时还不能启程,这就使新民学会会员中的一部分人出现了急躁情绪。
毛泽东一方面安慰大家,反复说明充分准备的必要性,一方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频繁奔走于有关各方,积极协商。后来在杨怀中的协助下,华法教育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安排湖南青年学习和赴法问题。蔡元培同意为湖南先办一个预备班,共60人。
预备班在方家胡同召开了一个有不少湖南名流应邀参加的成立大会,会议由蔡元培主持,杨怀中讲了话。会后,有关方面又在报纸上发了预备班成立的消息。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其它各省的青年也陆续来到了北京。
留学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学习法语。预备班分设3处,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熊光楚、罗学瓒等人,留在北京大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以及李富春、贺果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一面学习法文,一面学习机械学和机械制图。蔡和森等人则到了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他在学习法文的同时,还担任了初级班的国文教员。
后来,华法教育会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又增设了一个班。
毛泽东始终没有参加预备班。原因是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可每个学生在出国之时还需要花上不少路费的,此时的他早已债台高筑,再也无法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了,所以就只能留在北京做一些协调工作。
且说毛泽东见诸事安排已毕,就急于谋求一个职业,以便能够获取一点生活之资。后来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了一个条子,他写道:
“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
毛泽东带着推荐信来到北京大学沙滩红楼一楼,在图书馆馆长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他拿出蔡元培写的条子,向李大钊说明了来意。就这样,毛泽东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毛泽东在图书馆上班的地方是第3阅览室,也叫“日报阅览室”或“新闻纸阅览室”。他的职责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新到报纸和阅览人姓名。他管理的中外文报纸有15种之多,其中有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甲寅日报》等等。
他上班时,身着一件褪了色的蓝长衫,脚下一双布鞋,或忙碌在大窗户下的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这种工作既平凡又琐碎,待遇也菲薄,月薪只有8块银元。但这8块银元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战场。这一局面的出现,要归功于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办学方针,正是这种指导思想才使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各种思潮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鱼得水,尽情施展,在全中国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这一切对于矢志要进行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毛泽东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他看来,这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他像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学生时的那个样子,贪婪地阅读着各种报纸。利用管理之便,不必花钱,就可以把许多需要读的报纸读个够,了解、汲取自己还不知道的那些新知识和新思想,对于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实在是太实惠了。
毛泽东住的景山东街,与杨怀中先生家相距不远,他们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此时的杨开慧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豆蔻年华,情窦已开。他乡遇故知,欣喜自不必说。毛泽东常常把一些进步书报和自己的日记及学习笔记送给杨开慧看,有时两人还一起阅读书刊,探讨问题,点评时事,这些交往进一步增进了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不知不觉中,这对年轻人双双坠入了爱河。
女儿心中的秘密自然逃不过父母的视线。杨怀中夫妇开始对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交往予以更多的关注。
有一次,杨怀中先生的好友、北大教授章士钊来家做客,杨开慧也忙着为客人沏茶。章士钊随口问杨怀中:
“令爱是否已经许配人家?”
杨怀中说:
“有位叫毛泽东的青年与开慧有些往来。他原来是我的学生,就学识来说是很不错的。就人品来说,也很不错。可有位先生曾对我说,毛泽东行动举止与众不同,劝我不要把女儿许配给他。”
章士钊说:
“有机会,你是不是让我见见毛泽东?”
后来在章士钊举行的一次讲演会上,有人告诉他毛泽东就坐在几排几号。章士钊在了意,演讲中总时不时地瞟一眼毛泽东。这毛泽东比一般学生要高出半个头,他那长长的头发朝脑后梳去,露出宽宽的额头。他听课全神贯注,很少记笔记,偶尔记上几笔,动作潇洒利落,举止大方。讲座结束后,章士钊顾不上回宿舍休息,径直来到了杨怀中家中。他非常认真地对杨怀中说:
“杨先生,你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把令爱许配给毛泽东。”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他1881年3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善化县,就是现在的长沙;早年曾任《苏报》主编;1907年赴英国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士钊弃学归国,在上海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兼任江苏省教育司长、都督府顾问。1913年7月,孙中山任命他为讨袁军秘书长;讨袁失败后,亡命日本。他在东京与陈独秀创办了《甲寅》月刊。1917年11月,章士钊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18年,他推荐李大钊继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且说杨怀中夫妇眼见得毛泽东和自己的女儿爱得越来越深,也就默许了女儿的选择。自此以后,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常常和杨开慧一起外出,他们或漫步于古都街头,或徜徉于公园之中,故宫、北海、香山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秋天的红叶,冬天的腊梅,在这一对年轻人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此时与毛泽东的处境十分相似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新结识的北大穷学生许德珩。
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由于家境贫困,他穿的衣服非常单薄,不能御寒,所以在课余时间就常常待在有炉火的图书馆里读书,这样既取了暖,又获得了知识。
毛泽东本是好学之人,他对于勤奋好学的许德珩很有好感,于是二人时时在一起交谈读书心得,研究社会问题,志趣甚是相投。
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不断增长,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了。他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就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这期间,身在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的蔡和森,还时常和毛泽东保持通信联系,他把自己到北京后的一些见闻和想法,一一告诉给毛泽东,信中还特别提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事情,并表示要效法列宁,以列宁为导师。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还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有选择地去旁听他所感兴趣的一些新派学者的课,去拜访结交一些校内名流。
胡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省绩溪县,1891年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他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有一次,毛泽东去听胡适的讲座,他趁着提问的机会斗胆写了一个条子传上去。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他一看毛泽东的穿着打扮并不怎么样,而且还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顿生不屑之色。这位一向激进而洒脱的教授,竟然拒绝回答毛泽东的问题。
傅斯年和罗家伦是北京大学学生中的风头人物。他们主编的《新潮》杂志,激烈地抨击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毛泽东对他二人很是感兴趣,便有意结识他们,可傅斯年、罗家伦却看不起这位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
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曾经谈到了他在北大图书馆期间的情况: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往来。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毛泽东还提到了张国焘,他说:
“我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1897年出生在江西萍乡的一个官绅世家,其父张鹏霄曾任浙江象山知事,同时经营钱庄。1917年春,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理工预科,在学生斗争中逐渐成为一位“狂热爱国的人物”。1918年10月20日,张国焘同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了“国民杂志社”;自此以后,他与“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一样,俨然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
毛泽东尽管被很多人看不起,可他却得到了李大钊的器重。这一时期,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比毛泽东年长4岁。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1917年冬受聘于北京大学;1918年5月出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并继章士钊之后,兼任了图书馆主任一职。他一接管图书馆,便积极购进一批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其中有许多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一类书籍。不少激进学生常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并和他一起讨论各种新思潮,讨论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已经成了北京大学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毛泽东因工作关系,与李大钊朝夕相处。他在李大钊翻阅报纸的时候,或是在工作之余,时常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的名气虽然很大,却为人谦和,与毛泽东也很谈得来,二人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正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一边工作,一边认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8年10月,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参加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的工作。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到会的有数千人。毛泽东也专程赶来参加。李大钊穿着棉布长袍,昂首阔步登上讲台,发表了题目为《庶民的胜利》这一著名演说,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后来,毛泽东还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积极参加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各种新思潮研究活动,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清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放弃了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毛泽东在很短的时间内所表现出来的不凡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了李大钊的尊重和赞扬。他称赞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他还说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中国“新青年的创造”。
这一时期,毛泽东经杨怀中先生介绍还认识了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通过几次短暂的接触,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使毛泽东十分叹服。
1936年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这样说过:
“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且说毛泽东一面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学习,一面积极组织在京新民学会会员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陈独秀等人,一起探讨学术和人生及各种新思潮等问题。他还同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邓中夏,还有他的老朋友罗章龙等一些进步青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参加了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到海淀、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农民传播新思想。
这时,来自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青年,有一部分被安排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里。毛泽东先后两次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看望在这里半工半读的青年们,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工厂进行了详细调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小到生产细节,大到工厂的规模、效益及职工工资。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大型现代产业工厂的深入解剖,对促使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据何长工回忆说:此时毛泽东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为湖南预备班学员们出国做准备。此时最要紧的是筹措一笔赴法经费。毛泽东为筹这笔经费,还真的动了不少脑筋。在杨怀中先生的协助下,他想方设法把控制在湖南籍名流范源濂、熊希龄等人手中的一笔款子的利息,也就是存入大俄国道胜银行的前清户部应该退还给湖南的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取了出来,这才解决了湖南籍勤工俭学学生赴法旅费问题。
毛泽东热情而卓有成效工作,受到了新民学会会员和勤工俭学学生们的好评。罗学瓒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
“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钦佩。”
且说在1918年冬季,毛泽东和好友萧子暲结伴踏上了去天津的旅途。
原来他俩都觉得没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为着看一看大海,二人先是乘火车到了天津,然后转车来到大沽口。待他们到了海滨,只见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哪里有万顷波涛?连一滴水也没有,完全是一个冰的世界。毛泽东提议说:
“既然来了,就是结了冰,也得在上面走走才过瘾呀!”
萧子暲欣然道:
“如此最好。”
他俩相约,各自朝一个方向走,转一圈还在这原地会合。商量已毕,毛泽东向西,萧子暲向东,沿着海滨走去。
萧子暲走了多时,见前面有一座木头小屋,便径直走上前去。小屋内一中年男子正在生火烧水,闻得脚步声,抬头见来了一陌生青年,看他一身书生打扮,又不似本地人,甚是诧异,便问道:
“你从哪儿来?”
萧子暲说:
“我是南方人,是来看海的。”
不一会儿,毛泽东也到了,主人给他们泡了茶,又坐下来和他们随便聊了一会儿。二人谢过主人,又分头沿海滨绕去。
萧子暲转了许久,回到了原地。可他左等右等,感觉两只脚都冻麻木了,就是不见老朋友的踪影。毛泽东终于转回来了,萧子暲问他去了哪儿,毛泽东笑道:
“我有意找‘蓬莱仙岛’的,谁知什么也没找到。”
二人上得岸来,乘车回到天津已经是晚上了,街上一片灯光。他俩都急着小便,却找不到厕所,毛泽东只好去问警察。那警察听他一口湖南话,又见萧子暲抱着一个皮包,就起了疑心,说是要打开皮包检查一下。毛泽东有意逗他,从萧子暲手里拿过皮包,紧紧抱住。警察愈加怀疑了,硬是要看,毛泽东硬是不给。那警察抢过去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两条毛巾和牙膏牙刷之类外,尽是些蚌壳。毛泽东和萧子暲看着警察一脸的窘态,竟忘记了内急,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们找到一个小摊位买了几个天津锅贴,顺便进店找了便所才算了事。
转眼到了1919年1月,毛泽东除了抽空继续在北大旁听著名教授的课以外,又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邓中夏也是哲学研究会的会员,他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研究新思潮、新理论,一道进行社会调查。
毛泽东在哲学研究会里又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人。邵飘萍此时担任《京报》总编辑,同时还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里有关办报业务的主讲老师。在他的帮助下,毛泽东也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
这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在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蔡元培曾在成立仪式上发表了演说。新闻学研究会每周活动两次,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研究会的活动。
1919年2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中有这样的记载:
“新闻研究会于19日午后,在文科第34教室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是日,会员到会者为毛泽东等24人。”
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里曾多次听邵飘萍讲《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他还常常去拜访邵飘萍,在新闻理论方面得到了许多教益,这对他后来回湘主编《湘江评论》等刊物,产生了积极影响。
1919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理科第16教室,聆听了李大钊对新闻研究会会员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这是他在北京期间最后一次听李大钊的演讲。
正是:牛儿得草鱼得水,马有伯乐自奋飞。
高人尚需高人识,来日春风谁能追?
欲知毛泽东今后将向何处发展,请看下章介绍。
东方翁曰:毛泽东是一个最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又是一个最无私的人。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尽管生活清苦,债台高筑,却能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同学们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他自己之所以不参加预备班,不是他不想去法国勤工俭学,而是经济条件不允许罢了!事事因人制宜,不可强求。出国深造固然重要,可在国内深造也未尝不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就是一个实例。他在北大期间尽管多受冷落,但他并没有妄自菲薄,依旧是依靠旧友,广交新朋,不断地向周围的人们学习,以提高自身的素质。特别是在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之后,就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伟大转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至于在多少年之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这两个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