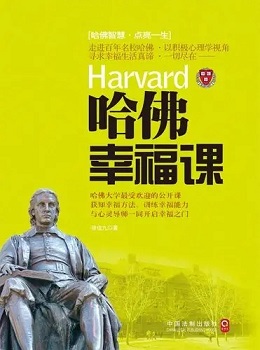2月17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学习的决议,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全党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2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干部教育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讲话,强调了干部学习的重要性。他还号召大家说:
“要在工作或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
此后,中央干部教育部在3月份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这个计划把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3类,编班编组,按照他们文化素质的高低分类教学,做到因材施教。
2月20日晚,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并转陈伯达。
原来,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很重视,就请张闻天将他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转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在给张闻天转陈伯达的信中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的几个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二、“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三、中庸问题,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地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四、说孔子“患得患失”时不必引孔子做鲁国宰相“有喜色”一例,因为不能指出当做了官的时候除了“有喜色”之外应取什么更正当的态度,问题在于那个官应不应做,不在有无喜色。
五、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六、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七、此外,文没有一个总的概念,使初学看了觉得缺乏系统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对于孔子哲学加以概括的说明,指出其根本性质则更好。我看过的伯达的几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点。
以上几点并未深想,只是随说一顿而已。
毛泽东 2月20日夜
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按照毛泽东的7点意见,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审阅。
2月22日晚,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转陈伯达,他在信中写道: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
一、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
二、在最末一段前我加了一句,似更醒目。
三、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即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笔者注)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地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老子等两篇已发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敬礼!
毛泽东 2月22日夜
2月23日,新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央委派,借回乡省亲之名,和叶挺一起从重庆绕道桂林,抵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周恩来此行的任务一是传达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二是力促新四军的内部团结。
原来在六中全会期间,叶挺因和项英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便致电中央和项英,去了香港,因此项英未等会议结束即返回皖南,未听到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对会议后期批判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确立“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方针等重要精神均不了解。六中全会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做叶挺回新四军的工作。叶挺于1939年2月初到了重庆,同周恩来、叶剑英长谈后,于2月16日陪同周恩来飞抵桂林。
2月23日这一天,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新四军军部干部和教导总队干部学员共2000多人,在码头附近列队迎接周恩来和叶挺。
第二天,新四军军部为周恩来举行欢迎晚会,项英在会上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和叶挺并致欢迎词。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向新四军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
晚会结束后,周恩来听取了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意见,向他们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与从前线归来的陈毅、粟裕、傅秋涛等深入交谈,召开了军部各部门人员参加的座谈会。
此时,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处于一面临敌、三面被围的极为不利的境地。新四军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铜陵大通镇这一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狭长地带,遇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因此,帮助新四军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根据新四军所处的区位、周边敌情,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反复研究,商谈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最后确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活动方针。
2月28日,周恩来在云岭召开的新四军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原则、方法及其发展前途等重大问题。
此后,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并多次与项英恳谈,中肯地指出,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他还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中央考虑,目前叶挺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些。我们要像信任党内同志一样信任叶挺同志,军事上要放手让叶挺指挥,你着重于总的领导和东南局的工作。
据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此后叶挺、项英之间开始保持一种和谐状态。
3月6日,周恩来应邀给军部和驻皖南地区干部及教导总队学员作报告。
上午9时,周恩来身着绿色哔叽军装,下着马裤,足蹬马靴,系武装带,挂中将军衔,在叶挺军长陪同下,来到云岭村陈家祠堂军部大会堂。
与会者每人一个背包或蒲团,席地而坐。见到戎装入场的周恩来,会场先是一阵激动的低语,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健步走上由四张八仙桌拼成的讲台,频频挥手向与会者致意,然后以洪亮而又抑扬顿挫的声音开始作报告。叶挺、项英等人及美国记者艾·史沫特莱,围坐在讲台附近的几张八仙桌旁。
此后不久,周恩来在3月14日离开新四军军部,回了重庆。
2月间的一天下午,冼星海应邀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冼星海,曾用名孔宇,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家庭。192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师从作曲家萧友梅和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1928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音乐,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1934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1935年毕业回国,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和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2队,并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2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11月3日,他和妻子钱韵玲到了延安。在毛泽东关照下,有关部门每月发给冼星海15元津贴(此时朱德每月津贴只有5元),同时享受鲁艺的教员津贴12元。这样,冼星海每星期能吃到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
且说毛泽东正在门前小河边的坡地上种菜,见冼星海来了,便放下锄头,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
“欢迎你呀,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
冼星海说:
“主席,你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怎么也种起菜来了?”
毛泽东爽朗地说:
“开荒生产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也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我就可以例外呢?”
冼星海说:
“你是主席,多考虑一点抗日救亡的大事,岂不是更有意义吗?”
“你这个意见我可不能同意。”毛泽东摆动了一下右手,说:“星海同志,开荒生产是有战略意义的。我们要完成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第一个条件是要有饭吃,第二个条件是要有衣穿。这粮食、衣服从哪儿来呢?向国民党政府乞求吗?他们希望我们早早饿死冻死!向边区、根据地的人民征派吗?不行!老百姓够苦的了,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动手,生产自救。”
他见冼星海没有说话,便又说:
“星海同志,我是主席,不但要带头开荒生产,而且还要求你们这些艺术家,参加到开荒生产的行列中来,要超过第一个参加农业生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自己的诗中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相信你们鲁艺的师生一定比他强得多。”
冼星海忍不住笑了。毛泽东一边引着他往自己的住处走,一边说:
“我是湖南人,你是广东人,种水稻算得上半个里手。在延安种谷子,可就变成十足的外行了。星海同志,你会打渔、种稻,再学会种谷子,比起孔老夫子来就高明多了。”
冼星海说:
“主席,我懂了,回去以后,我一定带头开荒,争当一名生产模范。”
“好,很好!这就对头了。”毛泽东满意地说:“作曲家种粮食,在欧洲有无先例我不知道,但在我国却是破天荒的事情。当然,你在种粮食的同时,还要积极地生产精神的粮食。换句话说,人民更需要你写的音乐!星海同志,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吧。”
走进窑洞,毛泽东示意冼星海落座,他点上了一支烟,真诚地说:
“星海同志,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我是一个真正的音乐盲,至多算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万事都有规律可循。我想请教你这样一个问题:从西洋的音乐史看来,一位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应当和他建立本民族的艺术学派有关吧?”
“是的,很有关系。”冼星海说:“格林卡的伟大,就在于他把俄罗斯的音乐从欧洲,尤其是从德国的音乐学派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俄罗斯音乐学派。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沃夏克等人的历史功绩,也是终生为创建本民族、本国家的音乐学派而奋斗。我在巴黎音乐学院的恩师杜卡斯教授,同样也是因为与同辈大师德彪西、拉威尔一齐倡导、创建了法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印象派,而闻名于世的。”
“这就对了。”毛泽东高兴地说:“星海同志,艺术上的流派,恐怕是要受着时代、民族、地域等条件所制约的。你想过没有?如何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建立起科学的、民族的、为广大的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中国音乐学派?”
冼星海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过,你的话启发了我,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要有意识地为建立中华民族的音乐学派而努力。”
“好,很好。”毛泽东说:“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同时又给实践以指导。无论怎样说,一种学派的诞生,总是要建立在最广泛的社会实践上的。没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不会诞生马克思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恐怕艺术上也不会完全确立各种不同的民族流派。”
他见冼星海不住点头,就接着说: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很不彻底,最后,只好把领导革命的大权交给我们无产阶级。这在艺术上也应当有所反映吧?”
冼星海觉得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新鲜,可他一时又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毛泽东忽然站了起来,说:
“星海同志,举个例子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坛大致出现了这样三大派人。”
他举起左手,伸出3个指头比划了一下,又用右手一个一个掰着左手的指头:
“以胡适为代表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以林纾为代表的,认为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皆好;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要创建中国新时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民粹派很快会消亡的,尽管它在一部分知识阶层还会有地盘。但是,像胡适他们那些舶来文化却会很有市场。这些舶来文化是半殖民地社会造成的,也是我们继承鲁迅传统,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大敌。我们如何持久地向这些舶来文化作战呢?”
冼星海已经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沉思片刻,说道:
“一、要努力创作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二、要花大气力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创建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中国音乐学派。”
“完全正确。”毛泽东提高了声音:“中国要革命,必须引进马克思主义。要创建中国音乐学派,恐怕也要引进西洋的音乐技术,但一定要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我希望学西洋音乐的人,不要顶礼膜拜洋人,单纯地做西洋音乐的传声筒,翻译员。要立志借鉴西洋音乐的技术,创建中国的音乐学派。”
毛泽东的话使冼星海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教育,而要他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的嘱托,更让他激动不已。后来当他见到塞克时,就将毛泽东的期望和嘱托说了出来,并说要塞克写个“厉害的、新的、带劲的”歌词,尽快“创造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