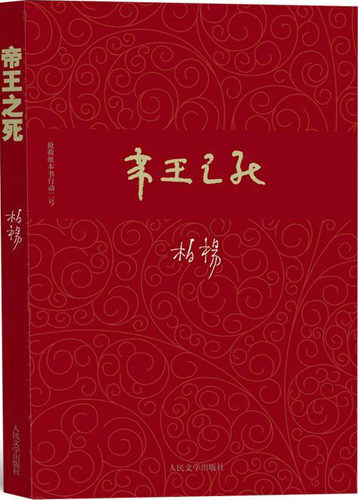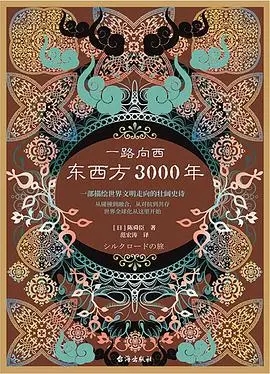读了这篇,王安石怎样做学问和怎样教导别人做学问都很清楚了。用心传授,以意传授,恳切求教,深刻思考,而将所学的东西施行于世间,王安石研究经书 的目的都在这里了。我认为不只是研究经书,百科的研究,都应当是这样。如果不按这样的方法,而只靠在讲堂上听传授讲义,那么即使记诵极多,最终也不能有创 造性地阐释发挥,一国的学术,也就没有进步了。《宋稗类钞》说王安石闲居静坐,研究经书,用意良苦,曾放几百颗石莲子在几案上,边咀嚼边思考,吃完了还没 有想出来,往往咬到手指流血而自己还没有感觉到。这种说法虽说不知可不可信,但他致力于学问的坚韧刻苦,思考的深刻投入,可见一斑。黄山谷诗中说:“荆公 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牗。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可以说是公正的评论。自从元祐初年,国子司业黄隐毁掉 《三经新义》的版,这书就很少在世间流传,元明以来就亡佚了。本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存《周官新义》一种(今“粤雅堂丛书”中有 这本),王安石的遗言,才能借此得以没有失传。我曾取来阅读,它的阐述和发挥很多,不是后代的儒者所能赶得上的。全谢山说:“王安石解经,最有孔、郑家 法,言简意赅,只是他那和字说纠缠在一起的部分,不无穿凿的内容。”(见《宋元学案》卷九十八)这仍在赞誉王安石专句之学。章 句之学,是王安石学术中的糟粕。
后人动不动就说王安石诋毁《春秋》,说它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现在考证林竹溪《 斋学记》中说:(《宋元学案》引)
尹和靖说:“王安石不曾废《春秋》。废除《春秋》,把它当做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都是后来无所忌惮的人托王安石的话。韩玉汝的儿子宗文,字求仁, 曾给王安石写信,请教六经主旨,王安石回答他,只是关于《春秋》说,此经比其他的经尤其难,盖三传都不足信也。王安石也有易解,言辞很简,疑问处缺少,后 来有印行的,名为《易义》,这不是王安石的书。和靖距离王安石的年代不远,他这么说,很公平。现在的人都把王安石说《春秋》是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作为他 的罪名,冤枉啊。”
今按《答韩求仁书》,被存于他的本集中,确实如和靖所说。王安石不但不回答求仁问《春秋》的话,就是对于问《易》的内容也不回答,大概是这两种经书 微言大义,比其他的经书都深奥,如果不是受孔子亲口教授,没有办法理解。如果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没有不谬以千里的。王安石不敢臆测,正是孔子所说的君子 被蒙蔽是因为他还有不知道的东西,我们正应当因此而认为王安石做的对,而怎么能诋毁他呢?况且古代的学校,春秋教授《礼》、《乐》,冬夏教《诗》、 《书》,而孔子正言,也仅在诗书执礼,难道不是因为《易》、《春秋》的大义,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能说的吗?而王安石只把三经设立在学官中,也是效法古人罢 了。
(考异十九)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后序》中说:“王安石想要解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孙莘老的传已经出来,一看到感到很好,自知不能再比他写得好 了,于是诋毁《春秋》而废止。说: 这是本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不能在学官中教授,不用于科举。 ”李穆堂驳斥他说:“王安石想解释《春秋》,还没有著书,别人是怎么知道的?见到孙莘老的传而嫉妒,诋毁他的传就足够了,何至于因为传而诋毁经呢?诋毁传 容易,诋毁经难,舍弃容易的,而选择难的,傻子也不会去做,而王安石会那样做吗?而且据邵氏辑的序文,说孙莘老晚年时为儒士们穿凿的说法而忧虑,于是为 《春秋》作传,那么孙莘老的这个传,应该成于晚年。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年六十八岁,孙莘老在元祐元年才拜谏议大夫,而死于绍圣年间 (公元1094年~1097年),死时六十三岁。这样孙莘老要比王安石小十多岁,他晚年所著的书,王安石大概没有看到,而嫉妒的说法是从何而来呢?周麟之 胡乱编造,后人相信了他,这些人的丑陋和周麟之没有什么区别。”又说:“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这种说法,曾从先达那里听说过,说是见于临汝闲书,大概痛恨 解经的人,而不是诋毁经书。王安石的弟子陆佃、龚原,共同研究《春秋》,陆佃著《春秋后传》,龚原著《春秋解》,遇到疑难处就认为是缺少文字。王安石笑着 说 缺文如此之多,那么《春秋》就成了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了。 大概是说研究经书的人自己不理解经书,就不应当把它当缺少文字对待,意思实际上是尊经,而不是诋毁经书。”现在看孙莘老的《春秋传》,不只是周麟之有跋, 杨龟山也有序。杨龟山说:“熙宁初,崇儒尊经,训示开导了许多贤士,认为三传的异同,无法考证,对于六经尤其难以了解,因此《春秋》不被列在学官,并不是 废而不用。而士人正急于科举的学习,于是就缺少不讲了。”这正和尹和靖的说法相同。杨龟山平时最好诋毁王氏的学说,而他这样说,为什么后人不提起这些,而 只信周麟之的话呢?
王安石生平所著书,有《临川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现在流传的是元金谿危素搜辑而成,共一百卷,后集也在其中,不是原来的版本),《周官义》 二十二卷(今《四库》所收录的《永乐大典》本为十六卷),《易义》二十卷(见《宋史·艺文志》,而根据尹和靖说这并不是王安石的书),《洪范传》一卷(今 存集中),《诗经新义》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礼记要义》二卷(今佚),《孝经义》一卷(今佚),《论语解》十卷(今佚),《孟 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说》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一生对于书是无所不看,到老更加热心,在晚年写的《与曾子固书》中说:
(前略)我从百家诸子的书到《难经》、《素问》、《本草》、各种小说,没有不读的,农夫女工方面的内容,也无所不问。后代的学者,和先王的时候不一 样,如果不这样就不能了解圣人的原因吧。有了真知然后再去读,就可以有所选择,所以异端的学问就不能使自己混乱;也因为不使自己迷乱,因而就可以有所选 择,更加明了大道。子固看我所掌握的,还能被异端的东西所迷乱吗?现在迷乱的风俗,不在于佛学,而在于学问上。士大夫们沉浸在利欲之中,相互用言语恭维, 不知自己约束自己罢了,子固认为是这样吗?(案:子固来信规劝王安石学习佛学,这是王安石的回信。)
王安石晚年潜心于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真谛,佛学和道学两方面,都有所得,而他理论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世,在他的《读老子》一篇中讲:
道术有根本有末流,根本是万物生长的基础,末流是万物成就的条件。根本出于自然,所以不用假借人力就可以表现出来,万物依靠它生长。末流涉及外形器 用,所以要依靠人力然后万物才会长成。不用假借人力万物可以依靠它生长,圣人可以不用说、不用做;到了要依靠人力然后万物才能长成,这就是圣人不能不说、 不能不做的原因。所以当初圣人在位,把万物生长、长成当做自己的责任,一定要有四种治理措施,这四种措施就是礼法、音乐、刑罚、政治,是万物长成的条件。 所以圣人致力于培养万物长成,而不说使万物生长,大概是因为生长效法自然,不是人力能够实现的。老子却不这样,认为涉及外形和器用,都不值一提、不值得去 做,所以抵触礼法、音乐、刑罚、政治,只讲道。这是不能明察事理而又要求过高的错误。道是自然的东西,又何必干预呢?只是因为涉及外形器用,一定要等人去 说、等人去做。《老子》上讲:“三十车辐共用一辙,因为它是空的才会用在车上。”毂辐能有用处,本来就在于车没有用处,然而工匠砍削雕琢木料从来没有达到 无的地步,是没有用到自然的力量,可以不用参与。现在造车的人知道造出毂辐从来没有达到无的地步,但可以把车造成,是因为毂和辐具备了,那么无就有了用 处。如果知道无的用处却不去造毂和辐,那么造车的技术自然就生疏了,现在知道无可以用于造车,用于治理天下,却不知道为什么有用。所以无可以用于造车是因 为有了毂和辐,无可以用于治理天下是因为有了礼法、音乐、刑罚和政治。如果在车上废弃了毂和辐,在天下废弃了礼法、音乐、刑罚和政治,只是坐着等待无发生 效用,就是近乎愚蠢了。
现代西方学者宣讲哲学来推动社会学、国家学,他们的理论繁多,总结起来说,不外乎两种说法:一是说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出自天演,都是由自然规律 决定的;驳斥他们的人说,优胜劣汰,天没有慈悲之心,择优是人们自己的选择。如果听从第一种说法,就是遵从命运;如果听从第二种说法,就是遵从力量。遵从 命运而不知力量重要,就会造成放任而社会不再进步;遵从力量而不听从天命,就会过于干涉而社会也因此不会进步。明白了命运和力量的相互关系,是不是也差不 多明白了大道了呢?王安石的这番论述,也许有所创见。两千年来学者们论说老子,没有像王安石这样精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