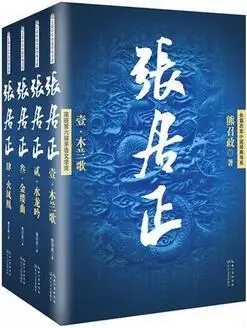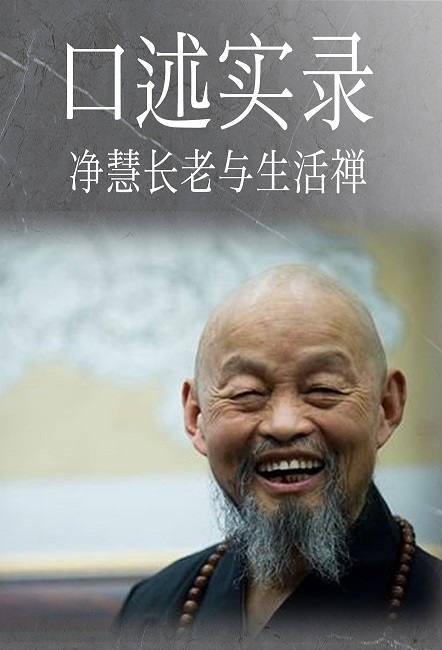打坐就是和我们的身体、心念打交道。昨天我们讲到数息、观呼吸,通常在汉传佛教里,另外一个比较被重视的方法就是观察心念、念头。
相比观呼吸来说,这种禅修的方法更细腻一点,要有一定的止的修行作为基础,坐在那里心能静下来,能听话,才可以做观心的修行。观察心念的禅修,比数息更加直接,它是在那最核心的要害问题上用功。这种观察要能念念相续,每个当下都能生起来。
实际上禅宗参话头也是一种观心,但是它以话头带来的疑情作为方便,让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其中,行住坐卧、昼夜六时不放弃,被这个疑情吸住,它的善巧的地方在这里。也有不用话头,直接观每个心念当下的生灭。这里面最重要的技巧就是平等心。
关于平等心,禅宗三祖僧璨大师有一个重要的文献,叫《信心铭》。这个偈子不长,都是讲怎样用功。在这个铭文中,他开始就讲:“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讲的就是平等心。“拣择”和“憎爱”就是分别、不平等。
后面他还讲到,“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这个实际上是观心的技巧。因为我们的心,常常会有一些妄想出现,在那里念念生灭,你希望不要有念头出来,想要压制、止住妄想,你想止住本身就是一个妄想,所以会越来越麻烦、越来越动。
“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平怀”就是平等心,不管念头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不要分别;“泯然自尽”,就像长空的烟霞,它自己就会消失。在这几句话里,他道出了观心最要害的东西,就是对于这些妄想心,你没有必要当真、执著,在妄想上再生妄想。它自己会解决自己。它本身也是缘生缘灭、幻化的。
这种缘生缘灭、幻化的道理,在禅宗里讲得不太多,但唯识宗的有些经讲得多,如《楞伽经》,就是展开讲这个道理的。所以我也建议喜欢禅修的人,特别是喜欢观心、参禅的人应该花时间好好地研读一下《楞伽经》。它把我们的心念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它的体性是什么这些问题讲得很透彻。
这种学习会使我们有正见,这种正见在我们观心的时候——当然我现在讲的也不是参话头的方法,参话头是把一切都放下——使我们能慢慢地契入、明白我们那些念头的体系。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不了解一个人,不认识他,如果天天跟他打交道,慢慢就会摸透他的脾气。对于一个工具,我们不了解,但慢慢地、天天跟它打交道,我们也能掌握它的特性,乃至运用它。
我们的心念也是同样的道理,但冤枉的是,我们一直都把注意力向外驰求。所谓“向外”,其实就是执,不一定是身体外,只要有执就是向外——内、外都是权立的假名。
当然,从我们的心理结构来说,我们有一种不安定、不满足感,总想向外抓个东西,这也就是向外的意思。现在我们要和心念相处,跟它打交道,把它的脾气摸透。它的脾气被摸透以后,就不会牵着我们的鼻子,主宰和奴役我们了。这样讲,问题好像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什么呢?
复杂的是你在和你的心念打交道的时候,会幻化出来种种心念,包括各种见解、以前沉淀的各种印象、往事、情绪、心里的很多结、很多我们在意的东西。当这些东西被牵扯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又往往随之而动,那几乎是本能反应、条件反射,不需要时间。
禅修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中间看出空缺来。平时我们都是本能地反应,其实中间都有空缺,有念头的起落。你在那里找到下手处,用功就容易得力。
在这里,我们就能重新认识到参话头的价值。它的价值是什么?话头是外在的,是祖师们留下来的,所以对初打坐的人来讲,每次提起话头,刹那之间就有看到自己心念起落空缺的机会。当然,这种机会本来念念都有,任何时候都有,但平时我们完全被动、完全被主宰,所以要靠提起话头、内在反照。
观心的要害是不要压制心念。但在《圆觉经》里讨论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心念它生起的时候你完全不处理、放任,自己被它裹挟而去,这是一种病,叫“任病”。所以,既不能压制它,又不能被它裹挟而去,这里就是我们要用功之处。
如果我们能经常体味祖师大德的这些开示,像《信心铭》,然后将之运用在观心的禅修中——不仅仅是打坐,日常生活起心动念都可以运用,长时间持之以恒,你一定会有收获。
慢慢你能做自己的主,不会完全被淹没在各种情绪妄想的大海中, 这是“主看宾”,主在主的位置,客在客的位置,关系已被扶正,没有颠倒,这样你就有信心了。
通常我建议学禅的人要研读一下祖师的这些教导。像《信心铭》这样的开示非常简要,但也是精华。祖师是过来人,过来人把自己的经验用简单的话讲了出来。与禅修相关的经典,像《楞伽经》《首楞严经》《圆觉经》等都很重要,它们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禅修。
本文选自明海大和尚《无门关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