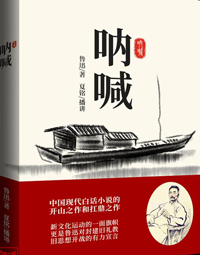隆冬之时,嬴政皇帝开始了最后一次大巡狩的秘密谋划。
对于嬴政皇帝的巡狩,天下已经很熟悉了。平定天下之后的短短十年里,皇帝已经四次巡狩天下了。若从秦王时期的出行算起,则自秦王十三年开始,嬴政的出行与巡狩总共八次,一统之前的秦王出行视政三次,一统之后的皇帝巡狩五次。大要排列如下:
秦王十三年(公元前234年),时年嬴政二十六岁,第一次东出视政到河外三川郡。其时,桓碕大胜赵军于河东郡,歼赵军十万,杀赵将扈辄。嬴政赶赴大河之南,主要是会商部署对三晋进一步施压。就秦之战略而言,秦王这次出行,实际是灭六国大战的前奏。
秦王十九年(公元前228年),时年嬴政三十二岁。其时,王翦大军灭赵。嬴政第二次东出赶赴邯郸,后从太原、上郡归秦。这次出行两件大事:一则处置灭赵善后事宜并重游童年故地,二则会商灭燕大计。
秦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时年嬴政三十六岁。其时,王翦大军灭楚。嬴政第三次东出,经过陈城,赶赴郢都,并巡视江南楚地,会商议决进军闽越岭南大事。
依照传统与帝国典章,嬴政即皇帝位后的出行称之为巡狩。
巡狩者何?《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适诸侯日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也就是说,就形式而言,巡狩并非秦典章首创,而是自古就有的天子大政,夏商周三代尤成定制。《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礼记·王制》、《国语·鲁语》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记载了这种巡狩政治的具体方面。大要言之,在以征伐、祭祀为根本大政的古代,巡狩的本意是天子率领护卫大军在疆域内视察防务、会盟诸侯、督导政事、祭祀神明。然从实际方面看,春秋之前的天子巡狩,其实际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则祭祀天地名山大川,二则会盟诸侯以接受贡献,三则游历形胜之地。就其行止特征而言,一则以舒适平稳,一则以路途短时间短,一则以轻松游览。真正地跋涉艰险,将巡狩当做实际政事而认真处置,且连续长时间长距离地大巡狩,唯嬴政皇帝一人做到了。
第一次大巡狩是灭六国的次年,始皇帝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时年嬴政四十岁。这次是出巡陇西、北地两郡,一则巡视西部对匈奴战事,二则北部蒙恬军大举反击匈奴事。这次出巡的路线是:咸阳——陈仓——上邦——临洮——北地——返经鸡头山——经回中宫入咸阳。这次路程不长,然全部在山地草原边陲行进,且多有匈奴袭击的可能性危险,其艰难险阻自不待言。
第二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时年嬴政四十一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河外——峄山——泰山——琅邪——彭城——湘山——衡山——长江——安陆——南郡——入武关归秦。从路程之遥与沿途举措之多看,大体是初春出初冬归,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的主要使命,是宣示大秦新政之成效,确立帝国威权之天道根基。是故,其最主要举措是四则:其一,峄山刻石以宣教新政文明;其二,泰山祭天封禅,梁父刻石,以当时最为神圣的大典,确立帝国新政的天道根基;其三,登之罘山,刻石宣教以威慑逃亡遁海之复辟者;其四,作琅邪台并刻石,系统全面地宣教新政文明。
列位看官留意,这个伟大帝国的直接史料在后来的战乱中消失几尽,帝国华夏大地所留下的实际遗迹便成为弥足珍贵的直接史料。譬如峄山刻石文、之罘山第一次刻石文皆未见于《史记》,对于非常注重言论记载的太史公而言,绝不会有意疏漏,完全可能是司马迁时已经湮灭,或被掩盖隐藏,而后世重新得以发现。唯其弥足珍贵,不妨录下三篇刻石文辞①,以窥帝国风貌——
峄山刻石文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悠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梁父刻石文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琅邪台刻石文
维廿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事。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专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优恤黔首,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成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
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
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富。节事以时,诸产繁殖。
黔首安宁,不用兵戈。六亲相保,终无贼寇。欢欣奉教,尽知法式。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琅邪台刻石文之后,附记了这篇最长刻石文产生的经过:李斯王贲等十一位随皇帝出巡的大臣在“海上”会商,一致认为古之帝王地狭民少动荡不休,尚能刻石为纪,今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天下相与传颂皇帝功德,更该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于是,产生了这篇专一地全面地叙述灭六国之后帝国新政举措的文辞。
列位看官留意,这三篇刻石文极易被看做歌功颂德之辞,而忽视了它对历史真相真实记载的史料价值。就后世史家对秦史的研究而言,至少忽视了琅邪台刻石文中的两处事实: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谓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谓一量,统一规定形制尺寸重量也。这一事实是说,秦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等之外,还有一个统一,这就是统一大军装备的形制尺度与重量。在诸多史家(包括军事史、兵器史等专史)与文化人的知识认定里,都以为兵器衣甲装备的标准化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历代兵书中,只有宋代编定的《武经总要》规定了各种兵器的尺寸重量。对秦帝国的兵器装备标准化,既往的通常说法是史料无载,一直到当代考古学者在秦兵马俑中发现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镞,方才提出了这一理念。事实上,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便是确实无误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将“器械一量”与“同书文字”并列,可见其重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对此条的解释是:“内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属。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属。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确。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被人忽视而没有作为公认史料提出罢了。其二是“六亲相保,终无贼寇。”当代人大多激烈抨击秦政中的连坐制,几乎没有哪个史家或学人提出连坐制在当时的实际意义。这一条给我们展示了秦帝国自家的实际解释:连坐制的实际意义在于“六亲相保”,其实际效果则是“终无贼寇”。也就是说,起于战时管制的秦法连坐制,通过相互举发犯罪,而达到共同防止犯罪,进而族人亲人互相保护的目标。对于社会总体效果而言,没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没有贼寇这种罪犯了。因为这一实际效果,秦统一中国之后,连坐制非但没有废除,反而是推向了整个华夏。自秦之后,后世断续沿用连坐制而始终不能彻底丢弃,应该说,这种实际效果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在战时社会。
就是在这次大巡狩滨海之行的后期,卢生徐福等几个方士第一次上书皇帝,万分肃穆地说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居之,请求携带童男童女出海求仙。从一个方面说,始皇帝亲临大海,眼见其壮阔辽远,对流传久远的海中有仙之传闻不可能完全拒绝相信,更兼其时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时常发作,遂允准了卢生徐福之请,准许其筹划出海求仙。从另一方面说,其时六国贵族多有逃亡,许多贵族后裔都逃遁到海岛藏匿;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为名目,派出精干斥候于护卫求仙的军士之中,以求查勘贵族藏匿之真实情形。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时年嬴政四十二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三川郡(在阳武博浪沙遇刺)——胶东郡——之罘山——琅邪台——返经恒山——经上党——西渡河入秦。从时间看,是仲春(二月)出发,大约在立冬前后归秦,也是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与上次紧紧相连,其使命大体也与上次大体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达海滨,登临之罘山,留下了两篇刻石文字,其内容与峄山石刻大同小异。这次大巡狩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阳武县博浪沙路段的刺杀皇帝事件。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来见诸于史册:旧韩公子张良携力士埋伏道侧壕沟,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掷嬴政皇帝座车,结果误中副车,刺杀未遂。但在当时,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不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也没有缉拿到罪犯。
也就是说,这件震惊天下的大谋杀,案件当时并未告破。
为此,这次大谋杀给帝国君臣敲响了复辟势力已告猖獗的警钟,将帝国君臣从“天下和平”、“靡不清静”的时势评估中解脱了出来。时隔年余,嬴政皇帝微服出行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遭数名刺客突袭。若非随行四武士力战击杀刺客,嬴政皇帝也许那一次就真的被复辟势力吞没了。博浪沙大谋杀事件,兰池宫逢盗遇刺事件,是帝国新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嬴政皇帝与帝国权力的注意力,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变化——从全力关注构建文明盘整天下,转为关注对复辟暗潮的查勘,终于导致了三年之后(始皇帝三十四年)对复辟势力的公开宣战。从大巡狩而言,博浪沙大谋杀事件,也导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变——从相对简单的新政宣教,转变为巡边、震慑复辟与督导实际政务三方面。这一转变,从马上就要到来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轨迹。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时年嬴政四十五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经旧赵之地——入旧燕之地——辽西郡——碣石——返回再经燕赵旧地——经上郡进入边地——巡视北边——南下归秦。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记载得最为简单,然实际意涵却最为丰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导迟滞工程(坏城郭,决川防),部署求仙事,巡视九原并部署反击匈奴战事。若将史料残留的“点”联结起来,这次大巡狩的实际作为,则立即清楚地表现出内在的轨迹——这次大巡狩,无疑是嬴政皇帝即将实施的内外战略的预备举措。这个内外战略是:对外大举反击匈奴,对内大举镇压复辟。这两个大战略,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镇压复辟必须以肃清长期边患为保证,巩固边地又必须以整肃内政为根基。
尽管史料对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简单的九个字:“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然只要将前后事件通联,这九个字的分量便大大的不同了。就事实说,匈奴长期为患北边,此时的秦军已经退守到九原黄河以南的北地郡与上郡驻扎,连紧靠大河的“河南地”也成了匈奴的不固定领地。要一举占据河南地,并扫灭阴山草原的匈奴主力,将匈奴部族驱赶得远离华夏,便要大举歼灭匈奴的有生主力骑兵;而要真正做到一举大胜,没有通盘的战略筹划是不可能的。此时的九原直道尚未修成,粮秣兵器仍得通过上郡输送,诸方协同尤其要紧。事实上,正是在这次北巡之中,嬴政皇帝与蒙恬、扶苏等协同各方会商部署,最终议决:来年大举反击匈奴,战胜之后立即开始修筑长城。第二年的事实进展,几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战略筹划完成了。
唯其了解这一轴心目标,立即便可明白:所谓东游碣石,所谓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语言说,是造势以惑人。惑谁?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窥见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内外敌对势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这次大巡狩的东部之行中,将求仙之事铺排得很大,而且大举铺排了两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卢生出海,访求两位传说中的古仙——羡门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将离开东部之前,又大张旗鼓地派遣韩终、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队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药。
之后,嬴政皇帝的车骑仪仗销声匿迹了。
百年之后的司马迁,尚且只能留下九个字。此足以说明,直到后来的西汉时期,人们仅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边,至于究竟在巡边中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不是司马迁不想记述,而是因为没有依据。这成为了一个永远湮没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离开东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卢生入海归来了。卢生求仙无着,却带回了那则载于史册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谶言。这则谶言的形式载体很是不清楚,只说是“图书”。若依据传统分析,这则预言当是图谶形式,也就是某种皮张上画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图画,旁边一句字迹古奥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谶言。这幅画究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这句谶言,却是明白无误地被记载了下来。
这件事至少说明:其一,嬴政皇帝在东部碣石逗留的时间不会很短,估计至少两个月上下,否则以古代船只之航速卢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认定:皇帝东游只是要求仙,别无他事。其二,天下复辟势力也关注着边患,企图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制造了这则谶言,借以扰乱嬴政皇帝心神,并激发秦军早日与匈奴大战。因为,在六国贵族看来,匈奴正在强大之时,而秦军正在多年大战后的疲弱之期。与强大的匈奴开战,时日越早,对秦军越是不利。若秦军主力一旦战败,则复辟势力自可趁机大举起事。
以帝国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浅薄的伎俩,更不可能如《史记·集解》中东汉经学家郑玄所解释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距始皇帝仅百年之遥的司马迁,自然清楚这则谶言之实际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却相对暖昧了许多,只录谶言,而不直说因果关系,只在记载谶言之后说了事实:“始皇乃使蒙恬发兵……”虽然,司马迁的指向显然也与郑玄相同,然却硬是不明说。这里显然有两个原因:一则是司马迁“信则存信,疑则存疑”的相对严肃的治史态度,自知此等说法荒诞不经,遂不予置评;二则是司马迁基于西汉时期之大势,对秦帝国的历史只能是表面相对公正,而实则腹诽。此等堆积烟云的录史笔法,笃信怪力乱神的解说手法,是后世史家与注释家解读秦帝国历史的两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丛生,遂使秦帝国的种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变得分外艰难。这是后话。
依据常理解析,嬴政皇帝与随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会为谶言所动。然在表面上,帝国君臣却向外界释放了这则谶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谶言为白头北上巡边。这当如何解释?若果然如郑玄所言,看作帝国君臣愚昧不识天机,诚可笑也。显然,这是帝国君臣的将计就计——你要出谶言么,我便正好借此反击胡人,做好这件最该做的大事。
当然,嬴政皇帝在东部的时日,也非全然耗费在求仙事上。毕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过,则未免太假,总得有些许政事作为。于是,有了嬴政皇帝对燕齐旧地的迟滞工程的有力督促。这便是坏城郭、决川防。碣石之地,正当旧燕赵齐三国拉锯地带,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决,堪称天下川防为害最烈之地。尽管此时中原川防已经顺利疏通,然此地却是迟滞了许多。嬴政皇帝就此彻底解决,正好一举两得。诸般工程雷厉风行地开始之后,随行群臣会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门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说的主要是帝国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门刻文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成服。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成抚。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列位看官留意,这篇碣石门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并诸侯”。与此相联,从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东观刻石文开始,帝国宣教中开始强调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业叙述与新政内容叙述为主,正面强调皇帝之德者很是浅淡,琅邪刻石文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极。”显然,并没有将皇帝之德扩展到一统之前。这次不同,将平定六国第一次提为“德并诸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经开始向彰显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鲜明,其文辞为“奋扬武德”,东观文辞则为“皇帝明德”。然则,都没有从总体上将统一天下、开创文明的大功业归结为“德”的力量。这次的“德并诸侯”四个字,显然是大大地彰显了德功德政。马上将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大巡狩的会稽山刻石文,对“德”也同样做了鲜明强调,文辞为:“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这一宣教转折,是帝国君臣在反复辟中的策略转变。
秦奉法治,更兼为政求实,对王道德政历来嗤之以鼻。虽然,秦政理念认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爱民;但是,由于王道德政已经成为先秦治国理论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与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从来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时为何有此一变?根基在时势之变也。秦一天下之后,六国贵族与儒家门派对秦政的攻讦有一轴心言论,便是“暴政失德”。这一攻讦性评判,既因秦政文告从来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众有所惶惑,又因复辟势力的日渐活跃而大有加剧之势;尤其是焚书坑儒之后,秦不言德,似乎已经成了秦政本身无德的一个表征。对此,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帝国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没有觉察。当此之时,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为一种时势所必须的策略,一种反击复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与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纵观嬴政皇帝的历次大巡狩,其艰难险阻每每令人惊叹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屡抵边陲,却从来没有涉足过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阳大梁新郑的风华地带都是必经之路,却没有一条史料记载过嬴政皇帝在此间的逗留。旧齐之临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两赴旧齐滨海,却都没有进入临淄。东临碣石,濒临燕国,嬴政皇帝也没有去燕都蓟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陇西北地与上郡,三地俱为蛮荒边陲,俱为连绵大山,路况最差,气候最恶,又兼有匈奴游骑袭击之风险,安有舒适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几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颠簸。登泰山封禅,而骤逢“风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树下避雨。当代人皆知,雷电风雨之中在大树下避雨是极为危险的,而其时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学道理,幸未被雷电击中,何其大险也!后过江水,则“逢大风,几不得渡”,连随身玉璧也颠簸沉入江水。再从湘水登衡山,“遇风浪,几败溺”,也就是说,险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险,所以这次大巡狩“至此山而免”,才踏上了归程。
如此奔波一年,刚刚过了冬天,嬴政皇帝又立即再度出巡。这第三次大巡狩更险,方出函谷关,便在三川郡博浪沙路段突遭大谋杀——旧韩世族公子张良带其结交的力士,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击行刺!若非误中副车,嬴政皇帝很可能就此归天了。归来途中,嬴政皇帝为一睹当年长平大战之胜迹,硬是舍弃了相对舒适平坦的河内大道,而穿越了崇山峻岭的上党山地,其崎岖艰难无须描述。年余之后,嬴政皇帝微服出巡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突遭数名刺客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遇刺险境只有淡淡两字:“……见窘。”就实而论,随行有四名高手武士力战护卫,尚且陷入窘迫之境,可见其性命之险!
第四次长距离大巡狩,又是直接抵达滨海之碣石门。那时的滨海地带,是人迹罕至的荒莽边陲,与今日之沿海万不能同日而语,其艰难险阻多矣!碣石门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进入匈奴流窜的北边之地巡视,部署完军政大略后,又从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阳。
后世皆知,秦帝国之驰道、直道、郡县官道相交错,交通网络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应该是极为快捷且相对舒适的。然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迹所过,十有八九都是没有大道的险山恶水,其迂回绕远自不待言,其艰脸难行更是亘古未见。姑且以大数计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万里上下计,则五次大巡狩便是五万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时期的三次出行,七八万里之数当不为夸大也。在以畜力车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在华夏山川之绝大部分尚未开发的时代,要走完七八万里山水险地谈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岁劳碌力竭,岂非古今君王之绝无仅有哉!——
注释:
①此三篇刻石,皆以韵断意。《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前两篇为三旬一韵,琅邪台文为两句一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