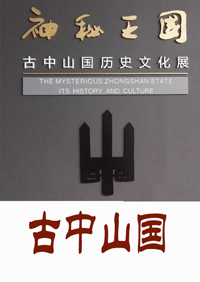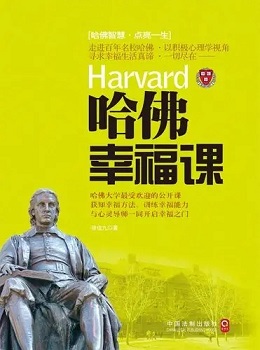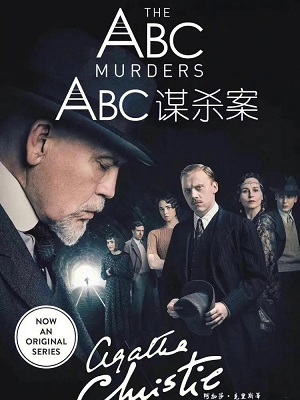从频阳归来,嬴政皇帝第一个召见了丞相李斯。
皇帝直截了当地对李斯提出了一个主张:停止骊山陵与长城两大工程的远途徭役征发,骊山陵教内史郡老秦人修建,长城各段由附近郡县征发修建,中原与旧楚地不再征发徭役。末了,嬴政皇帝问了一句:“丞相思之,是否可行?”李斯默然思忖良久,终于一拱手道:“陛下,此策虽好,有利于安定民心,然却难以实施。”嬴政皇帝很是惊讶:“为何难以实施?有人阻挠?”“大秦律法严明,安得有人阻挠哉!”李斯摇头叹息了一声,又道,“陛下多年执掌大政,可能忽视了关中人口的变化。据老臣所知民户数,目下之关中人口总共五百万上下;其中,老秦人只占两成左右,堪堪百万人而已,且大多为老弱妇幼;其余七八成多,都是近十年迁入的山东人口,计四百万余。若以关中民力修建骊山陵,老秦人实则无可征发。所能征发者,依然是迁入关中的山东六国贵族与平民人口。然则如此一来,骊山陵工地则有可能成为骚乱动荡之根源。”嬴政皇帝惊讶道:“何以有此一说?”李斯道:“灭六国之后,骊山陵开始大修,集中了十万余六国罪犯,人云刑徒十万也。若再将迁入关中的六国贵族青壮征发于骊山,则骊山将聚集数十万山东精壮人口。若六国贵族趁机生乱,便是肘腋之患。此前,已经有黥布作乱,陛下安得不思乎!”嬴政皇帝默然了,良久,大是困惑地问了一句:“怪亦哉!关中老秦人如何快没有了?”
“陛下龙行虎步,无暇顾及细节矣!”李斯怅然一叹,提起案头大笔在备用的羊皮纸上边写边道,“陛下想想:以秦昭王后期领土计算,老秦人总共千万上下;其中陇西、河西、巴蜀、关外几郡人口,大约占秦人六成,有五百万上下;关中腹地人口,大约占秦人四成,有三百万余。关中腹地这一半人口,加上整个陇西数十万人口,是真正的嬴秦部族,也就是老秦人了。自灭六国大战开始,秦国主力大军连同咸阳及各要塞守军,再加皇室与各种官署护卫军士等,总数是将近百万。这一百万之中,真正的老秦人至少占去七成上下。如此,以全部秦人总数计,大体是十人一兵;而若以秦国成军人口①基数计,则已经是两男一兵了,到顶了。平定六国大战中,秦军将士战死三十余万,后续征发又如数补入,这就是一百三十余万了。平定六国之后,又征发三十余万民力进入南海,其中八成是秦人男女;再加几次征发老秦人赴北河守边,又有几次与山东人口互换迁徙。总体说,关中迁出的老秦人计一百余万,入军带前后伤亡八十余万,总计两百余万……目下之关中老秦人,除了在军男子,八成都散布到边陲去了……”
嬴政皇帝第一次长长地沉默了,脸色阴沉得可怕。
也是第一次,嬴政皇帝没有理睬李斯,一个人径自转悠出去了。及至外厅值事的蒙毅察觉有异而匆匆进入书房,李斯还一个人木然坐着不知所以。蒙毅低声道:“丞相连日劳碌,回去歇息也。陛下若有事,我及时知会便了。”李斯长叹一声道:“蒙毅啊,大秦新政该有所盘整了。皇帝忧心,老夫也是寝食难安也!”蒙毅一时无对,李斯也就一拱手踽踽去了。
寒风料峭,嬴政在那片皇城仅有的胡杨林中转悠着,第一次觉得有一丝凉意爬上了脊梁,渗入了心脾。秦人从马背部族鏖战到诸侯,再鏖战到战国,再鏖战到天下共主,靠的是甚?靠的是打不垮的以嬴秦部族为轴心的老秦人!数百年来,无论如何艰危局面,秦国都能坚挺过来,全部的根基都在于精诚凝聚万众一心的老秦人,在于无可撼动的嬴秦轴心。而今,嬴秦部族一朝消散了?老秦人一朝消散了?竟只有关中腹地的百万老弱妇幼了?果真如此,天下一旦有事,关中一旦有变,秦政之底气何在?嬴政啊嬴政,若非李斯近日算账,你还是懵懂不知所以也。多少年来,你忙于运筹大战场,忙于运筹创制文明,尽情地挥洒着老秦人,老秦人被征发成军,老秦人被派往南海,被派往北河,被派往淮北淮南,被派往辽东,被派往一切应该镇抚的地方……老秦人无怨无悔,总是高呼着那句“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老誓言,义无反顾地走出函谷关,义无反顾地踏上陌生的土地,将自己丰腴富庶的故乡留给了昔日的敌人……若是天下安宁秦政无事,骄傲宽厚的老秦人或可在青史留下巍巍然一笔。然则,如今是复辟暗潮汹涌猖獗,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六国贵族在密谋举事,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山河社稷!若果真面临与复辟势力的生死决战,嬴政啊嬴政,你手中的力量何在?若有三百万老秦人在关中,嬴政何惧天下复辟骚乱?今日如何,你这个皇帝在关中连十万兵力也拉不出来了,何其大险也!以战国强力大争之惯性,六国贵族的复辟大潮必然再次到来,没有再次决战的胜利,大秦新政便不能真正地巩固。今日看来,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之必然了。然则,果真决战之日来临,大秦何以安天下?
仔细想来,嬴政深深地懊悔了。悔之者何?大大低估了复辟势力的顽韧抵抗也。身为总领天下的皇帝,你嬴政全部用尽了后备力量,消散了秦政的轴心力量,而只全力以赴地创制文明盘整华夏抵御外患,竟没能给镇压复辟留下最为可靠的一支生力军,如此短视之嬴政,何堪领袖天下哉!若是战场,你便是只看到了当下战胜,而没有看到即将到来的再次决战。你也看了上党的长平大战遗迹,可你做到了武安君白起那般深谋远虑么?没有!你嬴政多么像那个颇有几分迂阔的乐毅,一心只想以“化齐”结束灭国之战,结果如何?非但没有化得了齐国,反倒是六年不下一座孤城,最终导致了齐国的死灰复燃。
战场便是战场,打仗便是打仗。打仗要流血,要死人,要歼灭敌方;而不会是不流血地感化对方。身在战场却心在感化,何其迂腐哉!政治战也一样,你嬴政灭人之国,夺人之地,毁人之社稷,还打算教他们真正地服从你的新政,做你的驯服臣民,当真岂有此理哉!若是秦国被灭,你嬴政能甘心臣服于人?当初若看透此点,看透复辟势力之顽韧,自当留下老秦人根基力量。若当真有三百万老秦人在,只怕六国贵族也未必敢如此猖獗。你嬴政今日才清醒的事,六国贵族只怕早早已看到了。否则,那么多接踵而来的谶言流言刻字,纷纷说秦政必亡嬴政当死,其根基何在?由此看去,若果真有一日复辟势力大举起事,安知不是自己的方略缺失所诱发?嬴政一生历经大风大浪,何惧决战,然则,对此等因自己犯错而诱发的决战,嬴政却感到钻心地痛楚……
思绪潮涌,嬴政皇帝很有些埋怨李斯了。
皇帝想不通一件事:如此重大的隐患,李斯又如此清楚地了解,为何不早日说出来?是他这个皇帝不容人言?清醒地说,自己这个皇帝对言路尚算是广泛接纳的,至少,不足以使李斯这样的首席大臣缄口不言。是李斯没有看到这一隐患的巨大风险?以李斯的敏锐透彻,以及今日说及这一隐患时的忧虑与对老秦人口散布的熟悉,不能说李斯没有想到。是李斯在选择进言的最好时机?不会也。果然在选择时机,岂不是说李斯连防患未然未雨绸缪这样的谋划意识都没有了?那,究竟是何等原因使李斯一直没有提出这个如此重大的失误?嬴政皇帝一时想不明白了。自李斯用事以来,二十余年中李斯始终与自己保持着惊人的一致。即或是反复回想,嬴政皇帝仍然想不出李斯与自己曾经有过何等重大歧见。当然,《谏逐客书》那次不算,那时李斯还没有进入中枢。嬴政皇帝曾经为此深以为欣慰,几乎时常有一种先祖孝公与商君的君臣知己的感喟。若非如此,皇室如何能与李斯家族结成互婚互嫁的多重联姻关系?嬴政皇帝自来秉性刚烈明澈,若非深感投合,绝不会基于巩固权力而去结婚姻之盟。在嬴政皇帝内心,也从来没有将这种君臣私议带入国政。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因为姻亲关系而不加辨识地认可过李斯。之所以每次大事都能契合,实在是李斯与自己太一致了,一致得如同一个人。在整个帝国群臣中,只有李斯做到了这一点,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从当年老臣一个个数来,王绾、王翦、蒙恬、尉缭、顿弱、郑国、姚贾、蒙武、王贲、蒙毅、冯去疾、冯劫、李信等等等等,谁没有与自己这个皇帝有过政见争执?确实,独独李斯没有过……且慢,这,正常么?心头一闪念,嬴政皇帝竟然吓了一跳,耳畔蓦然响起了王贲的临终遗言:“丞相李斯,斡旋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莫非,李斯二十余年与自己这个君王的惊人一致是刻意的,是时时事事处处留心的结果?笑谈笑谈,不能如此想!果真如此,权力机谋之神秘岂非不可思议了!且慢,换个角度想想。李斯会不会不是机谋,而仅仅是畏惧自己这个君王变幻莫测而谨慎从事?毕竟,李斯并没有附和过自己的明显错失,也没有附和过某些特定事件。譬如,用李信为大将灭楚是一次明显错失,李斯便没有附和,当然,也没有反对;当年软禁太后,灭赵之后默许赵高杀戮太后家族昔年在邯郸的所有仇怨之家,这两件事李斯都没有附和。李斯与自己一致的,都是被事实证明了的正当决断。既然如此,夫复何言?一时之间,嬴政皇帝又想不明白了……三日之后,皇帝再次召见了李斯。
窗外大雪纷飞,君臣两人围着木炭火通红的大燎炉对坐着,一边啜着热腾腾的黄米酒,一边低声地说着。嬴政皇帝没有提说上次会谈的一个字,只坦诚地对李斯说了来春准备出巡的谋划,要李斯预为谋划。李斯既随和又谨慎,沉吟片刻方道:“老臣本心,陛下体魄大不如前,不宜远道跋涉。陛下威望超迈古今,居大都而号令天下,无不可为也。陛下劳碌过甚,国之大不幸也……”见皇帝默然不语,李斯又道,“当然,若陛下意决,老臣自当尽心谋划,务使平安妥善。”嬴政皇帝道:“来春出巡,定然是最后一次了。这次回来,哪也不去了,只怕也去不了了。这次,我想看看东南动静,挖挖那班煽风点火的复辟渣滓。还想看看,能否将散布的老秦人归拢归拢。若有可能,还想看看万里长城,那么长、那么大的一道城垣,自古谁见过也,一起,去看看。”嬴政皇帝断断续续地说着,却没有一个字触及李斯前边的劝谏之辞。李斯遂一拱手道:“出巡路径不难排定。须陛下预先定夺者,留守咸阳与随同出巡之大臣也。其余诸事,无须陛下操心。”
“冯去疾、冯劫留守。丞相与蒙毅,随朕一起。”
“陛下,要否知会长公子南来,开春随行?”
“扶苏?不要了。那小子迂腐,不提他。”
嬴政皇帝不明白自己如何一出口便拒绝了李斯,且将自己的真实谋划深深地隐藏了起来,竟不期然承袭了赶走扶苏时的愤懑口吻。其实,嬴政皇帝一瞬间的念头是:不能教扶苏再回咸阳陷入纷争了,必须亲自为扶苏蒙恬廓清一切隐藏的危机,全面谋划一套应变方略,而后再决断行止。这一想法,嬴政皇帝不想说。虽然,嬴政皇帝又说了许多出巡事宜,可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再也没有将这一最深图谋知会李斯的欲望了。
暮色时分,李斯走出了皇城,消失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
李斯的心绪沉重而飘忽,如同那沉甸甸又飘飘然的漫天大雪。秋冬以来,皇帝的言行似乎发生了某种不可捉摸的变化,有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心事。何种变化?何种心事?李斯似乎隐隐约约地捕捉到了某种影子,可又无法确证任何一件事情。以嬴政皇帝的刚毅明朗,不当有如此久久沉郁的心绪。然则,这又能说明何事?皇帝盛年操劳,屡发暗疾,体魄病痛自然波及心绪,不也寻常么?皇帝主持完王贲葬礼归来,第一件事便想减轻天下徭役,究竟动了何等心思,仅仅是听到了刘邦结伙逃亡与黥布聚众作乱么?果真如此,倒也无可担心。然则,皇帝的沉郁,皇帝那日听到关中老秦人流散情形后的肃杀默然,似乎都蕴藏着某种更深的意味。况且,历来敬重大臣的皇帝,那日径自将他一个人丢在书房走了,这也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了。然无论皇帝如何扑朔迷离,至少,有一点似乎是明白无误的:皇帝开始思索新政得失了,开始想不着痕迹地改正一些容易激起民众骚动的法令了,提出改变徭役令便是显然的例证。那么,为何有如此动议?是皇帝对整个大秦新政的基本点有所松动,还是具体地就事论事?若是后者,无须担心,李斯也会尽力辅佐皇帝补正缺失。然则若是前者,事情就有了另外的意味了。举朝皆知,对大秦新政从总体上提出纠偏的,只有长公子扶苏一个人,扶苏的主张是稍宽稍缓,尤其反对坑杀儒生。若基于认可这种总体评判而生发出补正之议,将改变徭役征发当做人手处,则李斯便需要认真思谋对策了。原因很清楚,李斯既是大秦新政的总体制定者之一,又是总揽实施的实际推行者;帝国君臣与天下臣民对大秦新政的任何总体性评判,最重要的涉及者,第一是皇帝,第二便是首相李斯。而自古以来的鉴戒是,天子是从来不会实际承担缺失责任的,担责者只能是丞相;没有哪个臣子会公然指斥皇帝,更不会追究皇帝的罪责,但言政道缺失,第一个被指责的必然是丞相;丞相固然为群臣之首,但也是臣子,并不具有先天赋有的不被追究的君权神授的神圣光环。也就是说,假若皇帝真正地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扶苏的主张,他这个首相便须得立即在总体实施上有所变更,向宽缓方面有所靠拢;否则,秦政“严苛”之名,便注定地要他李斯来承担了。可是,皇帝是这样么?他有意提到扶苏,皇帝如何还是一副厌恶的口吻……
“禀报丞相,回到府邸了。”
辎车停住了。李斯静了静神,掀帘跨出了车厢。
冰冷的雪花打在脸上,李斯蓦然觉察到自己的脸颊又红又烫,心头似乎还在突突乱跳,不禁自嘲地笑了。李斯啊李斯,你这是如何了,害怕了么?不。你从来都是无所畏惧的,从来都是信心十足的,从来都是义无反顾的,你怕何来?论出身,你不过是一个上蔡小吏,一个自嘲为曾经周旋于茅厕的厕中鼠而已。是命运,是才具,是意志,将你推上了帝国首相的权力高位而臻于人臣极致。李斯没有辜负这一高位,李斯不是尸位素餐者,李斯尽职了,李斯尽心了,李斯的功勋有口皆碑,皇帝对李斯的倚重有目共睹;自古至今,几曾有过大臣的子女与皇帝的子女交错婚嫁?只有李斯家族做到了……那么,你究竟心跳何来?害怕何来?对了,你似乎觉察到了皇帝意图补正新政的气息,你觉察到了有可能的朝局变化。对了,你李斯怕皇帝补正治道,你这个丞相便要做牺牲,上祭台。是也是也,假若当初你不那么果决地反对扶苏,而只是教冯劫姚贾他们去与扶苏辩驳,今日不是便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么?可你,立即向皇帝禀报了扶苏的不当言行,使皇帝大为震怒并将扶苏赶去了九原监军,如此一来,扶苏岂不成了你李斯的政敌?扶苏是谁,是最有可能的储君。与储君相左,你李斯明智么?如今,皇帝有可能与储君合拍了,你若再与皇帝政见疏离,与储君政见相左,你这个丞相还能做下去么?而一旦被罢黜查究,安知对秦政不满者不会对你鸣鼓而攻之?其时,所有的功业都抵挡不住那潮水般的汹汹攻讦。商君功高如泰山,尚且因君主易人而遭车裂,你李斯的威望权力功业能大得过商君?若将“苛政”之罪加于李斯之身,又岂是灭族所能了结?李斯啊李斯,谨慎小心也,一步踏错,千古功罪啊……
踩着寸许新雪,走进火红的胡杨林;嬴政皇帝觉得这个早晨分外清爽。
“父皇!”一个清亮的声音从红叶中飘来,流露出浓郁的惊喜。随着喊声,一个少年手持短剑飞跑而来,扑到了嬴政皇帝怀中。“啊,长不大的胡亥也!”嬴政皇帝慈爱地拍打着少年汗水淋漓的额头,抚摸着少年一头乌黑厚实的长发,“大雪天,起这么早做甚?”少子胡亥抬头赳赳高声道:“雪天练剑!胡亥要杀匈奴!”嬴政皇帝不禁一阵大笑:“你小子能杀匈奴?来,砍这根树桩看看你力道。”胡亥脆生生说声好,退后两步站定,嗨的一声吼喝,双手举剑猛力剁向面前一棵两三尺高的枯树桩。只听嘭的一声闷响,短剑卡在了新雪掩盖下的交错枝权中。胡亥满脸通红,使足全力猛然拔剑,剑未拔出,双手却滑出了雪水打湿的剑格,噗地向后跌倒,人便滚进了雪窝之中。嬴政皇帝乐得仰天大笑,拉起了一身黑白混杂的小儿子,右手轻松地拔出了短剑笑道:“父皇少时也用过这般短剑,看父皇还会用不会,教你小子看看。”说罢马步站定,沉心屏气,单手缓缓举剑将及头顶,陡然一喝斜劈而下,只听咔嚓一声大响,树桩的三分之一便飞进了雪地。与此同时,嬴政皇帝也瘫坐在了雪地上呼呼大喘,一时脸色苍白。
“父皇万岁——”胡亥兴奋地高喊着。
“万岁你个头!”嬴政皇帝喘息着笑骂了一句。
“父皇起来起来。”胡亥跑过来扶起了父亲,比自己劈开了树桩还高兴。
“你小子说说,方才看出窍道没?”
“父皇大人,力气大……”
“蠢!”嬴政皇帝又笑骂一句,“那是力气大小的事么?”
“父皇明示!”胡亥一脸少不更事的憨笑。
“记得了。短剑开物,忌直下,斜劈,寸劲爆发,明白?”
“明白!”胡亥赳赳高声,两眼却分明一团混沌。
“你小子也!看着灵气,实则猪头!比你扶苏大哥差几截子!”
嬴政皇帝很是生气,骂出来却禁不住一脸笑意。不知为何,嬴政皇帝看见这个小儿子便觉得可乐,从来生不出在长子扶苏面前的那般威严肃杀。这个胡亥也是特异,十五六岁的大少年了,永远地一副童稚模样,脆生生的声音,憨乎乎的笑容,白白净净的圆面庞,恍然一个俊俏书生一般。不管父皇如何训斥,这小胡亥永远都是脆生生地答话混蒙蒙的眼神憨乎乎的笑脸,教嬴政皇帝又气又乐。后来,皇帝也就索性只乐不气了。此刻,胡亥便脆生生道:“不!胡亥的法令修习第一!扶苏大哥比不过!”
“噢?那你小子说,以古非今,密谋反秦,该当何罪?”
“儒家谋逆,一律坑杀!”
“问你儒家了么?”
“禀报父皇!这是老师教的!”
“老师?啊,赵高教的好学生也!”嬴政皇帝大笑起来。
“父皇!儿臣一请!”
“噢?你小子还有一请?说。”
“儿臣要跟父皇游山玩水!不不不!巡视天下,增长见识!”
“啊呀呀,你小子狗改不了吃屎,还装正经也!”
嬴政皇帝乐不可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时自觉胸中郁闷消散了许多。小胡亥红着脸不知所措。嬴政皇帝抚摸着胡亥厚实乌黑的长发笑道:“小子别噘嘴了,开春之后,父皇带你去游山玩水,啊。”胡亥哭丧着脸道:“父皇,儿臣没记好,没说好,你不要学了嘛。”嬴政皇帝又是一阵大乐,笑道:“你小子也!赵高教你两句话都记不住,自家说本心话也便罢了,还卖了人家老师。”胡亥赳赳高声道:“胡亥没卖老师!老师好心,教胡亥教父皇高兴,说这是头等大事!”“好好好,头等大事。”嬴政皇帝连连点头,“左右教你小子跟着游山玩水便是了。父皇也多笑笑了。”
少年胡亥高兴地走了,说是该到学馆晨课了。
嬴政皇帝兀自嘿嘿笑着,骂了句你个蠢小子读书有甚用,径自徜徉到白雪红叶交相掩映的胡杨林中去了。对于自己的二十多个儿子,十多个女儿,嬴政皇帝亲自教诲的时日极少,可说是大多数没见过几面。可以确知的是,嬴政皇帝叫不全儿女们的名字,记不全儿女们的相貌,更不清楚大多数儿女的学业才具。依据嬴氏王族的法度:由驷车庶长(帝国时期为宗正)在每季的末月,对皇子公主的诸般情形向君主归总禀报。在秦王嬴政之前,这一法度的具体实施的通常形式是,君主亲自听取禀报,而后再亲临考校,对王子公主一一督导,每年至少四次。
自从嬴政亲政,皇族法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废除了皇后制,实际上也自然地废除了嫡庶制。这一变化也必然带来了后宫秩序的变化:最是人际繁杂交错的后宫没有了主事的国母,即或是爵位最高的妻子,也无法具有王后皇后那样的权威。于是,历来自成体系的皇室后宫不再成为最特异的封闭式天地,而一并纳入了皇城辖制体系——事务人事俸禄等以皇城体系各自归署辖制,皇帝的一大群妻子与一大群儿女,则由太子傅官署与宗正府会同管辖(除了皇子公主的学业归太子傅官署,其余有关血统认证爵位确定等一概由宗正府管辖)。
从实际效果说,这一变革完全打破了此前数千年稳定的君王后宫传统,带来了诸多无所适从的混乱,也带来了诸多未曾预料到的开放与方便。最大的混乱是,包括皇帝一大群妻子在内的后宫的所有女子,其言行功过没有了细腻有度的考察,过错也很难做到及时制裁。因为,对皇帝的妻子们与各等级的女官宫女们,由内侍官署的太监们履行督导是很难的,而由分别隶属于郎中令与宗正府的皇城机构与皇族机构的朝官们履行督导,更是不可能的。于是,皇帝的妻子们尽管爵位高低不同,但因为其荣辱不再与所生子女的嫡庶地位相连,而在实际上没有了差别。这种嫡庶之别,是宗法制根基之一,在古代的地位差别几乎是本质性的。由于没有了这一最为重要的差别,其导致的实际后果便是:所有的后宫女子都可以做皇帝的妻子,不同仅仅在于爵位高低;而只要能为皇帝生下一个子女,则立即便是实际上的妻子。于是,女子们的诸般矛盾自然多了起来,谁能与极少见到的皇帝尽可能多地同榻共枕,便成了最为实际的争夺内容。
与这种表面混乱相连,最大的好处是后宫女子相对开放了,活动方便了。后宫管理的官署化,使女子们和皇子公主们接触朝官的机会大大增多,与外界交往的机会自然也大大增多了。自然而然地,后宫不再是全封闭状态了。当然,这里有一个大根源,这便是战国的奔放风习依旧在焉。战国之世,各国风习都很奔放自由。起自马背部族的秦人赵人,更是远远没有后来的拘谨。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能对着外国使节公然谈论丈夫与自己的性交方式;嬴政的母亲赵姬能与外臣公然私通,且与后来的嫪毐生下了两个儿子。凡此等等,皆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那时的大自由风习。
然则,嬴政皇帝并没有因为这种奔放与自由,而成为糜烂的君王。事实恰恰相反,全副心思都在国家政务的嬴政,除了外出巡政,只要在咸阳,几乎总是不分昼夜地在书房忙碌。用当时老百姓的话说,皇帝忙,忙得连放屁的空儿都没有!如此一个皇帝,根本不可能如后世皇帝那般,将每晚需要同榻的女子事先选定,而后再由太监侍寝,站在榻旁记录交配的时刻,以确证子女血统无误。嬴政皇帝天赋异禀,体魄壮伟精力超人,然却对男女性事既缺乏浓烈的兴趣,也缺乏或细腻或狂热的各种癖好——譬如后世诸多皇帝都具有的那种色痴色癖——为此,实在没有刻意将某某女子铭刻在心的要死要活的心情。嬴政皇帝的时间被政务排得满满,性事很匆忙,也很简单;往往是走进后宫便要发泄,要找女人,没有任何特定目标,见谁是谁,完事即刻走人;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连交合女子的相貌都记不得了。往往是宗正府报来一个新皇子新公主出生,并同时报来母亲的名字,嬴政皇帝才依稀想起连连发问,啊,是否那个女子?细细的,软软的,眼窝大大的?嬴政皇帝记得,自己在生下第十八个儿子胡亥之后,体魄莫名其妙地大见衰竭,对男女性事没有了任何念想。后来,嬴政皇帝才从一个交合女子的口中得知,后宫人群之所以将胡亥称为少子——最小的儿子,原因便在女子们彼此心照不宣,皇帝不行了。可后宫女子们未曾预料到的是,自老方士徐福医护皇帝后,情形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皇帝又骤然雄风大长了。有时,嬴政皇帝还得接连与两三个女子交合方能了事。所以,胡亥的少子名号还在头上,妻子们却又为嬴政皇帝接连生了几个儿子几个女儿……
从古至今,嬴政皇帝在女子事上是最为不可思议的一个,说浑然无觉亦不为过。帝国后宫女子众多,因为没有了皇后制与嫡庶制,所以整个后宫女子都泛化为皇帝的妻子群。如此一来,似乎嬴政皇帝拥有成千上万的女子。六国贵族与后世史家更是加油添醋,将六国宫女也连同六国宫殿一起算给了嬴政皇帝,说秦宫女子之多,连渭水也被染成了胭脂河。尽管如此,嬴政皇帝却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一则宫廷秽闻,大概是因为嬴政皇帝的性方式不可思议的简单化也。而这种宫廷秽闻,后世任何一个时期的皇宫都是大批量的。
嬴政皇帝只熟悉两个儿子,长子扶苏,排行第十八的少子胡亥。
他还依稀地记得,为自己生下第一个儿子的,是一个齐国商贾的女儿。那是母后赵姬在最后几年操心自己老是不大婚,委托那个茅焦为自己物色的一个女子。因为是第一个,嬴政皇帝还记得那个女子的名姓,齐姬。也因为是第一个,嬴政皇帝也还记得齐姬的美丽聪慧与明朗柔美。齐姬虽是齐国女子,却一直跟随着商旅家族在吴地姑胥山(姑苏山古名)长大,一口吴越软语经常教嬴政大笑不止。不幸的是,齐姬生下第一个儿子后没有几年,便因随他进南山章台宫而受了风寒,一病去了。那时候,第一个儿子还很小,有一日在池畔咿呀念《诗》,被嬴政听见了两句:“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嬴政感慨中来,便给这个长子取名为扶苏。扶苏者,小树也。山上生满小树,洼地长满荷花。这是《诗·郑风》中的一首歌。儿子慢慢地如同小树般长大了,伟岸的身架,明朗的秉性,极高的天赋,像极了父亲,嬴政很是为此欣慰。嬴政皇帝对扶苏的唯一缺憾,是很早察觉出扶苏秉性中宽厚善良的一面。自然,对于寻常臣民子弟而言,宽厚善良绝非缺憾,然对于有可能成为一个君王的少年,明显的宽厚则多少有些教人不踏实。然无论如何,扶苏无疑是二十多个皇子中最具大器局的一个,也是众皇子中唯一拥有朝野声望的一个。总体说,嬴政皇帝还是满意的。
最熟悉的另一个,胡亥,则大为不同。胡亥的生母是不是胡女,嬴政皇帝已经记不得了。胡亥因何得名,嬴政皇帝也记不得了。嬴政皇帝记得的,是这个儿子从小便有一个令人忍俊不能的毛病——外精明而内混沌,经常昂昂然说几句像模像样的话,两只大眼却是一片迷蒙混沌;读书不知其意,练武不明其道,言不应心却又大言侃侃,总教人觉得他哪根心脉搭错了茬。用老秦人的话说,一个活宝。嬴政每每被这个小儿子逗得大笑一通之后,心头便闪烁出一个念头:我嬴政如何生得出如此一个儿子?我的心脉也搭错了?有一次,嬴政心头终于闪现出一幕:一个明眸皓齿的灵慧女子正在他身下连连喘息,他不知何来兴致,气喘吁吁地问女子姓名与生身故里。女子突然开口,话语却粗俗得惊人:“你噌噌只管弄哩,说啥哩先!”嬴政当时禁不住一阵哈哈大笑,倒很是大动了一阵……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嬴政皇帝只要一想起那个女子的惊人美丽与惊人粗俗,都不禁会突然地大笑一阵。那个当时只顾享乐而没有告诉他姓名的女子,便是胡亥的生母,一个至今也不知道姓名的可人儿,她那迷蒙的目光与胡亥何其相似乃尔……
“出巡带上这小子,也是一乐也!”
嬴政皇帝兀自喃喃一乐,大踏步回书房去了。一个早晨的雪地徜徉,又不期遇上胡亥这个活宝儿子大乐了一番,嬴政的沉郁心绪舒缓了许多。来春要大巡狩,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毕竟,这次巡狩不比往常,一定要从容不迫地赶赴九原幕府,不能急匆匆引发天下恐慌,要压压复辟气焰,要见到扶苏蒙恬,要做好长远部署。这步大棋,不能再耽搁了。从九原归来,这盘新政大棋便大体没有后顾之忧了,自己便可以歇歇了。不然,真得劳死了。那时候,若徐福他们能真得求回仙药,自己这个皇帝就得变个活法了——
注释:
①成军人口不是军队数量,而是男子中的适龄男子总数。以传统征发规律,成军人口的三分之一可征为兵员,三分之二当承担国民生计,征发成军人口之一半的时候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