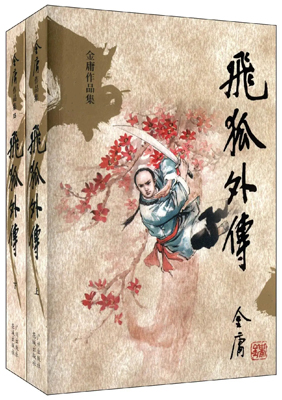年羹尧开言了:“哦,既是万岁有旨,你们可以去掉甲胄,凉快一下了。”
大将军一声令下,众军将这才“扎”的答应一声,三下五去二地把甲胄卸掉。一个个只穿单衣,露出了胸前健壮的肌肉,还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雍正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阴寒的凶光,但稍瞬即逝。他换上一副笑脸说:“同处一室,却冷暖不一。我们穿的是薄纱,还热得出汗。你们哪,穿的是厚重的牛皮销甲,还要在户外表演。现在脱去这身衣服,是不是好了一点啊?”
这些在边关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大兵们,早就听人说过,皇上的性子最是阴狠毒辣。可今天真的听到皇上说出来的话,却又觉得传言不实。皇上说的既温存诙谐,又可亲可近,让人一听就打心眼里觉得舒服。只听皇上又问:“毕力塔,今天操演你全部见了,有什么观感吗?你的兵若和他们相比,能赶得上吗?”
毕力塔看着年羹尧那神气活现的样子,早就在心里骂娘了。可是,如今是皇上在问话,他只能顺着“圣意”回答:“回皇上,奴才今天开了眼,这兵确实带的不错。奴才是托了祖荫,从十六岁就跟着先帝爷西征的。但奴才却是第一次见到这阵法,真得好好地向年大将军学学。”
雍正也不胜感慨地说:“是啊,是啊,朕心里实在是欢喜不尽。说起来,年羹尧是朕藩邸的老人,与朕还沾着亲。他这样努力,这样会打仗,带出的兵士又是这样的勇猛无敌,很为朕露了脸、争了光。朕前时有旨,说年羹尧是朕的恩人。这不但是为他能报效朕躬,更因为他替朕、替先帝爷洗雪了过去的兵败之耻!朕与圣祖皇帝一体一心,能不能打好这一仗,是朕的第一大心事。只因祖训非刘不得称王,所以才只封了他一个公爵,但朕待他如同自己的子侄。朕也知道,前方打了胜仗,不是一人之功。今天在座的各位军将,都是一刀一枪地拼杀出来的勇士。没有你们在前方拼杀,天下臣民怎能共享这尧天舜地之福?因此,众位将军功在社稷,如日月之昭昭永不可泯!廷玉——”
“臣在!”
“今日会演的将佐、弁员着各加一级。此外,年羹尧保奏的所有立功人员,转吏部考功司记档,票拟照准。”
“扎!”
“传旨:发内帑银三万两,赏给今日会操军士。”
“扎!”
“传旨:着刘墨林草拟征西大将军功德碑,勒石于西宁,永作记念!”
“扎!”
允禩听到这里,猛然一惊:不好,刘墨林还在自己府里跪着晒太阳呢,这可怎么办?
张廷玉已经在答话了:“万岁,圣旨勒碑,差谁去西宁办理?”
雍正略一思索便说:“还是让刘墨林去吧。给他个钦差身份,实授征西大将军参议道也就是了。”
“扎!”
允禩越听就越坐不住,心想,这事瞒得一时,瞒不了长远,便上前来说道:“皇上,刘墨林虽有才华,但素来行为不检……”于是,他便将早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只是瞒住了让他在自己府里晒太阳这一条。“因此,我请他暂留在我书房,等候我下朝以后再去教训他。那苏舜卿不过是个歌妓,是个贱民。她的死,其实是刘墨林和徐骏争风吃醋引起的。为这么一点小事,刘墨林竟在臣的府门前放肆地侮辱朝廷命官,用他来为年大将军撰写功德碑,似乎不大合适。”
允禩自以为说得头头是道,可他恰恰忘记了,雍正是最忌讳别人提到“贱民”这个词的。去年,雍正皇帝亲下诏谕,要解放贱民。当时,连马齐这样的元老也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办这件并不紧要的事情。可是,今天在座的年羹尧因为是皇上藩邸的旧人,心里却非常清楚。他早就知道雍正当年的这段风流韵事,甚至连小福、小禄这两个女孩子的名字都知道。
允禩刚一说到“贱民”这字眼,敏感的雍正皇帝,马上就想到了那个被允禵带到遵化去的女孩子。他心里的不满也立刻就表现了出来:“哦,刘墨林不过是有点风流罪过,这有什么要紧?朕看比那些假道学、假斯文的人要强得多呢!至于你说的这个苏舜卿,刘墨林并没有瞒朕,朕也知道她是隶属贱籍的。但要是真的追究起来,徐骏的祖母不也是个贱民吗?还有——”他向允禩看了一眼,就以不可商量的口气说,“今天这事就这么定吧,大家都不要再说了。”
皇上这“还有”二字的后面,包含着对允禩的不满和非难,允在能听不出来吗?因为他的生母良贵人卫氏,原来是皇家辛者库里的浣衣奴,也是隶属贱籍的人。雍正故意没有明说,只是点到为止。允禩听了既羞愧,又后悔,想说又无从说,想辩又不能辩。唉,我今天怎么这样糊涂,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他怀着一肚子的怨恨,向端坐正中的雍正皇帝狠狠地盯了一眼,再也说不出来话了。
年羹尧是个明白人,见皇上亲自敲定了这件事,他也只得顺坡向上爬:“皇上,刘墨林的才气,奴才在军中时已经领教过了。奴才那里也正缺着一个办文案的人,墨林能来,以后明发的奏折,就省得奴才动笔了。”
雍正看也不看允禩,就回过头来对太监高无庸说:“你去一趟八爷府书房,向刘墨林传旨,让他在申牌以后,到养心殿见朕。”
“扎!”高无庸飞也似的跑去了。允禩干瞪着两眼,却又无计可施。保徐骏固然重要,却不能为他得罪了皇上。
年羹尧又向皇上说:“圣上,阅兵一过,奴才就不准备再滞留京师了。请旨:奴才何时离京最为合适?奴才带的人马太多,打前站、号房子、安排供应、粮草都要先行一步的。”
雍正向进来参见的军将们一摆手:“你们都跪安吧,都挤在这里让朕热得难受。”看着他们退了下去,雍正才站起身子慢慢地说,“你明天进宫去见见皇后和年贵妃,后天是皇道吉日,由廷玉和方老先生设席,代朕为你送行。岳钟麒给朕来了密报,说他们川军和你的部下常为一点小事闹磨擦。你回去以后,要好好地部勒行伍,要和岳钟麒精诚共事。将军们和好了,部队才能安定。至于你要的军饷等物,朕都已吩咐让户部办理了。”
雍正说得很随便,好像是关切备至,可他的话却使年羹尧大吃一惊!怎么?皇上要夺走我的兵马吗?他看看皇上还是在笑着,便仗着胆子问:“皇上,奴才刚才没听明白,这三千军士不和奴才同行吗?”
雍正笑了:“怎么,你舍不得了?十名侍卫,原来就是朕派到你那里学习的,他们另有使命,要回到朕的身边。你的三千军士当然还是你的兵,不过朕要借用他们几天。这些个兵练得确实好,朕看了很高兴。朕想把他们留下来,到京畿各处军官里作些表演,让那里的将佐们也都看一看、学一学。你不知道,他们那里的兵哪见过这样的世面,这样的军容呀?部队留下来,你自己走,路上不也省心嘛!这样各方面都照顾到了,可以说是四角俱全,你何乐而不为呢?”
雍正说得亲切随和,年羹尧想驳不能驳,想顶又怎么敢顶?可是,这三千兵士全是他年某人一手提拔的心腹啊!他们不但打起仗来不要命,还都是年羹尧用银子喂饱了的。只要年某一声令下,要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砍头、拼命也只是一句闲话。他知道皇上那说变就变的性子,假如有一天皇上变卦了,自己的老本不就要输得净光吗?但如今西线已经没有战事,自己没有一点理由可以堵住皇上的嘴!他思忖了好久才说:“皇上,兵虽然是我带出来的,可他们吃的都是皇粮,连奴才自己也是皇上的人。主子怎么调度,奴才自当怎样听令。可是,奴才斗胆,要驳主子一回。主子知道,岳钟麒进驻青海后,他手下的兵和奴才的兵很不和气。当然奴才回去,是要和岳将军同心同德地共事的。可奴才下头的那些楞头青们,却又实在难缠。一旦闹出事儿来,奴才身边没有得力的人去弹压,怕是不行的。再说,下边出了事儿,于主子面上也不好看,岂不是辜负了主子的一片心意?”
雍正耐住心烦,听他说了这么多,却只是付之一笑:“哦,不会有这样的事,你尽管放心地回去吧。朕这就下旨给岳钟麒,要他好好地部勒队伍,避免磨擦。你一回去,天大的事,都会烟消云散的。”他一边说着,就站起身来走到门边。年羹尧也只好同毕力塔等人一起,恭送皇上到大营门口,眼睁睁地看着皇上的御辇走出了丰台大营。
回宫的路上,雍正兴奋异常:年羹尧有什么可怕?朕略施小计,就吃掉了他的三千铁军。这是投石问路,也是釜底抽薪!
一群上书房大臣们,扈从着雍正皇帝回到西华门时,天已将近黄昏了。张廷玉只是在早上喝了两口xx子,便来到皇上身边侍候。一天中几次皇上赐膳,都有人找他谈事,到现在还没吃上一口饭呢。正想离开皇上去找点吃的,却听皇上叫他:“廷玉,马齐,你们要到哪里去?不是说好了要和朕一起见人的吗?”
张廷玉连忙说:“哟!皇上不说,臣竟忘记了。只想着皇上辛苦了一天,也该着让皇上歇一会儿再进去……”
“哎,朕吃得饱饱的,只是去了趟丰台,又总是坐着,累的什么?允禩身子不好可以先回,舅舅,你也进来吧!”
除了允禩,谁也不敢说走了,都跟着皇上回到养心殿。在殿门口见刘墨林、孙嘉淦和杨名时等人都正跪在那里。杨名时是进京述职的,孙嘉淦是从外地巡视刚回来。雍正只是说了一句:“起来等着吧。”
副总管太监邢年见皇上回来,连忙上前禀报说:“回万岁,李绂和詹事府的史贻直都递了牌子。他们没有旨意,奴才叫他们暂且在天街候着。主子要是不想见,奴才就让他们先回去了。不然,宫门下了钥,不奉特旨出不去,他们就得等一夜了。”
雍正刚走了两步,忽然听到史贻直这名字,站下问道:“史贻直?哦,年羹尧的同年进士,传他进来。告诉李绂,明天再递牌子。方先生来了吗?”
在一旁走着的隆科多,一直想知道皇上为什么要留下他。此刻,趁着机会瞧了一下皇上的脸色,却什么也没看出来。张廷玉暗暗叫苦,天哪,都到这时候了,还要见这么多的人,皇上,你真是不嫌累吗?站在丹墀下的方苞,听到皇上提到自己,忙上前参见。因为皇上多次说过不让他行大礼,便只作了一揖说:“臣刚才去看了十三爷,进来还不到半个时辰。”
“好好,都进来吧,免礼,赐座!这么热的天,你们一定都渴坏了,赐茶!”雍正的兴奋溢于言表。
史贻直在一个小太监带领下走了进来,向皇上见礼后,退下跪着等候皇上问话。雍正看了他一眼说:“嗬,你倒是后来居上了。詹事府是个闲衙门,你夤夜求见,为的是什么呀?”
史贻直的个子很高,头长得像个压腰葫芦。细而又长的脖子上有个硕大的喉结,一说话便上下滚动,看起来十分好笑。听到皇上问话,他就地行了个礼回道:“皇上,国家向来没有‘闲衙门’之说。愿意干的就有事可干,不愿意干的忙着也是偷闲。”
雍正想不到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赞赏地说:“好,说得好!那么,你今天又有什么事要忙着见朕呢?”
史贻直叩头回答说:“今春从四月至今,直隶山东两省久旱不雨,不知皇上知道吗?”
“什么,什么?你就是为了这事,巴巴地跑来的吗?”雍正觉得他这话问得又可气又好笑,“朕焉有不知之理?告诉你,朕早就处置过了,要等你想到这一点,岂不误了大事。”
雍正觉得,自己这番话说得够硬气了。哪知,话刚落音,史贻直就顶了回来:“不,皇上。天旱无雨乃小人作祟所致,朝中有奸臣,也不是只靠赈济能够免灾的。”
在场的众人一听这话,全都惊住了。史贻直这么胆大,又说的这么明白,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张廷玉本来饿得直出虚汗,也打起了精神。他想听听史贻直有何高见,也想看看这个从地下突然钻出来的“土行孙”,究竟要指定何人是“作祟的小人”?
雍正却被他这活吓得打了个激凌,连杯中正喝着的xx子都溅出来了。他冷冷一笑说:“你大约是喝醉了,到朕跟前耍疯的吧?朕身边的大臣,今天都在这里,你说说,他们谁是‘小人’,谁是奸臣?”
“年羹尧就是朝中最大的奸臣!”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殿内殿外的大臣、侍卫,甚至太监们都吓得脸如土色。不过,今天从进来就心里吊得老高的隆科多,却放下了一块石头。
雍正看看众人的表情,又压了压自己的情绪说:“好啊!你敢弹劾年羹尧,真是了不起。要捉拿年羹尧,并不费事,只需一纸文书就可办到。不过,年某刚刚为朕建立了不世之功,他的清廉刚正,又是满朝文武尽人皆知的。你要告他,总得给他安上个什么罪名,而不能是这‘莫须有’三个字吧?”
雍正这话,可说得真够狠的。但满殿的人听来,却又觉得他说得随和,说得平淡如水。只有和雍正皇帝打过多年交道的张廷玉,却深知这位皇上的性情。他越是心里有气,话就越是说得平淡;而越是说得平淡无味,就越是那狠毒刁钻性子发作的前兆!张廷玉心里一阵紧张,怕万一皇上发起怒来,会立刻下令处置了史贻直。他正在思量要如何从中调停时,无意中却见方苞的脸色,似乎是泰然自若。只是他的那两只小眼睛,却在不住的眨着。嗯,他也是在想主意哪!
刚才皇上的活,很出史贻直的意料之外,不过却没有吓住他。他在要求觐见皇上之前,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年羹尧做过什么事,结交了哪些人,干预了多少案子,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坑害了哪些善良百姓等等,全都在史贻直心里装着哪!他知道皇上那阴狠歹毒的性子,也估计到了自己将要面对的一切。他没有丝毫的恐惧,哪怕为此捐躯,也在所不惜。他自信一定能说服皇上,让他看清年羹尧的嘴脸,把这个害国害民的独夫民贼,从他窃取的、高高的宝座上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