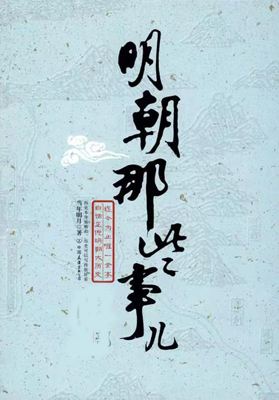李卫咬着牙说:“主子,奴才怎么也不相信这话。不过奴才敢说,谁要是想谋反,奴才立刻就回南京,带着人马来京勤王保驾!”
雍正平静地说:“狗儿,朕以万乘之尊,还能和你打诓语吗?有人背着朕,联络八旗铁帽子王爷,串通他们来京。明面上说是要‘整顿旗务’,要‘召集八王会议’,要‘恢复八旗制度’。其实是要‘议政’,要逼着朕下‘罪己诏’,要逼宫,要废了朕呀!”
李卫可真是恼了:“皇上,您说的全是真的吗?那,奴才就不回南京去了。奴才要在这里替主子守好家门,看他们谁敢胡来!”
雍正笑了:“咳,你呀,怎么还是这样沉不住气呢?告诉你,朕的江山,铁桶一样地结实,他们谁也别想动它一动!你立刻就回南京去,带好你的兵,也当好你的总督。朕已经给兵部下了谕旨,连湖广所有的旗营和汉军的绿营兵,也全都归你节制。记着:没有朕的亲笔手渝,无论是谁说什么,你都要为朕牢牢地握好兵权!”
雍正的一番直言,把个机灵能干的李卫惊得直打寒颤。他轻声但又坚定地说:“主子放心,奴才立刻就回南京,得先动手调理一下这些兵。奴才知道,他们当甩手大爷当惯了,不狠狠地治治他们,谁说话他们也敢不听的。”
雍正笑了笑说:“兵权交到你手里了,杀伐决断自然要依你的话为准。除你之外,朕的三个儿子,也全要派上用场:弘历马上就要到你那里去;弘时留在北京;弘昼则要到马陵峪。你看,如今毕力塔管着丰台大营的三万人马,步兵统领衙门现在是图里琛在那里。李绂已经回到北京,接管了直隶总督的职务。兵权全在朕的手里,他们无兵无权,别说是八个铁帽子王爷,就来了八十个,在朕的面前他们也还是不敢站直身子的。”
李卫也被皇上说得笑了:“皇上这话说得奴才心里热乎乎的。其实要依奴才看,一道圣旨颁下,不准他们进京!奴才就不信他们还敢不服不成?”
“哎,怎么能那样做呢?不管怎么说,他们总是先帝爷留下来的人嘛!不过朕现在怕的,倒是他们会缩回去不敢来了,那不是让朕白忙了一场吗?朕真想看看,这些光吃粮不干活的王爷,究竟做的什么美梦。好了,不说他们了。朕已乏透了,你也回清梵寺吧。不过,千万不要惊动了张廷玉,他太累了。朕刚才说的事情,全是廷玉替朕筹划的,不容易啊!你在京可以多住些日子,见见你十三爷,然后再回你那六朝金粉之地去。哎,对了,翠儿如今是一品夫人了,不过朕还是要用她。你让她再给朕做几双鞋来,只有她做的,朕才穿着最舒服。告诉她,要全用布做,一点绫罗也不用。”
李卫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他哽咽着说:“扎!奴才替她谢谢主子。她能在主子跟前出点力,也是她的造化嘛。”
出了养心殿,冷风一吹,李卫的头脑更清醒了。前天他还在心里琢磨,不就是带来乔引娣这个女子吗,我李卫还能办不下这差事,至于让十三爷带病跑那么远的路?现在,他才知道,原来还有对付八王进京的这件大事。哦,十三爷一定是察看那里的兵备的。要不,那天夜里他为什么要说那番话呢?
是的,李卫猜测的确实不错。十三爷允祥这次到马陵峪来,就是对这里的军事布置不能完全放心。马陵峪大营,和丰台大营、密云大营并称为三大御林军。不但装备精良,马步军配套,火炮鸟枪俱全,还有一支水师营。虽然北方根本用不着水师,但他们是专为三大营制作舟桥的,类似近代的“工兵”。马陵峪这里的兵力布署设置,还是熙朝留下的。当时,三藩之乱刚平,国力还不像现在这样强盛,罗刹国不断在边境骚扰,这里实际上是大清将军巴海对抗罗刹国的“第二防线”。熙朝名将周培公精心地布置了这个马陵峪工事,也成了后世仿效的一大杰作。整个大营,以马陵峪为中心,像蛛网一样向北幅射,中军大营设在棋盘山旁边。山上溪泉密布,山下旱道纵横。山背后景陵西侧有大片房屋,可用来贮存粮食和军火。登上棋盘山北望,连绵数十里的军营可尽收眼底。这里不但进退自如,左右逢源,处置得当,还能把敌人包围甚至全歼于谷口之内。允祥视察了大营后,又在范时绎的带领下,登上棋盘山沿着山路走下,一边走,一边对这里赞不绝口:“好,今天我真是开了眼界了!我看过多少大营,这里是头一份。周培公真是一代奇才呀!可惜我生得太晚,而他又死得大早。我们只见过一面,他长的什么模样,现在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范时绎用手搀着病弱的十三爷走下石阶,口中说道:“十三爷,您说的不错,就连我也没有这样的福啊!我只是在年轻时,听我爹说过周培公的情形。他说,那时的周培公,外表看,不过是个文弱书生,可打起仗来却如诸葛在世白起重生。他笔头文章写得好,口才更是让人叫绝。要不,他怎么会说降王辅臣,骂死了那个吴三桂的谋士、号称‘小张良’的汪士荣呢?周先生修的这个营盘已经快五十年了,十三爷您瞧这布署,真是天衣无缝。不但有掐不断的粮道,堵不断的水路,而且,北边不论哪方面出事,这里全能快速出动接应。唉,他化到这里的心思,真不知有多少啊!”
允祥也是不胜感慨:“唉,老一辈的英雄,都已风云飘散了,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这话一点不假。到这里来看看,真是大有好处。先帝爷当初创业的艰难,他老人家长治宏图的远见,都令我辈钦佩。我们不好好地干一番事业,就不配作他的子孙!”
两人边说边走地回到了大帐,正要休息一会儿。十三爷却突然身子一歪,从椅子上滑了下去瘫倒在地。范时绎吓得连忙过来,将他抬到床上躺好。军医闻信也匆匆跑来,用手去试允祥的额头时,不但没有发烧,反倒是一片冰凉。慌得那些军医们,又是把脉,又是掐人中地忙个不停。可是允祥却仍是脸色焦黄,昏睡不醒。正在乱着,突然,从辕门外跑进一个小校禀报说:“军门,外面有位道士一定要进来,说有事和与军门商议。”
“不见,不见!”范时绎一肚子的火,“你没长眼?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哪有闲功夫去见什么和尚道士?”
那军校没有退下,反倒笑着说:“军门,是小的刚才没把话说清楚。那个人说,他是从龙虎山娄真人那里来的,叫贾士芳。他说,只要一提他的名字,军门是一定会见的。他还说,要是军门不想见他,那他可就要走了。”
范时绎一愣:“嗯,难道这个道士是为十三爷而来的吗?”他又瞧了一眼昏睡不醒的十三爷,不得已地说了声:“那,你就请他进来吧。”
不大会儿功夫,便见那位贾士芳飘然而入。他一脚踏进门里便说:“有贵人在此遭难,贫道特来结个善缘。”
范时绎一边命令军医们全都退出去,一边赔笑着对贾士芳一揖说:“道长一言道破这里情形,足见法力洪大。军营不同民间,道长休怪这里太简慢了些。就请道长为王爷施治,如能使王爷转危为安,范某定当重谢。”
贾士芳说:“将军勿须言谢,贫道只是为结善缘而来。”只见他转过身去,从褡包里取出黄裱纸、朱砂、毛笔等物来,口中说道:“王爷是去参见康熙爷了,爷儿俩说得高兴,就忘记了回来。我书一道符请他转回就是了。”他口中呢呢喃喃地念着咒语,手拿朱笔在黄棱纸上写画着。此刻,书房里点着十几支腊烛,亮如白昼。范时绎站在一旁仔细瞧看这位贾道长,只见他个头儿也就是五尺上下,孤拐的脸又瘦又长,脸色青白得简直没了血色,小嘴巴,尖下额,塌鼻梁两边,是一对骨骨碌碌乱转的小眼睛。不过,别看他满脸都是破相,凑到一齐倒并不难看,煞像是一位弱不禁风的书生。范时绎心想,就这么个人物竟能替十三爷治了病?那可真叫稀奇了。
贾士芳却像是知道范时绎的心事一样:“范军门,常言说:人不可貌相。你觉得是不是有些道理呢?”他不等范时绎回答,就站起身来将写好的符轻轻一吹,也不作法,更不念咒,说了声:“疾!”就把那符向灯烛上燃着,并且看着它们化成灰烬。然后,他坐了下来轻松地说:“稍等片刻,王爷就会被放回来的。”
范时绎让兵士们献上茶来,他看着这位仙长似笑非笑地说:“贾道长一定知道,十三爷是皇上的第一爱弟,他不能在我这里有任何失闪。我说句放肆的话,万一十三爷有什么意外,恐怕我就要让你殉了他!”
贾道长平静地说:“万事都有定数,王爷若已无救,我也不敢到此与他结缘。我既然来了,他就死不了。他能活得好好的,军门你也就不能殉了我。比如前几天我们见到甘凤池时,我说他不能见到汪景棋,可是,他就是不听,结果如何?再比如我们俩今晚在此闲坐,这也是上天定好了的,你想不听也办不到。”
范时绎哪有心思和他说这些没用的话呀,他的心现在全在十三爷身上呢:“贾道长,你不要和在下说这些没用的话,我关心的是我们十三爷……”
他的话尚未说完,就见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人事的十三爷,突然坐了起来。范时绎此时被惊得神魂颠倒,不知说什么才好,允祥却向他笑着问:“怎么,你的眼睛为什么瞪得这样大,不认识我了吗?哦,我心里好难过,这,这是在什么地方……嗯?眼前站着的不是位道士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范时绎未及答话,贾士芳已经站起身,走到允祥身边微微笑着说:“十三爷,您刚才只顾了和圣祖老爷子说话,是贫道把您请回来的。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梦。人世间,本来就是一场大梦嘛!贫道还知道,您心里惦记着雍正爷。贫道可以告诉您,他正安坐北京,除了一点小病之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是有铁帽子王爷要进京,他们也改变不了这个大数。我说得有道理吗?”
允祥边思忖边说:“哦,原来是我的大限到了,是你把我救回来的。是吗?”
“大限到了,是谁也救不回来的。”贾士芳冷冷地说,“十三爷不过是身子太弱,走了元神而已。我知道,你现在最想问的话就是,刚才的那个梦究竟是真是假?我可以告诉王爷,这大千世界就是个梦境。佛家说的空幻色,道家说的虚映实,道理实际上是一样的。王爷饱览群书,知识渊博,应该想到,也许现在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正在那梦境之中呢。”他说这番话时,一直面向着允祥,二指并拢,指着允祥的前胸。允祥觉得似乎有一股温热之气,如丝如缕,悠悠地扑面而来,从眉心直透胸臆,横贯全身。刹时间,他感到阵阵春风吹拂,蕴藉温存,周身上下无一处不舒畅通泰。又过了一时,他气清神明,浑身充满了力量。他纵身跳下床来,向贾士芳一躬说道:“允祥有缘,得遇道长。道长悠游于空色虚实之间,通行于幽时造化之途,真仙人也!允祥将何以为谢呢?”
贾士芳一笑说道:“王爷这话说得过了。贫道刚来时就对范将军说,我是来和王爷结缘的嘛。”
范时绎在一旁简直看呆了。他听十三爷和那贾道长的话,好像都是些似懂非懂的玄机,一直插不上嘴,这会儿瞅着有了空子,才走上前来说道:“王爷真是和仙长有缘。奴才适才只顾了忙乱,还没有给二位引见哪。十三爷,这位就是奴才在路上和王爷提过的那位贾仙长。他还是龙虎山上娄真人的关门弟子呢!”
允祥此时心中舒服了,也打起精神来说:“哦,如此说来,小王失敬了。既是今日有缘,仙长能否随我到京华一游呢?当今皇上虽然素以儒家之仁孝治天下。但他胸中的学术却是包罗万象,并不排斥佛道。如有善缘,道长还可以为天下社稷做更多的善事,岂不更好?”
贾士芳不动声色地说道:“如果有缘,那当然是再好也不过的事了,这也是光大我道门的大善缘嘛。不过,小道能不能让皇上满意,还要看天数怎么安排。王爷,您现在能这样兴致勃勃地长谈,是因为贫道用先天之气护定了的缘故。所以,您还不能过多地劳神,就请王爷安歇了吧。”
范时绎连忙走上前去,帮允祥躺下。回过头又对贾道长说:“贾神仙的居处,也已安排好了,就在对面的静室,请到那里去休息吧。”
贾士芳一笑答道:“修道之人,是从不睡觉的,我只是打坐而已,何需费事?况且,王爷这里还需要贫道护持照料。你有事,尽管去忙吧。”说完,他走向东墙,面西而坐,刹时间,便已闭目入定了。
范时绎瞧着他这样神密,自己怎么敢睡?他走到门前看看,见已是三更时分了,便搬了把椅子,守护在十三爷的床头边,一直坐到天色放明。
允祥这一觉睡得十分香甜,醒来时,已是红日初升了。他揉着惺松的睡眼坐起身来,旁边的范时绎正在看着他笑。他见范时绎坐在一边为他守夜,觉得很是感动,又回头看看正在闭目打坐的贾士芳,便轻轻地打了个手势,带着范时绎走出了房间。他们一直走了很远,十三爷才轻声说:“难为这个道士,为我作了一夜的功,我现在觉得好多了。我知道自己的心血不足,能睡这么一个好觉,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他为我治病,其实也是很累的。嗯?你们这里为什么没有晨练?”
“回王爷,因为您昨儿犯了病,奴才怕早上出操会打搅您,让他们到下边练去了。”
“唉,真难为你给我打算得这样周到。”允祥对着初升的晨曦,沿着小道,不声不响地走了下去,范时绎一步不拉地走在他的身后。两人谁也没有说话,似乎都在想着心事。突然,允祥站住了脚问:“老范,你现在想的什么?”
范时绎一愣,但他马上明白过来,悄声地说:“十三爷,奴才看这贾士芳像是个妖人!他太玄了,也太神了。我们在沙河店见到他时我就觉得有鬼,今天他怎么又追到了这里?依奴才看,他像是在故意卖弄本领。十四爷是万岁屡屡提到要严加管束的人,奴才一多半心思全都在他身上。您这次来,要带着十四爷回京,要是再跟上一个半仙儿,叫奴才怎么能放心呢?”
允祥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很对,我想的也正是这件事。不瞒你说,我也在防备着他哪!但他昨晚所说的,似乎又都合乎正道。万岁如今身子不太好,正在寻访能医善法之人。所以,我才想自己亲自试试他。如果他可以为我所用,就送上去让他见见万岁;如果不行,那也就算了。十四爷是不能让他见到的,我也不会带着他回京城。等我走时,你设法软禁了他,然后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范时绎点头答应,两人又十分机密地商量了一阵,才一同回到住处。但这里却不见了那位贾道长。范时绎把一名小校叫过来问:“贾道长呢?”
那个小校说:“回军门,贾道长已经走了。走时,他说不让小的禀报军门,他还给军门留下了这个条子。”说着递过一张纸来。范时绎接过来呈给十三爷,允祥打开看时,上面写的却是一首诗:
道家不慕冲虚名,
奈何桃李疑春风?
无情心香难度化,
有缘异日再相逢。
允祥苦笑一声说:“他大概是看到我们不信任他,有些不高兴,所以就悄没声响地走了。”
范时绎却笑着说:“十三爷,要叫我说,他走了更好。要不,叫奴才今天怎么过呢?他一走,也免得我们多操那么多的闲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