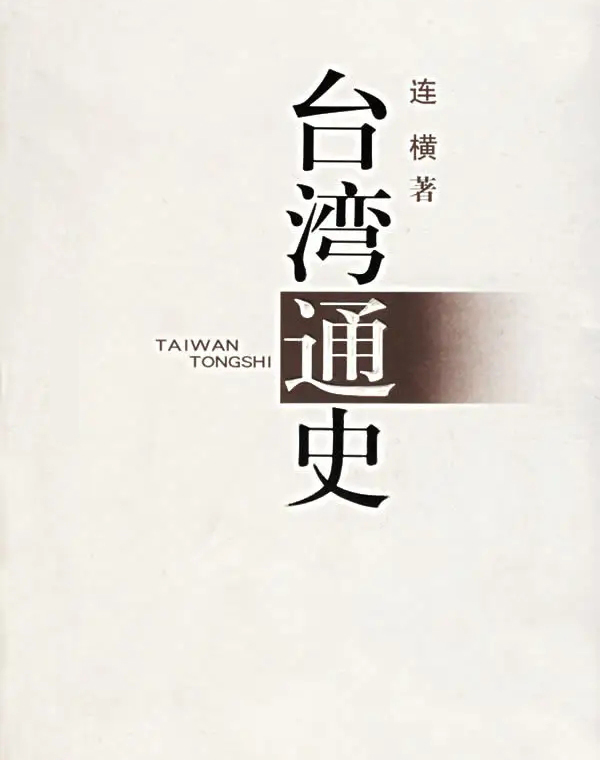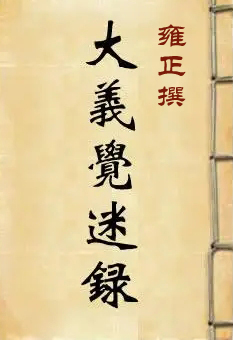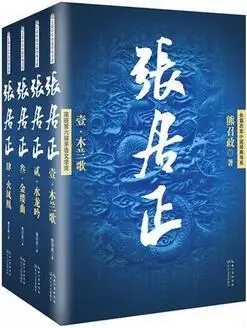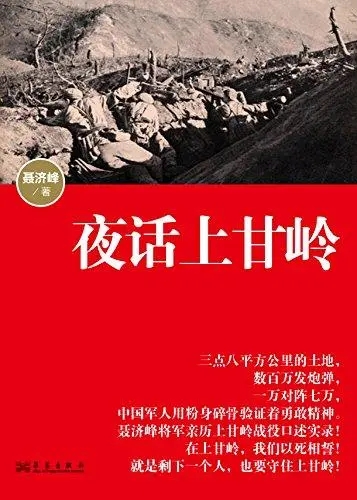雍正见俞鸿图走也不是,留也不好的那惶惶然无所适从的样子,他在心中笑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微末小吏,竟有这么大的本领,挽既倒于狂澜,这样的人被埋没掉,真是太可惜了!朕假如早一天发现了他,绝不会让他屈就内务府的一个小小官吏的。他看了一眼这个立了大功的人说:“俞鸿图,你的话还没有说完,怎么能和大家一齐走呢?回来,回来,把你想说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吧。”
“扎!”俞鸿图痛快地答应一声,就要继续说话。可是,在一旁坐着的十四爷允禵不干了:“慢!俞鸿图不过是一个撮尔小吏,能值得皇上把他看得比王爷们还重吗?我也有话,我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来呢!”
趁着允禩他们寻衅闹事的由头,允禵也跳了出来向雍正发难。他不让那个内务府的俞鸿图说话,而是抢先诉起了心里的怨恨:“皇上,我也还有话没来得及说呢?你能开开恩容许我说话吗?你有这个胆量敢让我把心里的话全都倒出来吗?你能担保殿外站着的侍卫们不对我们下毒手吗?如果你能让我们说话,并且真地作到了言者无罪,你才能算得起是个皇帝,是个立得住,站得稳的皇帝!”他略微停了一下,见雍正没有制止,便说起了压在心底的牢骚,“今天,这里议会的是政务,你们说的那些个事情,什么‘火耗’呀,‘官绅一体当差’呀,都与我无关,我也不想当这个乌‘议政王’,我只是憋气!我想问问皇上,我究竟犯了什么法,你就把我囚在东陵?让我过着人不人,鬼不鬼,死不死,活不活的日子,连个身边的人都保不住?我没有在西海打了胜仗吗?我不是万岁您的同胞兄弟吗?说实话,我听了十六弟的劝告,今天本来是不想开口的。可是,那么多的官员们对你的‘新政’不满,难道你就不该听从一下民意吗?”
坐在一旁的方苞,一眼就看出这次十四爷也要出来和皇上叫阵了。在他的身后,还站着允禩哥几个和东来的诸位王爷,绝不能让他们占了先,更不能让允禵得了理!他出来说话了:“十四爷您说到了‘民意’,我倒想问一下十四爷,您知道‘民意’该怎么讲吗?您过去曾管过兵部,又曾经出兵放马,回来后又在东陵读书。这些年来,您一直是深居简出、养尊处优的金枝玉叶。您知道一郡之内有多少田地吗?这些田地里头大业主占了多少,小业主又占了几成?您知道平常人们说的那个‘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都是从哪里得来的吗?前明灭亡,李自成革命,全是因为土地兼并过甚,官员贪墨无度才引发的!十四爷呀,我劝您好好地想一下,您不懂的地方还多着呢?不要只是抓住了一点,或者看到了一件事情,就信口开河地说三道四。天下之大,要作的事情有多难,您也要思量一下才对啊!”
鄂尔泰刚调到军机处来,对于全局的形势还不很了解,但十四爷他却是熟悉的。方苞刚刚住口,他就朗声接着说:“先帝爷驾崩,十四爷大闹灵堂;太后病重时,十四爷侍疾又言语不慎,这难道都可以说是无罪的吗?若是平常人,早就发往刑部去论罪了。可是只因十四爷是皇上的胞弟,皇上才念及兄弟情分,不予深究,仅仅削去王爵,请十四爷守陵读书。这一片保全抚爱之心,十四爷为什么就不能体贴呢?汪景祺和蔡怀玺等人相互勾结,图谋要劫持十四爷参与作逆造反,万岁除首恶之外,一概不间,而只是将他们从十四爷身边遣散,这不是法外施恩,又是什么?十四爷,您平心静气地好好想想,主子还有哪一点不是仁至义尽?”
允禩一看,好嘛,方苞和这个鄂尔泰都这样地能说会道,一番话竟把允禵问了个脸红脖子粗,张口结舌地答不上来了,他的心里这个急呀。平日里他虽然也恨允禵不肯与自己通力合作,但眼下已到了节骨眼上,他却不能不出来帮允禵一把了。他一改平日那温文尔雅的风度,大大咧咧地跷起二郎腿来怒声喝道:“十四爷正在和皇上说话,你们插的什么嘴?”
朝臣们全都退出去了,雍正的心里早就平静了下来。他不急不躁地说:“朕早就说过,今日是言者无罪嘛,允禵你何必这样浮躁呢?”他的声调并不很高,但话音却特别的刁蛮,“你们不就是因为乔引娣的事,想说朕是个‘淫暴昏君’吗?回头你们可以去见见她,问一问朕是否对她有非礼之事。不过,话又说回来,朕看你们今天这样不顾身家性命的闹法,恐怕还不是为了乔引娣,大概还是要弄那个‘八王议政’的吧?朕告诉你们,不要再搞那些个玄虚了,还是开门见山地谈更好一些。”
允禵咬着下嘴唇恶狠狠地看着雍正,过了好半天才说:“就算是要八旗议政又怎样?那是列祖列宗的旧制,我们在朝会上光明正大地提出来,也说不上是犯上作乱!皇上,你不是也有旨意,说‘八王议政’也不是不能提的吗?”
“朕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这样的话?”
“你问问允禄。”
这次该着雍正吃惊了,他带着狐疑的眼神盯着允禄问:“老十六,朕一向知道你是最老实的,想不到你竟然敢矫诏乱政。嗯?”
允禄吓得扑通一下就跪了下去。他多么想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说这是弘时说的话,而他自己从来就没有说过呀!可是,他一瞧弘时那凶狠的眼神,又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人家是皇子,是阿哥,皇上能信得过他允禄吗?他只好吞吞吐吐地说:“啊……是,是三贝勒……他说的……说这是皇上的意思……”
雍正只觉得浑身一颤,掉过头去又盯上了弘时。弘时怎么能不害怕?他连忙跪了下去颤声说道:“阿玛知道,儿子最是胆小,怎么敢编造圣意害国乱政呢?想必是十六叔听错了。儿子的原话是,八王议政的事,皇上自有安排,议政议的就是旗政,儿子这话和皇上今天说的是完全一样的呀!”
“嗯?!”
别看允禄平日里不大管事,可他心里清楚着呢。弘时一改口,他马上就意识到了灾难即将临头。自己怎么能和弘时这位皇阿哥作对呢?昨晚上他们在一起说的话,是无法对证的,要硬说是弘时对自己说了谎言,说不定更要倒霉。他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叩着头说:“臣弟这会儿实在是记不清了……皇上知道,臣弟是出了名的十六聋,也许是我把三贝勒的话听错了……”
雍正勃然大怒:“好,你错得好!”他快步向着允禄走去。张廷玉吓了一跳,以为皇上要踢允禄一脚的。可是,走到半路,雍正却又忍住了。只听他冷笑一声说:“这件事,是朕自己糊涂了,不该用你这聋子来办事!削去你的王爵,你回家去闭门思过吧。滚!”
允禄的眼里饱含泪水,十分委屈地看了一眼雍正,叩着头说道:“是……”他爬起身来退出去了。
图里琛正好在这时走了进来,他看了一眼退下去的允禄,却没敢和他说话,径直走到皇上身前跪下奏道:“礼部刚才派人进来让奴才代奏说,文武百官已经遵旨在午门前按班跪候,请示主子有什么旨意?”
雍正满意地看了一眼全身戎装的图里琛说:“叫他们等着!等会儿朕还有旨意。告诉各部尚书,有私议国家大政者,休怪朕今天要开杀戒!”
“扎!”
雍正的眼睛里闪着阴狠的光,突然转过身来格格地一笑说道:“朕即位之初就曾经说过,朕无意来做这个皇帝。但圣祖既然把皇权交给了朕,朕也只好勉力地做好这件苦差使。圣祖德近三王,功过五帝,就是废除八王议政,也是在他老人家手里发生的事。你们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中,突然发难,要求恢复八王议政制度。朕现在要问你们一句,是圣祖当年措置失误呢,还是朕有什么失德的地方?你们之中,要是谁想来当当这个皇帝,就不妨站出来直说!”
自从朝臣们被撵出了乾清官,退到午门外边起,允禩的心里就觉得忐忑不安。平常日子里,他们在自己的府邸里密议的时候,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雍正的无能,是雍正的不堪一击。但是今天他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也感觉到掌握中央大权后有多么大的权威,指挥起来又是多么的容易!从敞开的乾清官殿门口向外看去,黑鸦鸦集中起来的御林军,早已像铜墙铁壁样地站在那里,整装待命了。他知道,如今是大势已去,打心底泛起一阵悲凉的叹息。他强忍着又惊又恐的心境,叩头说道:“万岁的这番话,做臣子的如何能够担当得起?臣等并没有自外于朝廷的心,更不敢作乱造逆。八王议政乃是祖制,就是永信、诚诺他们也无非是想出来为国效力,辅佐皇上治理天下,臣弟担保他们谁也没有异样的心思。”
雍正没有理会他的话,却笑着对睿亲王都罗说:“睿亲王请起身说话。朕很高兴你没有和他们掺和在一起。”
允禟听出来雍正的话意了,眼看着形势急转直下,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他觉得八哥刚才的话说得太软弱了,就是上了刀俎的鱼,还要蹦达几下呢,何况面对宿仇死敌?他站起来抗声说道:“万岁既然是这样说了,臣弟还有话要说!睿亲王入京,和其他亲王们一样,我们在一起议了整顿旗务的纲目,也一起谈了八王议政,并没有人暗地里另起炉灶啊!不知万岁说的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也不知万岁所谓的‘掺和’,又意在什么?”
允禟的话一出口,允禩就意识到自己的失策了。“服软”就是“理屈”嘛!他马上又说:“别说我们没有私地里阴谋,就是说了些什么,万岁也大可不必这样讲话。皇上若无失政之处,何必要如此堵塞言路?皇上若是有失政之处,又何必拒谏饰非?”
雍正冷笑一声:“嗬,朕堵塞了你们的言路了吗?你有什么话,想说朕有何失德之处,不妨明言嘛。”
一句话又把两人说闷了。允禵看到这情景,在一旁大声说:“田文镜明明是个小人,是个敲剥聚敛的酷吏,河南官民人等,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皇上你却树他为‘模范’,对他任用不疑,这难道不是失德吗?”
“你身在东陵,他是小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听刚才众位大臣们说的。我觉得他们说得有理!”
“有理?有什么理?你有的是大业主,大豪绅的理!”雍正厉声驳斥说。
“皇上难道要杀富济贫?”
“哈哈哈哈……”雍正皇上仰天大笑:“说得好!但朕不是要杀谁济谁,朕是要铲除乱根,创一代清平之世!”突然,他止住了笑声,急促地在大殿里走来走去,脸色也涨得通红。他似乎是对别人,又似乎是对自己说:“朕就是这样的皇帝,朕就是这样的汉子!父皇既然把这万里山河交付给朕,朕就要把它治理得固若金汤!谁阻了朕的志向,朕就对他毫不留情!”他转脸向殿外高喊一声:“图里琛!”
图里琛就在殿外檐下,听见雍正召唤,他一步跨进殿来,“叭”的打了个千儿:“奴才恭听主子吩咐。”
雍正面冷似铁地说:“你八爷、九爷和十四爷今天累了。由你带步兵统领衙门的兵士们护送他们回府。”
“奴才遵旨!”他站起身来向外一招手,立刻就进来四名千总,向雍正行了军礼,肃立一旁看着图里琛。图里琛脚下马刺踩得金砖地吱吱作响,直向允禩等人走了过去。打了个千儿说:“八爷、九爷、十四爷,奴才奉旨送你们回去。”
允禩霍地站起身来说:“无非一死而已!老九,老十四,不要装脓包,也不要再去求他!”他转身向雍正一揖道:“皇上四哥,兄弟我等你来杀我哪!”说罢昂然向殿外走去。允禟也是一揖,只有允禵更是格外不同,他站起身来,用极其轻蔑的眼光瞧了一下雍正,“哼!”了一声便离开了这座高大宏伟的乾清宫。
雍正的脸色突然变得血一样的红,他对着傻坐在那里的几位王爷也是“哼!”了一声,便回到御案前坐了下来。他提起笔来,似乎是想写点什么。可是,不小心,朱砂蘸得太饱了,还没有下笔,就滴了两滴,而且还正滴在明发的诏纸上。那血红的颜色十分注目,让他也吃了一惊,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一样,呆坐在那里不动了。张廷玉知道皇上这是在想着怎样处置这些“铁帽子”王爷,他倒是很愿意借这个机会,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便假装没有看见。可是,鄂尔泰却深知这事情的重大。本来,满洲的旗人们就对皇上不满了。自从整顿旗务以来,每天都有西林觉罗本家到他府上去哭叫,有的人甚至质问他“皇上还要不要我们这些满人了”?如果照今天这些旗主们的所作所为,发到部里,至少也得问一个“斩监候”!可是,那样一来,不但旗务整顿变成了一句空话,就连奉天也要受到极大的震动。说不定连蒙古诸王,也都要被株连。满蒙是大清的国本所在呀,一旦乱了起来,那大清岂不要崩溃了吗?他上前一步来到皇上身边,躬身小心地说:“皇上,当天命六年时,太祖武皇帝曾与诸王对天焚香共同祈祷说:‘吾子孙中若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勿开杀戮之端’。这些话尤在耳边,请皇上留意。”
“唔?”雍正的精神好像有点恍惚,他抬起头来,却正好看见了墙上的那个条幅:“戒急用忍”,这正是康熙皇帝亲手写给他的座右铭。他的心渐渐地平静了下来,踱到屏风前边,眼睁睁地看着诸王问:“尔等知罪吗?”
“知……知罪!”
“既然知罪,朕就不再加罪了。朕说一句诛心的话,你们现在只是‘畏罚’,却并不真正知罪。朕治理天下,遵循的其实只有两个字:一是孝,二是诚。就诚而言,上对天地,下对四方,御群臣,临万民,都出自本性,没有半点的虚伪矫揉。这上边还应该有个内外之别,要分而待之。朕对待天下臣民,犹如光风霁月,恩惠是人人均等的;但对满人,则又如一家子弟,有着骨肉的深情和满怀的挚爱。正因期之愈高,所以也求之愈苛,完全是一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你们今天跟着他们胡闹,是让别人当了炮筒子使呀。这就是不诚,也是对朕的不敬!再一点,你们身处奉天,管的事不出满旗满人,受人的挑拨,也想来分一份皇权。朕问,你们懂不懂治理天下的道理?你们知不知道,如今的形势早就不是开国之初了,汉人们比我们满人多着上百倍呀!如今各部官员中满汉各占一半,就有人怨声载道了,还能再架住你们这样胡闹?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却不能治天下,连这点普通的道理你们都不懂,还要跟着允禩他们闹事,朕若想发落你们,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