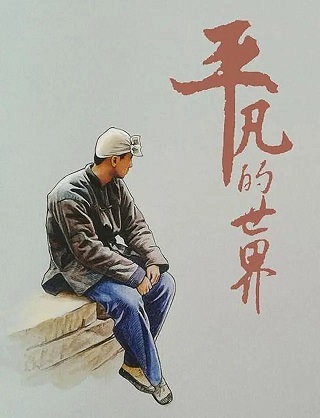弘历在河南历险的事,是瞒不了人的。别看弘时在这里时说得头头是道,可一转脸他就去了张廷玉那里,并把这消息添油加醋的告诉了这个老宰相。还说:“此事,请张相暂且不要上报,以免惊了父皇的驾。”可是,张廷玉却心里有底儿,他了解弘时,也知道弘时是在耍花招。他不让张廷玉上报,可他是一定要报告上去的。果然,当天夜里,弘时就叫自己的心腹旷师爷代写了奏折,呈给雍正了。而张廷玉也没有听弘时的话,同样也写了密折,发往奉天。不过,他们都晚了一步。此时,雍正皇帝已经到了承德,见过了到这里觐见圣颜的蒙古诸王公,也知道了弘历遇险的事。现在,皇上身边的两位大臣,正在听皇上训话呢!
“这件事值不得你们大惊小怪的。”雍正说话时,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一边让乔引娣给他敷着热毛巾,一边慢慢悠悠地说着。最近一段时间,他脸颊上的红疹子越出越多了,他勉力而为地说着,“怕什么?他不是毫发无伤地平安回京了吗?道路凶险自古如此,朕年轻时还曾经住过黑店呢!”他看了一眼身边的乔引娣,又想起了当年的小福,“这几天你们多留意田文镜那里的折子,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鄂尔泰躬身回答道:“是。田文镜没有马上写奏折,大概是因为还没有破案。他正在和李绂闹意气,又出了这样的大案,他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四爷没上奏本,恐怕是不愿让皇上看了担心。”他很想说:四爷是怕有人会受到株连,可话到嘴边,又想这样就会说到弘时,便马上打住了。
朱轼老马识途,他在一旁说:“宝亲王在外头巡视已近一年了。老臣以为,是不是召他到承德来。一来可以朝夕侍奉在皇上左右,二来也能把这件事问得清清楚楚。”
雍正好像根本就没听见似的说:“让弘时还照样在韵松轩维持一下,发文让弘历在京负责筹措天下钱粮的事,兼管兵部。你们俩还都在饿着肚子是吧?这样,朕到外头看折子,你们就在这里吃些点心吧。”说着,就带了乔引娣出去了。
雍正所说的“外头”,其实是“里间”。这里原来是康熙皇帝的书房,布置得分外雅致,墙上挂满了字画。其中,就有一幅《耕织四十六图》。乔引娣看了奇怪地说:“皇上,这不全是种庄稼织布的事儿嘛。怎么要画到画儿上去,又挂到这里面来呢?”
雍正笑了:“你干过农活,当然不新鲜。朕第一次见到它时,却觉得新奇得很哪!当皇帝的,不知民间疾苦,不懂得耕作辛劳,那怎么能行?晋文帝时,天下饿死了人。臣子们奏了上去,可这位皇帝却说:‘他们肚子饿了,为什么不喝点肉粥呢’?皇帝要当到这份儿上,那天下可就一走要完了。”
雍正见她老是愣神,就说:“你过去,把窗子支起来。”
乔引娣不知他要干什么,却听话地上前去支起了窗子。雍正望着窗外出了一会几神,又回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乔引娣看,还轻轻他说了一句什么。引娣却早让他瞧得羞红了脸,而又不知怎么才好:“皇上,你……”
雍正马上收回目光,却又忍不住地再看了一眼,这才说:“你确实是长得太美了。来,替朕把宣纸铺好,朕要写几个大字。”
引娣羞红着脸,又被他夸得心里直跳。她走上前来,将纸铺平了,又站在一边,轻轻地抚着宣纸。雍正定了定神,挥笔在纸上写着。他边写边说:“这是李卫请朕写的,他一心一意地想让朕巡幸江甫。可朕没把天下治好,怎能有这份闲心呢?”突然,他话题一转问道,“朕让你去看看十四爷,他都说了些什么?你知道,还从来没人敢既不缴旨,又没回音的呢。”
乔引娣轻声说:“我没有去。”
“为什么?你不想去了?”
“不,奴婢不知道十四爷在哪里,我曾问过高无庸;可他却说什么也不肯告诉我……”
“哦,你是不懂规矩。你向高无庸说,自己是奉旨去的,他敢拦你吗?高无庸,你进来!”
高无庸就站在屏风外边,听见招呼,马上就进来了。雍正吩咐说:“回京后,你领着引娣去看看朕的十四弟,可以在那里呆上一个时辰。你也顺便看看,他现在还缺什么东西,有没有下人在那里狐假虎威地耍威风作践他,回来向朕如实回话。”
“扎!回主子,朱先生和鄂尔泰已经用饱了,他们正等着主子召见呢。”
“叫进来吧。”雍正淡淡地说了一句,便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乔引娣此时却是千头万绪,再也难以控制自己了。从心里说,她想念十四爷,但现在她更感激皇上对她的恩情。这位每天不分昼夜只知道勤政的皇帝,对她这个弱女子,从来没有任何不规的行为,却像是一个年长的大哥哥。她闹不明白,那个生性豪爽的十四爷,怎么就不能和他一母同胞的哥哥合到一起呢?假如没有了这些政争,没有了朝中这些勾心斗角的事,他们两个和睦相处,自己既有一个疼爱着的人,又有这样一位大哥哥,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她知道,这又是绝对不可能的。唉!
朱轼和鄂尔泰进来了,雍正问他们:“对田文镜和李绂之间的争执,你们是怎么看的?”
皇上这话问得突然,他们俩谁都不敢开口。朱轼说:“下头还没有报上来……”
“你们就不能谈谈自己的看法吗?”雍正口气严厉地又问。
朱轼还是第一次领教皇上的软钉子,他头上的汗珠马上就掉下来了。他吞吞吐吐地说:“启奏皇上,臣以为,他们二人都是正人君子,也都是能够为国分忧之人。二人的分歧,不过是政见不同而已。见仁见智,不足深责。”
“哦,好人之间的误会,这是你的看法。鄂尔泰,你呢?”
“李绂与田文镜之间的私交一向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俞鸿图从河南发回了奏折说,田文镜报主心切,但也有一些失察的小事,以致让小人们拿来制造事端。而李绂则见事不明,又不能谅解,因此才酿出了政见之争。奴才所见未必就对,请圣上烛照明鉴。”
雍正好大半天都没有说话,只是在端坐饮茶。突然他说道:“朕不是让你们来评价人物,而是在这里论世情、世理的。朕是在朋党中吃过大亏的,深得其中三昧。那个‘八爷党’果然是消声匿迹了吗?不!从弘历遭险这事,你们应当看到,连外省的土匪们作案,都非要到河南境内不可。这就说明了,那个‘八爷党’还阴魂不散。如今,满天下都在议论着什么‘官闱秘闻’。甚至有人说,隆科多所以获罪,是因为他知道的内幕太多了,朕是要杀他灭口,真是奇谈怪论!”他越说越气,猛地一拍几案站起身来说,“阿其那他们犯的不但是家法,还犯了国法!传旨给六部众臣,议议他们该当何罪!”
朱轼他们简直傻了,怎么皇上正说着李绂和田文镜,却又跑到允禩等人身上了呢?还没等他们醒过神来,雍正又气愤地说:“你们不要以为朕说话跑了题,这和刚才所说的是一回子事,这就是朋党!跟着他们起哄的,有几个不是阿其那的旧人?!朕要推行新政,他们就拼死地反对。李绂自恃身正心也正,所以他才要搏名!他净捡着朕最疼处来揭疮疤,这就沾染了汉人的恶习,让朕十分痛惜。昔日孔明杀了马稷,朕又为什么不能浑泪斩李级!”
雍正的话如金石蹦响,掷地有声,朱轼和鄂尔泰早就听得惊心动魄了。他们长跪在地说道:“皇上高屋建瓴,深谋远虑,使臣等顿开茅塞。请旨:应当怎样办理。”
“发旨给六部,让他们从速议处。李绂的名字暂可不提,但不要再观望不前。明日朕就启驾返京。”
“扎!”
皇上在承德发怒,弘时却在家里捣鬼。他把旷师爷叫来悄声问道:“都掐断了吗?”
旷师爷小心翼翼地说:“三爷放心,连聂公公在内,全部处死。铁头蚊跑到抱犊崮,我派人去杀他了。”
弘时那颗悬得高高的心,这才安定了下来。他拿出太监秦狗儿送来的消息,将皇上和朱轼、鄂尔泰的谈话说了,并请教对策。旷师爷笑了:“三爷,上次学生让您赏这给秦狗儿三百两银子,您还觉得心疼。就这封信,您说它值不值一万?”
“我哪能那样小气?皇上宫规严厉,太监结交王公大臣的格杀无论!我是怕他万一说走了嘴,那可就要弄巧成拙了。老四他就不搞这一套,可他的消息却比我灵,也真邪性了。”
“三爷,您和四爷不一样啊!他早先就在先帝身边,又主持了这么多年的韵松轩,巴结他的人多了。里头随便一句话,他就什么都知道了,哪还用得着往外掏银子买消息?”
弘时不想多说弘历的事,却目光幽幽地看着旷师爷说:“这次,李绂就要倒大霉了!这件事还牵连着八叔等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其实,李绂和八叔根本不是一路人,而且他的人品文章比田文镜高上十倍,太可惜了!”
旷师爷说:“真正倒霉的还是八爷,因为皇上最怕也最恨的就是朋党。八爷没有失势的时候,遍交朝中文武,这些人也都是出了名的读书人。所以,表面上看,他们的头脑人物都被圈禁了,可这个‘党’依然还在。不知三爷注意到没有,那次闹‘八王议政’乱子时,从头到尾,没有一言是针对八爷的,全是在拿着田文镜作法。在皇上的眼睛里,谁攻击田文镜,谁就是不满新政。所以,明面上皇上是在护着田文镜,实际上是在护着皇上自己。您是了解皇上性子的,他老人家见了块石头还想踢三脚呢,怎么能容得这么多臣子和他离心离德?连他身上的病,也是由此而起的。”
“这可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应当怎样处置呢?”
“说来也很简单,不过就是两句话:一,狠打死老虎决不手软;二,坐定韵松轩拼命办差。您整治了‘八爷党’,就为皇上出了气,也顺应了皇上敌汽之情;而拼命做事,又迎合了他孜孜求治之心。至于四爷和五爷,礼尊之,诚布之,情爱之,心防之。反正大家都是皇子,比一比,看一看,看谁的孝心重,能耐大!”
弘时想了半天才又说:“我和弘历不能比呀,他现在又主管了天下钱粮和兵部的事,他……”
旷师爷一笑说:“三爷,您想得对。可是,您再想想,当年深得人望的八爷败了,而冷面冷心的‘办差阿哥’却夺得了天下。这里面的道理,您可以找出千条万条,可当时雍亲王始终处在机枢重地,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与您眼前的处境,不是一样的吗?”
弘时兴奋地大叫一声:“来人!给爷备轿。告诉账房上,西街口的那片房子,我赠给旷师爷了,让他们拨二十个家人过去侍候。”说完,他不等旷师爷辞谢,便出门上轿走了。
弘时本来是要赶往畅春园的,可走到半路又忽然想起,有好长时间没有去看十三叔了,他老人家在父皇面前,可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啊!他在轿里喊了一声:“停轿,转到清梵寺去!”
轿夫们“噢”地答应一声,便调转了轿头。这里离畅春园本就不远,不一刻功夫就来到了。但因为十三爷是住在寺里静养的,所以,他这个小院子里,就只有太监和宫女,而没有闲杂人等。弘时熟门熟路地推门而入,一挑门帘就进了房内。他上前一步,对着躺在病榻上的允祥叩头说:“十三叔,侄儿给您老请安来了。”
允祥的儿子弘皎也在一旁说:“父王,弘时三哥看您来了。”
允祥勉强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弘时说:“哦,是你来了。难为你这么大热的天还想着来看我,快,起来坐着吧。皇上就要回来了吗?我听方先生说了。可惜的是,这一次我可真帮不上他的忙了。”说完,他轻轻地咳了一声,就又闭上了眼睛。
弘时面对这位叔王,真是百感交集呀。曾几何时,他还是朝野人人称赞的‘侠王’,谁能想到现在却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了呢?他对弘皎说:“我不是告诉过你,让你去请贾神仙来看看的吗?你怎么还不去?”
“三哥,你今天来得正巧,贾神仙马上就到。”
他们这儿正说话,却听病中的允祥突然说:“来了,来了,他没有食言,真的是来了。”
此时就听外头一个太监说:“神仙爷,请您这边走。”说话间,那位贾士芳已经进到屋内。他还是以前的那身衣服,也还是那个打扮,但大热的天,他从外边进来时,脸上却是滴汗全无。只见他俯身走向允祥轻声说道:“十三爷,贫道稽首了。您的病其实是不相干的,这会儿已经好了些了,是吗?”
“是,我好像晕得不那么厉害了,眼睛似乎也明亮了许多。”
“不是似乎,其实是您心明了,自然也就眼亮了。您的胃气不展,饮食有亏呀!想不想吃点东西,比如说桂花糕什么的?”
“桂花糕?”允祥眼前一亮,竟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啊,真是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它?快,给我拿桂花糕来,你们快着点不行吗?”
弘皎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在过去的三天中,父王只是喝过两小碗粳米粥,可现在竟闹着要吃桂花糕!站在一旁的贾士芳含着微笑,看着允祥连吃了两块桂花糕,又要过一杯水去、竟然也是一饮而尽。吃罢,喝完,允祥微笑着对贾士芳说:“谢谢你,总有两年没有这样畅快地吃东西了,你是怎么捣的鬼,也没见你烧符念咒呀?”
“十三爷,《道藏》三十六部,共有一百八十六万六千七百八十卷。万道通幽,怎么能以一格拘之?那种故作姿态,装神弄鬼之辈,不过是入了道家的下乘罢了。十三爷您如此精明的人,也被他们哄弄了。哎,你想不想起来活动一下?”
“想,怎么能不想呢?”
“能不能做到呢?”贾士芳又问。
“恐怕不能。”
“您能的,一定能的。人人都会走路,怎么英雄一辈子的十三爷却不会走了呢?来,下地来吧,您能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