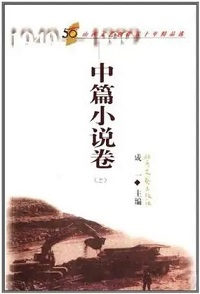曾国藩不识时务,得罪了咸丰皇帝。
在得罪皇帝的同时,曾国藩还把同事们也都给得罪了。
怎么把同事得罪了呢?
首先是他惹了几个大人物。曾国藩晚年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28页。]”就是说,我早年在北京的时候,专门爱批评大人物。官越大,我越不怕。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贵族,声名早达,三十岁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虽因鸦片战争而被道光“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但不久就获重新起用,任陕甘总督。咸丰即位后,有人参奏他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将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14,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161页。]。皇帝命将其革职交刑部审讯。
虽然两度获罪,琦善在京中人缘却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后,会审人员只寻“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是为他开脱罪责。有人还建议让传告他的萨迎阿随带的司员来对质,传命官与罪犯对质,并不合当时体制,显然有报复这些人之意。当时兼署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琦善虽位至将相,但是既然犯了罪,就一是一,二是二,得查清楚。司员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没有与罪犯对质的道理。如果你们这样办,以后大员有罪,谁敢处理?”(“琦善虽位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研鞫乃其职分;司员职位虽卑,无有传入廷尉与犯官对质之理。若因此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敢过问者?且谕旨但令会审琦善,未闻讯及司员,必欲传讯,当奏请奉旨然后可。”[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9页。])
曾国藩“词气抗厉”,“四座为之悚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慑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1852)四月,琦善被革职,凄凄惨惨地离开北京,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第二个被曾国藩得罪的,是大学士赛尚阿。赛尚阿也是朝中重臣,做过文华殿大学士,还一度当过首席军机大臣。
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并屡败清军。咸丰派大学士赛尚阿南下督师。曾国藩的好友、军机章京邵懿辰认为赛尚阿缺乏才干,又素不知兵,去了肯定坏事。于是马上上书谏止,但咸丰并没有采纳。后来的事实证明邵懿辰的判断非常准确,赛尚阿到了广西,胡乱指挥,贻误军机,果然一败涂地。
咸丰二年(1852),咸丰命将赛尚阿交刑部议处。同样,大部分人想当老好人,参照成例,放过赛尚阿一马。只有曾国藩坚持,“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20页。]。带兵打仗犯的错误,非同寻常。军务关系重大,直接关系国家安危,不严肃处理,以后谁还好好带兵?那国家不得亡吗?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则。
会议结束之后,他又专折奏请从严议处,赛尚阿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这个人特别爱交际,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他又热心肠,爱帮助人,所以在京官当中人缘是非常好的。
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的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赛尚阿更是人脉广阔,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钱仲联主编:《曾国藩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有一次有人请客,曾国藩也去了,见一个桌子上还有空位,桌上坐的,还都是自己认识的人,于是一屁股坐到那了。正想跟大家打招呼,结果他一坐下,这一桌人纷纷站起来,一言不发,都跑到别的桌上去了。当面这样,在背后曾国藩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曾国藩这才发现自己坚持原则,会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
得罪了皇帝和权要的同时,曾国藩还得罪了普通同僚。画稿事件就是曾国藩窘境的明显反映。
前面讲过,曾国藩上给咸丰的第一道奏折叫《应诏陈言疏》,批评了官场风气不正。他说,要改变官场风气,就得皇帝带头学习,带领大家学习圣人教导。所以他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皇帝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画个图,解释讲堂应该怎么布局。
曾国藩一听,也很兴奋,连夜就画。不过曾国藩没学过画画,湖南乡下的农家孩子,没有美术基础,这张图画得歪歪扭扭,相当难看。
图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其实又何尝不是北京官场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官场中人,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急不得。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开阔,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独着急?
曾国藩在奏折中把所有的官员都骂了一顿,说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科道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对皇帝上直言。看到他的奏折中把大家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好嘛,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皇帝下了一个求言诏,你就真的独抒己见,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
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笑眯眯地看着他,谁也不说话,显然他们在背后议论他已经很久了。这令曾国藩无地自容。
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多次表示,想回老家。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
早在道光末年,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城欠账将近一千,归家则途费接礼又须数百,甚是难以措办……”[《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46页。]
为什么在大清王朝做到“副部长”,却连回家的钱都没有?
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
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年俸是一百二十五两白银。用购买力换算的方法,可以算出晚清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二百元人民币。因此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约相当于今天两万五千块钱,一个月两千零八十块钱。今天的一个京漂这点钱都不够花,曾国藩那时当然也不够花。
在当时的等级社会,官员和平民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朝廷对官员的服装有着明确而烦琐的要求,如果置办齐一年到头的几套官服,就要花掉六百两左右的白银。再比如官员不能和平民混居,至少要租一套独门独院的四合院。曾国藩在绳匠胡同租了一套四合院,年租金是一百六十两。关于曾国藩日常生活的收支,我曾经专门写过两本《给曾国藩算算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因此在那个时代做京官实际上是一个赔钱的事。很多京官解决财务赤字,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靠家里补贴,另一个是营谋灰色收入。很多地方官愿意结交京官,让他们在北京为地方官探路。很多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的灰色收入。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因为曾国藩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他的理学修养体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不谋求任何经济收入。
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4页。]
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地自我批评。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所以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我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十日的一段日记,他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6页。],就是说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昨天有人送了他一笔别敬,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又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做梦,梦见有一个朋友发财,发了几十两银子的财,他在梦中就羡慕得不得了。他反省起这两点,觉得自己实在太下流了,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自己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一段日记也很有意思,在这一年的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20页。]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随朋友的分资都很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今天我想明白了,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儿贺礼,以度过目前的财政危机。想想自己是一个堂堂的京官,一个要发誓学做圣人的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儿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通过这两则日记的记载,我认为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么卑污、多么贪财,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的是清廉之员,鼓励的是贪官。
做初级低级京官时是这样,做了“副部级”高官,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的收入仍然不高。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咸丰初年(1851),曾国藩兼署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好几个部领津贴,收入应该更高。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
所以曾国藩在北京经常借钱,曾国藩的日记、账本上借银的数量,逐年增长,在升任侍郎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十五日,他在家书中提道:
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他更是说:
但京寓近极艰窘。
这时他的外债已经一千多两。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939)离家后,一直没有回去过。在这十多年间,他的祖父祖母先后去世,曾国藩都没能参加葬礼。母亲江氏夫人更是非常想念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子。
随着离家日久,曾国藩也越来越想念家乡、想念亲人,家书中一再流露想回家探亲的念头。但是曾麟书一直不同意曾国藩回家,要求他在京老老实实做官。曾国藩曾经提出一个“迎养”计划,要接父母到北京享两天福,江氏从此就心心念念去北京,但是丈夫曾麟书知道曾国藩经济紧张,怕他花钱,不同意这个计划。
就在曾国藩左右为难之时,喜从天降。咸丰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皇帝派他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
这次前往江西,是曾国藩盼了十多年才盼来的差事。
明清两朝,在北京为官的京官们个个都盼着被皇上派到各省去做主考官。一来,可以收纳许多门生,这些被他取中的举人当了官,一辈子会奉他为老师,感他的恩德。二来,到各地做主考,按惯例地方官场都会公送他一笔厚厚的“程仪”,再加上私人致送的礼物,收获总能在三五千两白银之间。这是清贫的京官生涯中难得的“加油站”。数年前,曾国藩到四川做乡试主考,就曾经发过这样一笔财。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这些收入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因此并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
除了会缓解财政困难外,更主要的是,皇帝已经同意考试结束后放曾国藩两个月的假,“赏假两月回籍”。江西与湖南相邻,他可以在乡试结束后顺理成章地回家探亲。
曾国藩满怀兴奋地于咸丰二年(1852)六月“驰驿出都”,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