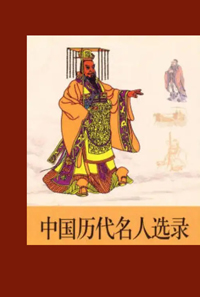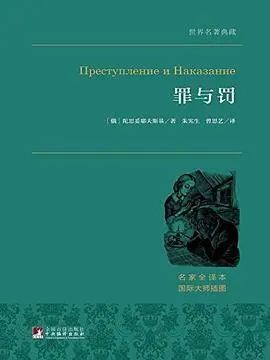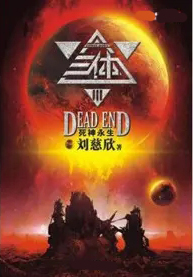“物有声色气味,人有耳目口鼻。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邵雍《乐物吟》)
《观物洞玄歌》出自清代《故宫珍本丛刊·术数》之《梅花易数》卷二,是对汉代《易》学中取象之法高度实践的歌诀,更是对格物之学“表象即表法”的具体指引,其中万物皆为我所备,万法“存乎一心”的运用之妙,令后世学人代代相传。
《观物洞玄歌》原文:
洞玄歌者,洞达玄妙之说也。此歌多为占宅气而发。昔牛思晦尝入人家,知其吉凶先兆,盖此术云。是故家之兴衰,必有镇详妖孽之谶,识者鉴之,不识者昧之,故此歌发其蕴奥,皆理之必然者,切勿以浅近目之也。
世间万物无非数,理在其中遇。
吉凶悔吝有其机,祸福可先知。
五行金木水火土,生克先为主。
青黄赤黑白五行,辨察要分明。
人家吉凶何堪见,只向玄中判。
入门辨察见闻时,于此察兴衰。
若还宅气如春意,家室生和气。
若然冷落似秋时,从此渐衰微。
自然馨香如兰室,福至无虚日。
鸡豚猫犬秽薰腥,贫病至相侵。
男妆女饰皆齐整,此去门风盛。
家人垢面与蓬头,定见有悲忧。
鬼啼妇叹情怀消,祸福到阴小。
老人无故泣双垂,不见日愁悲。
门前墙壁缺砖瓦,家道中渐歇。
溜漕水势向门流,财帛去难收。
忽然屋上生奇草,益荫人家好。
门户幽爽绝尘埃,必定出高才。
偶悬破履当门户,必有奴欺主。
长长破碎左边门,断不利家君。
遮门临井桃花艳,内有风情染。
屋前屋后有高桐,离别主人翁。
井边倘种高梨树,长有离乡士。
祠堂神主忽焚香,火厄恐灾殃。
檐前瓦片当门坠,诸事愁崩破。
若施破碗坑厕中,从此见贫穷。
白昼不宜灯在地,死者还相继。
公然鼠向日中来,不日耗资财。
牝鸡司晨鸣喔啼,阴盛家萧索。
中堂犬吠立而啼,人眷有灾厄。
清晨鹊叫连声继,远行人将至。
蟒蛇偶尔入人家,人病见妖邪。
雀群争逐当门盛,口舌纷纷定。
偶然鹏鸟叫当门,人口有灾连。
入门若见有群羊,家主病瘟黄。
舟船若安在平地,虽稳成淹滞。
他家树荫过墙来,多得横财来。
阶前石砌多残缺,成事多衰灭。
入门茶果应声来,中馈主家财。
三餐时候炊烟早,勤俭渐基好。
连宵灯火不成时,人散与财离。
千门万户难详备,理在吾心地。
斯文引路发先天,深奥入玄玄。
上《洞玄歌》与“灵应”,同出而小异。彼篇多为占卜而诀,盖占卜之际,随所出所见,以为克应之兆。此歌则不特为占卜之事,一时而入人家,有此事,必有此理。盖多寓观察之术也。然有数端,人家可得儆戒而趋避之,或可转祸为福。偶不知所因而宥有于数中,俾吾见之,则善恶不逃乎明鉴矣。
【解读】
洞玄歌,就是洞察抵达玄妙之境的歌诀。这个歌诀主要是为探究住宅环境的气机而阐发的。从前牛思晦先生就是运用这个歌诀,每到一户人家,都能判断出或吉或凶的先兆,运用得神乎其神。总之,这种方法是说:一个家道的兴与衰,都是有其吉祥与祸妖的先验迹象的,那些能够识鉴的人心中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而那些不能识鉴的人,就会困昧在其中,茫然无措。这个歌诀展示了环境中所蕴藏的奥妙,歌诀中对应的所有现象,你都会得到与之一致的确定结论,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内容浅显而不以为然。
两千多年前的先秦典籍《吕氏春秋·恃君览·观表》说得好:“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徵表。无徵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圣人之所以能超过一般人,就是因为他具备先知先觉的能力。而要想做到先知先觉,就必须先要能够审察事物的征兆和表象。没有了知征兆表象却想做到先知先觉,即使是尧、舜两位圣人也与凡人一样不可能做到。
邵雍这个《观物洞玄歌》展现的就是圣人先知先觉的功夫,更是中国格物智慧中取象表法功夫的精微展示。
“世间万物无非数,理在其中遇”
“物理窥开后,人情照破时。情中明事体,理外见天机。”(邵雍《窥开吟》)
世间万物,各有其运数,所有的成住坏灭之理,都尽在事物各自的运数之中。因此,《诗经·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告诉人们,上天生化万物,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气数规律。《吕氏春秋·季秋纪·审己》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如果不了解它,虽然你做得很像,但其实也跟不懂是一样的,到最后,一定会为其所困。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僧人僧肇在其《肇论》中就说:“圣人会万物为己。”圣人把万物与自己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万物是自己生命水乳交融的组成部分。
足见,在中国智慧中,人与自然之间,是一个生物链,相互之间紧密依存、互相影响。诚如三国曹操《观沧海》所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世间一切得失、生灭的变化,都在大道之中。“道不虚行只在人。”(邵雍)能否明白,全在于你自身的格物能力。
“吉凶悔吝有其机,祸福可先知。”
"吉凶悔吝”出自《易经·系辞上》第二章:"圣人设卦观象......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悔,就是后悔;吝,就是心中有事,导致犹豫不决的忧虞之象。这句话是说,人生的吉凶得失、悔吝迟疑状态的呈现,都各有发机,有迹可循,因此,智者对于福祸之事是可以预先判断的。在中国《易经》出现的先秦时期,诸如《左传》《国语》等诸多典籍都记载了与“吉凶悔吝”有关的神奇预测案例。其实这些并不神奇,只要掌握了中国格物智慧,就如同蚂蚁知雨而搬家一样,能够具有先见之明。
对于这种功夫的建立,作为一个抵达者,邵雍说:“心,一而不分则能应万变,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动也。”(《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上》)凡事不动心,则万化在我。而这,便是对中国文化最高妙功夫的概括!
“五行金木水火土,生克先为主”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基础,五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这个中国文化独有的智慧系统,被运用于经济、政治、饮食、医学、建筑、军事、社会等方面,指导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使中华文明成为全球有史以来 22个文明体中唯一没有断流的文化传承。
“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甘誓》。五行在古代,是治国的大法之一。商朝末年,商纣王暴虐无道,引发社会不满。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灭商,建立了周朝。姬发在治理国家之时,曾求教于商旧臣箕子,箕子便将治国安邦的“洪范九畴”告之武王,而九畴中的第一大法便是五行(见《尚书·洪范》)。无独有偶,《淮南子·本经训》亦云:“圣人节五行,则治不荒。”是说,圣人善于调节运用五行来治理国家,而不致朝政荒废。可见,圣人是知道如何协调五行之规律以合于时势并善于应对变化的。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气者也。在天为五星,在人为五藏,在目为五色,在耳为五音,在口为五味,在鼻为五臭,在上则出气施变,在下则养人不倦,故《传》曰'天生五材,废一不可’。是以圣人推其终始,以通神明之变,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来物,观形法以辨其贵贱。”这是《隋书·经籍志》对五行功用所作的更详细的总结。
孔子很佩服管子,《管子·五行》云:“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强调了五行经国序民的大用。众所周知,当年孔子一再申明其理想是“吾从周”,其中便包含了周朝治国理政的方法,而五行便是其一。
孔子也精通五行,其五行思想见于《礼记·礼运》篇,其中记载了孔子向子游传授礼的运转之道。
其他古代典籍,关于五行的记载有——
《国语·郑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
《左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
《白虎通义·五行》谓:“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
《史记·夏本纪》谓:“五行,四时盛德所行之政也。”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谓:“五行者,五官也。”
《元包经传》谓:“五行者,阴阳之精气,造化之本源。”
......
五行是天地间五种势能的形象概括。这五种势能,也称为五德,分别为:“土曰稼穑,水曰润下,火曰炎上,金曰从革,木曰曲直。”意思是土有播种和承载的势能特性,水有润下的势能特性,火有向上的势能特性,金有创新和变革的势能特性,木有屈伸的势能特性。
五行间的关系有三种——五行中的每一“行”都与其他“四行”有着相互“生、克、和”的五种关系,即“我生”、“我克”、“生我”、“克我”和“相和”。这些关系是从自然界抽象出来的,是“类象”的结果。五行就是通过这种“生、克、和”的关系来反映万事万物间的普遍联系。
五行“生、克、和”关系的原理表述如下:
五行相生,是指一事物对另一事物具有促进、助长和滋生的作用。如《淮南子·天文训》中所云: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生的关系,在《难经》中被比喻成“母子”关系:“生我”者母也,“我生”者子也。
五行相克,是指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生长功能具有抑制和制约作用。如: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克我”和“我克”的相克关系,在《黄帝内经》中被称作“所不胜”和“所胜”。所不胜,又称为“反侮”,如小刀砍大树,树未伤,但刀已受损。
五行相和,是指五行间的组合——金、金,木、木,火、火等相同五行的类聚,就是相和。
五行相互关系中,还有“制化”的现象。制是制约,化是化生。生中有克,克中有生,制中有化,化中有制,如此,事物的自然调控机制才得以完善。
但在五行生克制化的动能转换过程中,最令人费解的便是“化”字了。
古语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合同而化。万物的生长发展到极端就叫做“变”;变而无碍便是“化”;变化的不可揣测,就是“神”;神的作用变化无穷,就是“圣”。神明变化的作用,在天是深不可测的宇宙,在人就是深刻的道理,在地就是万物的化生。
五行就是凭借其生克制化的功能,来保持系统的动态平衡的。譬如,木旺盛而无金,主虽有仁义之心,却成就不了造化;火旺盛而木衰残,纵使很有学识也难得到尊贵显耀;水多而遇旺土,土克水,土便可成就堤岸之功;木旺盛而逢强金,金克木,其势可作栋梁之美。水火相停,火旺阻水,便成为《易经》中的“水火既济”之卦;土逢旺木,才能够作稼穑之功;金火之气势均力敌,便可炼出锋刃之器。这些五行的造化,皆因那些幽冥不可见的势能而形成。
邵雍之子邵伯温说:“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谓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间者也。”金木水火土是作用于万物的,也正因有此大用,才被称为是五种运行于天地之间的能量。而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变化皆为阴阳之机所展现,若是阴召阳、阳召阴,则天地合正,五行气融。若是阳从阳,阴从阴,则“孤阳不生、孤阴不长",这种阴阳偏出之情形,必会导致动静失序,无论是祸还是福,皆了了分明。因此,阴阳偏出,其造化是不能成就五行清奇势能的。比如,火多金少,聚散不得成形;火少金多,不但不能起到销铄的作用,还会反有淹灭之灾。其他例推即可。再比如,木败之因,在于丧却木德之仁而恣意妄作;金衰之由,乃是不见金德之担当反而寡义无恩;火灭之时,便见不遵礼法之徒;水浊之际,必是利令智昏之辈。土遭到木克,主所言经常失信;金多作鬼,常见算计、杀伐之事;水盛泛滥,必定多淫招乱。明代张三丰云:“顺则凡,逆则仙,只在其中颠倒。”从以上所言五行的“败、衰、灭、浊、克”可见,“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天不赋慧于无德之人,而失德者亦皆有迹可循。也更可知,《易经》所言“进德修业”实乃醒世的无方之药。
关于五行应用,体现在中医、军事、建筑、政治、社会、科技、鉴人法、文学作品等方面,文献中记载的案例也非常丰富。比如,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正式出场顺序即是按照五行相生的排序而来——第一回,孙悟空出场(红色);第十一回,唐僧正式出场(黄色);第十五回,白龙马正式出场(白色);第十八回,猪八戒正式出场(黑色);第二十二回,沙和尚正式出场(青色)。红色五行属火,黄色五行属土,白色五行属金,黑色五行属水,青色五行属木。唐僧师徒出场顺序依次是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递进相生关系。足见《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精通阴阳五行之道的。
中国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智慧。而关于五行与人相匹配的方法,在隋代萧吉《五行大义》中早有记载。
汉代王充《论衡》和唐代虞世南编纂的《北堂书钞》记载了一个与前述《梅花易数》所载邵雍“傍晚有人借斧”相似的案例,讲的是孔子门人子贡作为使者到各地游说,到了归期仍未归来。孔子于是占了一卦,得鼎卦,以变爻九四占断,其爻辞为“鼎折足”。孔子的门人们依据这个爻辞推断:“卦中说没有足,看来,子贡暂时回不来了。”唯独颜回笑而不语。孔子问其故,颜回答道:"子贡一定会回来,即使没有足,也会乘船回来。”颜回之所以说“乘船”,是因为鼎卦的下卦是巽,巽为木。后来果然如此。
所以,邵雍强调:“五行金木水火土,生克先为主。”
(以上内容选自米鸿宾《一代传奇:邵雍的智慧》,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