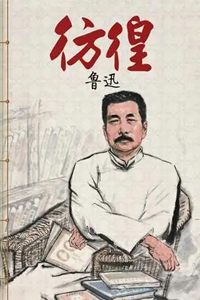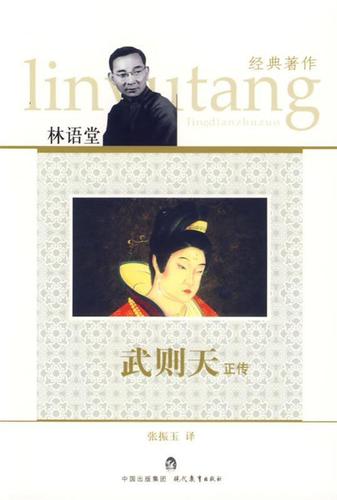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份西奴名单中,现华中科技大学(下称“华科”)哲学系教授邓晓芒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骨干西奴”和“哲学西奴”两栏下,同列的还有易中天、钱刚、贺卫方、江平等知名学者。
这个被极左分子怒斥为汉奸西奴的邓晓芒却成长在一个红色年代下的一个红色家庭。
他出生于1948年,父亲在长沙第一师范加入地下党,母亲亦在早年投奔解放区。1949年后,父母均在湖南日报社(当时叫“新湖南报”社)工作,父亲是继李锐、朱九思之后的《新湖南报》第三任社长。
当时母亲从报社资料室借回家给邓晓芒读的书,诸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画报《知识就是力量》,都是革命的进步书籍。
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长大,邓晓芒对自己接受的红色教育深信不疑。1958年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读小学的他就积极投入到班级组织的宣传活动中。
邓关心报纸上登的“放卫星”的消息,每天还把粮食亩产多少万斤的报道讲给外婆听。来自农村的外婆不相信,说她知道一亩田有多大,邓晓芒只觉得外婆“年纪老了就是顽固不化”,“不开窍”。
反右运动时,九岁的邓也跟着老师唱:“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说好,背面破坏……这是什么?是坏东西!他要是不改,把他扔进垃圾箱里,把他扔、进、垃圾箱——里!”
直到有一天,邓在学校办公大楼批判右派的漫画上看到父母亲的名字,他“吓了一大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第二年,邓的父母就双双被定性为右派。父亲贬职,母亲下放劳改。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顿随之而来,正在长身体的邓饱尝饥饿之苦。
雪上加霜的是,在1961年冬天他失去了外婆。
1964年中考,班上成绩前三的邓晓芒打算报考长沙市一中,发榜前夕政策突然变了,他被告知:凡是家庭有政治问题的一律不予升学。多年以后他才知道那次是由于在湖南推广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但邓那时对自己所受的红色教育坚信不疑,家庭问题使他产生一种“原罪”感,“觉得自己应当到农村去进行一番切实的‘思想改造’,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于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升不了学,邓晓芒就带上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三千多名长沙知识青年(绝大部分是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一起,主动报名下放千里之外的江永县。
临行前,母亲“想不通”,偷偷把户口本藏了起来。当时是邓说服了母亲,最终交出户口本。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从“地富反坏右”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
他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支持他们对“反动派”的造反行为。一时间,从农村到城市,中国处处都祭起了“造反”的大旗。
毛泽东号召群众造反夺权的号召传到江永,江永县的知青们立刻响应。他们自发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当晚就在厅屋里的毛主席像下庄严宣誓:“我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我当年是绝对的愤青啊,准备牺牲生命的。很多人都像我那样,我们非常地遗憾,我们因为年纪太小,没有赶上抗日战争、没有赶上解放战争也没有赶上朝鲜战争,但是我们现在赶上文革了,所以我们很高兴的,文革是狂欢呐,我们终于可以显示一下我们的爱国主义了!”邓说。
次年初,邓所在的江永县白水知青成立了“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后改名为“湘江风雷”,是当时长沙声势最为浩大的群众造反派组织。
然而,到了二月,运动的风向突然逆转。中央“元老派”与“文革派”公开抗争,引发“二月逆流”事件,曾是奉旨(毛领导的“文革派”)造反的“湘江风雷”,被“元老派”把持的中央定性为“反动组织”,一大批头目被抓。邓也因造过反而挨了捆、挨了批。然而波折远远没有结束。
“二月逆流”不久就被“文革派”镇压下去。五月份,江青在中央发出号召:“革命造反派要掌握武装”,“湘江风雷”又被平反,全国再次掀起造反的高潮。当时邓正从家中赶回江永,一跳下车,他和同伴们就直接冲到武装部去夺枪。
但所谓的“形势”再一次戏剧性地逆转,毛泽东对红卫兵的造反行为逐渐不满,中央的态度下达到地方,结果是“湘江风雷”的头目被捕,邓晓芒发现,折腾来折腾去,“出身不好”的自己还是属于被歧视的对象。
他开始反思自己所受的红色教育,反思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主要是觉得理想被玷污了。我们那么样满腔热忱的真诚的那种理想,青春热情。这些理想破灭了以后,回过头来反思,我为什么会信这样一些东西。
“当年号召我们起来造反,造反以后说我们是这个分子,那个分子,说我们是反动组织,后来又要平了反,平了反以后又还是属于被歧视的,因为出身不好,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都不反思,那就真的动物都不如了。”
当时知青中流传着杨小凯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作者杨小凯曾被康生(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点名批评,也因此入狱十年。
这篇文章让邓感到震惊又惭愧——和自己同龄的杨小凯竟可以冷静客观、头头是道地理性分析局势。邓如梦初醒:原来神一样的毛泽东也是可以分析、可以评价的。他开始反思毛泽东。
“我学哲学就是要掌握一种思想武器,为什么要掌握思想武器呢?(掌握思想武器)就是要活得像个人。你没有思想你活得就不像个人,随便你叫什么摆弄你。”邓晓芒后来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涯,说:“读书是为了‘成人’”。
邓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五年的学习计划,后来又有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找到所有当时最容易找到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阅读所有能到手的书。
“啃完”几本理论书后,他发现自己逐渐超越一些原以为不错的人,因为“再没有人可以请教问题了”。
当知青的十年也是生活在农村的十年,邓晓芒亲身接触原生态的农民生活,过去对农民的浪漫想象逐渐被现实认知取代。那时他已经看清文革的实质,开始思考起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必然性来。
文革结束后,大量知青从农村返回城市,大多数选择读大学或是去学一门手艺,不少人赚了大钱。而邓晓芒返城后选择去干最粗笨的体力活,挑土和搬运。
对他而言,“要养活自己一张嘴是不值得全力以赴的,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能够继续思想”。邓把对物质的需求降到最低点,只要可以维持他精神生活就足够。”
在做民工的日子里,他永远随身带着一本书,一有空就会拿出来读。有次忘带书了,那在无聊中空耗的两个小时成为邓晓芒记忆中最漫长的时间。他知道自己再也离不开书了。
1978年邓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研究生,但父母的“右派”问题让他没能通过政审。
他改考西哲,花了8个月的业余时间苦学他认为代表哲学最高水平的德语,次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师从陈修斋、杨祖陶。
此时的邓晓芒31岁,初中学历。
在《我的大学》一文中,邓写道:“当我走进正规大学校门时,我其实基本上已经‘学成’了,需要的只是一些必要的技术训练和补充。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所走的学术道路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今后不会再有我们这样的学者了。”
这是文革那一代人特有的幸与不幸。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风云激荡,陈丹青称为“沙龙的黄金年代”。从文革中走出的研究生们志趣相投,常常聚在一起谈论国家、学术和未来。
8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校园里,“一派精神生活的盛宴”,从以下这份邓晓芒聚谈名单中得窥一二:
西哲陈家琪、陈宣良,马哲的黄克剑,中文系的程亚林、易中天,经济系的肖帆、陈志龙,德语班上结识的张志扬,湖北省美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省社科院的黄忠晶……
邓与陈家琪、陈宣良三人曾用整整一天时间绕整个东湖走过一圈,一路上讨论的都是当时的学术状况、国家形势、未来走向;三人去内蒙开会,会后绕道西安去爬华山,吃住都在一起……
“这样的事太多了。一般都是宣良话最多,我居中,晓芒话最少,但常有很精彩的只言片语让大家哄堂大笑。”现在同济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陈家琪回忆道。
那时候邓丽君的歌声红遍大陆,邓晓芒的宿舍一度成为偷听邓丽君的歌声的据点。“那时他不知从哪里搞到一个砖头大小的录音机,于是就开始偷听邓丽君的歌。”那是陈家琪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当时常去听的还有易中天。
这是邓晓芒人生中极为珍贵和快乐的一段时光。
此后,邓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7年,讲师。1988年,副教授。1989年,教授。1993年,博士生导师。
邓用“在导师的提携下,没费什么事”概括这段破格升迁的经历,并对接踵而至采访这位“自学成才”的天才的记者们说:
“‘自学’二字首先不通,学习不可能是‘他学’;其次,哲学和哲学家并非可用之材,非但无用,而且还要拿钱来养活。”对他而言,“哲学体现了人的本质,即人最终说来不是工具(材),而是目的”。
与老师杨祖陶合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合集》给邓晓芒带来极大的声名,然而邓体会最深的不是康德,而是黑格尔和马克思。
他关心的是怎么样分析这个社会,“那康德就无能为力了还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更加锐利一些,更加强大一些”。
他给自己的哲学命名为“打工者的哲学”。他看到转型期的中国,出现了这样一批“打工者”:
“没有故乡,甚至于话都不会说,他说城里人的话,到美国说美国话,他没有故乡的归属感包括那些“蚁族”,那些大学毕业生,还有农村到大城市里面去拼搏的农民工们。”这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处境。
“他们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大群人,但是他们最大的困惑就是处于一种道德思想、价值观的断裂,他们满脑子的还是传统的东西。
但是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过时了,都不能适应他们现在所面临的现实,都不能解决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是精神上最苦恼的一群人。”
邓认为自己是为打工仔做研究,“哪怕是做研究康德还是黑格尔,也是在为他们做研究”。
他希望能讲明白普世价值,讲明白那些西方法律、制度赖以生效的理念。他认为核心问题是普世价值没有建立,而他的所做的是去扫清理论上的障碍。
“你不研究康德、黑格尔,你哪里读得懂《刑法》、《民法》那些东西啊,它们根据什么原则啊。你不能把那些东西搬过来就觉得可以了,何况你还没能搬过来呢。即使搬过来条文,你也不能执行,你不懂它的意思。”邓说。
杨云飞是邓晓芒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现在武大哲学院任教。1999年杨读大三时在一家书店偶然翻到了邓的《灵魂之旅》,书拿起了就再没法放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考的导师”,因为他面对的就是邓所描述的问题。
“其实我也是个打工者。只要我们不是像传统一样、像小农经济一样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关系、这样一个宗法关系中,我们都是生活在城市中的被抛者。”杨云飞说。
邓晓芒提出“新批判主义”,他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这种出于救国目的对国民性的批判带有很强烈的“功利”、“世俗”色彩。邓试图超越这个层次而抵达“普遍人性”的层次。
邓喜欢给学生们讲玄奘取经的故事。他说:
“佛家本来是从精神上关怀人,到中国就变成从物质上关怀人了,信佛的人都是到庙里去求发财啊得子啊避祸啊,为了得利所以信佛,玄奘就看不过去了,他要把真经取回来,真经就是拯救灵魂的。”
“为了一种纯粹的学问取经”、从精神上“救世”,某种程度上邓以玄奘自居。
邓和玄奘同样做着精神上的事情,也同样经受着肉体上的考验。
邓有十二指肠溃疡的老毛病,“一到冬天有时候就犯”,这要追溯到他在农村当知青的那段日子,“乡下饱一顿,饥一顿”。
犯病最严重的一次是写《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时,他因胃出血住院。“那也是做多了,一天到晚呆在家里,思考啊,写作啊,坐到那里动都不动,身体上付出代价。”邓晓芒说。
“记得90年代,他(邓晓芒)患肾结石,极痛”,陈家琪回忆探病的情形,当时邓晓芒对他说:“反正《思辨的张力》已经写完了,死而无憾。”陈当时泪流满面。
“晓芒对学术有一种至死不渝的执着。”陈家琪说。
当下中国的喧嚣与骚动,连哲学家也不能无动于衷,至少邓晓芒不。
1999年的时候,邓晓芒开始觉得大学“没法呆了”。邓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因为缺少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武汉大学学位委员会拒绝授予学位,他就提出辞掉博士生导师,这在当时引发一阵轰动。
请辞的结果是他停招了一届博士研究生。
邓没办法,他没地方可以去,因为这并不是武大独有的现象,因为“中国没有大学,中国大学都是衙门”。他当时“就想把所有头衔都去掉,然后自己少担点责任,我就干点自己的活”。
后来邓在《南风窗》发表了一篇文章,怒斥“中国的大学什么都是,是衙门,是企业,是工厂,是商场,是赌场,是‘地王’,是‘战线’,甚至是‘桥头堡’,当然,附带也是大学——要辩证地看哦!而大学教授则更像政客、幕僚、老板、袍哥。所以,中国的‘学界’既是商界,也是政界,还是‘江湖’。”
2001年时,邓晓芒批判学术腐败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同在哲院的武汉大学前校长陶德麟。
邓领衔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是可忍,熟不可忍》的文章,痛斥“年届七旬、在中国哲学界神通广大、却不曾写过任何一本个人学术专著的‘著名哲学家’陶德麟长期以来一直操控着湖北省哲学界的成果评奖、职称评定和社科基金评审的大权”。
随后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公室在《博览群书》上发表了题为《一篇严重歪曲事实的文章——评《是可忍,孰不可忍》》。
哲院某位老师告诉我们,在这件事情中,邓老师与陶德麟校长间可能有所误会。但这样的批判却最终让邓受到影响。
事实上,这件事不仅影响了邓晓芒,可能还连累了武大的外国哲学。武大的现代外国哲学学科是第一个评上的国家重点学科,马哲是第二个。
第二次外哲没评上,邓晓芒带人去北京开会时,就有人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怎么敢如此对待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第三次因为邓晓芒也没评上。“邓晓芒太纯粹了,他太相信制度了,也就会成为制度的牺牲品。”
某大学哲学院在一次评选活动中,有人给邓晓芒打电话,说“我们互相投票,你投我,我投你吧”,邓答道:“那——我们武汉大学的规矩是我们按照水平来。”实际上他投了该学校的票。
“他是个很直的人,很硬的人。”邓的一位好友举了个类似皇帝的新装的例子。皇帝没有穿裤子,大多数人会说:皇帝啊,你的裤子真漂亮。另一种比较聪明又想说实话的人,他会说:皇帝,你是不是有点冷啊。
“但邓晓芒会直接说:‘皇帝啊,你怎么没穿裤子。’他会说你根本就没穿,不会委婉一点,他不懂。”
在儒学热、国学热的当下,邓晓芒站在了传统热的反方。中国古代讲“君子之德”,邓提出“小人之德”;他批判中国人“忠孝立国”的观念。
邓对儒家伦理的批判植根于他对“文革”的反思。在《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一文中,他写道: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大复辟,是中国20世纪抗拒西方文化、抵制启蒙思想的最后最猛烈的挣扎。批儒的人其实就是当代最大的儒。”
“像邓晓芒那样纯粹的学者是没有多少的。他觉得这个不好,他就应该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这很多人接受不了。”邓晓芒的学生,武汉大学哲学院老师苏德超说,“他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情绪跟理智区别清楚。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父母很优秀,是个伟人,但实际上他们是很猥琐的人也有可能,要敢于承认这一点。邓晓芒就说我们要敢于承认。”
“他的学术是很有个性的、很有根基的、也很有勇气的,尽管他做的学术完全可以避开中国社会上很敏感的一些社会话题。”邓的好友、作家胡发云这样评价。
但在直面这些敏感社会话题的同时,邓晓芒自己也卷进了漩涡中,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邓被指责“不热爱中国文化”、“不爱国”。在进步社会网(类似乌有之乡的左派网站)公布的一份西奴名单中,邓晓芒的名字出现在“骨干西奴”和“哲学西奴”两栏下,同列的还有易中天、钱刚、贺卫方、江平等知名学者。
他仿佛被架在“道德”、“传统”、“中国文化”、“爱国”、“东方文化”的对立面上,这和他自己颇推崇的鲁迅面临极为相似的困境,鲁迅称之为“无物之阵”:
掷出投枪的战士射中敌人的心窝,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邓的学生杨云飞却认为邓是真正的想从骨子里更新和重建中国文化:“你只有真正的拷问,才能在现代的冲击下,让传统真正的活出来。这个可能是理解邓老师特别关键的一点。”
“邓晓芒批评谁,一定会署名,这是他的特点。”邓的一位好友说,“但很多人批判邓晓芒是不署名的。”在2008年邓晓芒被指责“坑师”,邓没回应,因为这是匿名的,匿名就陷入了“无物之阵”,像唐吉可德大战风车一样,不知对手是谁,只会让自己受伤。两年后方舟子重提此事,邓晓芒就写了封公开信解释。
在公开信中邓写道:
您是这个所谓‘案子’发生三年多来第一个以实名发表不利于我的言论的人。在此之前,我只看到网上那些以虚拟的假名躲在阴暗处的魑魅魍魉对我狂吠,而我又是一个和您一样的无神论者,从来不和鬼打架。
邓晓芒常说自己是个“个体户”。他对学生说:“不要把武大当做你的家,你只是给武大打工的,武大没什么了不起,你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机构也不需要他,因为他不是任何一个学术评议组的成员,在现今的学术考评体系内他起不了任何作用。
但邓的一位好友说:“因为他的学术分量、他的学术地位,主流团体显然是不能够忽略他的,应该说他还有进入一主流话语的条件和机会,但显然他不是那种最核心主流那些可以获取很多国家资源的学者。”
苏德超回忆说:“一年之中,我主动给他打电话就一回两回,他主动给我打电话也就一回两回。他只搞他的学问。”
有一次,博士生们跟着邓晓芒一起走路,走着走着都没话说了,上了电梯,大家又开始问康德的问题,然后邓晓芒自己就笑了,说“其实我们可以聊一点别的问题”。
邓晓芒的女儿肖朵说,她和父亲长聊的次数并不多,“似乎很难把父亲的注意力从书桌上拉开”。有一次聊得比较长久是关于硕士课程里面一个现象学的问题,聊天的结果是学建筑的她写了一篇建筑现象学论文。
事实上,在学问之外,邓兴趣广泛。拍蝴蝶、逮蜻蜓,上树抓蝉,掏洞找蟋蟀,都是他小时候的拿手好戏,采蘑菇,摘乌泡子和刺泡,捡掉在地上的野柿子,则是外婆教的。
女儿上小学时,邓把这些引以为豪的知识教给她,结果小时候的肖朵因为和别的小孩不一样还隐隐有些自卑。“刚学写作时有些人一下笔就是范文,一看就是模范家庭,而我一看就是农民的孩子,就知道写关于玩蛐蛐捉知了。”肖朵说。
知青生涯把邓锻炼成了做农活的一把好手。有次装修房子时,邓帮民工装修,“他有个铝合金的框框嘛,那个纱他怎么装上去他不会装。他用手扯这个个地方,我说怎么是这样呢?我说你搞一个棍子,把那个纱卷在棍子上面,这样一推过去,不是很平展吗?”邓晓芒笑着说。
邓喜欢文学,曾出版《灵魂之旅——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意境》等数本文艺批评;他曾和作家残雪聊了三天三夜的文学,然后合出了一本《于天上看见深渊:新经典主义文学对话录》。
《如焉@sars》作者、作家胡发云的评价是:“邓晓芒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之余写的那些文艺批评都可以让武大的一批专吃文学批判饭的人没饭吃。”
但邓晓芒深知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尽管他也介入现实,但他“主要的兴趣、爱好和理想还是在学问方面。”
在40岁时,邓开始有一种紧迫感,担心自己要做的事一辈子也做不完了。
“我放下了一切爱好,一切交游的机会,除了讲课之外就是埋头于书斋,抓紧一切时间,拼命追赶着某颗遥远的命运之星,经常梦见自己误了火车。”
在给好友的信中,邓晓芒写道:
“我这一辈子,只想做好自己想做的几件事情,其他的人际纠葛,越少越好。我是为未来而活着的。
我相信我们这个星球上一切人类在某些事情上一定会达成一致,就像所有的人都直立行走、都说语言、都制造工具一样,将来所有的人都会按照普世价值生活。”
来源:小为斋